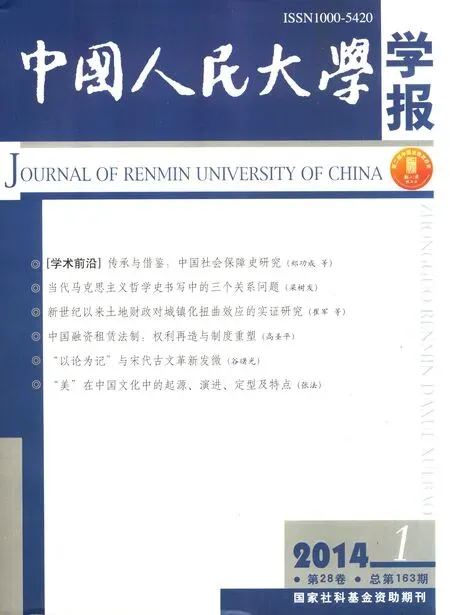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書寫中的三個關系問題
梁樹發
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書寫中的三個關系問題
梁樹發
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的書寫中遇到了以下三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客觀歷史事實和“哲學事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關系;非主流思潮及“相關因素”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關系;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兩種表現形式之間的關系。對這三個關系的正確處理不僅是提高著作質量的要求,而且是一個哲學史觀問題。一定的客觀歷史條件和“理論實踐”構成哲學發展的“背后故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要講好這個故事;“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否應該寫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的問題,引發對思想史類著作書寫的方法論的思考,即如何處理主流思想與其發展的“相關因素”的關系;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存在兩種表現形式,能否正確對待和解讀、闡釋存在于國家主導思想體系中的以間接形式表現的哲學思想,是對哲學家們的一種挑戰和期待。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書寫;問題;意義;方法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中我們遇到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既反映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現狀,也反映了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新特點。要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水平,提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的質量,就必須處理好這些問題。其中較為突出的是以下三個問題:客觀歷史事實和“哲學事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關系;非主流思潮及“相關因素”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關系;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兩種表現形式之間的關系。
一、哲學的“背后故事”與哲學思想發展的關系
一些西方學者批評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簡化了,這種簡化表現在哲學原理和哲學史兩個方面。西方學者的批評有它的片面性,也包含某種意識形態因素,但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
當然,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教材的編寫是允許一定程度的合理的簡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的編寫,都有適當簡化的要求,但是,簡化是有條件的和有限度的。一部通史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的編寫,由于有內容全面的要求,因而不能有過多的簡化。編寫中一些細節不被或未被納入著作內容,往往不是簡化的結果,而是這些內容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無關緊要,或者沒有發生實際影響。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的編寫,簡化是必要的,但是,簡化什么和簡化到什么程度,要服從著作、教材的結構和內容的需要,不能任意簡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著作、教材的編寫,以保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結構的完整性為前提,不能發生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概念、范疇和重要理論的遺漏。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編寫中,一定的內容被舍棄和簡化后,應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基本理論內容、基本過程和基本線索不僅更加清晰,而且不發生重要遺漏和斷裂,以反映和保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真實、完整面貌。當然,在實際編寫過程中,由于對問題的理解和對文本的掌握情況,遺漏總會有的,但這不是刻意簡化的結果。一般說來,遺漏是非目的性的行為,簡化則是目的性的和自覺的行為。
簡化的確有個適當與不適當的問題。造成不適當簡化的原因,除文獻掌握方面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哲學史觀問題。哲學史是一定的概念、范疇、觀點、思想形成、演變的歷史,它不是歷史事實本身,但它不脫離歷史并且總是形成于和表現于歷史之中,它是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任何一種哲學概念、范疇、觀點、思想的形成都能夠從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中找到根據。而作為歷史事實的首先是存在于一定時間和空間中的客觀歷史形勢,是以世界性的和根本性的歷史形勢為內容的時代,是一切進步階級和廣大群眾的偉大實踐。列寧在論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幾個特點時,談到了馬克思主義“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認為“忽視那一方面,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就會抽掉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即關于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就會破壞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的一定實際任務,即可能隨著每一次新的歷史轉變而改變的一定實際任務之間的聯系”。20世紀初的俄國,“因為具體的社會政治形勢改變了,迫切的直接行動的任務也有了極大的改變,因此,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的各個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地位”。[1](P279)列寧關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特點和經驗的以上論述告訴我們,要理解和發現一定時期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定主題(即被提到首要地位的那一方面)和一定概念、范疇、觀點和理論的形成,就必須考察作為其根據和根本條件的客觀歷史形勢(它通過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具體方面表現出來)、無產階級行動的條件和實際任務。就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來說,不能認為我們不了解或根本不懂得這個道理,不能說我們完全不去分析決定一定概念、范疇、觀點、理論形成的背后的事實。但是,又不能不承認我們不大善于做這種分析和說明,不大善于從一定的哲學思想與事實的聯系中說明一定哲學思想的產生。在已有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中,歷史事實往往只是形式化地被作為理論、思想形成的一般背景放置在理論、思想陳述的前面,而缺乏事實與理論的有機連接。這里存在的簡化,可能不是對事實本身的簡化,而是分析環節上的簡化,是書寫者思想懶惰或認識能力低下的表現。
作為哲學形成和發展基礎的不僅有客觀的歷史事實,還有哲學生活或“理論實踐”方面的事實。本文把這一方面的事實稱為“哲學事件”。“哲學事件”是指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相關的各種大的活動,如在重大哲學問題上發生的爭論、圍繞重大哲學問題舉行的重要會議、對重要哲學思潮開展的有組織的批判、重要著作的出版和重要學術組織的建立等。這些事件、活動由哲學問題引起,有哲學家的廣泛參與,對一定時期或長遠時期的哲學發展產生了或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一定背景,當然也是其發展的一定條件,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過程不能沒有這些事件、過程的陪伴。它同樣是我們理解一定哲學思想如何得以形成、發展的線索。客觀的歷史事實和“哲學事件”共同構成一定哲學思想或一定時期的哲學發展的“背后故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以及教學都要講好這個“背后故事”,即講好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每一嶄新觀點、思想產生的“背后故事”。只有講好這個故事,才能夠講好一定的哲學,才能夠理解一定的哲學。我們要講好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情況,不能不聯系我國這一時期發生的哲學上的“三次大討論”,即我國過渡時期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矛盾性質問題的討論、過渡時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的討論、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討論。同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相聯系的“哲學事件”還有: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2](P289-306);毛澤東在讀到發表于《自然辯證法通訊》1963年第1期上的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文章后,于1964年8月18日—24日先后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在北京同參加科學討論會的坂田昌一和各國科學家、同周培源和于光遠談“物質無限可分”和“關于人的認識問題”[3](P389-394);毛澤東在看到徐寅生關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講話稿和賀龍副總理的批語后,于1965年1月12日所做的批示,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公布后,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和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熱潮。而要講好“文化大革命”后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又不能不談到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關于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大討論、關于實踐唯物主義問題的大討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講好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的這些“背后故事”,是講好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這個大故事的前提。
問題不只在于要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背后故事”,還在于如何講好這個“背后故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思想史,要求從歷史的事實中發現、發掘思想,要求從事實、事件的連續中把思想的連續揭示出來。不能從事實、事件的聯系和連續中發現和揭示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書寫中的另一種弊病。這個情況在關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闡述中和關于我國一定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闡述中,表現得比較突出。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過程常常被淹沒在蘇聯發生的幾次“哲學事件”①“兩次哲學論戰”(20世紀20年代“辯證法派”與“機械論派”的論戰、米丁為首的“正統派”與德波林學派的論戰)和“三次哲學大反思”(第一次是1947年6月關于亞歷山大洛夫《西歐哲學史》一書的全蘇哲學討論會,第二次是蘇共20大前后哲學界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第三次是1987年4月“哲學與生活”討論會)。參見李尚德:《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118~126頁、148~18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中。而我國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發生前的哲學發展,也往往滿足于對幾次“哲學事件”的闡述,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主題或主導線索沒有被清晰地揭示出來。“哲學事件”可能引領了哲學的一定發展方向,也在其中深化了對某一哲學問題的認識,但是,全面的哲學發展不可能僅限于幾次“哲學事件”,“哲學事件”之外的哲學的日常發展是整個哲學發展的基本過程。在關注“哲學事件”的同時也能夠深入到對哲學的日常發展過程的研究中,才是對哲學發展全過程的和全面的研究,才可能避免重要哲學思想發展的遺漏,才能防止哲學思想發展鏈條的斷裂。就蘇聯哲學研究而言,如能深入到蘇聯哲學的日常發展中,我們將有可能對蘇聯哲學的總的發展有新的發現和新的認識。國內有學者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對蘇聯“哲學事件”做了詳細考察之外,還從社會哲學、科學哲學、經濟哲學、語言哲學、人的哲學等方面比較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的發展。[4]但這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著作,而是一部關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門著作。
二、非主流思潮及相關因素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關系
這個問題是由“西方馬克思主義”要不要寫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引起的。有學者從“‘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出發,主張“西方馬克思主義”不要寫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國內出版的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把“西方馬克思主義”(有著作使用“新馬克思主義”概念,其中包含“西方馬克思主義”)列入著作的附錄。[5]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結論都過于簡單化,因此,以此為理由而把“西方馬克思主義”排斥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之外的做法是欠妥當的。這里,我們暫且不去爭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而先假定它不是馬克思主義,探討在這種認識前提下它是否應該寫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的問題。我們說,盡管在性質上“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屬于馬克思主義,但只要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相關,它就應當被寫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是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發展的著作,它的一個基本過程,也是它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同一切錯誤思潮的斗爭,包括同一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斗爭”,當然只是一種概括的或簡單的說法,就其過程來說,它包含研究、對話、批判等具體環節。理想的結果是把包括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內的一切錯誤思潮消滅掉,但思想、理論的東西與實體性的東西和制度性的東西不一樣,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夠被徹底消除的,客觀上有一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同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長期并存的過程和時期。所以,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存在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生存環境”,斗爭成為馬克思主義生活中的常態和存在與發展的方式。斗爭對斗爭的雙方都會產生影響。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積極的結果是從對方獲得對自己發展有益的資源,獲得激勵自己發展的力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把真理同謬誤的斗爭看做真理發展的規律,看做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6](P230-231)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著作就應該反映馬克思主義同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過程,揭示它在同一切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得到發展的規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甚至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看做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相關因素”。“西方馬克思主義”即使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相關因素”,也是應該寫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的,或者說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書寫不能回避的因素。假若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有所懷疑,那么試想,我們今天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如果在內容上沒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涉及“西方馬克思主義”,那么,這個著作、教材會是什么樣子?它不可能是一部反映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客觀過程的著作、教材,當然它也不會是受讀者歡迎的著作、教材。
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呈現的是一種蘇聯哲學(即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三足鼎立”的態勢。“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或者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與探討,核心內容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和關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是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現實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現狀而對馬克思主義所做的批判性反思。它與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又稱東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具有不同的思路、范式、話語甚至結論(其中可能包含許多錯誤),它也始終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新”闡發中保持同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話(它往往是批評性的,并包含誤解和攻擊的成分)。正是這種對話、交流和相互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20世紀的發展。因此,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現實表現與意義,使它同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一起構成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完整畫面。沒有“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畫面就不夠完整,就不能完全地和客觀地說明20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不能完全說明20世紀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解體后,蘇聯哲學終結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①“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為了與那種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寬泛地理解為全部當代歐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研究區別開來而提出的概念。所謂“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是本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它創始于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的“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后有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流派。它是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末這一特定時段的西歐激進馬克思主義研究流派。參見王雨辰:《加強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觀念與方法》,載《河北學刊》,2009(4);梁樹發、于樂軍:《關于“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載《理論視野》,2010(8)。也終結了,但是,具有與其相同或相異理論傾向和傳統的“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流派還在,獨立的個性化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現象還存在。假若按照“‘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現在應換成“‘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因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著作、教材不能夠將其納入其中的簡單邏輯,罔顧當代歐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那么,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豈不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花獨放”?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談到事件、人物、思想、流派在著作中的“寫入”,其意義可能有以下方面:第一,不分事件、人物、思想、流派的性質,只看其歷史影響,在著作(與歷史同義)中“記上一筆”。第二,具有價值選擇和褒貶意味,“寫入”著作意味著對一定事件、人物、思想和流派的肯定。第三,通常意義上的“內容包含”。沒有特別的價值選擇和主觀意圖,寫入與不寫入僅僅取決于內容的需要,即取決于客觀歷史和理論歷史闡述的需要。以上所談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應該被寫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的主張,是第一種和第三種意義上的,繞開了對它的性質與意義的價值評價。我們無論是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看做馬克思主義的(它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支流甚至異端),還是看做非馬克思主義的,它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的“相關因素”,并且是值得“記上一筆”的相關因素。沒有這個因素,就沒有內容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就不能完全地和客觀地說明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
專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規律問題的思考,也使我們遇到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相關因素”問題。馬克思主義發展規律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除了有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般性規律和基本規律外,還有其他一些“規律性現象”。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基本規律與這個過程中的主要現象和基本現象相聯系,它們是前面提到過的客觀歷史形勢和由此決定的無產階級的行動任務,是現實的階級斗爭及其影響下的理論斗爭,是科學文化發展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創新能力,以及對理論生活具有直接影響的國家意識形態管理。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相關因素”的“規律性現象”,是對主要現象和基本現象的補充,是一種“副現象”。它們是:關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提問;馬克思主義與方法的關系問題的提出;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系問題的爭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誕辰和逝世周年紀念性話語,等等。這些帶有哲學意義的規律性現象要不要或者可以不可以寫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呢?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理論目的在于發現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發展的規律出發,它們是應該寫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的,或者說,我們應該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著作中,發現和能夠讀到這些規律性現象。因為它們是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實踐”中的事實。它們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書寫中的被吸收,可能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更具有可讀性、更有色彩,并且更為可信的一個主要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是我們以往的研究沒有發現的,也可能是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編寫所忽略了的。
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兩種表現形式之間的關系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哲學家們以標準的(或專業性的)哲學語言、思維方式和表達形式在有關著作和活動中直接顯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一種是以非哲學的語言、思維方式和表達形式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大理論成果中,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間接顯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以該形式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需要通過哲學家的解讀、闡釋與發揮而得以呈現。
不能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種表現形式與它的兩種形態混淆起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種形態分別指毛澤東哲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思想。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種表現形式是指其中每一形態的兩種具體表現形式。它們中的每一形態都有兩種具體的哲學表現形式,這兩種表現形式按其表現的直接性與間接性而劃分。人們往往習慣于從語言、思維方式和文本的表面性質來判斷一種思想是否為哲學,而忽略或否認在一般理論體系中或在非直接的哲學文本或活動背后深藏的哲學思想。這當然是對哲學表現的一種誤解。這種誤解表現在文本方面認為:只有《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才算得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著作,而《資本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哥達綱領批判》等則不算他們的哲學著作;在毛澤東的著作中,只有《實踐論》、《矛盾論》才是哲學著作,而《反對本本主義》、《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則不能被視為哲學著作。就文本形式和敘述形式而言,似乎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不能被看做是哲學,而是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被看做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不能被看做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在當代實踐中,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哲學表現或履行其意識形態功能的形式,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形式與現實,特別是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際具有的哲學內容和哲學品質,顛覆了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表現形式的傳統認識,從而使哲學家們不得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來,即什么是哲學的問題上來。放棄以往那種關于哲學表現形式的單一性的認識已成為必然。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確不直接是哲學或表現為哲學,不是直接哲學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又不能簡單地說它們不是哲學。就其內容和具有的意義而言,它們當然是哲學,是一種以非哲學的形式表現的哲學,是蘊含在或深藏于一般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哲學,是需要通過哲學家的解讀、闡釋與發揮而得以理解和呈現的哲學。這種解讀、闡釋與發揮是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面臨的重要任務。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種表現形式,可能是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的和常態性的表現形式。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國家主導思想體系功能的發揮,一般是與作為國家主導思想體系總體即馬克思主義聯系在一起的,是融入這個總體中的。這就是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容和性質上具有的與政治的關聯性。要認識這個總體中的哲學并將它呈現出來,需要哲學家的解讀、闡釋和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另一種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哲學的常規的表現形式,是所謂以哲學的存在和表現形式而存在和表現的哲學,就形式而言,它在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無特殊性可言。這就是作為學科和專業而存在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容和性質上具有的與學術的關聯性。
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兩種表現形式的存在是客觀的。它們是一種哲學形態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它們各有所長,因而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它們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并且這種互補性不只在于它們的形式方面,而且在于它們的內容方面。存在于國家主導思想體系中的、間接顯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由于更接近于社會生活現實,并且在哲學創新方面往往有突出表現,因而一方面對于那種作為一種學術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具有啟發和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也在內容上不斷補充和豐富以直接形式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兩種表現形式的關系問題相聯系的,是與這兩種形式相關的兩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隊伍的關系問題,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書寫中以兩種表現形式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問題。我們知道,在西方學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中,一般沒有本文所說的以兩種形式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只有所謂作為學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因而在書寫形式上往往表現為對哲學家個人的哲學的闡釋,即哲學家個人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闡釋與記述。但在我們書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中,則少見或幾乎見不到我們的哲學家們的“個人的”哲學,特別是在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個人的”哲學。所以,我們書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其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部分,幾乎是無主體的哲學。我們的有鮮明個性和特色的哲學家個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中往往見不到。而作為哲學家個人(他們一般是已經不在世的)的哲學思想出現的又往往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主導思想體系的解釋和闡述。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教材中較為多見的是國家主導思想體系的哲學,但是,就是這一表現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書寫得也不夠好。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似乎不大善于、有的甚至不太情愿做這種解釋、闡述和發揮的工作。
總的來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和教材的編寫,一方面,在充分反映國家主導思想體系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成就的同時,不要忽視或遮蔽我們的職業哲學家們,特別是現世的職業哲學家們,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總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所做的貢獻;另一方面,我們的哲學家們也要積極地參與(至少不要有意規避)和善于解釋、闡述和發揮主導思想體系中的哲學思想,在兩種表現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有機聯系和統一中書寫好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特別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1] 《列寧選集》,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李尚德:《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5] 楊春貴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教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孫伯鍨、侯惠勤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和現狀》,下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6]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 李 理)
The Three Relationship Issue Concerning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LIANG Shu-f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we've encountered three pressing problems as follow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philosophical events”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mainstream thoughts,the“correlate factors”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anifestations of China's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Handling them properly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orks,but also an issue of historical outlook of philosophy.“The stories behind”,constituted by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theoretical practices”,should be told efficiently by the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question whether“Western Marxism”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brings about a rethink on how to write intellectual history,namely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stream thoughts and the parallel“correlate factors”.There're two manifestation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and it is a challenge as well as an expectation for philosophers to properly handle,interpret and expla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state-dominated ideological system but represented in an indirect way.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writing;problems;meanings;methods
梁樹發: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