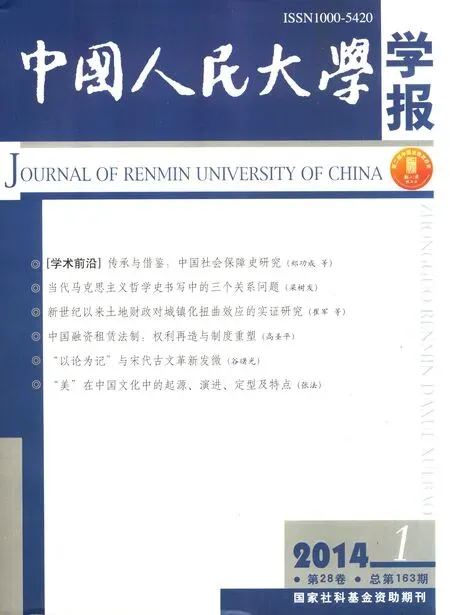新世紀以來土地財政對城鎮化扭曲效應的實證研究
——來自一二線城市的經驗證據
崔 軍 楊 琪
新世紀以來土地財政對城鎮化扭曲效應的實證研究
——來自一二線城市的經驗證據
崔 軍 楊 琪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出現了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速度,即城鎮化扭曲問題;與此同時,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亦有愈演愈烈之勢。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推動了空間城鎮化的快速擴張;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現實地決定了地方政府積極帶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因此,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對空間城鎮化的推動作用遠遠大于對人口城鎮化的推動作用,對城鎮人口密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是導致中國城鎮化扭曲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新世紀以來;土地財政;城鎮化;扭曲效應;一二線城市;實證研究
一、引言
當今中國,對城鎮化的重視和期待已達新的高度。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七次提及城鎮化,并且將城鎮化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四大載體之一,作為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重大結構性問題;201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3年3月“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由此可以看出,城鎮化在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將會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中蘊含的巨大內需空間和發展潛力對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中國的城鎮化迎來了全新的高速發展時期。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在《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中指出,中國在過去30年中的城鎮化速度極快,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①利用報告中的數據測算,1975—200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年均提高0.82個百分點,在城鎮人口規模最大的34個國家中,僅次于韓國(0.99個百分點)。對于城鎮化程度的衡量,即城鎮化率,國際上通常使用城鎮人口與總人口(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之和)的比率這一指標。顯然,其意在強調“真正的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這是正確的。但是,單純使用人口口徑的指標可能無法全面反映一國城鎮化的真實狀況,因為城鎮化是人口向城鎮集聚和城鎮空間向外擴展的復合過程,人口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并不一定同步,所以應該從城鎮人口變化和空間變化兩個角度去考察。[1]①從理論上說,人口城鎮化與空間城鎮化應該基本同步,世界各國的城鎮化進程大多如此,所以,國際上通用的人口城鎮化率指標是能夠反映大多數國家城鎮化的基本情況的。但不可否認,的確有一些國家的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滯后于空間城鎮化,或者相反。如此情況下,在研究城鎮化及相關問題時考慮空間因素就顯得尤為重要,應該同時采用人口城鎮化率和空間城鎮化率指標,或者采用能夠將人口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綜合起來的城鎮人口密度指標。這也正是本文實證研究所采用的指標。
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就存在著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速度②本文用建成區面積增長率來衡量空間城鎮化的速度。的問題,即伴隨著城鎮建成區大規模擴展的空間城鎮化進程,大量農村土地被占用,城鎮空間外延迅速擴張,而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卻沒有隨之同步提高。圖1顯示了自1995年有全國建成區面積這一統計數據以來歷年的建成區面積增長率和城鎮人口增長率,可以看出,2001年以前每年的城鎮人口增長率均高于建成區面積增長率;但自2001年起,僅有2006年和2008年兩個年份的城鎮人口增長率略高,其余年份的建成區面積增長率均高于城鎮人口增長率。對數據進一步計算:2001—2011年,中國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面積擴大了81.48%,年均增長6.14%,但人口增長卻只有43.72%,年均增長3.69%。上述城鎮人口數據的口徑是城鎮常住人口,若采用戶籍人口的口徑,即按本地城鎮非農戶籍人口測算,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速度的態勢就更加明顯。③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中國城鎮中戶籍人口少于常住人口是普遍現象,因此,以城鎮戶籍人口口徑計算的人口城鎮化率低于以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口城鎮化率。2013年4月15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盛來運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說,國家統計局2012年通報發布的城鎮化率是52.57%,口徑是常住人口;若按戶籍人口計算,城鎮的非農戶口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在35%左右。事實上,中國的戶籍制度并非只是人口管理手段之一這么簡單。本地和非本地戶籍、本地非農戶籍和本地農村戶籍背后承載著醫療、教育、社保、住房、就業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因此,采用本地城鎮非農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作為人口城鎮化的衡量指標在中國更具現實意義。本文實證研究部分采用的即是這一口徑。國內學者的一些定性研究成果也指出了這一問題。[2]這種空間城鎮化凌駕于人口城鎮化之上(即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速度)的“要地不要人”的城鎮化模式,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而是一種扭曲的城鎮化④也有專家學者稱其為“虛假的城鎮化”、“偽城鎮化”、“半截城鎮化”。。

圖1 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與人口城鎮化速度(1996—2011)
對于中國城鎮化的扭曲問題,現有文獻并未發現和強調“新世紀以來”⑤“新世紀以來”,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明顯快于人口城鎮化的這一時間起點恰好與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開始盛行的時點基本吻合(通過對比圖1和圖3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點),這不由得令人將土地財政與這一現象掛起鉤來。這也正是我們對此進行研究的起因和立意所在。這一重要的時間節點,而對于其出現的原因分析,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從對土地征用制度的剖析切入。按照現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相關規定,所有的城市建設用地從法律上都必須由地方政府首先征為國有,這實際上剝奪了農民與用地單位談判的權利。同時,在土地征用補償方面,現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土地被征補償給集體組織和農民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由此可見,土地由于用途轉換而升值的部分根本沒有列入補償范圍。不斷攀升的地價和長期固化的被征補償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巨額土地收益無疑是刺激城鎮空間不斷擴展的直接動因。二是從地方政府支出偏好的研究尋求突破。熊柴、高宏利用2000—200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基于財政分權的視角對中國人口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的不協調問題給出解釋,其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財政分權度(地方人均預算內收入與中央人均預算內收入的比率)越高,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的問題就越嚴重。[3]對于這一結果,他們并未作更加深入的探討,但實際上可以進一步分析出: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普遍偏好于城鎮的快速擴張和硬件建設,而非社會福利的提升,所以造成了財政分權度越高,城鎮化扭曲問題越嚴重的現象。這一結構性偏好的形成,顯然與當下的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指標和考核機制有關。①城鎮空間的擴張是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顯性載體,而人口城鎮化(本地城鎮戶籍人口)的成果則不夠直觀;同時,人口城鎮化的財政成本高昂,而且易遭到已有本地城鎮戶籍人口因擔心福利稀釋而產生的強烈反對。這些都是地方政府官員在目前政績考核指標與機制框架下不得不直面的現實問題。三是從戶籍制度的改革探討成因。戶籍制度改革長期沒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不僅主要大中城市的戶籍制度沒有真正放開,跨省區的戶籍改革也困難重重。在舊有戶籍制度依然存在并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外來人口雖身在城鎮本地,卻無真正的當地市民身份,無法享受與當地市民相同的社會福利。[4]顯然,舊有的戶籍制度限制了城鎮人口的增長。②決策層已經注意到現有戶籍制度對人口城鎮化造成的影響,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然而,由于中國大中小城市在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上存在較大差異,實際上人們向往的是成為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市民,但這與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承載能力產生矛盾。因此,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戶籍制度依然是阻礙中國人口城鎮化的重要因素。中國城市間的公共服務均等化任重而道遠。
上述研究從土地征用制度、地方政府支出偏好和戶籍制度方面對中國城鎮化的扭曲問題作出了解釋,得出了不少很有價值的結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會發現,這些都與土地財政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現行的土地征用制度為地方政府獲取巨額土地財政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失當的政績考核機制所決定的支出偏好制約了地方政府巨額土地財政收入的使用方向——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而舊有的戶籍制度則成為地方政府在財政資金(包括土地財政收入)用途方面推脫人口城鎮化責任的最好擋箭牌。③2012年4~5月,由國家發改委主管城鎮化工作的副主任徐憲平帶隊,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完成了對浙江、廣東、江西、貴州等8個有代表性省份的調研,調研發現,戶籍制度改革幾乎遭到所有市長的反對。由此可見,戶籍制度已成為地方政府在目前的財政壓力下推脫人口城鎮化責任的“擋箭牌”。由此可見,土地財政應該是中國“扭曲的城鎮化”諸多影響因素的關鍵節點。現有文獻對此研究很少,更缺乏嚴格的實證檢驗。基于此,本文嘗試利用具有代表性的一二線城市2001—2011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對城鎮化的扭曲效應。
二、背景分析和研究假說
中國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基本扭轉了之前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比重“倒掛”的局面,但也造成了地方政府事權與財力的不匹配。[5]此后逐步形成的“財力上移、事權下移”的中國式財政分權格局[6],雖然極大地改善了中央政府的財政困境,但卻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收支“剪刀差”,出現了近30%的收支缺口。④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數據測算得到。與此同時,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官員政績考核機制強化了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加劇了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使其產生了龐大的經濟性支出需求。在地方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擁有了更強烈的動機去拓展收入來源[7]。例如:通過土地征用并出讓獲得土地出讓金[8];通過“以地引資生稅”的手段,即大力發展房地產業、設立各類產業園(制造業)以及建設各種商圈(批發零售、物流和倉儲)獲得相關稅收收入。可以說,財政管理體制因素和政績考核機制因素共同催生了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出現和盛行。
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盛行是在進入新世紀之后開始的。從2001年起,土地財政收入規模越來越大,地方政府對其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自1998年有確切的全國土地出讓金數據以來,土地出讓金呈現年年攀升之勢。如圖2所示,從2001年開始,我國土地出讓金數額開始大幅度快速增長。2001—2011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共計近13萬億元,且增長速度極快。2001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僅為1 296億元,2011年則上升至32 126億元,是2001年的25倍,年均增長率為37.9%。在此期間,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亦大幅提高,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2001年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僅占地方財政收入的16.61%,對于地方政府的財力來說影響還較小,但是到了2009年,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上升至52.69%,占據了地方財力的“半壁江山”,2010年達到最高點67.62%, 2011年雖然稍有下降,但仍高達61.14%(見圖3)。

圖2 土地出讓金規模的變化情況(1998—2011)

圖3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的變化情況(1998—2011)
由此可見,新世紀以來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愈演愈烈,同時正如前文所述及的,它與中國扭曲的城鎮化進程在起始時點上基本吻合,而且在變化趨勢上也極其相似。其中的內在邏輯或者說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對城鎮化存在扭曲效應的影響機制并不難解釋。
從土地財政的收入形成機制來看,收入獲取的前提是有地可賣,在城鎮內部土地有限且日漸枯竭的現實情況下,其收入獲取過程必然伴隨著城鎮空間的擴張,或者說,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直接帶動了空間的城鎮化,建成區面積與土地出讓金有著大體一致的變化趨勢(圖4)。①土地出讓金收入=地價×土地出讓面積,因此不能否認地價對土地財政收入的貢獻。但這里主要強調土地出讓面積這一角度,突出土地財政收入對空間城鎮化的帶動作用。

圖4 土地出讓金的增長趨勢與建成區面積的增長趨勢(2001—2011)
從土地財政的資金支出結構來看,在以GDP為核心的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模式激勵下[9],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收入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具有與一般財政支出相同的結構偏好,即重城鎮建設和城鎮擴張(從而獲取更多的土地財政收入),輕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②地方政府在人口城鎮化方面并不是沒有投入,但相對于空間城鎮化的投入顯然是相去甚遠。而且土地出讓金與一般財政支出結構基本一致,所以說,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加劇了城鎮化的扭曲程度。表1列出了2008—2011年我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安排的支出情況,其中和空間城鎮化相關的支出③包括土地開發支出、城市建設支出、征地和拆遷補償支出、補助被征地農民支出。均超過3/4,說明土地出讓金收入的絕大部分并沒有投入到失地農民的市民化以及其他有利于推動人口城鎮化方面,而是用于土地開發、城鎮建設領域,推動了空間城鎮化的發展。

表1 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安排的支出與其中空間城鎮化的相關支出(2008—2011)
綜上所述,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的發展;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現實地決定了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如圖5所示)。基于這個分析思路,本文提出研究假說:這種以土地財政為主要原動力的城鎮化模式,是導致中國空間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不可忽視的因素,即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對城鎮化存在著扭曲效應。

圖5 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對城鎮化扭曲效應的作用機制
三、計量模型和數據
(一)變量選取和說明
1.被解釋變量的選取
城鎮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合過程。本文要研究的是城鎮化的扭曲效應,即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因此,被解釋變量指標應該體現出城鎮人口變化和空間變化兩個方面。從以往的研究來看,李力行曾使用城市單位面積人口密度這一指標來分析我國“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不均衡的狀況[10];周其仁指出,人口密度的下降意味著“土地進城快過人口進城”,是“反城市化”[11]。他們的研究僅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并未進行實證檢驗。因此,本文選取地區非農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城市人口密度——的對數序列(Lnupd)作為因變量。如果說非農人口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程度,而城市建成區面積可以衡量該地區的空間城鎮化程度,那么,非農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就能反映出該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程度。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當一個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時,說明該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地區非農人口是指擁有當地城市戶籍的人口,也就是說,這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城市中的公共資源和社會福利。
此外,我們還選取城市建成區面積與地區面積之比——空間城鎮化率——的對數序列(Lnsu)及地區非農人口與地區總人口之比——人口城鎮化率——的對數序列(Lnpu)作為被解釋變量分別進行實證分析(解釋變量仍然為土地出讓金,控制變量亦相同),并通過比較二者的實證結果來進一步驗證我們提出的假說。
2.主要解釋變量的選取
當前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土地出讓金收入、與土地和房產相關的稅費收入以及土地投融資收入。對土地財政的度量有兩種方法:一是直接用土地出讓金度量,二是將與房地產相關的各項稅費收入納入度量范圍,將其與土地出讓金加總。[12]在本文中,鑒于土地出讓金的數據可獲得性較強,而且在我國土地出讓金與土地財政收入有著相同的發展趨勢,我們選用土地出讓金的對數序列(Lnltf)來衡量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行為。
3.控制變量的選取
除土地財政指標外,影響城鎮化水平的因素還有很多,因此,必須選擇一系列控制變量來分析其他因素的影響。①本文對備選的控制變量和解釋變量進行了多重共線性的檢驗,計算了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和方差膨脹因子。綜合數據結果發現,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變量——人均GDP與土地出讓金之間存在非常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所以舍去了人均GDP這一控制變量。
(1)產業結構。城鎮化的過程必然伴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人口不斷向工業部門轉移,第一產業比重逐漸降低,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集聚,解決城鎮化過程中由農村人口轉變而來的城市人口的就業問題,所產生的集聚效應又進一步帶動城鎮化的發展。考慮到被解釋變量是人口和空間的復合指標,我們分別選取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ind2)、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ind3)來衡量產業結構。一方面,空間城鎮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與第二產業緊密相關;另一方面,在人口城鎮化的過程中,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強,解決了人口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就業問題。
(2)城鄉收入差距。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反映了城鄉生產力水平的差距,是引導人口在城鄉之間流動的重要因素。收入差距的拉大,將吸引農村人口加速向城鎮流動[13],導致人口城鎮化進程加快。有學者認為城鄉收入差距是促進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一個積極因素,并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來考察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鎮化的影響。[14]基于此,本文選取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gap)作為衡量指標,表征城鄉收入差距。
(3)基本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是指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廣大城鄉居民最關心、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項目,包括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等方面。城鎮化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城鎮空間的擴張和城鎮人口的增加,只有讓城鎮中的人真正享受到逐步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務,才是城鎮化的根本目標。[15]所以,城鎮化的發展伴隨著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增長,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也將促進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本文就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和城市環境四個方面選取指標: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選取的指標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積(平方米);衡量教育方面的指標是每萬人專任教師數(包括小學、普通中學和普通高等學校教師總人數)(人);醫療方面選取的指標是每萬人擁有的醫院床位數(張);城市環境的測量指標是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這主要是考慮到上述指標大體上涵蓋了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方面,而且可以獲得準確的公開數據。這些指標有著不同的單位,我們不能進行簡單的加總,但又希望能夠有一個綜合的指標來衡量總體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所以在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②主成分分析法(PCA)是通過降維技術把多個具有一定相關性的指標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的統計分析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指標合成。來解決指標無法加總的問題,計算得出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綜合指標(ps)進行后續分析。
(二)數據來源
我們選取了我國36個一二線城市③一線城市是指在政治、經濟、社會活動中處于重要地位且具有全國性的主導和輻射帶動能力的大都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4座城市,對此學界已有共識;對于二線城市,學術界和實踐部門目前均無統一嚴格的界定,本文綜合了各方觀點將其界定為對經濟和社會活動具有較大影響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包括除一線城市之外的直轄市、省會城市(首府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即天津、重慶、沈陽、長春、哈爾濱、石家莊、鄭州、武漢、長沙、合肥、南昌、濟南、杭州、南京、福州、海口、呼和浩特、太原、西安、西寧、銀川、蘭州、烏魯木齊、成都、貴陽、南寧、昆明、拉薩、大連、青島、寧波、廈門。為研究對象。④選取一二線城市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1)這些城市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在全國土地出讓金總收入中的占比十分可觀,2001—2011年年均占比高達48.52%(拉薩市因數據缺失,未計算在內),極具代表性。(2)這些城市具有重要的全國性或地域性影響力,能夠產生巨大的集聚效應,在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中具有代表性。由于拉薩市的數據缺失,南昌、海口、西寧、太原、大連5個城市均存在建成區面積多年不變的情況,有悖于常理,故剔除上述6個城市。這樣,我們最終選取了30個樣本城市,樣本區間為2001—2011年。所有數據由歷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國土資源年鑒》、《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以及各城市年鑒整理而成。為了剔除價格變動因素對土地出讓金的影響,我們根據CPI平減指數將其統一調整為以2001年為基準的土地出讓金和人均GDP。表2給出了各變量的統計描述。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設定
根據上述分析和本文的研究思路,檢驗土地財政是否對我國城鎮化產生扭曲效應,并進一步探究土地財政對于空間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的影響,即如何對城鎮人口密度產生作用,我們構建如下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城鎮人口密度方程:

空間城鎮化率方程:

人口城鎮化率方程:

其中,Lnupdit表示對數城鎮人口密度;Lnsuit表示對數空間城鎮化率;Lnpuit表示對數人口城鎮化率;Lnltfit表示對數土地出讓金;Xit為控制變量向量;α0、η0、λ0為常數項;uit為隨機擾動項;下標i代表地區,t代表時間,k代表控制變量的個數。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城鎮人口密度方程的估計結果
采用Stata 11.0對城鎮人口密度方程進行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結果報告于表3。對于面板數據,我們首先要通過Hausman檢驗來確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隨機效應要求外生變量和個體效應不相關,而固定效應模型沒有這一要求。Hausman檢驗的原假設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是系統一致的,如果檢驗結果能夠接受原假設,就要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反之,如果拒絕原假設,就要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我們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在模型1中,P值為0.4,并不顯著,因此接受原假設,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但是在模型2中,P值為0.0136,在5%的水平上顯著,故拒絕原假設,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
模型1作為基礎回歸模型,只考慮土地出讓金對城鎮人口密度的影響。從結果可以看出,土地出讓金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符合預期。這說明土地出讓金越多,城鎮人口密度越小,即隨著各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的增加,其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慢于空間城鎮化速度,土地財政對城鎮化產生了扭曲效應。當然,對于城市人口密度的影響因素還有很多,為了研究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土地出讓金是否依然對城鎮人口密度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我們在模型2中加入控制變量,分析其他潛在影響城鎮人口密度的因素。結果表明,在控制了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城鄉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等因素之后,土地出讓金的系數依然顯著為負,且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本部分的估計結果具有很高的穩健性,土地出讓金對于城鎮化存在明顯的扭曲效應,支持了我們的假設。從數量關系上看,在加入控制變量之后,土地出讓金的系數由-0.058 5逐步上升至-0.02,即土地出讓金每增加1%,城市人口密度將下降0.02%,同時,A-R2的值從0.188 9上升至0.385 2,說明這些控制變量對城市人口密度整體上有解釋作用,模型擬合度有所增強。

表3 城鎮人口密度方程的估計結果
在各項控制變量中,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這一變量基本符合預期,其對于城市人口密度的影響顯著為負,即第二產業產值占比越高,空間城鎮化的速度越快于人口城鎮化的速度。這是因為第二產業主要包括工業和建筑業,而目前土地出讓的用途往往就是滿足工業用地和城市建設的需要。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越高,意味著工業和建筑業更為發達,對土地的需求更為強烈,農村用地大面積轉化為城市用地,極大地推動了空間城鎮化的發展。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城市人口密度負相關,這與我們的預期相反,可能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構成指標中包含人均道路面積,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意味著道路面積的不斷擴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動了空間城鎮化發展的作用。
此外,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城鄉收入差距的系數不顯著,說明這二者沒有直接影響到我國城鎮化的扭曲。
(二)空間城鎮化率方程和人口城鎮化率方程的估計結果
表2的實證結果證實了我國的土地財政對城鎮化有扭曲作用。為了進一步驗證模型2所獲得的結論,并探究扭曲作用的形成原因,我們分別用空間城鎮化率和人口城鎮化率來替代城鎮人口密度作為被解釋變量(依然以土地出讓金作為解釋變量,并采用相同的控制變量),估計空間城鎮化率方程(2)和人口城鎮化率方程(3)。對兩個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P值都在1%的水平上統計顯著,因此都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表4報告了實證檢驗結果。

表4 空間城鎮化率方程和人口城鎮化率方程的估計結果
從回歸結果來看,空間城鎮化率方程(2)和人口城鎮化率方程(3)中土地出讓金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土地出讓金對空間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均有正向影響,即土地財政對空間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發展都具有推動作用。但是通過比較兩者系數會發現,在采用相同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前提下,土地出讓金對空間城鎮化率的影響系數是0.037,對人口城鎮化率的影響系數僅為0.008 7,前者是后者的4.25倍,由此可推斷,土地財政對空間城鎮化的推動作用遠遠大于其對人口城鎮化的作用。這進一步驗證了前文中土地財政對城鎮人口密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土地財政扭曲了城鎮化發展的結論。
五、結論與建議
基于逐漸擴大的土地財政規模推動城市空間快速擴張,但外來人口的市民化過程卻滯后的經驗事實,本文對其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理論研究發現,中國當前的土地財政收入已經占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相當高的比重,從而使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產生了很強的依賴性。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產生了扭曲效應。
第二,實證分析表明,在控制了產業結構、城鄉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務等影響城鎮化發展的因素后,土地財政對空間城鎮化的推動作用遠遠大于對人口城鎮化的推動作用,從而對城市人口密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是導致中國城鎮化出現扭曲效應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對于導致城鎮化出現扭曲效應的重要因素——土地財政,只有進一步改革并完善財政管理體制,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明確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籌集收入的體制誘因。針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對城鎮化存在扭曲效應這一現實狀況,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必須正視土地財政對城鎮化的扭曲效應,對土地財政的支出范圍進行相應的限定。在土地財政短期內無法替代的現實情況下,應該規定土地出讓金在社會福利,尤其是外來人口市民化方面的投入,從而為地方政府推進人口城鎮化提供更加充裕的財力支持。
第二,徹底轉變地方官員以GDP增長為核心的錦標賽晉升模式。中組部下發的《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政績考核要突出科學發展導向,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考核評價政績的主要指標;要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標準,把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社會和諧進步、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建設等作為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唯有建立了正確的考核導向和考核指標體系,才能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地方官員的政績。更進一步,要將其真正落實到干部考核的實際工作中去,同時逐步將公眾對于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納入官員的政績考核中,讓轄區內的公眾意愿能夠影響官員的政治前途,以此激勵官員完善地區內的公共服務,妥善處理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問題,積極推動人口城鎮化的進程。
第三,改革戶籍制度,推進社會福利制度改革。中國戶籍制度改革面臨的難題是,戶籍制度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口登記制度,其核心是與戶口捆綁的社會福利差異。僅僅只是簡單地改變戶籍登記的歸類方式或者放寬落戶條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其重點在于現行的財政體制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要能夠負擔起市民化成本,使按照條件落戶在城市的新居民能夠平等地享有城市人口所擁有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待遇,做到戶口與權利相伴,實現健康持久的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
[1] 蔡繼明、程世勇:《中國的城市化:從空間到人口》,載《當代財經》,2011(2)。
[2] 陶然、曹廣忠:《“空間城鎮化”、“人口城鎮化”的不匹配與政策組合應對》,載《改革》,2008(10);李力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現狀、挑戰和應對》,載《浙江社會科學》,2010(12);鄭風田:《“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應該終結》,載《農民日報》,2011-01-11;鮑宗豪:《“土地財政”驅動城市化的四大悖論》,載《光明日報》, 2011-01-28。
[3] 熊柴、高宏:《人口城鎮化與空間城鎮化的不協調問題——基于財政分權的視角》,載《財經科學》,2012(11)。
[4] 陶然、徐志剛:《城市化、農地制度與遷移人口社會保障——一個轉軌中發展的大國視角與政策選擇》,載《經濟研究》,2005(12)。
[5] 周飛舟:《分稅制十年:制度及其影響》,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6)。
[6] 崔軍:《三級財政框架下我國各級政府財力與事權匹配的基本構想》,載《經濟與管理研究》,2011(6)。
[7] 王文劍、覃成林:《地方政府行為與財政分權增長效應的地區性差異——基于經驗分析的判斷、假說及檢驗》,載《管理世界》,2008(1)。
[8] 陶然、袁飛、曹廣忠:《區域競爭、土地出讓與地方財政效應:基于1999—2003年中國地級城市面板數據的分析》,載《世界經濟》,2007(10)。
[9] 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載《經濟研究》,2004(6)。
[10] 李力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現狀、挑戰和應對》,載《浙江社會科學》,2010(12)。
[11] 周其仁:《城鎮化要汲取國家工業化的教訓》,載《經濟觀察報》,2013-01-14。
[12] 張雙長、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財政基礎分析——基于土地財政與房地產價格關系的視角》,載《財政研究》,2010(7)。
[13] 林曦:《我國城鎮化影響因素的計量分析》,載《市場論壇》,2006(1)。
[14] Zhang KH,Song S.“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China Economics Review,2003,14(4)。
[15] 黎華亮:《城鎮化進程中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載《決策咨詢通訊》,2009(4)。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istorting Effects of Land Finance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Century——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First-tier and Second-tier Cities
CUI Jun,YANG Q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century,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observed as distorted,which means that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gs obviously behind the spatial urbanization.Meanwhile,the trend of land finance within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is getting worse.It could be found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that:the formation of land finance revenue has directly stimulated spatial urbanization;however,constrained by the current mechanism of local officials evaluation system,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land finance determine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re taking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spatial urbanization but a negative one to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Thus,the impact of the land finance of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o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is far obvious on space than on population.The land finance of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density of urban population,and hence an inevitable factor that leads to distor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year of 2001;land finance;urbanization;distorting effects;first-tier and secondtier cities;empirical study
崔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地方財政研究中心主任;楊琪: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責任編輯 武京閩)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研究品牌計劃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13XN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