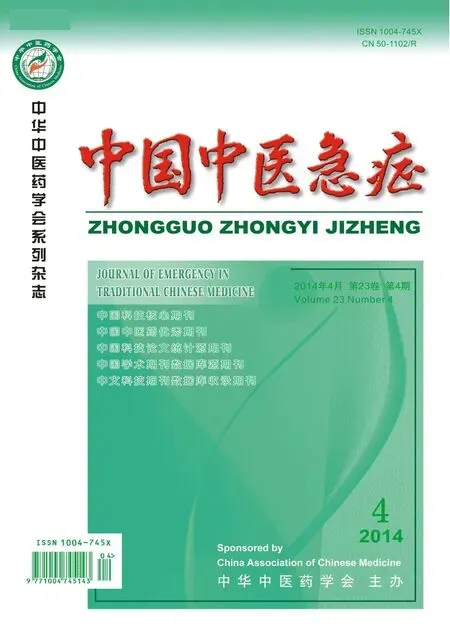涼血散瘀法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的立論依據
田同良 解姍姍 朱應征
(河南省鄭州市第九人民醫院,河南 鄭州 450053)
涼血散瘀法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的立論依據
田同良 解姍姍 朱應征
(河南省鄭州市第九人民醫院,河南 鄭州 450053)
急性出血性中風 瘀熱阻竅 涼血散瘀
中風根據有無神志改變分為中經絡與中臟腑,僅有肢體功能障礙等癥狀無神志改變稱為中經絡,合并有神志改變者稱為中臟腑。中臟腑又根據其虛實分為閉證與脫證。歷代醫家治療中風閉證多應用鎮肝息風、化痰清熱開竅、溫經活絡諸法,雖能取得療效,但效果不理想。筆者認為,急性出血性中風偏側肢體障礙、痰火上攻為標,其本在于瘀熱上行阻于腦部。筆者從瘀熱立論,應用涼血散瘀法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以期在理論上有所創新,療效上有所突破。
1 從瘀熱論治急性出血性中風的文獻依據
古代醫籍中無中風專論,散見于偏枯、眩暈、中風、厥證、風痱等論述中,其病理因素多為瘀、熱;病機多為瘀熱阻竅。《脈訣》中明確指出“熱則生風,故云風自火出”。劉河間曰“諸逆沖上,皆屬于火”。認為中風癱瘓因腎水虛衰,心火旺盛,水不能制火,火氣逆亂,導致偏側肢體癱瘓。強調了“火熱”對于急性中風發病的重要性。
中醫典籍中,中風發病與瘀血相關性的論述頗多。《醫方類聚》說“大中風”皆因陰陽臟腑失調,榮衛血氣錯亂,以至“經道或虛或塞”而發病。《赤水玄珠》論中風起初宜理氣消痰以息風,日久養血行血和血以息風,并指出“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順氣和血,斯得病情”,暗示瘀血是中風的重要病理因素;王清任更為重視瘀血,其所創制的活血化瘀方劑至今仍在中風的治療中廣泛應用。中風病位在腦。《素問·調經論》指出“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為大厥。”《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明·方廣《丹溪心法附余·附諸方》論述老年因怒而中風時曰“火載痰上,所以舌僵不語,口眼歪斜,痰涎壅盛也”。諸論述均提及其病位在上,即腦部。王肯堂在《證治準繩》明確指出病位在腦,認為“蓋髓海真氣所聚,卒不受犯,受邪則死不可治”。
古代醫家雖未明確指出中風病機為瘀熱阻竅,仍可見到類似論述。《內經》中“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為大厥”之“氣”實指“熱”;“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之“血菀于上”實指血與氣上沖于腦部,瘀血阻竅。
2 急性出血性中風瘀熱阻竅證的辨證依據
急性出血性中風臨床癥狀包括神志異常與形體改變。“神”的改變:卒然昏到,不省人事,或神志恍惚,或昏蒙不語,或躁擾不寧。“形”的改變:偏側肢體癱瘓、強痙拘急,舌強失語,口歪眼斜,腹脹硬滿,便干便秘,發熱甚至高熱,或身熱夜甚,或自覺煩熱、潮熱;面唇紅赤或深紫;舌質紅絳或紫黯,苔黃燥;脈弦滑數或結。氣血上沖于腦,腦竅閉阻,瘀熱之邪入里內陷心包,蒙蔽心神,神機失靈。典型表現為突然昏仆、不省人事;非典型者可表現為嗜睡、昏蒙不語、神志恍惚等神識抑制狀態,亦可表現為心煩、躁擾不寧、譫語等神識亢奮狀態,為所致。半身不遂、肢體抽搐、痙厥、舌強語謇等“形”的改變系瘀熱之邪內入營血,熱煎營陰成痰,瘀阻脈絡,邪陷心肝,經絡失潤。發熱甚至高熱,現代醫學認為,顱內血腫吸收,或呼吸道、泌尿道感染,或病變累及丘腦,皆可致體溫調功能障礙,體溫升高。中醫認為其病機為外邪內侵或內熱亢熾,煎灼津液,郁而不能外發;部分病人發熱表現為身熱夜甚,夜間在表之陽氣內藏,與血分之熱邪互結,煎津耗液;或表現為烘熱、煩熱、潮熱,為瘀血與熱邪相互搏結,內熱擾心,蒸騰于上所致;面唇潮紅或深紫為瘀熱阻竅,郁于上部不能外達的典型特征。腹脹硬滿,便干便秘,為脾胃運化失司,氣機阻滯,升降失調所致。急性出血性中風患者多見舌質紅絳或紫黯,苔黃燥;脈弦滑數或結,皆為瘀熱征象。
從CT或MRI檢查亦可以判斷瘀熱阻腦之輕重。CT或MRI示基底節區、腦葉出血小于30 mL,丘腦出血小于15 mL,小腦出血小于10 mL,出血量少,瘀熱阻竅的臨床表現輕,多無神志改變及明顯神經功能障礙[1]。CT或MRI示基底節區、腦葉出血大于等于30 mL,丘腦出血大于等于15 mL,小腦出血大于等于10 mL[1],腦絡破損,出血量大,壓迫生命中樞,瘀熱阻竅的臨床表現較重,出現神昏譫語等神志改變及神經功能障礙,此類病例變化多端,易迅速演變為脫證。此外,實驗室相關檢查亦可提示“瘀熱”的存在,“熱”與炎癥相關,“瘀”則與血液成分的改變相關。急性出血性中風患者血白細胞總數、中性粒細胞百分比升高顯著;纖溶、凝血系統異常,如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物(t-PA)[2]和尿激酶型纖溶酶原激活物(u-PA)[3]、血栓調節蛋白(TM)、纖溶酶原(PLG)、纖溶酶(PL)活性、血小板功能相關物質血栓素B2(TXB2)[4]、6酮-前列腺素F1α(6-keto-PGF1α)[5],凝血因子活性等物質發生異常;DIC形成,血黏度增高,血液流變學異常。瘀熱互結脈絡,灼傷陰津,血液黏稠,運行緩慢,進一步加重瘀熱阻滯經絡,甚至導致因瘀而出血,這些血液指標的改變,則從另一角度提示瘀熱病理因素的存在。
3 涼血散瘀法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的臨床依據
近幾十年來,諸多中醫臨床學家致力于中風的治療,實踐證明,若能從“瘀熱阻竅”的病機著手,應用涼血散瘀法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療效頗佳。周仲瑛教授依據涼血散瘀法創制涼血通瘀注射液和口服液(大黃、水牛角片、黑山梔、生地黃、赤芍等)分別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32例,隨機設西藥常規治療對照組31例。結果示用藥后意識障礙恢復率、存活率、神經系統總積分下降率,涼血通瘀注射液和口服液組皆明顯優于對照組。實驗證明涼血通瘀注射液、口服液均有促進腦內血塊的吸收、緩解腦水腫、改善神經功能缺損,恢復肢體功能等多種作用[6]。顧寧應用涼血通瘀注射液治療32例急性腦出血患者亦取得顯著療效[7]。黃桂華臨床觀察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瘀熱阻竅證64例,其中用涼血散瘀合劑治療確診為急性腦出血患者 (發病48 h內入院)30例,并與單純西醫內科綜合療法的對照組30例進行隨機對照。結果顯示治療組主要癥狀、體征的起效和消失時間均明顯短于對照組;血液流變學指標改善程度、腦水腫程度及血腫吸收時間均明顯優于對照組;治療前兩組血漿纖維蛋白原含量、D-D聚體、血紅蛋白、血小板計數、白細胞和血漿蛋白等指標均明顯升高,治療后,治療組較對照組均先行恢復正常。涼血散瘀法治療出血性中風既能清除血分之熱,又能止血、消散瘀血,從而改善血檢查指標,減輕腦水腫,促進血腫吸收,緩解神經受壓而導致的損傷,故能有效地治療出血性中風,恢復肢體功能[8]。
4 涼血散瘀法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的特點
“涼血散瘀”,寓有涼血清熱、散瘀通脈、通腑泄熱多方面的涵義。其特點概括為:見血不獨收澀止血,而在消散離經之血;攻瘀不在破血,而在涼血以散瘀熱;治熱不在清,而在順與降,使上亢之陽回潛下焦不妄動。此不同于活血化瘀、破血逐瘀、清熱瀉火諸法。(1)涼血清熱,直清血分之熱勢。張景岳曰“治熱必從血分,甚者用苦寒,微則用甘涼”,開創了涼血清熱法治療中風的先河。涼血與清熱相輔相成,涼血有助清熱,清熱有助涼血,針對直接病因,直折“熱”勢。血分之熱緩解,防止其繼續迫血妄行,出血量進一步擴大;同時預防血熱傷津,煎津成痰瘀,郁而化熱,熱勢進一步增加,從而病情加重;涼血清熱對已生之瘀熱亦有清除作用,使血流暢通。“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亦提示通過涼血清熱,以滅風火內熾之勢,有助于寧血止血,預防繼發性出血。(2)通腑順降,扭轉逆亂之血氣。瘀熱互結腦竅,亦與陽明熱結相關。胃腸為人體氣機升降之樞紐,“血氣并走于上”氣血壅塞腦部發生瘀血,則氣機不降,胃腑積滯內停,熱氣上蒸腦部,進一步加重瘀熱阻竅。故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須通胃腑瀉積熱,以順降陽明,熱從外解。及時應用通腑之法,既能給邪以出路,又能“釜底抽薪”,達到上病下取,“以下為清”的目的,以此平抑肝風痰火上逆之勢,平息血分瘀熱之蒸騰。(3)散瘀通脈以治血。此治血包括消除蓄血、暢通血行兩層含義。消散腦中血腫,緩解血腫對中樞神經的壓迫,降低顱內壓,是治療急性出血性中風的首要目標。腦中血腫既是瘀熱上沖的病理結果,亦是引起瘀熱阻竅、搏結不去的病理原因。散瘀通脈可以消散腦中之蓄血,以防郁而生熱,瘀熱互結;通脈散瘀亦可暢通周身脈絡,促進血液運行,以免血與熱結,灼傷陰津,致血液黏稠;血熱易生風,血行風自滅,行血散血可有效地防止動風及釀痰。
5 討論
現代中醫臨床醫師認為急性出血性中風病機為肝腎陰虛,肝陽上亢,氣血上沖腦部所致,治療以鎮肝息風,通腑泄熱為主,方用鎮肝熄風湯加減,忽略了瘀血病理因素的存在,受現代西醫觀點的影響,認為腦部出血,如加用活血化瘀藥物,易引起二次出血。嚴容通過實驗對比研究認為,急性出血性中風在6~24 h后應用活血化瘀藥較安全[9]。涼血散瘀藥攻破瘀血能力較弱,適合瘀熱阻竅之病機,更加安全,如丹參、生赤芍、牡丹皮之類。部分中醫師認為急性出血性中風病機為氣虛氣血無力上行而致腦部瘀血,治療喜用補陽還五湯加減。其實,急性出血性中風臨床證型為氣虛血瘀者甚少,多為肝陽上亢,血壓偏高,補陽還伍湯中黃芪與藥物溫熱的活血化瘀藥物合用補氣助推瘀熱上行,加重病情,更有人提出黃芪量大降壓,量小升壓,筆者不敢茍同。本文通過文獻、臨床辨證及西醫檢查、臨床治療效果多方面驗證,瘀與熱是急性出血性中風的主要病理因素,其病機為氣血上沖,瘀熱阻竅,應用涼血散瘀法即涼血清熱、散瘀通脈、通腑泄熱消除病理因素,適合病機,效果更佳。
[1] 王忠誠.王忠誠神經外科學[M].武漢:湖北科技出版社,2005:866.
[2] 叢玉隆.血液學體液學檢驗與臨床釋疑[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4:150.
[3] 邵澤偉.急危重癥實驗檢查[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7:139.
[4] 張玉英.現代急重癥臨床進展[M].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77.
[5] 宋景貴,吳家冪,馬存根.神經病學[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9:126.
[6]周仲瑛.出血性中風(瘀熱阻竅證)證治的研究[J].中醫藥學刊,2002,20(6):709.
[7]顧寧.涼血通瘀注射液對急性腦出血患者近期療效的影響[J].新中醫,2007,1(39):40.
[8]唐桂華.涼血散瘀法治療腦出血急性期機理探討[J].云南中醫中藥雜志,2006,27(1):71.
[9]嚴容.活血化瘀法在出血性中風急性期的運用及常見問題探討[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6,18(4):12.
R255.2
A
1004-745X(2014)04-0659-03
10.3969/j.issn.1004-745X.2014.04.041
2013-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