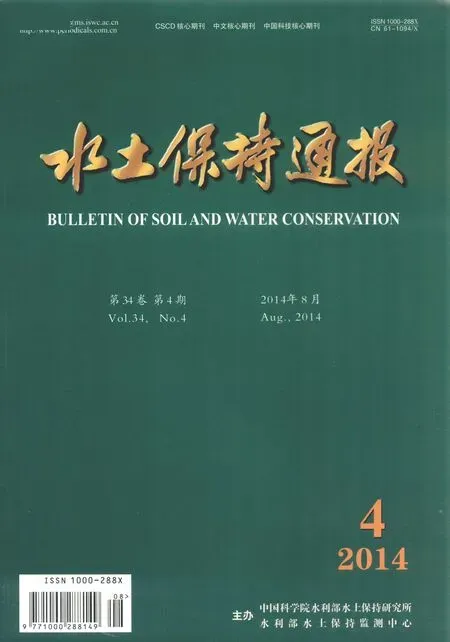窟野河流域徑流變化及人類活動對其的影響率
郭巧玲,陳新華,劉培旺,方海軍
徑流受氣候、地貌、土壤、植被等自然條件以及人類活動的耦合作用,其演變過程既表現出確定性的規律,同時也有強烈的隨機性[1]。隨著全球變暖和人類活動影響的加劇,河川徑流發生了顯著的時空變化,直接影響了流域水資源的配置、開發與利用,以及河流生態系統的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2]。窟野河流域隨著黃河沿岸能源化工基地建設步伐的加快,該流域徑流過程發生了巨大變化,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流域甚至出現嚴重的斷流現象。而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窟野河產沙特性[3-4]和洪水特征的分析[5-6],較少涉及徑流變化及人類活動影響的研究,僅有趙曉坤等[7]分析了1954—1993年間的徑流量變化。因此,很有必要對窟野河近年來的徑流變化及人類活動對徑流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深入認識窟野河徑流演化規律和人類活動影響程度,為流域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提供依據,同時為黃河中游治理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概況
窟野河發源于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東勝市,從神木縣石圪臺進入陜西省境內,于陜西省神木縣賀家川鄉沙峁頭村匯入黃河,干流全長241.8km,流域面積8 706km2。支流餑牛川與干流的交匯口以上為烏蘭木倫河,交匯口以下稱窟野河[7]。流域地處黃河中游干旱、半干旱地區,多年平均氣溫7.9℃,平均降水量410mm左右,無霜期280d。受大陸性季風影響,春季干旱少雨、夏季多有暴雨、秋季降霜早凍、冬季嚴寒稀雪。流域地形、地貌可分為風沙區和黃土丘陵溝壑區兩大類,窟野河神木以上位于毛烏素沙漠的南緣,屬風沙區,地勢平坦,地表大部分為沙層覆蓋,區內沙丘連綿,灘地、海子星羅棋布;神木以下為黃土丘陵溝壑區,區內丘陵起伏,溝壑縱橫,地形破碎,黃土土質疏松,植被稀少[3]。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窟野河流域現有王道恒塔、新廟、神木、溫家川等4個基本水文站。其中,溫家川是窟野河流域的出口控制站。本研究以王道恒塔站和溫家川站為代表,選用王道恒塔站1960—2010年和溫家川站1953—2010年逐月實測徑流資料和2個水文站1960—2010的降水觀測資料,數據來自黃河流域水文年鑒。
所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累積距平法,滑動平均法,Mann—Kendall法,R/S 分析法等[8-14]。
3 徑流變化分析
3.1 徑流年際變化特征分析
變差系數Cv和年極值比常用來反映河流徑流年際變化的總體特征。從表1可知,王道恒塔站歷年最大徑流量5.25×108m3,最小徑流量3.80×107m3,多年均值為1.73×108m3,徑流年際極值比為13.82,變差系數1.33。溫家川站歷年最大徑流量1.37×109m3,最小徑流量1.25×108m3,多年均值為5.31×108m3,徑流年際極值比為10.97,變差系數0.57。各站點的徑流年際極值比和變差系數都比較大,說明窟野河徑流豐枯變化比較劇烈,而且徑流年際極值比和變差系數從上游至下游呈減小的趨勢。
表2顯示了窟野河2水文站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年代際平均徑流量。由表2可以看出,2個水文站的年代際平均徑流量始終處于減少狀態。對于王道恒塔站,徑流減少幅度持續增加。21世紀初平均年徑流量是多年均值的38%,僅為20世紀60年代平均年徑流量的26%。就溫家川站而言,21世紀初的徑流量減少幅度最大,其徑流量是多年均值的30%,僅為20世紀60年代平均年徑流量的23%。

表1 窟野河徑流量年際變化特征 108 m3

表2 窟野河各水文站年代際平均徑流量 108 m3
3.2 徑流變化趨勢分析
圖1為窟野河2個水文站的年徑流量變化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近幾十年來2個水文站的年徑流量均表現出遞減的趨勢,王道恒塔站線性趨勢系數為-0.045,溫家川站線性趨勢系數為-0.125。為了更明顯地分析徑流量年際變化的階段,分別繪制了王道恒塔水文站1960—2010年和溫家川水文站1953—2010年天然徑流量累積距平曲線(圖2)。由圖2可以看出,王道恒塔站1960—1985年,徑流量基本處于上升趨勢;1986—1995年該站徑流量出現一定的下降趨勢;1996—2010年,徑流量下降幅度顯著增大。溫家川站1953—1979年,徑流量基本處于上升趨勢;1980—1997年,徑流量出現一定的下降趨勢;1998—2010年,徑流量下降幅度顯著增大。2站都是在20世紀末出現徑流量大幅減少的現象。

圖1 窟野河各水文站年徑流量變化趨勢

圖2 窟野河流域年徑流累積距平曲線
采用R/S分析法對窟野河2個水文站的年徑流量序列進行分析來說明徑流量序列未來的變化趨勢。由分析結果可知,王道恒塔和溫家川2個水文站的Hurst指數(H)分別為0.853和0.803,H 值均大于0.5,說明2個水文站未來的年徑流變化趨勢與過去相同,呈持續遞減的特征。若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依然按照現在的趨勢發展,窟野河年徑流量將繼續呈現遞減趨勢。
3.3 徑流變化突變點分析
利用M—K突變檢測方法對流域徑流序列進行突變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在0.05顯著性水平下,王道恒塔站1985年之前,UF值絕大多數大于零,說明在該時段徑流量呈增加趨勢;1985—1995年,UF值均小于零,說明在該段時間徑流量呈減少趨勢;UF與UB曲線交叉點發生在1995年,且交點超過信度線,說明1995年是其徑流突變開始年份,出現了徑流量的大幅顯著下降。對于溫家川站,1983年之前,UF值絕大多數大于零,說明在該時段徑流量呈增加趨勢;1983—1998年,UF值均小于零,說明在該段時間徑流量呈減少趨勢;UF與UB曲線交叉點發生在1998年,且交點超過信度線,說明1998年是其徑流突變的開始年份,徑流量出現顯著下降。
4 徑流變化影響率計算
4.1 徑流變化影響率計算方法
雙累積曲線法是進行時間序列分析的一種常用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兩個變量按同一時間長度逐步累加,一個變量作為橫坐標,另一個變量作為縱坐標,其拐點可作為分析變量階段性變化的依據[15]。當只有降水的變化而無其它因素影響時,雙累積曲線應為一直線;當受到人類活動等其他因素影響時,曲線將會發生偏移,可根據雙累積曲線發生偏移的年代確定下墊面受人類活動影響的劇烈程度。因此,降水—徑流雙累積曲線可以揭示人類活動對徑流影響的階段性變化。
4.2 計算結果分析
圖3是利用1960—2010年的同期降水、徑流量資料建立的王道恒塔站和溫家川站降水—徑流雙累積曲線,曲線分別在1968和1971年發生偏移,因此,可以確定1960—1967年和1960—1970年分別為王道恒塔站和溫家川站的基準期,并以此將兩個水文站徑流序列劃分為幾個階段(表3)。對基準期累積降水量和累積徑流進行回歸分析,建立基準期內累計年降水量∑P和累積年徑流量∑R序列的相關方程,其方程為:

依據基準期內兩個水文站年降水和年徑流資料,建立基準期內的降水序列和徑流序列的相關方程,其方程為:

根據年降水量與年徑流量的相關方程可得2站不同時段的理論平均徑流量,將其作為天然徑流量的近似值。基準期實測值與各時段計算值的差值即為此時段降水變化對徑流變化的影響值;基準期實測值與各時段實測值的差值減去降水變化的影響值即為人類活動對徑流變化的影響值;影響值與總減少值的百分比即為影響率。由表3可知,1968—2010年王道恒塔站降水對徑流量的影響率為-3.03%,是因為該時期的降水量相對于基準期有所增加,導致降水影響差值為負;但是,該時期徑流量總減少量占其實測徑流量的55.8%,主要是人類活動導致流域徑流量減少。對比不同階段,各階段人類活動和降水對徑流的影響程度亦不同。1968—1978年和1985—1996年2個階段,由于降水量相對于基準期有所增加,導致降水影響差值為負。1997—2010年,人類活動對徑流量減少的影響率達到80.48%,遠遠超過降水的影響。對于溫家川站,1971—2010年人類活動對徑流量減少的影響率是81.92%,是降水對徑流量減少的影響率的4倍多,說明人類活動是導致流域徑流量減少的主要原因。對比不同階段,人類活動對徑流量減少的影響率基本處于增加趨勢,到1997—2010年,人類活動對徑流量減少的影響率高達93.62%。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2個水文站徑流量都出現了顯著減少的現象,且導致徑流量減少的主要原因都是人類活動的影響。
在窟野河流域,改變徑流的人類活動方式以礦產資源開采和水土保持措施為主。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梯田建設、造林、種草和修筑淤地壩等。根據趙曉坤等[7]調查,20世紀70—80年代,梯田、壩地、造林和種草等水土保持措施的蓄水量分別達到1.19×107m3和2.54×107m3,80年代窟野河流域水保措施減水量約為1.60×108m3[6],水土保持措施發揮了較大的減水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煤炭大規模開采等人類工程活動成為徑流量減少的主要因素之一。1991年窟野河流域原煤產量為6.26×106t,2011年窟野河原煤產量為1.73×108t,為1991年的27.59倍。煤炭開采破壞了水資源形成與儲存環境及排泄途徑和方式,水資源的產、匯、補、徑、排等發生變化,直接表現為地表徑流減少,根據蔣曉輝等[16]研究成果,窟野河流域開采噸煤對徑流的影響大約為5.27m3。

圖3 窟野河流域水文站降水-徑流雙累積曲線

表3 降水和人類活動對窟野河徑流影響
5 結論
(1)近50a來,窟野河徑流年際變化表現出遞減的趨勢,尤其自20世紀末以來,呈現出顯著減少的趨勢。王道恒塔站徑流突變年份為1995年,溫家川站徑流突變年份為1998年。
(2)在現有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保持不變的狀況下,窟野河徑流量的遞減趨勢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會持續。
(3)導致窟野河徑流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人類活動,其次是降水。不同歷史階段,人類活動的劇烈程度不同,對徑流量減少的影響亦不同。影響最劇烈的階段為1997—2010年,該階段人類活動對徑流量減少的影響率在2個水文站分別高達80.48%和93.62%。
(4)氣候變化是河川徑流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資料所限,本研究在氣候要素中,僅考慮了降水,今后還應進一步研究蒸發、氣溫等對徑流的影響。
[1] 侯欽磊,白紅英,任園園,等.50年來渭河干流徑流變化及其驅動力分析[J].資源科學,2011,33(8):1505-1512.
[2] 曹建廷,秦大河,羅勇,等.長江源區1956—2000年徑流量變化分析[J].水科學進展,2007,18(1):29-33.
[3] 王小軍,蔡煥杰,張鑫,等.窟野河季節性斷流及其成因分析[J].資源科學,2008,30(3):475-480.
[4] 馬文進,慕明清,陳鴻,等.窟野河產沙特性分析[J].人民黃河,2008,30(1):22-27.
[5] 趙曉坤,王隨繼.窟野河洪水特性及變化趨勢分析[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2,26(4):92-96.
[6] 王璨,周秀平,王文圣.窟野河洪水序列變異點綜合診斷[J].水電能源科學,2012,30(7):50-53.
[7] 趙曉坤,王隨繼,范小黎.1954—1993年間窟野河徑流量變化趨勢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水資源與水工程學報,2010,21(5):32-36.
[8] 裴宇航,孫爽,王春麗,黑龍江省近50年日照時數變化特征分析[J].黑龍江農業科學,2012(8):41-43.
[9] 張群,徑流資料系列分析在實踐中的運用[J].水利科技與經濟,2010,16(9):1000-1001.
[10] Kendall M G..Rank Correlation Measures[M].London:Charles Griffin,1975.
[11] 魏鳳英.現代氣候統計診斷與預測技術[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7.
[12] 徐宗學,李占玲,史曉崑.石羊河流域主要氣象要素及徑流變化趨勢分析[J].資源科學,2007,29(5):121-128.
[13] 趙晶,王乃昂.近50年來蘭州城市氣候變化的R/S分析[J].干旱區地理,2002,25(1):90-95.
[14] 張曉偉,沈冰,黃領梅.和田河年徑流變化規律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07,22(6):975-979.
[15] Yue S,Pilon P,Phinney B.Canadian streamflow trend detection:Impacts of serial and cross correlation[J].Hydrological Science Journal,2003,48(1):51-63.
[16] 蔣曉輝,谷曉偉,何宏謀.窟野河流域煤炭開采對水循環的影響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10,25(2):30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