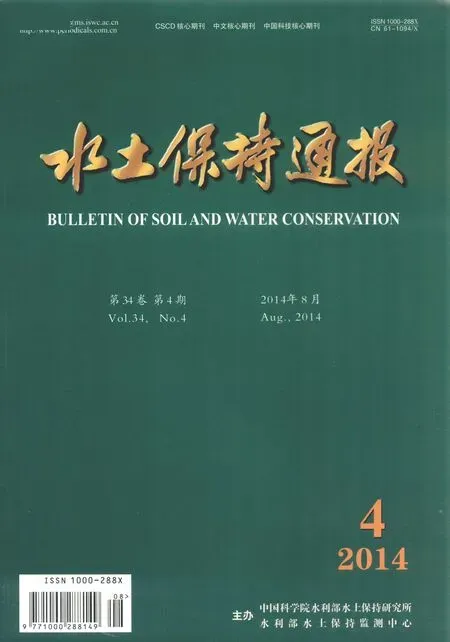基于荒漠化差值指數(DDI)的精河流域荒漠化研究
毋兆鵬,王明霞,趙 曉
監測土地荒漠化發展趨勢,掌握其動態變化規律,對土地荒漠化程度進行評估分級,為荒漠化綜合治理、全面規劃、管理決策提供實時資料和動態信息,是目前荒漠化研究的重要內容[1]。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新疆地區已成為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區域,而精河流域綠洲作為新亞歐大陸橋進出我國的西大門,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重點發展的天山北坡經濟帶重要組成部分,但其支撐資源開發的生態環境同時也極為脆弱。因此,對該區域開展土地荒漠化監測研究,不僅可以為當地生態環境治理和保障歐亞大陸橋暢通等提供決策參考,而且可為干旱區土地荒漠化監測研究提供范例。
荒漠化遙感監測目前主要采用監督分類、非監督分類、決策樹分層分類及神經網絡自動提取等方法[2-7]。半自動方法不僅工作強度大,效率低,會較大受到主觀影響,而且由于對遙感信息的利用程度不高,從而難以讓豐富的遙感信息在荒漠化監測中發揮作用。自動分類方法中,盡管現有的荒漠化理論研究已為其提供了較完整的分類評價指標體系,但多數指標為非物理參數,制約了其從遙感數據中的直接提取,使得分類精度的提高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發展荒漠化遙感定量評價方法是極具價值的方向[8]。由遙感圖像確定的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是反映地表植被狀態的重要生物物理參數,而地表反照率(Albedo)則是反映地表對太陽短波輻射反射特性的物理參量。隨著荒漠化程度的加重,地表植被遭受嚴重破壞,地表植被蓋度降低,生物量減少,地表粗糙度下降,在遙感圖像上表現為NDVI值相應減少,地表反照率得到相應的增加。荒漠化研究表明,如果不單獨依靠上述某一個參數,而是通過構造“反照率(Albedo)—植被指數(NDVI)特征空間”獲取植被指數和地表反照率的組合信息,則可以更加有效和便捷地實現荒漠化時空分布與動態變化的定量監測與研究[9]。本文以多時相遙感數字圖像為資料源,參考各類專題圖,結合實地野外驗證,針對精河流域綠洲的特點,系統分析研究區地表在Albedo—NDVI空間的形態特征,并依據荒漠化差值指數(DDI)獲取了研究區1990—2011年的荒漠化變化時空演變信息,以期為研究區今后荒漠化的控制、改造工作提供基礎數據和技術方法支撐。
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北部準噶爾盆地西南邊緣,天山支脈婆羅科努山北麓,介于81°07′52″—83°05′48″E,44°00′21″—45°00′56″N 之間,包含整個艾比湖區、精河縣城和精河流域綠洲,面積1.12×104km2。該區域屬“絲綢之路”新北道重鎮,是北疆交通要沖,經濟戰略位置突顯,具有東聯西出、西引東進、商貿發展的優勢。由于地處亞歐大陸腹地,遠離海洋,加之高大山脈的阻擋,導致該區夏季降水稀少,冬季干燥寒冷,大陸性氣候特征顯著。年均氣溫7.3℃,平原區多年平均降水量91mm。該區還是北疆沿天山一帶風沙天氣最多的區域,大風多,持續時間較長,干燥的氣候和強勁、活躍的風力決定了強烈的蒸發,多年平均蒸發量為1 625mm,達到年均降水量的20倍。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所用的圖像數據源包括1990年10月25日TM-5影像1景、2011年9月13日TM-5影像1景,影像的空間分辨率為30m。影像軌道號為146-29,成像條件均為無云。影像處理主要在ENVI 4.8圖象處理軟件的支持下進行,具體包括遙感影像的輻射定標,大氣校正,幾何精校正,圖像組合處理,圖像裁剪等,誤差小于一個像元。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的計算借助近紅外和紅光波段的反射值計算完成,地表反照率(Albedo)的反演采用Liang[10]建立的反演模型。

為便于后期數據的對比和特征空間的構建,對歸一化NDVI值(N)和歸一化Albedo值(A)全部采用歸一化公式進行了處理。

2.2 Albedo-NDVI特征空間的構建
根據曾永年等[9]的研究結論,遙感反演的NDVI(橫坐標)和Albedo(縱坐標)構成的散點圖特征空間應表現為梯形。為了研究精河流域綠洲荒漠化過程,選擇地表覆蓋類型比較全面的典型區,利用歸一化處理后的NDVI和Albedo值構建了Albedo—NDVI特征空間散點圖,散點圖呈典型的梯形分布(圖1)。圖中A點代表貧水低植被覆蓋地表(戈壁、城鎮及沙漠);B點代表富水低植被覆蓋地表(少部分農田及裸地);C點代表貧水高植被覆蓋地表(部分農田);D點代表富水高植被覆蓋地表(大部分農田)。

圖1 不同土地覆蓋遙感圖像與Albedo-NDVI特征空間對比
散點圖上界邊A—C為反照率上界線,表示在區域范圍內給定植被蓋度條件下,由于地表土壤水分缺失而導致的反照率最高上限。散點圖下界邊B—D為反照率下界線,標出了在給定植被蓋度條件下,由于地表土壤水分狀況相對較好而導致的反照率下限。利用ENVI軟件的2DScatter Plots功能,將實際不同地表覆蓋類型與其在Albedo—NDVI特征空間中的分布進行對照,結果表明不同地表覆蓋類型在Albedo—NDVI特征空間中能很好地加以區分。
3 結果分析
3.1 Albedo-NDVI空間下的荒漠化特征確定
研究表明,不同荒漠化土地對應的植被指數(NDVI)和地表反照率(Albedo)具有非常強的線性負相關性[9]。如果以此相關系數構建一個簡單的二元線性多項式,并用其在代表荒漠化變化趨勢的垂直方向上劃分Albedo—NDVI特征空間,便可以將不同的荒漠化土地有效地區分開來。

式 中:DDI——荒 漠 化 分 級 指 數 (desertification difference index),K值由特征空間中擬合的曲線斜率確定。
為確定公式(5)中的K 值,在研究區隨機選取1 848個樣點,對歸一化后的Albedo和NDVI柵格數據進行統計回歸分析,其R2達到0.84,這也表明在Albedo—NDVI空間中,研究區不同荒漠化土地類型對應的兩種指數同樣具有非常強的線性負相關。

將公式(6)中的斜率a,按a=-1/k求解,由此,確定DDI的最終表達式為

基于統計學Jenk原理的自然斷裂法能夠使各級的內部方差之和最小,因此利用該方法將DDI值分為5個值域區間,同時結合實地調查,最終確定了研究區的5級荒漠化指標(表1)。在ArcGIS 9.3軟件中利用上述方法和指標,提取荒漠化信息,最終得到研究區1990和2011年兩期荒漠化土地等級圖(圖2)。

表1 精河流域土地荒漠化遙感監測指標

圖2 1990和2011年精河流域土地荒漠化分布
3.2 研究區荒漠化過程
利用ArcGIS軟件對獲得的研究區荒漠化影像進行變化矩陣求解,結果詳見表2。從荒漠化面積數據可以看出,1990年研究區荒漠化總面積為9.16×105hm2,2011年總面積減至8.80×105hm2,20a間減少了3.54×104hm2。
為進一步反映土地荒漠化面積的年變化率,采用動態度K來描述荒漠化的變化速度:

式中:K——研究時段內研究區土地荒漠化的動態度;St——研究時段內研究區荒漠化土地面積的變化;Wa——研究時段初期荒漠化土地面積;T——研究時段(年)。

表2 精河流域1990和2011年土地荒漠化等級轉化矩陣 104 hm2
從研究區荒漠化面積的年變化率來看,1990—2011年極重度、重度、中度及輕度荒漠化面積的動態度分別為0.74%,0.38%,-0.82%和0.01%,表明21a間除了中度荒漠化面積以每年0.82%的速度減少外,極重度、重度和輕度則分別以每年0.74%,0.38%和0.01%的速度在增加,也就是說從1990—2011年,研究區雖然未荒漠化土地面積以每年2.89%的速度在增加,但其它荒漠化類型也同樣具有增加趨勢,尤其是極重度荒漠化的增長速度極為突出。
通過將轉化矩陣結果分別按強烈逆轉、逆轉、穩定、惡化、強烈惡化這5個級別進行統計計算(表3),對研究區荒漠化的空間動態變化進行了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研究區1990—2011年在荒漠化面積變化方面,除65.08%的未變化部分外,惡化級別類型所占比例最大,達1.58×105hm2,占總面積的16.23%;其次是逆轉、強烈逆轉等好轉趨勢類型,共計1.31×105hm2,占總面積的13.49%;強烈惡化面積雖不占主體,也達到900hm2,占總面積的0.09%。

表3 精河域荒漠化土地類型轉化分級

表4 精河流域1990-2011年土地荒漠化類型轉化面積
4 結果討論
客觀分析導致荒漠化區域分布格局的內外在物理和社會人文因素,對于研究區域荒漠化的未來發展趨勢至關重要。綜合分析精河流域綠洲荒漠化演變原因,主要表現在氣候環境變化和人類開發利用兩個方面。
4.1 自然因素
氣候變化是影響荒漠化發展和逆轉的主要因素之一[11]。氣候統計數據表明,研究區自1972年以來,降水量雖然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在經歷了2002年的高點之后,開始逐年減少,加之年蒸發量、年均溫波動上升的疊加效應,使得區域氣候逐漸干燥,加劇土壤水分蒸發,帶動土壤鹽分向上移動,給地表植被生長帶來極大影響,不利于自然修復,導致出現或加重了土壤鹽漬化。風速是風蝕荒漠化程度的主要決定因素。1972年以來,研究區大于3m/s的日數逐漸減少,有助于風蝕荒漠化土地面積的減少和風蝕程度的降低。但自1990年開始,變化幅度開始減小,大于3m/s的日數呈現階段性上升趨勢,仍存在潛在風蝕荒漠化風險。因此,總體來看,研究區1990年以來增加的荒漠化面積,屬于在自然因素綜合作用下的復合荒漠化的結果,并且具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在風險。
4.2 人文因素
精河縣人口數量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呈快速增長趨勢,從5.5萬人增長至14.4萬人,增長近3倍,研究區耕地面積近40a增長了近3倍共2.93×104hm2,占到近21a來研究區減少的荒漠化總面積的83%,表明宏觀數據顯示的荒漠化面積減少并不代表內部荒漠化趨勢的真正好轉。從2011年耕地面積的轉入量來看,耕地主要由低、中植被覆蓋區轉換而來,說明由于該區人口增長帶來的耕地面積擴大,主要是借助毀林開荒方式。與此同時,精河縣牲畜數量近40a來也呈現較明顯增長,由1970年16萬頭增長至2011年的近40萬頭,由于有限草場的過度放牧帶來的草地退化,加之人口增長導致的土地需求,可最終部分解釋研究區內部實際的土地荒漠化情形,即仍然以惡化為第1位,達1.58×105hm2。
實際上,管理與政策也是引起生態環境變化的原因之一。當地政府也采取了多種措施,積極應對荒漠化現狀,如在林業建設工作中,對于生態脆弱的地方,專門設立保護區(甘家湖梭梭林保護區、艾比湖保護區)、禁牧區、禁伐區,2000年以來共封育林地3 250 hm2,造林(喬灌)3 709hm2,退耕還林8 633hm2,“三北”防護林建設1 727hm2,這對于研究區1.21×105hm2荒漠化面積的逆轉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5 結論
(1)在遙感數據支撐下利用地表在Albedo—NDVI空間的形態特征,提取荒漠化差值指數(DDI),并以此為依據獲取干旱區荒漠化的時空動態變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用于土地覆蓋分類變化以及荒漠化監測分析研究。
(2)1990—2011年,精河流域土地荒漠化類型轉化以惡化為主。2011年研究區居第一位的是重度荒漠化,面積達3.66×105hm2,其次為中度荒漠化,面積達3.24×105hm2,表明精河流域的荒漠化治理工作任重而道遠。
(3)近40a來,年蒸發量和年均溫的波動上升,是導致研究區荒漠化面積增加的主要顯在自然因素,而大于3m/s有風日數的階段性上升,則存在潛在風蝕荒漠化風險。
(4)盡管氣候變化因素導致呈現出荒漠化發展的態勢,但其所產生的負作用,近些年來正被政府的各類生態保護政策機制及荒漠化防治等有利于荒漠化逆轉的人為因素所部分抵消。而人口壓力、不合理放牧、土地利用開發管理不到位和水資源低效利用等社會人文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仍在阻礙著精河流域的荒漠化防治進程,將成為未來荒漠化防治過程中需要克服的重點。
[1] 張洪玲.用MODIS數據監測遼西北地區的荒漠化狀況[D].遼寧 沈陽:沈陽農業大學,2006.
[2] Li Fang,He Yanfen,Liu Zhiming,et al.Dynamics of sandy desertificat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J].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2004,14(1):57-62.
[3] 毛曉利,趙鵬祥,王得祥,等.非監督數字化分類與GIS在土地沙漠化動態監測中的應用[J].西北林學院學報,2005,20(3):6-9.
[4] Li Sen,Zheng Yinhua,Luo Ping,et al.Desertification in Western Hainan Island,China(1959to 2003)[J].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2007,18(2):473-485.
[5] 王建,董光榮,李文君,等.利用遙感信息決策樹方法分層提取荒漠化土地類型的研究探討[J].中國沙漠,2000,20(3):243-247.
[6] 杜明義.決策樹方法在土地荒漠化分類中的應用研究[J].測繪科學,2006,31(2):81-82.
[7] 喬平林,張繼賢,林宗堅.基于神經網絡的土地荒漠化信息提取方法研究[J].測繪學報,2004,33(1):58-62.
[8] 王大鵬,王周龍,李德一,等.荒漠化程度遙感定量化評價中的尺度問題[J].自然災害學報,2007,16(6):140-144.
[9] 曾永年,向南平,馮兆東,等.Albedo—NDVI特征空間及沙漠化遙感監測指數研究[J].地理科學,2006,26(1):75-81.
[10] Liang Shunlin.Narrowband to broadband conversions of land surface Albedo I algorithm[J].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2001,76(2):213-238.
[11] 王占軍,邱新華,唐志海,等.寧夏1999—2009年土地荒漠化演變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沙漠,2013,33(2):325-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