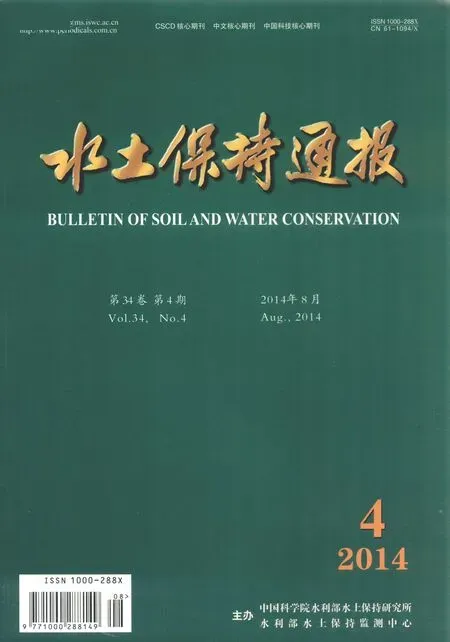安徽省城鎮化演進邊際生態環境效應的測度與分析
張樂勤,張 勇
1996年以來,中國城鎮化已進入加速發展階段[1],城鎮化演進所導致的資源過度開發與污染加劇等環境外部經濟性問題尤為突出,學者們對此展開過深入研究[2-7]。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將繼續推進城鎮化進程,并將城鎮化建設作為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同時提出,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方面,如何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兩者協調發展,管理層對此高度關注,也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針對城鎮化與生態環境關系,國內外學者展開過深入探索。美國環境經濟學家Grossman和Krueger[8]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基于42個發達國家的板面數據,揭示了隨著城市經濟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呈倒U形的演變規律,提出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設;王如松[9]利用生態協調原理的正負反饋和限制因子定律,揭示了城鎮化演進與生態環境間存在著反饋和限制性機理,并由此總結出了城市生長契合S形規律;黃金川等[10]研究表明,區域生態環境隨城市化的發展存在先指數衰退、后指數改善的耦合規律,交互耦合過程分別呈現低水平協調、拮抗、磨合和高水平協調規律;劉耀彬等[11-12]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及耦合協調度模型,對中國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進行了探索,揭示了城市化對生態環境的脅迫作用及生態環境對城市化的約束作用;喬標等[13]對河西走廊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的規律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兩者契合雙指數曲線演變規律;李玉恒等[14]對中國城鄉發展轉型中資源環境問題進行過解析,提出了城鄉轉型期的可持續發展機制,認為通過市場及政策力量引導生產要素向小城鎮聚集,是破解城鎮化演進中環境問題的關鍵;蔣洪強等[15]對中國1996—2009年城鎮化發展的邊際環境污染效應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城鎮化每增長1%,所帶來的污染效應呈上升趨勢。以往的研究多基于城鎮化演進對生態環境脅迫視角,對城鎮化與生態環境間動態交互耦合關系進行考察,然而,生態環境是一個包含生態環境水平、生態環境壓力、生態環境保護的復合系統,僅以生態環境壓力單方面表征城鎮化演進對生態環境影響較片面,有悖于生態環境的科學內涵,鑒于此,本研究以安徽省為例,基于多維視角對城鎮化及生態環境質量進行綜合評價,借鑒STIRPAT模型,采用回歸分析方法,實證探索城鎮化對生態環境邊際影響,研究結果可為城鎮化可持續發展規劃及生態環境與城鎮化協調發展綜合決策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思路
首先構建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依據主成分分析所得方差貢獻率作權重的綜合評價方法,計算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然后對城鎮化與生態環境間關聯關系進行分析,借鑒STIRPAT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歸方法,定量測度出城鎮化演進對生態環境的邊際貢獻;最后運用發展階段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科學發展觀理論對實證結果進行解析。
1.2 研究方法
1.2.1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依據城鎮化與生態環境概念內涵,遵循科學性、層次性、完整性、可操作性原則,將城鎮化劃分為人口城市化、空間城市化、經濟城市化、社會城市化4個要素層,將生態環境質量劃分為生態環境水平、生態環境壓力、生態環境保護3個要素層;基于CNKI數據庫,運用頻度統計法,遴選出近年來研究者使用頻度較高的指標,其中城鎮化評價指標設計借鑒文獻[16-18],生態環境質量 評 價 指 標 設 計 借 鑒 文 獻[7,19-20];最 后,征詢有關專家意見,對初步設計的評價指標進行調整(表1)。
1.2.2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方法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綜合評價法、層次分析法(AHP)、德爾菲法(Delphi)、熵值法、均方差法等,主成分分析綜合評價法通過將原指標變量進行變換后形成彼此相互獨立的主成分,可有效消除評價指標間關聯影響[21],在資源環境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1,22-24],本研究采用此方法。
(1)原始數據歸一化處理。運用極差標準化法對原始指標值進行無量綱化處理,若為正向指標(原始指標越大越優),采用公式:

若為負向指標(原始指標越大越劣),采用公式:

式中:Xi——原始數據xi極差標準化后值;xmax,xmin——原始數據系列中最大值與最小值。
(2)指標分值計算。將Xi輸入SPSS 17.0軟件中,選擇降維因子分析方法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對原始變量累計方差貢獻率超過85%的j個主成分,依據主成分關系式,可計算各指標分值得分,計算公式為:

式中:Yji——指標分值得分;kji——第j個關系式i指標回歸系數。
(3)綜合得分計算。以主成分分析所得方差貢獻率作權重,計算綜合得分:

式中:Y——綜合得分;Wji——j 主成分方差貢獻率。
(4)綜合指數計算。為了直觀考察城鎮土地集約利用或城鎮化水平,將綜合得分轉換為百分制形式,轉換公式為[23]:

式中:Y′——城鎮化水平或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Ymax——研究時序最高得分;Ymin——研究時序最低得分。依據Y′值,可對城鎮化水平或生態環境質量進行判別,當80<Y′≤100時,表示城鎮化水平高或生態環境質量為“優”;當60<Y′≤80時,表示城鎮化水平較高或生態環境質量為“良”;當40<Y′≤60時,表示城鎮化水平較低或生態環境質量較差;當0<Y′≤40時,表示城鎮化水平低或生態環境質量為“差”。

表1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
1.2.3 城鎮化對生態環境影響的測度方法
(1)STIRPAT 模型構建。York等[25-26]在經典IPAT等式[27]基礎上,提出了隨機回歸影響模型,即人口、富裕和技術的隨機影響模型,簡稱為STIRPAT模型,表達式為[28]:

式中:I,P,A,T——表示環境影響、人口規模、富裕度和技術;a——模型系數;b,c,d——人口、富裕度、技術等人文驅動力的指數;e——為模型誤差,STIRPAT模型是IPAT模型的衍生形式,當a=b=c=d=1,STRIPAT模型就還原成IPAT等式。STIRPAT模型是定量分析人文因素對環境壓力影響的一種有效方法,在資源環境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28-31],被認為是一個得到廣泛應用和非常成熟的模型[28]。
借鑒STIRPAT模型,可構建城鎮化對生態環境影響的計量模型,表達式為:

式中:E——表示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K——模型系數,胡求光等[32]研究認為,研究和開發(R&D)投入對技術效率的提高具有積極地效應,藉此,以研究和開發(R&D)投入占GDP比例表征;U——城鎮化評價綜合指數;ε——模型隨機項,表示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其它因素;a1,a2,a3,a4——彈性系數,表示當P,A,T,U 每變化1%時,分別引起E的a1%,a2%,a3%,a4%變化。
(2)城鎮化對生態環境邊際影響測度。借助SPSS 17.0軟件,采用偏最小二乘回歸方法進行測度。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自變量P,A,T,U進行分析與篩選,提取對自變量解釋性最強的綜合變量,構建綜合變量與自變量的線性關系式;其次,以E作因變量,綜合變量作自變量,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擬合,可得E與綜合變量的線性關系式;再次,將綜合變量與P,A,T,U 的線性關系式代入E與綜合變量的線性關系式,可得E與P,A,T,U 關系式,關系式系數a1,a2,a3,a4即為彈性系數,其中,a4表征城鎮化對生態環境邊際影響。
2 案例分析
2.1 研究區概況
以安徽省為案例展開研究。安徽省為中部內陸省份,地理位置處于114°54′—119°37′E 與29°41′—34°38′N,面積1.39×105km2,2011年,該省總人口6 876萬,GDP總量15 300.65億元[33]。安徽省地勢西南高、東北低,自北向南分為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區3大自然區域;氣候條件差異明顯,淮河以北屬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以南為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降水年際變化大,常有旱澇等自然災害發生;擁有優越的土地資源、生物資源、水資源和礦產資源稟賦。
安徽省為生態建設省,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安徽省城鎮化進程日漸加快,1996—2011年,城鎮化率由21.71%提升至44.8%[33],平均每年提升了1.54%,高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1996年,中國城鎮化率為30.48%,2011年為51.27%[34],1996—2011年,平均每年提升了1.39%),選擇安徽省作為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數據來源與說明
安徽省城鎮化、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原始數據及安徽省總人口,人均GDP,R&D投入經費占GDP比例數據均來源于《安徽統計年鑒(1997—2012年)》[33],其中,涉及因物價指數變動指標,如人均GDP,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二三產業產值,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等,采用不變價格進行調整,方法為:實際投資額=當年投資額×100÷CPI價格指數(以1990年為100計);2001—2011年郵電業務總量數據為郵政業務量與電信業務量相加所得。由于篇幅所限,城鎮化評價原始數據及人口,人均GDP,R&D投入和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原始數據略。
2.3 結果與分析
2.3.1 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 運用公式(1)—(2)安徽省1996—2011年城鎮化評價原始數據進行極差標準化處理,然后將其輸入SPSS 17.0軟件中,進行主成分分析,所得解釋總方差詳見表2,各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詳見表3。

表2 安徽省1996-2011年城鎮化評價主成分分析解釋總方差

表3 安徽省1996-2011年城鎮化評價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
由表2可知,特征值大于1有2個,表明可提取2個主成分,2個主成分可解釋原變量的94.612%,且所得相關矩陣的sig值小于0.05(限于篇幅,對主成分分析所得的相關矩陣予以省略),說明擬合非常好,依據公式(3)及表3的兩個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可計算2個主成分得分,再依據公式(4)及2個主成分分析所得方差貢獻率,可計算城鎮化綜合得分(表4)。依據公式(5)將表4中綜合得分轉化為百分制指數,所得結果如圖1所示。圖1表明,安徽省城鎮化率由1996年的21.71%提升至2011年的44.8%,年平均增長4.95%,而城鎮化評價綜合指數由1996年的43.83升至2011年的83.83,年平均增長4.42%,人口城鎮化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城鎮化綜合評價增長速度,由此表明,安徽省城鎮化綜合水平落后于人口城鎮化,加強社會城鎮化建設,提升城鎮居民生活質量,促進城鎮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亟待加強。進一步分析圖1可知,1996—2011年,安徽省城鎮化評價綜合指數呈波動遞增態勢,1996—2005年,指數年均值為53.42,年均增速為2.93%,城鎮化綜合水平較低,2006—2011年,指數年均值為74.36,年均增速為6.24%,城鎮化綜合水平較高,提升速度較快,究其原因,與國家實施的中部崛起戰略及安徽省發展思路有關,2006年以來,安徽省以中部崛起戰略為契機,實施了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省會經濟圈和皖北城市群“一帶一圈一群”等發展戰略,積極推進工業園區、舊城區改造、房地產及道路建設,使城鎮化演進速度及綜合水平提升明顯。

表4 安徽省1996-2011年城鎮化評價主成分分析綜合得分

圖1 安徽省1996-2011年城鎮化率及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
2.3.2 生態環境質量綜合評價 以生態環境評價原始數據為基礎,依據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方法,可對生態環境水平進行綜合評價,所得結果如圖2所示。由圖2可知,1996—2011年,安徽省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整體呈上升態勢,1996—2002年,均值為47.57,表明生態環境質量較差,2003—2011年,年指數均值為69.66,表明生態環境質量良好,分析其原因,與安徽省大力發展生態經濟,強化政策支持、科技支撐和執法監管,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有關。
2.3.3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質量關聯性分析 對安徽省1996—2011年城鎮化評價綜合指數與生態環境評價綜合指數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擬合模型符合線性關系,R2為0.9127,說明研究時段內,安徽省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質量間呈正向關聯關系。
2.3.4 城鎮化演進的生態環境邊際影響測度 依據城鎮化對生態環境影響的測度方法,以安徽省總人口數(以P表示),人均GDP(以A表示),R&D投入占GDP比例(以T表示),城鎮化評價綜合指數(以U表示)作自變量,生態環境評價綜合指數(以E表示)作因變量,運用STIRPAT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歸方法進行測度。首先,對P,A,T,U,E時序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所得結果以lnP,lnA,lnT,lnU,lnE表示;其次,將lnP,lnA,lnT,lnU 數據輸入 SPSS 17.0中進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結果可知,安徽省1996—2011年生態環境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為:

由公式(8)可知,研究時段內,安徽省人口,人均GDP,R&D投入占GDP比例,城鎮化演進對生態環境的邊際彈性系數分別為0.063 9,0.098 2,0.046 7和0.010 2,表示當人口、人均GDP、R&D投入占GDP比例、城鎮化綜合水平每增加1%時,將分別引起生態環境質量上升0.063 9%,0.098 2%,0.046 7%和0.010 2%,由此表明,1996—2011年,安徽省城鎮化演進具有弱正向生態環境效應。

圖2 安徽省1996-2011年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
2.3.5 城鎮化演進的生態環境效應理論解析 基于STRIPAT模型定量測度表明,研究時段內,安徽省城鎮化演進對生態環境具有弱正向效應,可用發展階段理論對此進行解析。發展階段理論認為,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呈環境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規律[8],經濟發展初期,農業經濟居主導地位,工業基礎薄弱,鄉村人口占絕對優勢,城市化水平不高,城鄉用地矛盾不突出,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較小;經濟發展中期,工業經濟發展較快,且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城鎮化水平提升較快,工業生產污染和人口聚集所帶來的生活污染在該階段都迅速增加[10],工業化、城鎮化的生態環境脅迫效應明顯,生態環境質量呈下降態勢;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階段,第三產業發展迅速,第三產業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及城市發展所引致的物質和精神誘惑力吸引著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鎮化水平繼續提升,隨著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更注重經濟發展質量,以科技支撐的創新發展,使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及現代服務業比例大幅提升,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此背景下,生產污染開始下降,同時,隨著政府對環保投入的加大及環境管理規制政策日臻完善,生態環境質量呈逐步提升態勢。
3 結論
(1)研究時序內,安徽省城鎮化評價綜合指數呈遞增態勢,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綜合指數也呈上升態勢,兩者具有正向關聯關系。
(2)安徽省人口城鎮化增長速度高于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增長速度,提高城鎮化演進質量,加強包括社會城鎮化在內的城鎮化復合體系建設,使城鎮居民分享城鎮化所帶來的紅利與福祉,是未來城鎮化建設方向。
(3)城鎮化綜合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城鎮化綜合水平每增加1%,生態環境質量改善0.010 2%,城鎮化演進對生態環境具有弱正向效應。
(4)將城鎮化演進視為復合系統,從人口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四維視角對此進行考察。案例研究結果表明,城鎮化演進對生態環境具有弱正向效應,而非脅迫關系,契合黃金川等[10]、喬標等[13]探索出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間耦合規律,與陳健等[7]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本研究認為在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及公眾生態文明意識不斷提升的時代背景下,政府將轉變發展方式作為主線,依靠科技進步,強力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完善能源綠色戰略支持體系,不斷加大環保投入,生態環境質量得到了較大改善,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必然會走向適應與協調。本研究分別選取了14和18個指標對城鎮化綜合水平與生態環境質量進行考察,而影響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因素較復雜,受定量研究數據獲取的限制,僅以上述指標表征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未考慮規制政策因素、下墊面景觀結構特征的改變等),這是本研究今后展開深入研究的方向。
[1] 戴為民,侍儀,陳雪梅.安徽省空間城市化安全指標體系構建及測度[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2,31(6):55-59.
[2] 王學峰.發達國家城鎮化形式的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1,30(4):54-59.
[3] 宋建波,武春友.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評價研究:以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中國軟科學,2010(2):78-87.
[4] 葉玉婷.廣東省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和諧度研究[D].山西太原:山西師范大學,2012.
[5] 安瓦爾·買買提明,張小雷,塔世根·加帕爾.基于模糊數學的新疆南疆地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和諧度分析[J],經濟地理,2010,30(2):214-219.
[6] 周忠學,張芳,劉佳.陜北黃土高原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空間協調程度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0,29(2):134-138.
[7] 陳健,查良松,黃艷妮,等.安徽省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和諧度分析[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34(6):568-573.
[8] Grossman G M,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9] 王如松.高效·和諧:城市生態調控原則和方法[M].湖南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10] 黃金川,方創琳.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機制與規律性分析[J].地理研究,2003,22(2):211-220.
[11] 劉耀彬,李仁東,宋學鋒.中國區域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的關聯分析[J].地理學報,2005,60(2):237-247.
[12] 劉耀彬,李仁東,宋學鋒.中國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2005,20(1):105-111.
[13] 喬標,方創琳,黃金川.干旱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的規律性及其驗證[J].生態學報,2006,26(7):2183-2190.
[14] 李玉恒,劉彥隨.中國城鄉發展轉型中資源與環境問題解析[J].經濟地理,2013,33(1):61-65.
[15] 蔣洪強,張靜,王金南,等.中國快速城鎮化的邊際環境污染效應變化實證分析[J].生態環境學報,2012,21(2):293-297.
[16] 曹廣忠,邊雪,劉濤.基于人口、產業和用地結構的城鎮化水平評估與解釋:以長三角地區為例[J].地理研究,2011,30(12):2139-2149.
[17] 黃木易,程志光.區域城市化與社會經濟耦合協調發展度的時空特征分析:以安徽省為例[J].經濟地理,2012,32(2):77-81.
[18] 陳曉倩,張全景,代合治,等.城鎮化水平測定方法構建與案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1,30(4):76-80.
[19] 劉耀彬,宋學鋒.區域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性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6,35(2):182-187,196.
[20] 李湘梅,周敬宣,張嫻,等.城市生態系統協調發展仿真研究:以武漢市為例[J].環境科學學報,2008,28(2):2605-2613.
[21] 于勇,周大邁,王紅,等.土地資源評價方法及評價因素權重的確定探析[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06,14(2):213-215.
[22] 朱天明,楊桂山,蘇偉忠,等.長三角地區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評價[J].資源科學,2009,31(7):1109-1116.
[23] 黎一暢,周寅康,吳林,等.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空間差異研究:以江蘇省為例[J].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42(3):309-315.
[24] 王廣杰.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評價方法及其系統研究:以成都市為例[D].四川 成都:成都理工大學,2011.
[25] York R,Rosa E A,Dietz T.A rift in modernity?assessing the anthropogenic source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ith the STIRPAT mod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2003,23(10):31-51.
[26] York R,Rosa E A,Dietz T.STIRPAT,IPAT and ImPACT:Analytic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J].Ecological Economics,2003,46(3):351-365.
[27] Ehrlich P R,Holdrens J P.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J].Science,1971,3977(171):1212-1217.
[28] 張樂勤,李榮富,陳素平,等.安徽省1995—2009年能源消費碳排放驅動因子分析及趨勢預測:基于STIRPAT模型[J].資源科學,2012,34(2):316-327.
[29] 張樂勤,陳素平,王文琴,等.安徽省近15年建設用地變化對碳排放效應測度及趨勢預測:基于STIRPAT模型[J].環境科學學報,2013,33(3):950-958.
[30] 王琳,吳業,楊桂山,等.基于STIRPAT模型的耕地面積變化及其影響因素[J].農業工程學報,2008,24(12):196-200.
[31] 張樂勤,陳素平,王文琴,等.基于STIRPAT模型的安徽省池州市建設用地擴展驅動因子測度[J].地理科學進展,2012,31(9):1235-1242.
[32] 胡求光,李洪英.R&D對技術效率的影響機制及其區域差異研究:基于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區的SFA經驗分析[J].經濟地理,2011,31(1):26-31.
[33] 安徽省統計局.安徽統計年鑒(1997—2012)[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34]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系列(1997—2012)[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