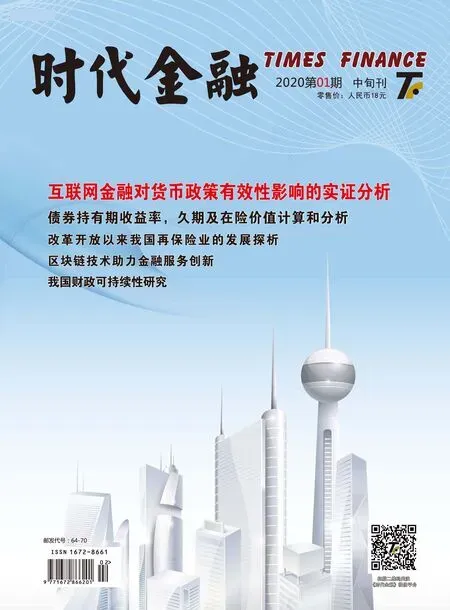危險犯的停止形態研究
溫雅璐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危險犯的停止形態研究
溫雅璐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刑法中的故意犯罪停止形態,是指在犯罪過程當中,行為由于某種原因停頓下來完成犯罪的一種狀態,主要表現為犯罪既遂、犯罪預備、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危險犯以危險狀態出現與否作為既遂狀態的標準,其也存在既遂、未遂兩種停止形態。同時,危險犯還可轉向實害犯,并成立實害犯的中止。
故意犯罪停止形態 危險犯 未遂 中止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態按其行為最后停頓時犯罪行為是否完成為標準,可分為兩種類型:(1)犯罪的完成形態,即犯罪的既遂形態,是指故意犯罪在其發展過程中進行到底、行為人的行為已經完全符合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某一具體犯罪構成的全部構成要件的情形;(2)犯罪的未完成形態,即故意犯罪在其發展過程之中由于主觀、客觀方面的原因停止下來,行為人沒有達到某一具體犯罪過程的全部構成要件的情形,主要為犯罪預備、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三種形態。這三種形態有其相同點。但在未完成原因(意志內外的原因)、停頓時間(預備階段、實行階段、實行后階段)及行為人主觀惡性等方面,又有著本質的區別。
危險犯,相對于實害犯而言,指以行為人實施的危害行為足以造成某種法定的公共危險。我國刑法通常將一些危害公共安全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危險狀態直接規定在分則之中,并設置相應的法定刑,與實害犯相區分。但由于危險犯是以危險狀態的出現為基礎的特殊犯罪類型,其停止停止形態的認定一直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危險犯有無未遂之分,如果有又該以何標準來區分;危險狀態出現后是否存在犯罪中止,若肯定則應屬于那種犯罪中止等等。筆者將結合理論界的主要幾種學說進行探究,以求得到較為清晰的解釋。
一、危險犯的未遂狀態之辨
關于危險犯是否存在未遂狀態,我國刑法學界主要存在否定說、肯定說和折中說幾種學說:
一是危險犯既遂說。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危險犯不可能存在未遂狀態是因為危險犯以危險狀態的出現為認定標準,也以此為犯罪構成要件。以此為基礎,危險犯的成立和既遂實質成了同一個概念。[1]還有持法定既遂說的學者認為,危險犯實質就是實害犯的未遂犯,只因危險狀態的出現危害到了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具有一定的危險性,而被法律擬制成為一類犯罪。既然是法定的獨立既遂犯,自然沒有未遂的余地。[2]
二是危險犯未遂說。此學說認為“刑法分則規定的危險犯,實際上是犯罪未遂”,無既遂可言。因為未遂的“未得逞”,就是指未達到行為人預期的犯罪目的。而在危險犯中,行為人的目的絕不僅僅是造成某種危險,而是為了追求某種危害結果。僅僅出現危險時,實質上是未得逞,即未遂。[3]
三是折中說。該學說認為危險犯既有未遂形態,也有既遂形態,危險犯的成立與既遂應該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擁有兩個不同的標準。從成立到既遂的時間段內,當然存在未遂的情況。因此,危險犯有既遂與未遂之分。[4]還有學者認為只有部分危險犯存在未遂形態,但對危險犯的范圍有分歧。第一種觀點認為,具體危險犯才存在犯罪未遂,而抽象危險犯沒有未遂形態。具體危險犯以發生一定的危險為要件,當行為人已著手卻因意志外原因未發生法定的危險狀態時,成立具體危險犯犯罪未遂。而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現實的危險狀態為必要,通常不認為有未遂狀態。[5]還有一種觀點正好相反。具體危險犯很難存在可罰性的未遂,而抽象危險犯在原則上就改承認未遂形態的可能。假如構成要件行為并不至于形成具體危險,則不但不會形成犯罪,甚至不會形成未遂犯。[6]
上述觀點中,前兩種觀點實質都否定了危險犯未遂狀態的存在,筆者認為都不可取。既遂說第一種說法把危險狀態或侵害法益的危險的出現作為危險犯成立的構成要件,又視為犯罪既遂的標準,混淆了成立與既遂的標準。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成立犯罪是指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此為刑法總則規定的修正的犯罪構成要件;而成立犯罪既遂則是符合刑法分則中具體每個罪名的一般構成要件。危險狀態的出現符合刑法分則對危險犯一般構成要件的要求,是危險犯既遂的標準。因此,法定危險狀態即使尚未出現,仍然可以成立危險犯,只不過會成立危險犯的停止形態。
既遂說的第二種觀點“法定既遂說”和“危險犯未遂說”立論基礎基本相同,即認為危險犯是實害犯的未遂犯,因此也存在相應的缺陷。“法定既遂說”看到了危險犯的獨立性這一點值得肯定,而未遂說不僅將未遂犯當作實害犯的一部分,還以犯罪目的作為犯罪既遂的標準并得出危險犯只能是未遂犯的結論,與學界公認的以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為既遂的標準理論相違背。
應當肯定,折中說具有一定合理性,也即是說危險犯不僅有犯罪完成形態,也有犯罪未完成形態。但認為具體危險犯或抽象危險犯只有一種存在未遂狀態的說法是片面的。無論是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都有相同的理論結構和基礎,都立足于對法益的侵害方式區別與實害犯的角度而言的,危險犯對于法益的侵害只是一種現實損害的可能性。在法益侵害可能性的角度上來看,二者并無構成基礎上之區別。危險的發生都依賴客觀的判斷,只不過對危險犯的危險狀態的判斷不僅滿足于構成要件行為的完成,還有待于危險狀態的時間點判斷,而抽象危險犯的危險判斷已有了立法者進行擬制,擬制的依據就是類型化的行為方式。[7]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危險犯作為與實害犯相對應的獨立犯罪,存在完成的既遂狀態,也存在未完成的既遂狀態,而非實害犯的未遂。
但犯罪過程中的危險狀態和實害狀態是一種發展并漸進的現象,危險狀態出現后還可能存在繼續發展成為實害犯的可能。所以,在這一過程中,行為人也有可能因為某種原因而產生停頓,這便有了危險狀態下停止形態的認定問題。
二、危險犯停止狀態的認定
在危險狀態出現前,由于行為人意志內、外的原因而停頓的,可能存在犯罪預備、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危險犯的既遂,則應以“公共危險”的危險狀態出現,并在犯罪過程中已經停頓作為標準。在危險狀態出現后,由于各種行為人意志外客觀原因產生停頓的,成立危險犯既遂;若是出現了實害結果,則轉化為實害犯既遂。但刑法理論界對于犯罪人在危險狀態出現后自動放棄犯罪或有效的阻止法定犯罪結果的出現該如何認定的存在較大分歧。此種情況應定犯罪既遂還是犯罪中止;若是以犯罪中止論,那是什么罪的犯罪中止這兩大問題眾說紛紜。
(一)犯罪中止與否的認定
1.否定說,即“犯罪既遂說”。法定的危險狀態出現以后,即出現既遂狀態,既遂后不存在犯罪中止。首先,這種既遂后的中止違背停止形態獨立原則。其次,危險狀態的出現即表示此類危險犯罪的完成形態,犯罪過程已結束,不符合中止的時間性條件。再次,危險犯的完成無實際的危害結果,“防止犯罪結果的出現”針對的是結果犯而言,也不符合中止的有效性條件。這些都會使犯罪中止的統一概念和原理遭到破壞。況且,對于自動防衛危害結果的危險犯,雖不作中止認定,但可將此行為做量刑從寬情節考慮,從而不影響罪行相適應原則的貫徹,[8]并有利于犯罪分子悔罪。
2.肯定說,即“犯罪中止”說。有觀點認為,危險狀態的發生并非就是犯罪既遂,只有犯罪結果的發生才是犯罪既遂(認為“犯罪結果”是危險犯既遂的標準),在此之前行為人放棄犯罪或有效組織法定犯罪結果的發生屬于犯罪中止。以“危險狀態出現”作為危險犯既遂標準的學者認為,犯罪中止只能出現在犯罪結果出現前而非既遂前,危險狀態出現后仍然可以成立犯罪中止。還有觀點認為,應借鑒“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的犯罪中止論的法理,將此種情況定位危險犯的犯罪未遂。雖在既遂后定為中止與犯罪停止形態的排他性原則相違背,但這有利于犯罪分子及時悔悟,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所以,應當作為一種特殊情況來對待。
應當肯定“否定說”中關于犯罪既遂后即不存在中止的觀點,這符合我國刑法理論中停止形態排他性的原理。但是犯罪停止形態是以最后的停頓點為標志作為標準的。危害狀態的出現從廣義來看實質是在出現危害結果前的一個階段過程,如前文所說,危險狀態出現后犯罪狀態還可能朝著犯罪危害結果發展,即存在著危險狀態向實害狀態發展的可能。所以,在危害結果出現后的停頓,不應視為一種既遂的標志,而應作為一種排除未遂的情形對待,具體定何種行為,還應視行為人的主觀意愿而定。此時行為人若出于主觀意愿而停頓,應視為從行為人開始預備行為至犯罪結果出現整個大犯罪過程中的中止停頓,即危險狀態出現后依然存在中止的可能。
“犯罪中止說”也承認中止的存在,但筆者認為持“犯罪結果”為危險犯既遂標準的學者論證觀點基礎本身就值得商榷,這一理由應當不被認可。而危險狀態出現后的自動防衛結果發生情況與“放棄重復侵害”不同,“放棄重復侵害”必須是第一個行為沒有引起結果發生從而存在實施第二個重復侵害行為的可能情況下行為人放棄侵害,前后行為具有統一性。而危險狀態出現后,危險犯行為已經完成,不需在實施同一行為危害結果也可能會發生,這一理由同樣不夠充分。
相較而言,筆者較偏向于“犯罪中止說”,危險狀態出現后依然存在中止的可能性。但論證理由則與其有不一樣的觀點。筆者認為,危險狀態后出現犯罪中止完全不違背犯罪既遂后不存在中止的原理。按照劉憲權老師的觀點,這是危險狀態出現后排除未遂情況下的一種停止形態,與“犯罪既遂后不存在犯罪中止形態”并未是同一層面的問題。當危險狀態出現后,行為人的行為實質上還處在不確定的狀態,即處在可能向實害犯轉化的狀態。若因客觀原因停頓,如前文論述,應構成危險犯的既遂;若保持這種狀態向實害狀態發展下去,則構成實害犯既遂。若在轉化過程中行為人自動停止犯罪或有效的阻止法定犯罪結果的發生,符合犯罪中止時間性、自動性、有效性三個特征,完全合乎法理,應以實害犯的犯罪中止定。
同時,定犯罪中止也十分必要。從形勢政策角度看,定犯罪中止有助于鼓勵行為人主動阻止結果出現的行為,這一法律的指示作用會對行為人產生積極的影響,充分發揮刑法設置犯罪中止這一“回歸的黃金大橋”的積極作用;定犯罪既遂則有失罪刑相適應的平衡,犯罪人中止即表明其主觀惡性的減小,定犯罪中止,更有利于保證法律的公正性,并從法律上保障了行為人從輕、減輕、免除處罰的量刑情節。
(二)實害犯的犯罪中止
危險狀態后的不僅存在中止形態,而且應該定實害犯的犯罪中止。關于這一界定,有學者認為應該定危險犯的犯罪中止,主要理由是:危險狀態出現后并不等于犯罪既遂,在既遂前出現犯罪中止是完全有可能的,自然也就認為是危險犯的犯罪中止。[9]關于這一觀點,前文已對其進行了辨正。從時間上來看,危險狀態出現后,雖然有繼續向實害狀態轉化的可能,但相對于危險犯來說,其法定的犯罪過程已經完結,不可能存在危險犯的中止形態。而相對于實害犯來說,其犯罪過程因還存在繼續向前發展的可能,在犯罪結果出現前整個犯罪過程并不會結束,自然也就存在包括中止在內的停止形態。所以,應成立與危險犯相對應的實害犯的犯罪中止。
從中止第二特征—有效性要求出發,也只能定實害犯的犯罪中止。若是定危險犯犯罪中止,則不符合有關“有效阻止法定犯罪結果發生”這一最重要的條件。盡管在危險犯和實害犯共存的犯罪中,危險狀態可能向犯罪結果發生轉化,但刑法以明文規定將危險狀態作為危險犯的犯罪法定后果,一旦危險狀態發生,很難想像危險犯行為人如何阻止危險狀態——這一法定的犯罪后果的發生,這一說法本身存在矛盾。而定實害犯的犯罪中止則可有效解決上述矛盾。在危險狀態出現后向實害狀態轉化的這一過程,表明危險犯犯罪過程已結束,實害犯犯罪過程仍在進行,即實害犯法定的危害結果有出現的可能性但現實中卻還未出現,此時行為人自動放棄犯罪或有效的阻止實害犯罪結果的出現,并不會影響危險犯的犯罪形態,但卻可以成立實害犯的犯罪中止。同時,從量刑上看,將實際出現的危害狀態視為實害犯中止所造成的損害,考慮了“危害狀態結果”存在的因素,又考慮了行為人自動停止或有效阻止“實害結果”的因素,并對其適用“應當減輕”的法定情節也更合理。
[1]楊興培.危險犯質疑[J].中國法學,2000(3).
[2]陳興良.陳興良刑法學教科書之規范刑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26.
[3]侯國云.刑法學[J].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184.
[4]張明楷.危險犯初探[J].馬俊駒主編:清華法律評論(第一輯),1998.
[5]趙秉志.犯罪總論問題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06,407.
[6]林山田.評刑法修正案草案[J].刑事法從論(2).
[7]高巍.論危險犯的未遂[J].法學評論,2010(1):116.
[8]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原理(第二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359,361.
[9]吳炳新.危險犯的停止形態研究[J].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3(2):46.
溫雅璐(1985-),女,江西吉安人,華東政法大學2012級刑法學方向法學研究生,研究方向:青少年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