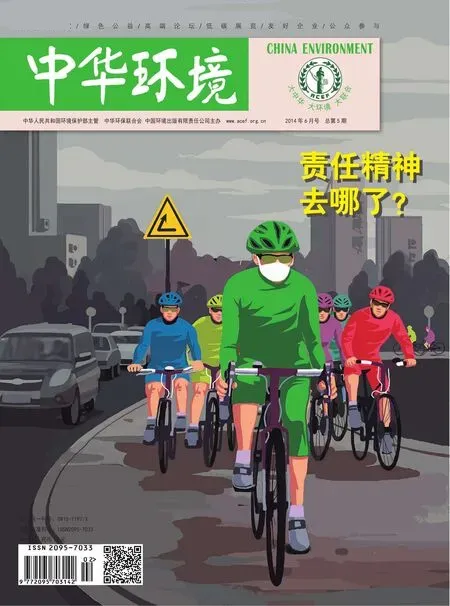“算黃算割鳥”與“麥客”
趙亮 天津綠領理事長
“算黃算割鳥”與“麥客”
趙亮 天津綠領理事長
在北京某個小區,一聲鳥鳴引起我的注意。打開窗戶,聽得真亮些許,確認是“算黃算割”鳥的聲音。
關于此鳥,在關中農村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年麥收,一個老漢看著鄰居急急下地割麥卻不著急,別人都勸他趕緊割麥,他回答等地里的麥子全都黃透了再割。過了幾天鄰居們的麥子都垛在了場里,他家的麥子也都黃透了。可準備開鐮時一場暴雨來襲,他氣得吐血,化做了一只鳥,每年麥子揚花的時候開始啼叫“算黃算割”、“算黃算割”,意思是麥子黃一塊就趕緊收割一塊,提醒人們不要錯過時機,不要僥幸于萬事俱備。關中人就把這種鳥叫“算黃算割”。
大人們說,聽到此聲,意味著即將迎來小麥收割的季節。在麥浪翻滾的田間地頭,經常能聽到“算黃算割”的鳥叫,清脆入耳,讓人心生喜悅。事實上,“算黃算割鳥”只是關中人對“四聲杜鵑”的昵稱罷了。
也許是得益于此鳥的傳信,大抵這個時候,家人們也開始打磨鐮刀,準備開工。待到小麥收割的時候,幾乎是全家上陣。收割,打場,晾曬……男女老少都會為此忙活一段時間。
與“算黃算割鳥”給人們播報麥情同時,一個群體也開始了遷徙。
麥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流行于陜甘寧地區。當代·殷謙雜文集《心靈真經》里有關于麥客的描述:“老人們說,大約是關中的人也走了西口,莊稼地里缺勞動力,麥子熟了要及時收割,那時候就有人成群結隊的趕去收麥子,是為了賺些貼補家用的錢,久而久之就有了專門以此為職業的,這就叫做麥客。”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為職業麥客。為了維持生計,父親也曾經去別的縣城做過麥客。
“得有好把式才能成。”父親給我講過他做麥客的經歷:“臨近的縣城如鳳翔、岐山等地,小麥成熟較早,村里的男人們一起坐車去那邊給別人家收割小麥。一般幾個人會在村口或人流量大點的地方呆著。然后會有人來打問價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被領走。”
大部分麥客白天工作,晚上隨意找個空地躺著,露宿街頭是常事。“有時半夜被蚊子咬醒,可一到田地里,就又忘得一干二凈,干勁兒十足。”父親說,他會像給自己家里收割一樣,整整齊齊地捆放好,低茬。
為了多收割幾畝地,很多人都是一天到頭在地里,即便是太陽火辣的時候。而這種看似微薄的收入,卻常常令家人們感到幸福。
那時我們還小,父親基本上是外出一周多時間。回家后,父親就跟變了一個人似的,皮膚黝黑,感覺蒼老不少。但是他總會眼睛瞇成條線喊道:“孩子們,快來看看有什么好吃的!”說著把一大袋子東西倒在地上。
黃瓜、辣椒、洋蔥、還有香瓜。然后滿院子鬧哄哄地,就像過節一樣。
隨著我們仨上學,父親就很少再去做麥客了。
后來,有河南等地的麥客來家鄉。他們一個人一天要收好幾畝小麥。這樣一個群體,常常是每人一個蛇皮袋子,一把鐮刀,些許干糧,一個茶杯,一頂草帽,行走江湖。
有一天,一位麥客路過鄰家菜園子,遲疑了一會,“能把你家的大蔥拔一株給我么?”鄰家嬸嬸隨手拔了一株。只見那人連聲道謝,簡單抖了下泥土,就就著干糧吃起來。
再后來,聯合收割機浩浩蕩蕩路過小鎮的街道。
“麥客來了!”這個熟悉的聲音漸漸遠去。
也許,這個群體會逐漸退出我們的視線,作為一種農耕文明下的文化片段,卻會留在我們的記憶里。
多少年后回望, 無論是“算黃算割鳥”,還是“麥客”,都會在內心深處被發現,在寂靜的夏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