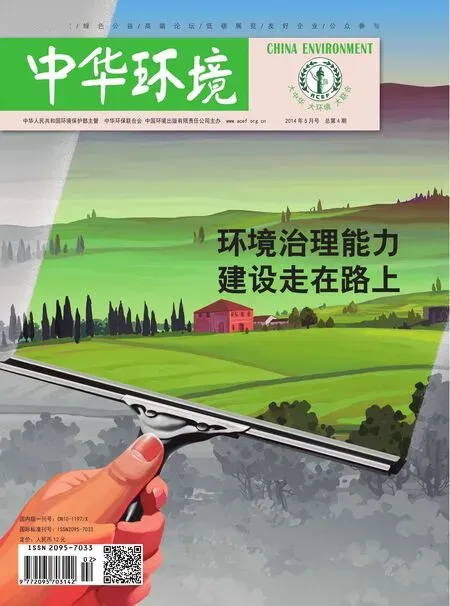怎樣考量環境治理能力
周宏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怎樣考量環境治理能力
周宏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從國家管理層面提升環境治理能力,已成為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一道考題,如何才能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
首先,環境治理能力的提高,至少應當有以下四方面的考量。
一是環境的公平性。或者說,居民享有公平的環境權益是治理能力提高的標志。已往“老板發財、政府埋單、群眾受害”的環境污染暴露的是環境權益不平等,是群眾沒有享受到公平的環境權益,提高環境治理能力就必須改變這一狀況。
二是環境的價值實現。以前“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透露的是對環境違法行為處罰太輕,因而常常出現污染治理要花費100萬但只罰款5~10萬的情況,造成變相“激勵”企業不處理污染物就直接排放的惡果,從而導致環境質量的“局部改善、整體下降”,甚至出現企業“光排污、不治理、過幾年搬走”的情形。
三是環境的目標導向。昔日“說起來重要、干起來不要”顯現的是將“發展是硬道理”扭曲為“GDP是硬道理”的偏執認識。改變這一認識,必須明確環境保護的目標是滿足居民的環境訴求、減輕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的不利影響。
四是污染治理的社會成本最小化。環保工作“干得好不如說得好,說得好不如忽悠得好”,是某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門的“懶政”和行政手段的“慣性”。某些重大環保專項實施后,只多了幾本拼湊的著作、SCI或EI等檢索的“會議”專輯文章,雖然個人有了提升的“資本”,卻沒有收到環境改善的應有效果。改變這一狀況,應當培育和發展第三方市場,以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途徑治理污染。
其次,要發揮政府在決策、執行和監督等方面的作用。
一要提高政策工具的運用能力。政策的本質是利益調整,即通過政策把一部分人的利益調整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政策制定和運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體現“公平”,通過政策運用,使原來的環境不公平變為“公平”,而不是由于政策的運用擴大了環境的不公平。
例如,“霧霾”對每個人的影響是“公平”的,因為大家“共呼吸”,但每個人對“霧霾”天氣的“貢獻”是不等的,因而需要通過政策加以調節。從一些大城市交通擁堵的實際出發,開征汽車尾氣排污費或擁堵費可能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措施。環境稅也是有效的宏觀調整途徑之一,通過對排污企業征稅,避免將污染治理的成本轉嫁給社會。目前,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已經寫入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發揮政策運用能力還要對政策進行與時俱進的自我調整,我國原來的環境經濟政策中,有一條“誰污染誰治理”政策,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執行中走了樣。《決定》明確了堅持“誰污染環境、誰破壞生態誰付費”原則,這一調整不僅回歸了政策初衷,還可以更好地發揮市場作用,收到專業化治理和規模化效果。
二要迅速提高執行能力。我國發展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如發展方式粗放、產業結構不合理、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加重、生態系統退化等,與一些地方奉行GDP導向的發展觀和政績觀不無關系。因此要加快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等指標在政績考核指標中的權重,解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不作為、亂作為問題。
我國“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也是執行力出了問題。因此,應加大群眾的環境知情權、監督權和舉報權,采用公報形式及時公布環境信息。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者嚴格實行賠償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外,迫切需要加強環境部門的執法力量,提高執法水平。同時,還應加大司法部門對環境保護、生態文明建設的保障作用。
三要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利用市場機制解決環境污染,可以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以較少的資金投入達到改善環境質量的目的。推行環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發展環保產業和環保市場,對于扭轉“環境保護靠政府”的認識,將起到重要作用。其他的市場措施還包括,對環境定價,使資源價格能充分反映生態、資源和環境的真實成本,讓污染者、資源開發和使用者承擔環境和生態破壞的損失、資源耗竭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應通過法律強制、政策激勵和約束,使企業樹立污染治理的主體意識,增強生態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感。此外,應不斷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發揮公共財政資金的“種子”作用,引導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保領域。
另外,從行為主體角度看,環境治理能力的提高還體現在政府、社會、公民三股力量的合作和博弈上,這也是環境治理的主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