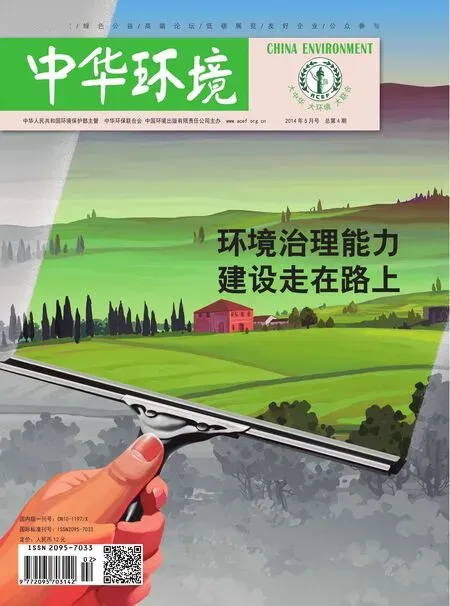政府有為、市場有效是環境治理體系并行不悖的基石
吳舜澤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
李新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博士
逯元堂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博士
政府有為、市場有效是環境治理體系并行不悖的基石
吳舜澤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
李新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博士
逯元堂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博士
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環保領域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構建“環境良治”、提升政策效能過程中,首要的也是處理好在環境保護這一特定領域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政府抓調控 市場管配置
目前關于這個問題已經出現了不同的認識和觀點。一些人提出市場在環境保護領域內發揮決定性作用,并以此作為國家環境治理體系的主基調,甚至把強化政府環境保護作用的一些做法視做違反三中全會精神。誠然,市場因素在過去相對薄弱,市場手段在過去應用較少,是需要大力加強的環節。但我們認為,從三中全會表述,以及市場作用提法的演變沿革來看,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主要適用于經濟領域及其相關領域,主要講的是資源配置問題,不能簡單化地將其平移、推廣到環境保護等政府事權范疇,更不能成為淡化或推卸政府責任的理論依據。
從環境領域看,不少環境產品具有公共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基本公共產品屬性。理論和實踐上,環境保護一直被視為公共產品或者半(準)公共產品的典型,市場機制對這類公共物品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低效率的,往往也是市場作用易失靈,這突出表現在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政府應在保護環境,尤其是提供環境基本公共服務中居于責任主體地位,率先履責,加強標準、法規、規劃、監管等宏觀調控,引導市場發展并對市場失靈進行干預和調節。基于此,三中全會特別強調國家調控,并將環境保護作為地方政府主要職責之一。
著力重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關系,由“雙失靈”轉變到“雙高效”上來,建立健全“國家調控—地方負責—政府有為—市場有效”的國家環境治理體系。
市場在環境保護領域應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環境領域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方式、方法和條件成熟程度與經濟領域有本質上的不同,其作用發揮的著力點、領域與政府作用有所差異但具有互補的效果。要避免一種誤區,不能將發揮政府作用等同于采用行政手段和干預措施,其實政府發揮作用也是可以采取市場化的方式來進行操作和履責。同時,市場作用的發揮也必須以政府有所作為、完善制度建設等為前提條件,兩者相輔相成。一些聯邦制國家在治污高峰時大多將環境保護作為中央投入的重點,以中央政府強力推動、宏觀調控帶動地方履責和社會監督到位,一般也不簡單地將政府和市場作用割裂開來、強行比較大小。
“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和市場在環境保護中的關系不明確,政府間環境保護事權劃分不清,環境管治“碎片化”特征突出,造成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缺位、越位、錯位、不到位現象嚴重。而環境的外部性特征、資源環境產權界定不清、環境污染責任難以明確,以及環境資源價格、環境損害成本價格改革不到位等問題,導致環境領域“市場失靈”現象突出。我國環境保護在不同程度上同時存在“政府缺位、市場失靈”的“雙弱”現象。當前既不能反對和畏懼市場,也不應該在政府履責這方面矯枉過正、予以削弱。
環境產品是公共產品,既要有政府“看得見的手”為主導加大供給、保障公平,又要有市場“看不見的手”長效驅動、提高效率。當前要避免將政府和市場完全對立、非此即彼、厚此薄彼,要特別防止改革過渡緩沖期的理論誤區、政策迷茫和雙重缺位。現階段政府和市場機制都需要大力強化、雙重加強,構建政府有為、市場有效、互為補充的環境保護政府與市場關系格局。
在環保投入、政策設計上下功夫
當前是我國環境治污的高峰期,需要持續加大政策設計、資金投入和治污力度。但從財稅體制改革方向上看,環境稅、專項轉移支付調整、事權財權劃分改革等帶來環保經費減少的態勢不容樂觀。如排污費改稅加大了環保投入減少、環境監管能力削弱的風險;專項轉移支付劃歸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及“營改增”將有可能助推地方環保投入“被統籌”;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改革,將對治污投入較多依賴上級資金來源的地方環保工作增加不少壓力。總體來看,目前政府與市場履責不足、經費保障缺失等問題將給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環境執法、監測預警等國家治理體系能力現代化帶來直接影響。
新舊制度的更迭期往往是系統最不穩定時期。環境治理體系的構建與能力的提升,不僅受到環境管理自身長期累積的機制體制束縛,也受到外在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個領域政策機制調整、改革態勢的影響。在改革路線圖、時間表的指引下,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正處于體制機制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期。目前體制機制改革過渡時期環境與經濟形勢、財稅體制改革短期“陣痛”等問題加大了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推進難度。
當前,最簡單、最可行的方案就是“治標”先行,政府突出抓好治污減排、制度建設、執法監管,明確地方政府環境責任,并為中長期財稅、事權、財權、財力等方面的“治本”性改革留出空間和時間,為最終市場機制發揮長效和更大作用創造條件、做好準備。
總體而言,過渡緩沖期應把握改革契機和有利因素,有效化解經濟社會改革和轉型等對環境保護的影響,優先推進易于改革的重點領域,強化中央、地方政府保護生態環境的職責,加大環境投入力度與環保經費穩定供給渠道,大力推進環境領域市場長效機制建設,循序漸進地進行制度調整和政策退出設計。
實現政府、市場“雙高效”
在當前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構建的初期階段,政府和市場關系不能亂,不能兩頭落空。政府環境保護職責主要在完善環境法律法規、政策標準、規劃制定與實施等,提升環保宏觀調控能力;提供安全飲水保障、城鄉污水和垃圾等公益性強的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獨立統一的環境監管服務等環境基本公共服務,實現環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強化環境保護市場監管與調節,承擔環境保護重大技術的試點與示范,環保產業發展引導與市場監管責任等方面。
中央政府是頂層設計的統領者,應加強環境保護的國家統籌和國家意志,解決跨區域環境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異問題,通過規劃、計劃等做好薄弱領域與環節的引導;地方政府重點解決環境產品的公共屬性,承擔地方環境質量改善的主體責任,保障地區環境安全;在剝離環境產品的公共屬性部分后,市場應在資源環境定價、環保產業、投融資等經營性和競爭性生產領域方面,構建長效機制,提高市場的配置效能。
坐等市場發揮作用、自動解決環境問題是一種“懶政”思想,也是回避矛盾,這會貽誤向污染宣戰的戰機。當前,最簡單、最可行的方案就是“治標”先行,加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投入,上收部分環境事權,突出抓好治污減排、制度建設、執法監管,明確地方政府環境責任,并為中長期財稅、事權、財權、財力等方面的“治本”性改革留出空間和時間,為最終市場機制發揮長效和更大作用創造條件、做好準備。
當前至2020年,是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的關鍵時期,環境形勢也處于快速變化、深度調整期。建立科學合理、系統完整、行之高效的環境治理體系,既要保持與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目標、路線圖及進度協調一致,又要根據環境與經濟形勢變化、環境治理重點調整、不同領域改革的難易程度,謀劃制定體制機制深化創新、環境管理戰略轉型的重點,其核心之一是著力重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關系,由“雙失靈”轉變到“雙高效”上來,建立健全“國家調控—地方負責—政府有為—市場有效”的國家環境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