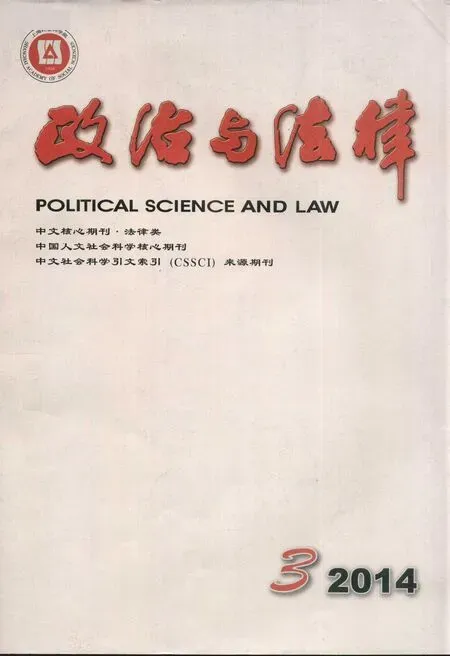后現(xiàn)代法律解釋主義批判
姜福東
(青島科技大學(xué)法學(xué)院,山東青島266061)
后現(xiàn)代法律解釋主義批判
姜福東
(青島科技大學(xué)法學(xué)院,山東青島266061)
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是一種自身帶有主觀主義、相對(duì)主義和虛無主義傾向的理論范式。在該范式下,解釋主體是視角主義的,解釋對(duì)象是情境主義的,解釋目的是游戲主義的,解釋方法是非理性主義的。該范式過分凸顯解釋的主觀性、恣意性、差異性、不確定性、游戲性以及方法的非理性,從而消解了解釋的客觀性、服從性、普遍性、確定性、規(guī)范性以及方法的理性等法治特質(zhì)。法律解釋的所謂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應(yīng)引起嚴(yán)肅的法治論者的高度警惕。
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法學(xué)批判
二十世紀(jì)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huì)出現(xiàn)了一股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開始主要是指建筑、繪畫、小說等藝術(shù)作品中的某種反現(xiàn)代主義風(fēng)格,之后很快波及哲學(xué)、法學(xué)等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在這股思潮的沖擊之下,歐美國家的法律思想都不同程度地發(fā)生了從現(xiàn)代主義向后現(xiàn)代主義的轉(zhuǎn)向。①參見陳根發(fā):《后現(xiàn)代法學(xué)的特征》,《環(huán)球法律評(píng)論》2008年第5期。解釋學(xué)領(lǐng)域的轉(zhuǎn)向尤其引人矚目。斯坦利·盧森(Stanley Rosen)形容當(dāng)代解釋學(xué)為“典型的著迷于后現(xiàn)代主義”。②Gregory Leyh(ed.),Introduction to Legal Hermeneutics:History,Theory,and Practi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td. 1992,p.16.這種后現(xiàn)代主義解釋學(xué)向以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為代表的傳統(tǒng)解釋學(xué)發(fā)起了全方位的挑戰(zhàn),主要表現(xiàn)在五個(gè)方面:一是對(duì)傳統(tǒng)解釋主體的消解,反對(duì)先驗(yàn)的自我和普遍的人性;二是對(duì)傳統(tǒng)解釋對(duì)象的改造,強(qiáng)調(diào)文本的意義要由讀者來創(chuàng)造;三是為“成見”正名,主張解釋以傳統(tǒng)為前提,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新的理解、新的傳統(tǒng);四是對(duì)傳統(tǒng)解釋目的之否定,強(qiáng)調(diào)解釋只是游戲而已;五是對(duì)傳統(tǒng)解釋真理觀的批判,否認(rèn)認(rèn)識(shí)和對(duì)象相符合的真理觀,主張真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無窮的解釋。③參見王治河:《后現(xiàn)代哲學(xué)思潮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頁。隨著解釋學(xué)的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德國哲學(xué)解釋學(xué)家伽達(dá)默爾(或譯作加達(dá)默爾)的名言——“如果我們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們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被國內(nèi)外一些學(xué)者津津樂道、反復(fù)援引。除了伽達(dá)默爾式的口號(hào),德里達(dá)式的口號(hào)、巴爾特式的口號(hào)也成為了我們的時(shí)代“顯著的甚至是奇怪的流行時(shí)尚”,乃至于“‘這僅僅是你的解釋’,已經(jīng)降格到雞尾酒派對(duì)聊天的層次了,成了我們表達(dá)對(duì)任何東西的形而上學(xué)的或者認(rèn)識(shí)論上的懷疑之首選方式”。④[美]安德雷·馬默主編:《法律與解釋》,張卓明等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頁。
在法律領(lǐng)域,“解釋”一詞甚至可以說已經(jīng)被泛化、被濫用了。正如陳金釗教授所指出的:“解釋的過程中隱含著人們對(duì)解釋對(duì)象和解釋的普遍懷疑,解釋成了一件純粹裝飾性的外衣,隱含著對(duì)法律文本的自主性看法。”⑤陳金釗:《反對(duì)解釋與法治的方法之途》,《現(xiàn)代法學(xué)》2008年第6期。不少法學(xué)家還參與了一場(chǎng)關(guān)于“法律解釋的現(xiàn)代性抑或后現(xiàn)代性”的論戰(zhàn),其中美國學(xué)者斯蒂芬·菲爾德曼、丹尼斯·帕特森、斯坦利·費(fèi)什、羅納德·德沃金等人之間的交鋒尤為引人注目。從某種意義上講,該論爭(zhēng)體現(xiàn)了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者為自己在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爭(zhēng)得合法性、正當(dāng)性地位的努力。⑥參見高中:《后現(xiàn)代法學(xué)思潮》,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但以筆者之陋見,后現(xiàn)代主義解釋范式自身存在著難以解決的痼疾,其與法律解釋的普遍性、客觀性、規(guī)范性、確定性等法治特質(zhì)是背道而馳的。對(duì)于法律解釋的所謂“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嚴(yán)肅的法治論者必須予以高度的警惕。以下,筆者將從解釋主體、解釋對(duì)象、解釋目的、解釋方法等不同側(cè)面,對(duì)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展開批判性反思。
一、“這僅僅是你的解釋”意味著沒有客觀公正的法律解釋嗎
弗萊德·戴爾梅耶(Fred Dallmayr)在《解釋學(xué)與法治》一文中指出:根據(jù)西方政治強(qiáng)勢(shì)傳統(tǒng)觀念,良善的政府與理想的制度被界定為法律的統(tǒng)治,而非人的統(tǒng)治。這一法治的信條乃是與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核心前提和理性預(yù)設(shè)(central premises and hierarchical postulates)相聯(lián)系的。西方文化特別推崇理性的統(tǒng)治優(yōu)于獨(dú)斷專行,普遍原則的統(tǒng)治優(yōu)于個(gè)案化和特殊化的臨事處斷。⑦同前注②,Gregory Leyh書,第4頁。在該理念之下,法律解釋者的任務(wù)就是努力去發(fā)現(xiàn)針對(duì)個(gè)案的法律規(guī)范的客觀性存在。解釋法律時(shí),解釋者應(yīng)盡量摒棄自身偏見,拒絕來自外界的各種非法干擾,對(duì)待雙方當(dāng)事人不偏不倚,保持一顆客觀公正之心。這個(gè)時(shí)候的法律人就是一個(gè)“理性的主體”,一個(gè)有自覺意識(shí)的、無偏私的“理性人”。
然而,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學(xué)者卻否認(rèn)該種理性主體的存在,主張法律主體的概念只不過是某種形而上學(xué)的虛構(gòu),是理性主義者所杜撰的一個(gè)神話。在他們看來,由于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和法律制度語境,作為個(gè)體的人必然會(huì)帶有特定社會(huì)環(huán)境所賦予他的價(jià)值判斷與行動(dòng)指南。所謂的主體其實(shí)是碎片化的、無中心的。法律主體只不過是特定社會(huì)中的主流話語為了自己的利益,以法律的名義人為建構(gòu)的產(chǎn)物。⑧同前注⑥,高中書,第23頁。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學(xué)者用來解構(gòu)理性主體的重要武器是“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他們認(rèn)為,有各式各樣的眼睛,就有各式各樣的真理。人總是歷史地存在著的,理解也總是歷史地進(jìn)行著的。按照海德格爾和加達(dá)默爾的說法,就是人們都擁有“前理解結(jié)構(gòu)”,根本無法消除“成見”。⑨同前注③,王治河書,第173頁。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每個(gè)人的解釋都必然來源于一種特殊的視角(視點(diǎn))(perspective),所有的解釋都是主觀化的,個(gè)人偏見不可避免,解釋不可能是客觀公正的。解釋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無盡的解釋。如德沃金就聲稱,法律乃是“一種解釋性活動(dòng)”。這是德沃金“法理學(xué)的中心主張”,其實(shí)質(zhì)就是一種“視點(diǎn)性認(rèn)識(shí)論”(a perspectival epistemology)。⑩[美]丹尼斯·M·帕特森:《法律與真理》,陳銳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頁、第134頁。然而,筆者認(rèn)為,視角主義解釋論是存在著重大缺陷的,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gè)方面。
(一)視角主義解釋過分渲染了解釋的恣意性,漠視了其服從性
帕特森批評(píng)道,德沃金的解釋思想給人們帶來的是一幅錯(cuò)誤的“法律圖像”。該思想企圖“拋棄那種將知識(shí)建基于一定基礎(chǔ)之上的任何說明”,而代之以各種所謂的視點(diǎn)(視角)。然而,由于視點(diǎn)因人而異,所以從根本上講,我們沒有辦法在競(jìng)爭(zhēng)性的解釋之間進(jìn)行選擇。這就很容易滑向相對(duì)主義。“因?yàn)樵诮忉尩臒o限后退中沒有一個(gè)停留點(diǎn)。每一種視點(diǎn)都是由另一視點(diǎn)而來,一個(gè)接著一個(gè),最終,我們似乎全部是建立在自己的感覺基礎(chǔ)之上”。①同前注⑩,丹尼斯·M·帕特森書,第104-105頁。如此一來,解釋者就陷入了一個(gè)無窮的解釋過程,一種永無止境的、無法自拔的囚徒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中,解釋者將永遠(yuǎn)無法獲得文本的真諦。相對(duì)主義、主觀主義的唯我論(Solipsism)將洶涌而至,對(duì)人類理性造成毀滅性打擊。②同前注⑥,高中書,第78頁。面對(duì)這種解釋的囚徒困境,某些后現(xiàn)代解釋學(xué)者將權(quán)力話語抬了出來,認(rèn)為“法律文本的解釋活動(dòng)本身并沒有什么基本意義,而只是一種對(duì)規(guī)則體系的暴力性質(zhì)的或偷偷的挪用,以使某個(gè)指令得以實(shí)施,或者使規(guī)則服從于一個(gè)新的權(quán)力意志,或者迫使規(guī)則的參與者進(jìn)入另一種游戲……”③同上注,高中書,第39頁。實(shí)際上等于說,法律解釋不過是一種政治權(quán)力運(yùn)作的機(jī)制。
毋庸置疑,法律解釋是一種權(quán)力運(yùn)作,但與此同時(shí)絕對(duì)不能夠推導(dǎo)出,法律解釋僅僅是解釋者從個(gè)人好惡、個(gè)人偏見出發(fā)的權(quán)力展示。法律解釋的真諦,在于其是一種服從法治理念與精神、促進(jìn)與完善普遍規(guī)則治理的事業(yè)。法律解釋首先必須強(qiáng)調(diào)的是其對(duì)普遍規(guī)則的服從性,而非自由裁量性;法律解釋首先必須強(qiáng)調(diào)的是其權(quán)力的理性,而非權(quán)力的武斷性、恣意性。否則,人治將大行其道,而法治的文明大廈勢(shì)必灰飛煙滅。對(duì)此,弗萊德·戴爾梅耶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他指出,根據(jù)激進(jìn)的視角主義者的假設(shè),一種無法避免的人性與政治的因素,似乎以某種威脅到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議題的方式,進(jìn)入到了法律或法律實(shí)踐之中。法治正處于一種潰退至人治境地的危險(xiǎn)之中。這一危險(xiǎn)引出了一連串相關(guān)的擔(dān)憂:今日之法律豈非變成了武斷任意的俘虜,或者特定解釋者的隨心所欲的工具?今日的我們豈非正親眼目睹權(quán)力對(duì)法律、唯意志論對(duì)理性的勝利?④同前注②,Gregory Leyh書,第16頁。
(二)視角主義解釋過分強(qiáng)調(diào)了解釋主體的差異性,忽視了其同一性
在筆者看來,法律解釋主體不僅僅是具體主體,而且是抽象主體;法律解釋不僅僅依賴個(gè)體主體性的存在,而且依賴群體主體性的存在。按照經(jīng)典解釋學(xué)的觀點(diǎn),理解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同一性和差別性基礎(chǔ)之上的。如果只有同一性而無差別性,那么我們就不需要理解,因?yàn)槟闼v的就是我所具有的。而如果只有差異性而無同一性,那么我們就不可能相互理解,因?yàn)槟闼v的是我完全不具備的。只有同一性和差別性的辯證統(tǒng)一,理解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同一性是理解的基礎(chǔ)和所要追求的,而差別則是相對(duì)的,并可以設(shè)法盡量消除的。雖然在任何情況里,總是有某種思想差別存在于講話者和聽話者之間,但這種差別并不是不可消除的差別。⑤參見洪漢鼎:《詮釋學(xué)——它的歷史和當(dāng)代發(fā)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頁。不能因?yàn)榫唧w主體之間的某些差異性,就徹底否定主體同一性的抽象存在之可能。我們當(dāng)然知道,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但是我們同時(shí)也知道,可以很容易地、很明確地將柳樹的樹葉和楊樹的樹葉進(jìn)行分類,以利于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和把握現(xiàn)象世界。“一”與“多”、普遍性與差異性既是相互對(duì)立也可能是相互轉(zhuǎn)化的關(guān)系。視角主義解釋者所犯的一個(gè)錯(cuò)誤就在于,其僅僅關(guān)注解釋主體多樣態(tài)的、無中心的、碎片化存在,卻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拒斥了解釋主體同一性、普遍性、內(nèi)在規(guī)定性的抽象存在。
(三)視角主義解釋過分凸顯了解釋的主觀性,而排斥了其客觀性
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論者認(rèn)為,任何文本都具有多種可能的含義,而解釋就是選擇其中一種含義的過程。法官在作出解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表達(dá)個(gè)人的價(jià)值觀。法官總是帶著自己的有色眼鏡看世界的。因此,法律解釋總是個(gè)別化、特殊化的,毫無客觀性可言。“這僅僅是你的解釋”遂成為了一種時(shí)尚話語。歐文·費(fèi)斯就此指出:客觀性解釋并不要求法律解釋“完全由法官之外的某種力量決定”,而僅僅要求解釋受到必要的限制。解釋者一方面要受到“解釋規(guī)則”的約束,另一方面也要受到“解釋共同體”的約束。解釋者的自由并非毫無限制。“解釋者不能隨意地將他們所希望的意思強(qiáng)加給文本。他們受到一系列規(guī)范的約束,這些規(guī)范詳細(xì)說明了材料應(yīng)當(dāng)具有的相關(guān)性和分量(例如,語言、歷史、意圖、后果),同時(shí)他們還受到基本概念的約束。當(dāng)某些程序性條件具備的時(shí)候,必須進(jìn)行解釋。”①[美]歐文·費(fèi)斯:《如法所能》,師帥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頁。法律解釋規(guī)則和法律解釋共同體是在長期的司法實(shí)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具有廣泛的公眾和職業(yè)認(rèn)同基礎(chǔ)。在法律解釋過程中,解釋規(guī)則和解釋共同體作為某種確保客觀公正性的力量,共同形成了對(duì)解釋主體的視角的強(qiáng)力約束,抑制著其主觀恣意性的自由釋放。
二、情境主義解釋必然導(dǎo)致“一般命題不能決定具體案件”嗎
格里高利·雷(Gregory Leyh)指出,后現(xiàn)代主義解釋反對(duì)如下的觀念,即人類事物最終能夠被形式化為清晰的規(guī)則,該規(guī)則能夠而且應(yīng)當(dāng)起到使裁決程式化的作用。②同前注②,Gregory Leyh書,第12頁。后現(xiàn)代主義解釋學(xué)者所運(yùn)用的一個(gè)重型武器,就是由所謂的解釋學(xué)難題而導(dǎo)致的情境主義。弗萊德·戴爾梅耶在《解釋學(xué)與法治》一文中提到了這個(gè)解釋學(xué)難題。他指出:“規(guī)則治理或法治,首先意味著,法律可以被視為一種獨(dú)立于情境的純粹理性命題,而且法律規(guī)則對(duì)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或者以同樣的方式適用于所有的個(gè)體,或者至少適用于所有處在同樣情境之中的個(gè)體。然而,此時(shí)出現(xiàn)了一個(gè)解釋學(xué)的難題(或者毋寧說一大堆難題),亦即,既然法律永遠(yuǎn)不可能詳盡規(guī)定其適用范圍,那么離開了任何具體化的語境,法律或其內(nèi)容如何才能被充分地加以理解呢?而且,既然所有的個(gè)體和具體的情境永遠(yuǎn)不可能完全相同或者具有可替換性,那么離開了解釋,規(guī)則的一視同仁或者其適用的一視同仁如何才能被把握呢?”③同上注,Gregory Leyh書,第12頁。這個(gè)情境主義的追問,凸顯了法律解釋的普遍性與偶然性之間的深刻矛盾。
(一)“一般命題不能決定具體案件”只不過是“一個(gè)抽象的反對(duì)”
實(shí)際上,這個(gè)追問也是法學(xué)界長久以來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話題。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理論先驅(qū)之一、法律現(xiàn)實(shí)主義代表人物霍姆斯大法官就曾提出,“一般命題不能決定具體案件”,司法判決更多取決于“判斷力和敏銳的直覺而不是清晰的大前提”。對(duì)法律進(jìn)行形式主義解釋的法官“要么看不見,要么裝作看不見,對(duì)規(guī)則的一般性條款進(jìn)行不同的解釋是允許的”。④[美]斯蒂文·J.伯頓主編:《法律的道路及其影響》,張芝梅、陳緒剛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3頁。霍姆斯認(rèn)為,“一般命題不能決定具體案件”是對(duì)法律不確定性特征的“實(shí)際描述”,該特征是法律的“一個(gè)缺陷”,而且是“不可彌補(bǔ)的”。⑤同前注④,安德雷·馬默主編書,第106頁。然而,在黑格爾看來,這并非法律的什么缺陷,恰恰是法律的一個(gè)基本特征,是法律之所以可能的一個(gè)條件。黑格爾承認(rèn),法律受制于偶然性;但他強(qiáng)調(diào)這是必然的,理性本身承認(rèn)這樣一種限制。“實(shí)質(zhì)上法律有這樣一個(gè)方面……即受制于偶然性(contingency),其所以如此,乃由于法律是適用于個(gè)別案件的一種普遍規(guī)定(determination)。如果有人要反對(duì)這一偶然性,那將僅僅是一個(gè)抽象的反對(duì)……(因?yàn)椋┻@一偶然性本身是必然的。”①同前注④,安德雷·馬默主編書,第103-105頁。法律規(guī)則的本質(zhì)并不在于,相關(guān)的法律概念能夠指定一個(gè)獨(dú)一無二的結(jié)果,而在于:它必須總是包含基本原則,即使對(duì)于特殊的實(shí)例,它也必須提供判決的依據(jù)。對(duì)“一般命題不能決定具體案件”,黑格爾并不愿理解為,不管法官愿意不愿意,他必須卷入政治;而是理解為,在其哲學(xué)的一面,法律追求的是普遍性而不是黨派性。②同上注,安德雷·馬默主編書,第105-106頁。
筆者認(rèn)為,黑格爾的上述看法彰顯了一般性法律命題對(duì)于司法的重要性。從認(rèn)識(shí)論的角度講,人們對(duì)任何事物總是可以而且必須作一些實(shí)質(zhì)特征和瑣碎特征的預(yù)設(shè)與區(qū)分。法律也不例外。法律規(guī)則抽象設(shè)定了事物的實(shí)質(zhì)特征,而有意舍棄了某些瑣碎特征,使得法官等法律人在面對(duì)紛繁復(fù)雜的情境時(shí),能夠很快根據(jù)法律規(guī)范的明確指引,找到解決個(gè)案糾紛的辦法。無論是普通法系遵循先例與區(qū)別技術(shù)的運(yùn)作模式,還是大陸法系以制定法一般規(guī)范涵攝個(gè)別案件事實(shí)的運(yùn)作模式,都是某種把握普遍性、忽略偶然性的技藝,就好像是指引法官在叢林中找到回家的路。
(二)一般命題提供了法律解釋的意義框架
一般性法律規(guī)范命題為法律解釋者預(yù)留了一個(gè)意義空間,使得司法實(shí)踐一方面可以不脫離法治的運(yùn)行軌道,另一方面又可以適應(yīng)于各種不同但卻類似的具體情境,使得法律具有了某種靈活性而避免過分的僵硬。凱爾森指出:一般性法律規(guī)范構(gòu)成了一個(gè)意義的框架(a frame of meanings),這個(gè)框架包含了一系列可能的適用(a range of possible applications)。如果“解釋”可理解為——發(fā)現(xiàn)被適用的法律規(guī)范的意義,那么結(jié)果就只能是:發(fā)現(xiàn)被解釋的規(guī)范所描繪的框架,以及在該框架內(nèi)的各種適用可能性的認(rèn)知。簡(jiǎn)單地說,理解一個(gè)規(guī)范就是去澄清它,而澄清它就是去說明和鎖定那個(gè)意義的總體(the ensemble of meanings),而該意義的總體揭示了法律規(guī)范作為可能的適用之框架的特質(zhì)。這才叫做“法律解釋”。③Hans Lindahl,Dialectic and Revolution:Confronting Kelsen and Gadamer on Legal Interpretation,Cardozo Law Review,Vol. 24,2003,p.772.凱爾森認(rèn)為,通常情況下,對(duì)成文法的解釋就是要回答,當(dāng)把一般規(guī)范適用于一個(gè)具體的事實(shí)時(shí),人們?nèi)绾潍@致一個(gè)相應(yīng)的個(gè)別規(guī)范。在該意義上,法律解釋就是對(duì)將要被實(shí)現(xiàn)的一般規(guī)范所代表的框架的發(fā)現(xiàn),以及在這個(gè)框架中對(duì)實(shí)現(xiàn)規(guī)范的幾種可能性的認(rèn)知。在這個(gè)意義框架中,每個(gè)司法判決行為與該一般規(guī)范是相一致的。④參見[奧]凱爾森:《論法律解釋理論》,李鑫譯,載陳金釗、謝暉主編:《法律方法》(第7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頁。也就是說,法律解釋的自由度,其實(shí)就依賴于法律規(guī)范所設(shè)定的那個(gè)意義框架。法律解釋者在該意義框架中所做的所有解釋,都能夠涵蓋在法律解釋的概念之內(nèi)。否則,就不叫法律解釋,而應(yīng)歸于其他概念或范疇,如法律續(xù)造或法官造法。
(三)個(gè)人解釋不能凌駕于既存規(guī)則之上
由于后現(xiàn)代主義解釋學(xué)者熱衷于情境主義,認(rèn)為法律的一般性概念和命題不能決定具體案件,因此出現(xiàn)康奈爾的如下見解就不足為怪了——“規(guī)則本身被適用時(shí)是一個(gè)不斷被重新解釋的過程。是解釋給了我們規(guī)則,而不是相反。”⑤同前注④,安德雷·馬默主編書,第54頁。這無異于在說,是法律解釋者給了我們規(guī)則,并非是解釋者在依規(guī)則行事。因此,重要的是解釋者的存在,而不是什么作者或文本。費(fèi)什的讀者反應(yīng)論(reader-as-center)也持相同看法。費(fèi)什認(rèn)為,意義在讀者之中,而不在文本之中。文本作為惰性的客體,它是沒有意義的。所謂文本的意義,不過是數(shù)不清的讀者解讀出來的意義。法律命題的真理依賴于讀者的解釋。
對(duì)此,帕特森批評(píng)道:意義并不是從解釋而來,而是從日常的使用而來。我們并不是由于“解釋”才擁有共同的世界。恰恰相反,我們之所以擁有與他人和諧共存的世界,乃是因?yàn)槲覀儭袄斫狻苯M成該世界的各種各樣的活動(dòng)。“理解”的本質(zhì),就是緊緊抓住和參與這些活動(dòng)。如果我們認(rèn)為“理解”是最原始的東西的話,那么“解釋”就是一種次要的活動(dòng)。“解釋”實(shí)踐的存在,必然依賴于先期存在的“理解”。①同前注⑩,丹尼斯·M·帕特森書,第136頁、第170頁。帕特森通過將“理解”與“解釋”區(qū)分為初級(jí)規(guī)則和二級(jí)規(guī)則,有力地駁斥了個(gè)人解釋凌駕于既存規(guī)則之上的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觀。高中先生對(duì)其給予了高度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帕特森的理解觀“避免了解釋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充當(dāng)著挽救我們“免于唯我論、相對(duì)主義、虛無主義危險(xiǎn)”的護(hù)身符的作用。而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者未能意識(shí)到,“沒有理解,解釋只不過是在空中亂舞的精怪而已”。②同前注⑥,高中書,第79-80頁。
三、法律解釋是任意開啟或關(guān)閉文本意義的自由游戲嗎
解釋主體的視角主義和解釋對(duì)象的境遇主義,似乎注定了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學(xué)的解釋目的是游戲主義的。諸多后現(xiàn)代主義論者把游戲性作為解釋活動(dòng)的本質(zhì),強(qiáng)調(diào)解釋是為了解釋者自身的意圖而為的。斯坦利·盧森指出,按照后現(xiàn)代解釋學(xué)“視角主義的虛構(gòu)”,人的自身存在是一種“自我解釋”,理解(解釋)遂成為了“在符號(hào)學(xué)想象的舞廳里的‘能指’的舞蹈”。③同前注②,Gregory Leyh書,第16頁。巴爾特將文本的解釋視為“能指”的自由漂移和嬉戲。“能指”總是在滑移過程中不斷從“所指”的把握中逃逸。因此讀者可以隨心所欲地追隨“能指”而無視“所指”,自由地開啟或關(guān)閉文本的意義過程。讀者可以毫不理會(huì)作者的意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文本和各種意義聯(lián)系起來,從中獲得快樂。④參見葛校琴:《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6頁。德里達(dá)則直接鼓吹一種自由游戲的解釋學(xué),認(rèn)為法律解釋中“每一種情況都是例外,每一次決斷都不相同,都要求一種絕對(duì)獨(dú)一無二的解釋,沒有任何現(xiàn)存的法律規(guī)則能夠或者應(yīng)該絕對(duì)地?fù)?dān)保這種解釋”,因此法官的解釋是在為“自我立法”,法律解釋是一種“自由決斷的解釋”。⑤汪堂家:《汪堂家講德里達(dá)》,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56頁。然而,法律解釋真的是一種任意開啟或關(guān)閉文本意義的自由游戲嗎?
(一)游戲主義解釋混淆了“文本性范疇”
汪堂家對(duì)此種游戲解釋論提出了強(qiáng)有力的質(zhì)疑。他指出,德里達(dá)片面強(qiáng)調(diào)了法官每次解釋的獨(dú)特性,而消解了法律的客觀性存在。試想,如果每一次解釋都是獨(dú)特的,與上一次解釋沒有什么共通的東西,所謂的理解就完全是不可能的,人們之間的交流也成了各說各話。那么,法律是否還具備什么客觀有效性呢?⑥同上注,汪堂家書,第256頁。的確,如果法律解釋就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自由自在的解釋,自由自在的討論,沒有任何規(guī)范的依據(jù)和判斷標(biāo)準(zhǔn),只有游戲式的快樂,那么如何讓人們相信法律裁斷的公正性、客觀性呢?立法者頻頻制定、頒布法律規(guī)則又有什么實(shí)際意義呢?況且,縱然法庭審理確實(shí)像一場(chǎng)游戲,那也得講究特定的游戲規(guī)則,而不可能無限開放、率性而為。法律訴訟和足球比賽一樣,裁判者必須以內(nèi)在規(guī)則為準(zhǔn)繩,參與者或游戲者必須接受特定的規(guī)范權(quán)威。⑦同前注⑥,高中書,第204頁。我們?nèi)绻邮芊傻慕y(tǒng)治、規(guī)則的治理,就必須接受法律所確立的規(guī)范權(quán)威。作為行使公權(quán)力的主體,法官等法律解釋者必須認(rèn)同法律的規(guī)范性存在,反對(duì)解釋的游戲觀。
法律是一些規(guī)范行為的指令,這種指令的文化功能暗示了,法律文本在意義確定上是有嚴(yán)格的限度的。法官等法律解釋者在解釋這類文本時(shí),必然是受限制的。而后現(xiàn)代解釋論者對(duì)法律的游戲式解讀,恰恰忽視了不同的文本類型服務(wù)于不同的文化功能這一“文本性范疇”,他們不加區(qū)別地將一些適用于文學(xué)文本的范疇強(qiáng)加給那些在類型上迥然不同的文本,從而造成了大量認(rèn)識(shí)上的混亂。①參見[美]喬治·J.E.格雷西亞:《文本性理論:邏輯與認(rèn)識(shí)論》,汪信硯、李志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4頁。對(duì)于法律文本的特殊文化功能——教義性的無視或者忽略,造成了后現(xiàn)代主義自由游戲解釋論的濫用。
(二)游戲主義解釋忽視了法律職業(yè)特性
游戲主義解釋學(xué)是一種開放自由的文學(xué)解釋,它背離了法律解釋的本來宗旨和內(nèi)涵。法律解釋并非一種提供自由意見的解釋,而是一種教義學(xué)的解釋,一種以法治國為目的導(dǎo)向的解釋。誠如歐文·費(fèi)斯所言:“法官并不是因?yàn)閷?duì)特定問題或解釋持有相同的意見才屬于同一解釋團(tuán)體,而是因?yàn)樗麄兂兄Z以捍衛(wèi)和推進(jìn)法治為己任,因?yàn)樗麄兊穆殬I(yè)特性。文學(xué)解釋可能有多種流派,但是正如我的學(xué)生約旦·弗萊爾(Jordan Flyer)曾說,法律解釋只有一個(gè)學(xué)派,并且必須加入。所有法官都必須將自己視為這一學(xué)派的成員,只有這樣才能行使他們的職業(yè)特權(quán)。”②同前注?,歐文·費(fèi)斯書,第203頁。
確實(shí),職業(yè)特性決定了法律解釋與文學(xué)解釋是根本不同的。法律是作為規(guī)范人們行為的工具來到人世間的。法律是嚴(yán)肅的、權(quán)威性的、體現(xiàn)立法者規(guī)制意志的載體。人們對(duì)待法律不可能像對(duì)待文學(xué)藝術(shù)那樣輕松自如,尤其是當(dāng)值法官、案件當(dāng)事人及其律師,更不可能在法律規(guī)范面前自娛自樂。人們?cè)V諸法庭的目的,無非是尋求司法機(jī)關(guān)這種國家級(jí)的權(quán)威主體做出有效性、強(qiáng)制性的明確裁斷,案件當(dāng)事人雙方可以據(jù)此厘清各自的權(quán)利、義務(wù)和責(zé)任。因此,法官就案件事實(shí)和法律條文所作的解釋是一項(xiàng)規(guī)范性的事業(yè),而不是文學(xué)探究性的活動(dòng)。法律解釋是“根據(jù)法律”的解釋,是“據(jù)法審判”的官方治理行為,而不是個(gè)人化的自由詮釋和自我鑒賞。
(三)游戲主義解釋忽視了法官的角色定位
斯蒂芬·M·菲爾德曼指出,在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和司法判決過程之間,存在著一種內(nèi)在的緊張關(guān)系。“很多后現(xiàn)代學(xué)者贊美文本含義和真理的多重性,但是最高法院的權(quán)威性宣示實(shí)際上壓制了或殺死了不同的可選擇的含義。雅克·德里達(dá)及其在法理學(xué)界的信徒可能宣稱一個(gè)文本的含義是無法決定的,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必須作出決定。法律教授可以陶醉于文本的模糊性,……但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必須宣示法律。……因?yàn)樽罡叻ㄔ旱纳矸菥褪欠傻臋?quán)威宣示者。”③[美]斯蒂芬·M·菲爾德曼:《從前現(xiàn)代主義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美國法律思想》,李國慶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頁。或許,后現(xiàn)代法律解釋論者會(huì)質(zhì)疑道,法官們通過權(quán)威性宣示法律的意義,似乎掩飾了一些東西。但實(shí)際上,剛性的法律規(guī)范迫使法官非這樣做不可,否則他們就會(huì)陷入無休無止的爭(zhēng)吵之中。從根本上講,任何法律條文都是可以無窮追問下去的,最終可能使得理解與解釋法律條文變成某種“嬉戲”。然而,法官們往往滿足于善意地解釋法律規(guī)范,而非惡意地解構(gòu)法律文本。他們知道,這個(gè)社會(huì)永遠(yuǎn)都會(huì)有一些無法最終解決的問題,很多事情并不是他們?cè)诙潭痰膶徟衅陂g內(nèi)所能夠徹底解決的。幸運(yùn)的是,法治國的原則也沒有向他們苛求過多。
僅從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實(shí)踐來看,正如菲爾德曼所指出的,某些大法官似乎已經(jīng)生活在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之中了。“后現(xiàn)代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融入了他們的司法實(shí)踐;一些大法官,包括一些政治上最為保守的大法官,有時(shí)顯得在自己的意見中暗示了或吸取了后現(xiàn)代的主題。”④同上注,斯蒂芬·M·菲爾德曼書,第336頁。以倫奎斯特大法官和斯卡利亞大法官為例。在美國計(jì)劃生育協(xié)會(huì)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ν. Casey)、美利堅(jiān)合眾國訴弗吉尼亞案(United States v.Virginia)等案件中,倫奎斯特和斯卡利亞“通過在自己的意見中加入有些古怪的段落”以及“對(duì)詩人、歌曲作者”加以引用,看起來“這兩位大法官是在擺弄這些碎片”,似乎“代表了一種對(duì)讀者的擠眉弄眼”,以此“來喚起一種后現(xiàn)代的諷刺的態(tài)度”,暗示“自己無法達(dá)到現(xiàn)代主義的客觀性”。①同前注?,斯蒂芬·M·菲爾德曼書,第342頁。盡管如此,大法官也清醒地意識(shí)到,美國的司法權(quán)必須被理解為“申明什么是法律”的權(quán)力,而非“改變法律”的權(quán)力。所以,“即使倫奎斯特和斯卡利亞是在擺弄碎片,但是他們?nèi)匀皇纸?jīng)常使用司法判決過程的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主義工具,比如遵循先例的原則。他們解析各種各樣的先例的被認(rèn)為很精確的含義,編織在理性上前后一貫的法律命題的精細(xì)網(wǎng)絡(luò)”。②同上注,斯蒂芬·M·菲爾德曼書,第342-343頁。大體上可以這樣認(rèn)為,作為一種文化的自然反映,在美國大法官的判決中出現(xiàn)了某種程度的后現(xiàn)代主義;但是“大法官們——至少在他們作為大法官的角色當(dāng)中——不大可能具有像法律教授那樣的后現(xiàn)代性”,他們只不過是“以工具性的方式”,作為一種工具“借用后現(xiàn)代的洞見”而已。③同上注,斯蒂芬·M·菲爾德曼書,第355-356頁。從根本上講,美國的司法判決仍然是現(xiàn)代主義的,法官的角色行為仍然是符合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學(xué)的“游戲規(guī)則”的,并不是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自由游戲”式的解釋。
四、法律解釋究竟是“個(gè)性體驗(yàn)”,還是“理性建構(gòu)”方法
從方法論層面來看,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有一個(gè)非常重要的特點(diǎn),即“貶低客觀推理而褒揚(yáng)隨心所欲,貶低認(rèn)知的真理而褒揚(yáng)自發(fā)的沖動(dòng)”。④同前注②,Gregory Leyh書,第16頁。一方面,后現(xiàn)代解釋主義者不遺余力地批判主觀、客觀二分法的科學(xué)主義方法論范式,試圖將其逐出精神科學(xué)領(lǐng)域;另一方面,后現(xiàn)代解釋主義者又極力宣揚(yáng)多元化思維,倡導(dǎo)多樣化看問題的方法,直接或間接賦予情感、直覺、體驗(yàn)、想象等以方法論的價(jià)值,將各種非理性的東西紛紛推到前臺(tái)。由此造成解釋方法上非理性主義的極度泛濫,造成法律解釋的理論依據(jù)和功能定位的紊亂,從而消解了法律解釋學(xué)對(duì)法治事業(yè)本應(yīng)作出的貢獻(xiàn)。這樣一來,就給嚴(yán)肅的法治論者提出了一個(gè)不得不回答的問題——法律解釋究竟是“個(gè)性體驗(yàn)”的方法,還是“理性建構(gòu)”的方法?
(一)法律解釋能否“被引入理性設(shè)計(jì)的軌道”
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加達(dá)默爾開宗明義地批判自然科學(xué)方法論范式對(duì)人類社會(huì)生活的無孔不入的滲透與宰制,試圖在精神科學(xué)領(lǐng)域“探尋那種超出科學(xué)方法論控制范圍的對(duì)真理的經(jīng)驗(yàn)”。⑤[德]加達(dá)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導(dǎo)言,第18頁。他認(rèn)為,自然科學(xué)與精神科學(xué)有著各自不同的把握方式。自然科學(xué)立基于主觀、客觀二分法的思維模式,強(qiáng)調(diào)排除認(rèn)知過程中的主觀偏見,以達(dá)致對(duì)客觀存在的真理性把握。而精神科學(xué)則遵循主客觀統(tǒng)一的思維模式,強(qiáng)調(diào)理解并非主體對(duì)于某個(gè)被給定的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行為,“理解本質(zhì)上是一種歷史性的理解,也就是說,在這里僅當(dāng)本文每次都以不同方式被理解時(shí),本文才可以說得到理解”。⑥同上注,加達(dá)默爾書,第400頁。傳統(tǒng)解釋學(xué)追求客觀化的、理性認(rèn)知的解釋方法,無疑是因襲了自然科學(xué)的方法論范式。但在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論者看來,這是一個(gè)錯(cuò)誤。加達(dá)默爾的弟子、德國法學(xué)家阿圖爾·考夫曼說:“在取向于意義內(nèi)涵的知性科學(xué)中,主體、客體圖式原則上不起什么作用。一個(gè)想要理解某種意義的人完全必然地將其先入之見,從而也首先將其自我理解帶進(jìn)理解過程。這樣一種理解并不是對(duì)象性的,但也不是主觀的。相反,它始終是主體——客體同時(shí)并存。任何一種要把知性科學(xué)中的唯理性和知性個(gè)性分離開來的嘗試,都是注定要失敗的。”①[德]考夫曼:《后現(xiàn)代法哲學(xué)——告別演講》,米健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頁。
而在齊佩利烏斯看來,法律解釋是可以“被引入理性設(shè)計(jì)的軌道”的,盡管并不存在“精確的解決方法”。法律解釋是以(有限)理性的形式展開的,盡管各項(xiàng)“解釋論據(jù)”(方法)常常留下一個(gè)開放的解釋空間,法律解釋者可以借此空間進(jìn)行不同的選擇和評(píng)價(jià)。法律解釋論據(jù)常常起到“關(guān)鍵概念”的作用。借助它們,可以“概念性地建構(gòu)和展開關(guān)于正義問題的討論”,“并由此使正義問題獲得具體的、概念性的形式”。②[德]齊佩利烏斯:《法學(xué)方法論》,金振豹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1頁。他強(qiáng)調(diào),盡管法律解釋過程中留有某些非理性的因素,但在進(jìn)行解釋時(shí)仍應(yīng)窮盡理性論辯的可能性。“理性論辯使得對(duì)正確解釋的尋求進(jìn)入了有規(guī)可循之思考的領(lǐng)域,從而有助于對(duì)司法評(píng)價(jià)加以約束。通過這樣的方式,法學(xué)上的考量按照不同的根據(jù)被分解,并被納入理性的衡量模式。……法律解釋學(xué)的獨(dú)特理性表現(xiàn)在,它使其非邏輯性分散在小的,可界定的跳躍當(dāng)中;也就是說,解釋被拆解為一個(gè)個(gè)思想要素;由此,(法律解釋當(dāng)中的)批評(píng)必須分別針對(duì)并被納入整個(gè)論辯體系中某一十分確定的問題點(diǎn)才行。”③同上注,齊佩利烏斯書,第91頁。齊佩利烏斯的“理性建構(gòu)”的法律解釋論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筆者認(rèn)為,從法律發(fā)現(xiàn)的層面看,既然法律被視為裁判依據(jù),法官等法律人必然會(huì)面臨對(duì)法律條文進(jìn)行解釋的情形。而要作出有理有據(jù)的解釋,法律解釋者就必須將目光聚焦于法律規(guī)范文本之上,努力發(fā)現(xiàn)文本中所實(shí)際蘊(yùn)含的立法意圖。這就是在發(fā)現(xiàn)文本之“真”,類似于發(fā)現(xiàn)某種“真理性”存在。法律解釋遂成為了一種針對(duì)文本、專注于文本的意義發(fā)現(xiàn)的過程。事實(shí)上經(jīng)典法律解釋的文義、邏輯、歷史、體系諸要素,就是各種發(fā)現(xiàn)法律之真的有效手段。從法律論證的層面看,法律解釋乃是被法律適用者用來證成法律這種權(quán)威性理由,并據(jù)此斷案的。法律解釋方法能給具體的法律決定提供理性支持。每一種解釋方法的功能都有所不同,其實(shí)也就意味著運(yùn)用不同的法律解釋規(guī)則——語義學(xué)解釋、立法意圖解釋、歷史解釋、邏輯與體系解釋——給法律決定提供不同性質(zhì)的理由支持。一個(gè)法律決定受到支持的不同理由越多,該法律決定的武斷性就越少、越理性、越確定、越具有可預(yù)測(cè)性和可接受性。因此,每一個(gè)法律決定應(yīng)該盡可能多地受到不同法律解釋規(guī)則的支持。④參見王夏昊:《法律決定或判斷的正當(dāng)性標(biāo)準(zhǔn)》,載陳金釗、謝暉主編:《法律方法》(第八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頁。這就是法律解釋作為一種理性建構(gòu)的方法論之價(jià)值所在。而后現(xiàn)代主義法律解釋論者熱衷于發(fā)掘法律解釋中的非理性因素,誘使自己陷入了法律虛無主義的泥淖。
(二)個(gè)性體驗(yàn)的方法能否融入現(xiàn)代主義法律方法論
在反對(duì)理性主義方法對(duì)精神科學(xué)領(lǐng)域的統(tǒng)治之基礎(chǔ)上,后現(xiàn)代主義解釋論者鼓吹多元主義方法論,各種非理性因素遂受到極力推崇。例如,加達(dá)默爾將“經(jīng)驗(yàn)”(生命體驗(yàn))、“周旋”(參與)、“教化”等作為精神科學(xué)的“把握方式”。⑤參見洪漢鼎:《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兩大思潮》(下冊(cè)),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版,第582-583頁。晚年的加達(dá)默爾甚至將解釋學(xué)定位為一種“幻想力或想象力”,認(rèn)為“在我們這個(gè)充滿科學(xué)技術(shù)的時(shí)代”,我們需要“一種詩的想象力”。他反對(duì)解釋學(xué)由科學(xué)方法論來統(tǒng)治,鼓吹“解釋學(xué)想象”才是精神科學(xué)家的標(biāo)志。⑥洪漢鼎主編:《中國詮釋學(xué)》(第二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質(zhì)言之,解釋是一種想象的藝術(shù)、詩的文化。
然而,以筆者之見,后現(xiàn)代主義解釋論者倡導(dǎo)多元化思維模式,旨在鞭笞理性的宰制、弘揚(yáng)意志自由,但并不意味著其符合法律解釋的基本理念和范式。誠如洪漢鼎所言,想象藝術(shù)與精確科學(xué)是相互對(duì)立的。精確科學(xué)的特征在于它的精確性,即“真理的客觀性和唯一性,方法的嚴(yán)格性和規(guī)范性”;相反,想象藝術(shù)的特征在于它的非精確性,即“真理的境緣性和多元性,方法的開放性和自由性”。①同前注?,洪漢鼎主編書,第17-18頁。與想象藝術(shù)相比,法律其實(shí)更接近于精確科學(xué),盡管它不同于自然科學(xué)意義上的那種精確科學(xué)。情感、直覺、體悟這些非理性的方法本身具有混沌、無序、變動(dòng)不羈的特性,它們?cè)龃罅朔山忉尩牟淮_定性與不可預(yù)測(cè)性。而法律解釋最需要的不是想象力,而是確定性;法律解釋最需要的不是個(gè)性體驗(yàn)的方法,而是理性建構(gòu)的方法。
“在科學(xué)上,方法是指這樣一種路徑,它以理性的,因而也是可檢驗(yàn)的和可控制的方式導(dǎo)向某一理論上或?qū)嵺`上的認(rèn)識(shí),或?qū)驅(qū)σ延姓J(rèn)識(shí)之界限的認(rèn)識(shí)。”②同前注?,齊佩利烏斯書,第1頁。傳統(tǒng)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xué)就是作為一門理性主義方法論學(xué)問而存在的。它的正當(dāng)性在于:尊奉科學(xué)主義的范式,將主客觀二分法作為一種客觀現(xiàn)象,認(rèn)為法律文本是一個(gè)有著穩(wěn)定意涵的客觀存在物,我們可以通過某種科學(xué)的方法(理解和解釋的規(guī)律)達(dá)致對(duì)其意義的準(zhǔn)確認(rèn)知和把握,并將其視為(預(yù)設(shè)為)衡量某些事實(shí)和行為的權(quán)威性標(biāo)準(zhǔn),來規(guī)范人們的生活世界。現(xiàn)代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文本、法律規(guī)則,為法官等法律人依法辦事、據(jù)法審判提供了準(zhǔn)據(jù)。法律解釋方法論則進(jìn)一步為法官等法律人正確理解法律文本、法律規(guī)則,準(zhǔn)確把握立法者的意圖和精神,提供了一定的可實(shí)際操作的、可重復(fù)性的“法則”,并為解釋結(jié)果提供了某些正當(dāng)化的基礎(chǔ)。如果說法律規(guī)范文本是法治事業(yè)的“大堤”的話,那么法律解釋方法論則不啻為法治事業(yè)又筑起了一道“防波堤”。
方法論就好比是法律工作者的一個(gè)工具箱。在這個(gè)工具箱里,存放著一些有用的工具,以供法律工作者需要時(shí)使用。“現(xiàn)代主義的律師和學(xué)者帶著一個(gè)工具箱,其中有遵循先例、邏輯自洽、文本的平白含義、制憲者或者當(dāng)事人的意圖、政策論辯以及平衡測(cè)試等諸如此類的工具。現(xiàn)代主義者伸手拿出那些他們需要的工具,以滿足自己具體的工具性的目的,構(gòu)建論辯來支持或反對(duì)某些實(shí)體的立場(chǎng)。學(xué)習(xí)選擇適當(dāng)?shù)墓ぞ吆土己玫厥褂盟鼈儯@是學(xué)習(xí)像法律人一樣思考的過程的組成部分。”③同前注?,斯蒂芬·M·菲爾德曼書,第349頁。而后現(xiàn)代主義者所倡導(dǎo)的個(gè)性體驗(yàn)的方法,總的來看,作為非理性因素是不符合現(xiàn)代主義法律方法論的法治特質(zhì)的。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個(gè)性體驗(yàn)等非理性因素不可以被馴服、被放進(jìn)現(xiàn)代主義者的工具箱中,以便需要時(shí)拿來使用。也就是說,個(gè)性體驗(yàn)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現(xiàn)代主義者視為一種實(shí)用主義的工具,作為構(gòu)建現(xiàn)代主義論辯之用。就像史蒂文·D·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樣,“馴服一兩個(gè)后現(xiàn)代的主題,然后把它們?nèi)拥椒扇说墓ぞ呦渲小.?dāng)有用的時(shí)候,這些法理學(xué)者會(huì)拿出自己的后現(xiàn)代的小工具,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它們,然后把它們安全地放起來。換言之,后現(xiàn)代主義潛在的激進(jìn)的特質(zhì)會(huì)被征服,只有幾樣后現(xiàn)代的殘留物會(huì)偶然被從工具箱里拉出來當(dāng)做復(fù)雜的政策論辯”。④同上注,斯蒂芬·M·菲爾德曼書,第362頁。這或許就是個(gè)性體驗(yàn)方法等非理性因素的歸宿。
(責(zé)任編輯:鄭平)
D F0
A
1005-9512(2014)03-0070-10
姜福東,青島科技大學(xué)法學(xué)院副教授,吉林大學(xué)法學(xué)博士后科研流動(dòng)站研究人員,法學(xué)博士。
*本文系中國博士后科學(xué)基金資助項(xiàng)目“轉(zhuǎn)型期中國法治思維的矛盾及其化解”(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3M540240)和山東省社科規(guī)劃重點(diǎn)項(xiàng)目“當(dāng)代中國法治思維的矛盾及其化解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13BFXJ01)的研究成果。
- 政治與法律的其它文章
- 行政強(qiáng)制執(zhí)行法律保留規(guī)則之反思
——以侵害程度為標(biāo)準(zhǔn)的重構(gòu) - 論實(shí)質(zhì)合并破產(chǎn)規(guī)則的統(tǒng)一適用
——兼對(du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的思考 - 責(zé)任主義與量刑規(guī)則:量刑原理的雙重體系建構(gòu)*
- 環(huán)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經(jīng)驗(yàn)與中國借鑒*
- 以“控制”彌補(bǔ)“經(jīng)營者合并”的缺陷
——兼論以“控制”為標(biāo)準(zhǔn)構(gòu)建反壟斷法“經(jīng)營者集中”的審查制度 - 論刑事程序?qū)λ囊缸飿?gòu)成體系的隱性修正與重整
——以“犯罪認(rèn)定一體化”與“相對(duì)化”為視角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