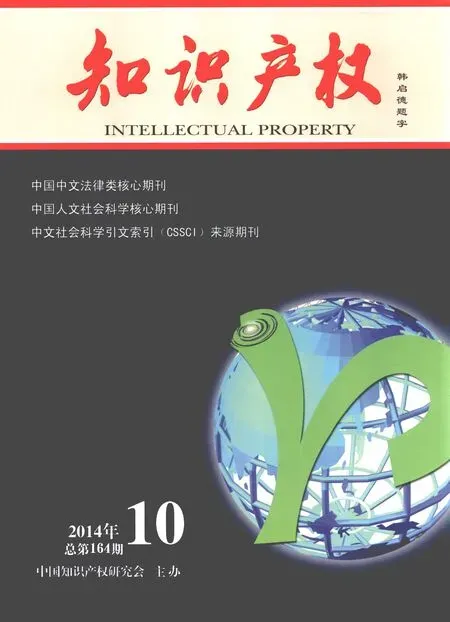未闡明的規則與權利的證成
——不正當競爭案件中法律原則的適用
謝曉堯
未闡明的規則與權利的證成
——不正當競爭案件中法律原則的適用
謝曉堯
編者按:9月23日,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知識產權》雜志理事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在江蘇省常州大學召開。會議由常州大學協辦。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利商標事務所、江蘇大學、南京理工大學等雜志理事單位的3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學術研討會以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主題,反不正當競爭法專家謝曉堯、范長軍等做專題講演,與會學者圍繞該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現將研討會上部分專題發言予以刊登,以饗讀者。
法律原則存在一個“樹狀結構”,我國法院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踐中,面臨法律原則既泛濫成災,又不敷使用的困境。法律原則是需要去證成的,既可以是對基本原則的具體化,也可以是基于案件進行的歸納和抽象,必須確保多元的法律價值不能缺位。依法律原則判案是權衡的藝術,涉及到利益考量、類推、案例類群、論爭程序等保障手段。競爭秩序需要更多的原則,更少的規則,司法不宜更多地干預市場。
法律原則 原則證立 原則權衡 不正當競爭 司法適用
法律原則是當今法律理論的核心話題,a[比]馬克·范·胡克:《法律的溝通之維》,孫國東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頁。在司法中的地位重要,“幾乎排他性地主宰著整個判決領域”b約瑟夫·拉茲:《法律原則與法律的界限》,載《比較法研究》2009年第6期。。然而,探討法律原則似乎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其歧義叢生、惱人不休,宛如“在陰雨天猜謎做游戲”c[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信春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頁。。在我國,依法律原則裁判的案件日益增多,d有人對1990年~2006年間《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登的520個案例進行了統計,適用法律原則進行裁判的有47個,接近公報案例總數的10。參見李克誠等:《論法律原則在我國司法裁判中的適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為范本的研究》,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3期。在在不正當競爭領域尤為突出,但學界對司法的回應整體較為冷淡。e一個耐人尋思的現象是,國內研究法律原則的法理學論文鮮見有討論中國司法中的法律原則,德沃金討論的“任何人皆不能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利”,是最為學者津津樂道的。法律原則的認識離不開司法場景中的具體案例,否則,就會成為空洞的概念;法律原則的實踐也離不開法理學和法律方法的指導,否則,司法裁判就會缺乏必要的章法。本文無意厘清高度復雜的理論和司法問題,只是結合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司法實踐,提出個人粗淺的看法。
一、法律原則的范圍
(一)反不正當競爭法法律原則的結構
按通說,法律規范采取二分法可劃分為原則和規則。法律規則設定了具體的假定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惟其如此,法官在判案中,才能“目光往返”于規則與事實之間,進行“三段式”的推理。法律原則不同,其本身不預設任何確定的事實狀態,只是給出概括性的評價標準。由于超然于具體事實之外,原則是開放性規范,具有適用上的普遍性。
不過,具體到何種程度稱之為“規則”,概括到何種程度成為“原則”,具有很大的模糊 性,f恩迪科特指出模糊性以及因模糊性產生的不確定性是法律的特征,沙堆拿走一粒沙子還構成“一堆”,一個禿頭即使長了一根頭發依舊是禿頭,對于“邊際情形”需要容忍。([英]蒂莫西·A.O.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是 一 個 漸 層 化 問 題g[比]馬克·范·胡克:《法律的溝通之維》,孫國東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頁。。 以 美 國 《 謝 爾 曼法》第1條為例:“凡是限制貿易的合同一律無效”,在適用中,美國法院在“限制”前加上了“不合理的”評價詞。德沃金的解釋是,立法中的規則“在實質上又是作為原則起作用”h[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信春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頁。
法律原則具有多樣性,黃茂榮先生認為,法律原則既可由個案歸納而出,也可由上位價值具體而來,結果皆會形成其體系架構之“樹狀結構”i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頁。。建構原則的“樹狀結構”,首要工作是對其識別。有人將原則視為目的、政策的等價詞和同義語j德沃金多將“原則”指稱規則之外的原則、政策等總體。([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信春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頁。)伯頓用“目的”取代“原則和政策”。([美]史蒂文·J·伯頓:《法律和法律推理導論》,張志銘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有人將其分為“結構性原則”(“默示”)和“(純粹)意識形態性原則”,前者從成文法中推演,后者涉及道德、政治或其他非法律意識形態。k[比]馬克·范·胡克:《法律的溝通之維》,孫國東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頁。學者舒國瀅區分“實定的法律原則”和“非實定的法律原則”,前者為制定法和判例所明示,后者要從歷史和倫理道德背景去考察,甚或潛于人們的意識之中。l舒國瀅:《法律原則適用的困境——方法論視角的四個追問》,載《蘇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按通常的認識,反不正當競爭法法律原則之“樹狀結構”,可勾畫如下:
第一,上位階的法律原則。反不正當競爭法源于侵權行為法,屬于民法的特別法,平等、自愿、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則,當屬上位階法律原則。這些原則高度抽象,實際是道德原則的法律化。
第二,同位階的法律原則。具體包括:(1)從立法標題可推導出:“正當競爭”原則;(2)從第1條立法目的可推導出:“公平競爭”、“消費者合法利益受保護”、“經營者合法利益受保護”、“有利于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等原則;(3)從第2條推導出:“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不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不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等原則。
第三,下位階的法律原則。對上述法律原則進行具體化,或者從案例中歸納和提取,可以形成次級規則——這一重要層級常被忽略。比如:在百度公司與奇虎公司案中,法院使用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m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2352號民事判決書。,在“海帶配額”中,法院認為“他人可以自由參與競爭來爭奪交易機會”,皆屬此類。這方面的法律原則在司法中非常多。n以避讓原則為例,“對他人已經知名的商業標識應 當保持合理的避讓”,在眾多裁判文書 中都有體現,如:宏濟堂阿膠有限公司訴宏濟堂制藥公司(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民三終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寧波長城精工公司與商丘長城精工公司(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民終字第93號民事判決書),江西寶島公司等與晶華寶島公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772號民事判決書),中電變壓器公司與中電電氣公司(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蘇知民終字第0144號民事判決書)。
將法律原則按其位階與序次來組合,并非為了簡單地判斷不同原則效力上孰優孰劣,而是為了立體化地呈現法律原則“樹狀結構”的深度或者說階度。通常認為,上位階的原則通過下位階原則去具體化其價值,而不得與其相左。越是下位階的法律原則,其適用范圍越有限,越趨近于規則。法律原則的識別和適用,必須同時保持“向上看”和“向下看”的思維方法。
法律原則的“樹狀結構”原本應該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狀,但在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法律原則存在“結構性失調”,呈現出“倒金字塔”現象,該法被負荷的抽象價值過多,而對其具體原則和經驗命題則重視不足。一個解釋是:市場經濟初期,商業倫理缺乏足夠的時間去累積;在變動不居的轉型時代,難以達成社會共識;司法案例、法律方法、法學理論不足以支持原則的提取。
(二)作為法律原則樣態的一般條款
對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司法文件中多稱之為“原則”o《關于貫徹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9]16號)規定:“對市場上新出現的競爭行為,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原則規定予以規范和調整”。還可參見《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9]23號),《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1]18號)。,裁判中則交替稱之為“一般條款”和“法律原則”p在“海帶配額中”,表述為“一般條款”(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號民事裁定書),在騰訊公司訴奇虎公司案中,表述為“法律原則”(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終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學界幾乎無差別地替代使用。嚴格地講,兩者還不能簡單地等同,法律原則是上位概念,范圍更為廣泛。在司法中,對法律原則的偏狹理解,會限縮立法的目的和價值,消費者利益保護問題就經常被視為可有可無。q在優酷公司與 金山公司案 中,金山獵豹瀏覽器對優酷視 頻貼片廣告 進行了攔截,法院 一方面認定 金山公司的攔截行 為,“是為 了迎合廣告過多、過長的不良體驗”,另一方面又認定其構成不正當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消費者利益的保護。(海淀區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3155號民事判決書)。
狹義上,一般條款屬于法律原則的特殊樣態。恩吉施將一般條款視為是與列舉條款相對應的概念:法律規則包含事實判斷,明確具體,但是也會掛一漏萬、“計劃不及變化快”。作為對羅列方法的替代性設置,“一般條款的真正意義在于立法技術領域”,可以無漏洞地適應任何場合。好的選擇是,將兩者結合起來的“示例方法”。r參見[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4頁。今天,各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基本上采取了一般條款+典型事例相結合的“示例法”,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關于反不正當競爭示范規定》體現得最為突出,該規定全部六個條文無不如此。一般條款因此而具有“標準”的色彩,有學者拒絕“原則—規則”的兩分法,引入“規則—標準”的劃分s拉里 ·亞 歷山大就明 確反 對法 律原則,道 德原 則本 身指示著法 律規 則的 制定,法律 原則 ,既 無規則的指 引優 點又 無道德正確 性優點,法律規范可以采取規則和標準的二分法,“標準是靈活的、具有情景敏感性的法律規范,在適用中需要作評價性的判斷”,多數法律規范是復合的,因為它們既有類似于規則的成分,又有類似于標準的成分。(拉里·亞歷山大:《反對法律原則》,載[美]安德魯·馬默主編:《法律與解釋:法哲學論文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411頁。),理由是,“合理的(注意義務)”、“不公正的(說法)”等概括性語詞,包含評價色彩,具有原則的特點;同時,這些評價標準基于列舉的事實狀態,具有規則的特性。
一般條款對應于列舉條款,是羅列事例基礎上合乎邏輯的概括性表達。但是,要恰如其分地給反不正當競爭法設定這種概括條款并非易事:如果對具體事例的抽象程度不高,與經驗事實的距離越近,涵蓋面不廣,普適性就不大。如果抽象程度過高,主觀價值的成分就大,有可能背離規范制定的事實基礎,導致特定法律的一般條款缺乏特質,成為多余條款,不如直接援引民法基本原則。
比如:“善良風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則,被視為概括了法治內在的倫理道德和現今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道德”。t[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下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99頁。開放性不謂不大,有人埋怨其寬泛到了“不過是一句空話”的地步u[德]沃爾夫崗·黑費梅爾:《通過司法和學說使〈反不公平競爭法〉的一般條款具體化》,鄭友德譯,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3卷,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即便如此,也有人批評其不能很好滿足時代變遷的需要,拘泥于傳統領域,涵攝范圍有限,“并沒有將經濟問題考慮在內”v[日]大村敦志:《民法總論》,江溯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頁。。梅迪庫斯就坦誠,善良風俗的主要難題在于如何查明其所指的內容,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與民法典的意義就甚為懸殊,“在一個‘多元社會’中,人們對道德價值及其位階的共同看法越少,這一任務就越難。”w[日]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512頁。這種質疑影響到了立法,2004年德國修改《反不正當競爭法》,將“善良風俗”予以刪除,究其因,一些學者認為其已經無法體現市場競爭中的基本內容。x蔣舸博士分析了德國立法修改的背景,她認為,修法的出發點是“去道德化”:“立法者至少在概念層面已經以競爭本位標準替代了道德標準”。(蔣舸:《關于競爭行為正當性評判——泛道德化之反思》,載《現代法學》2013年第6期。)這一觀點值得商榷,效能原則同樣是市場的道德原則,立法的修改不是“去道德化”,而是為了吸納日益發展中的“新道德”。法律從來不可能去道德化,有關法律原則與道德的論述非常多,比如,德沃金指出:“法律原則通過自身的協調反映了我們的道德情操,使法律獲得了道德特征,獲得了道德權威。”([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信春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頁)。格雷也指出,“所有文明社會中的法院都被暗示根據道德原則作出判決”。([美]約翰·奇普曼·格雷:《法律的性質與淵源》,馬馳譯,中國政法大學2012年版,第260頁。)
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述一般條款,在高度抽象的法律原則與非常具體、零碎的事例之間架起一道“橋梁”?各國表述不一,“誠實信用”、“誠實的商業做法”、“善良風俗”,等等。客觀地評價,這種努力多為徒勞。為學者津津樂道的表述多為民法原則的照搬或變形,甚至也是多此一舉的事:一般條款是否專門設定均不影響法律原則發揮作用。就反不正當競爭法而言,一般條款其實已經寫在它的立法標題之中。這或許也能解釋德國修法的原因。
回到我國,非常吊詭的是,一般條款面臨既泛濫成災,又不敷使用的困境。從前者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使用了諸如“自愿”、“平等”等7個價值詞,在全世界或許絕無僅有。從后者看,真正的法律原則不能僅僅停留于道德大詞,而必須具體化,第2條的適用整體上缺乏經驗知識的制度性支持。一般條款必須保持與列舉條款的對應關系和邏輯順暢,侵權責任法的一般條款值得借鑒y《侵權責任法》第2條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本法所稱民事權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股權、繼承權等人身、財產權益。”,未來的修改可以考慮設計為,“一切不正當的競爭方法以及其他危及競爭秩序的行為都應依法承擔責任。”
二、法律原則的證立
(一)法律原則的量度與深度
德沃金的法律原則理論具有很大的解釋力,有兩方面的內容最為重要:z參見[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信春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9頁、第43~46頁。
第一,法律原則的數量。原則的適用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包容并存,可同時適用兩個或兩個以上原則。這區別于規則,規則對于特定事件的反應是固定的,其適用“以完全有效或者完全無效的方式”。原則的作用方式是,通過指引我們將其納入考慮的因素予以評價,并不阻止其他原則的評判,“權衡”是原則的特定屬性。按照我國學者的理解,“一條原則只是支持這般判決的一個理由,而同時卻可能存在另一個更優越、更適切的原則,要求裁判者作出不同的判決。”7陳林林:《基于法律原則的裁判》,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3期。
第二,法律原則的分量。規則以全有全無的方式適用,不存在共同作用的“議價空間”;按照原則判案則需要具體探詢不同原則的重要性和分量。按照德沃金的看法,“原則具有規則所沒有的深度——分量和重要性的深度。當各個原則互相交叉的時候要解決這一沖突,就必須考慮有關原則分量的強弱。”麥考密克也認為,法律原則只是一個證明與解釋理由,“原則的存在為法官的判決給出了一個許可的范圍”8[英]尼爾·麥考密克:《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姜峰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158頁。
這無疑極具啟發性。在適用法律原則的場合,原則是多樣、相互競爭的,可以討價還價、擇優選擇。這也可以解釋為,法律原則更大程度屬于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事實具有唯一性,價值則是多元的。特定案件采取何種價值取向,取決于多個原則之間的權衡,才能在競爭性選擇中,判斷出各自的優勢和份重,運用法律原則判案,首要的任務應當是,抽離出不同的法律原則,給予其出場與論辯的機會,避免法律原則的缺位。具體到反不正當競爭糾紛,法律原則權衡和適用的數量是不確定的,并非以明示的一般條款(第2條)為準,必須以個案為依歸,離開個案談論法律原則的數量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支配案件的法律原則,難以預先設定,而是由特定案件的事實以及隱含在事實后面意義系統所決定。原則之間是并列和競爭性的,一條原則只是支持某方當事人的理據之一,未經權衡并不預設天然的優越性。同一法律原則,在不同的案件中,其優越性和適切性并不一樣,其分量并不絕對,因案而異。
(二)法律原則的具體化和篩選
原則指向的是對事實的評價,法律原則層級越高,主觀價值越強,越難徑行導出判決,而需要進一步具體化。阿列克西指出,“基于原則的論證的難題主要不在于對原則的證成,而毋寧在于:有待證立的規范通常并非在邏輯上根據原則(直接)推導出來。這就需要藉助進一步的規范性語句將原則加以具體化。”“原則是高度普遍化層別的規范性命題,所以通常若沒有其他前提的補充,它們就不可能被應用,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還要遭受其他原則所施加的限制。原則能夠作為對其所生效的事態之描述而不是作為規范性命題被引入討論過程。”9[德]羅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作為法律證立理論的理性論辯理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頁、第321頁。德國學者比德林斯基將法律原則定位為法理念與實定法具體規定之間的媒介,要求法律外的評價標準必須經過“法規范的篩選”。0
法律原則的具體化和提取,是還原價值規范的事實背景的過程,也可以理解為,主觀價值尋求客觀化、情節化再現的努力。通常認為,法律規則的制定需要通盤的論證,規則一旦形成就遮蔽了其背后的道德理由1陳林林:《法律原則的模式與應用》,載《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為此,規則具有省力性,其適用毋需再度探尋背后的理由與細節,“規則的可取性源于人類的無能為力和限度”2[美]邁克爾·D·貝勒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原則不同,它是“需要去證成的東西”3[美]邁克爾·D·貝勒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法律只是界定了一個一般性“框”,具有多種解釋與選擇的可能性,法官須結合個案另行探究和評價,只有經由具體化之后,方能轉化成判決的依據和標準。
具體原則產生的基礎大致有三方面:(1)從倫理價值觀、社會共識中提取;(2)根據上位原則派生;(3)在個案中歸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和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法發[2012]15號)規定,“……妥善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原則條款……有效遏制各種搭車模仿、阻礙創新的新類型不正當競爭行為……”
作為一種嘗試,筆者將上述內容理解為確立了如下原則:“針對創新行為的各種模仿行為應當禁止”,這是對一般條款的具體化。這一原則若獲成立,必須尋求有效的論證。顯然,該原則缺乏合理的基礎去證立,表現在:
第一,商業倫理和社會共同性認識,不支持一概禁止模仿的做法。有觀點就認為,“模仿是創造之母”、“照抄是美德”、“模仿是理性的行為”。哲學家蒙田也指出:“聰明人向傻瓜學習的東西,比傻瓜向聰明人學習的東西更多。”4[日]井上達彥:《模仿的技術:企業如何從“山寨”到創新》,興遠譯,世界圖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頁。
第二,缺乏現有法律原則和規則的“制度性支持”。比如:商標法禁止“模仿”的情形只限于馳名商標;商業秘密保護中并不禁止反向工程的模仿;著作權法并不禁止對他人思想的模仿,滑稽模仿構成合理使用;專利法并不排除滴漏效應。
第三,該原則缺乏廣泛的案例支持,甚至自相矛盾5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三提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為例,在藝想公司與帕弗洛公司案中,法院制止模仿旨在,“防止因仿冒行為影響知名品牌的發展”6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623號民事裁定書。;在拉科斯特公司與鱷魚公司案中,適用的條件是,“有惡意抄襲模仿意圖的前提下”7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終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在法藍瓷公司與加蘭德公司案中,法院“并不禁止他人適度的模仿”8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392號民事裁定書。;在翁正文與外星公司案中,法院禁止的是“刻意模仿”9最高人民法院(2000)知終字第4號民事判決書。。在費列羅公司與蒙特莎公司案中,法院禁止“足以引起市場混淆、誤認的全面模仿”$0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三提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在白云山公司與康特公司案中,法院禁止的是“刻意模仿”$1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民三終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
顯然,最高人民法院“有效遏制各種搭便車模仿”的命題是不能成立的。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原則證立上的基礎不夠扎實。將上述原則修改為:“各種惡意(一味、盲目)模仿行為應當禁止”,或許更具合理性。
(三)具體原則的獨立性和自洽性
不同的法律原則彼此具有獨立性、自洽性和融貫性,按各自的邏輯去證立和判斷,多元的價值不能簡單地替代、混同和取舍。這正如昂格爾所言:“在所有文化中,道德生活大部分都是由不同社會角色相互之間的道德要求和期望組成的。我們持有的合理公正的行為觀念大多以我們選取的社會角色為依歸。”“標準的語境論和司法審判的類推方法通常都能夠自覺符合以社會角色為基礎的大眾對公正的理解。法官可以成功地讓訴訟當事人在社會生活所確立下來的道德期望和類推判斷的目的性實踐之間產生聯系。”$2羅伯托·曼戈貝拉·昂格爾:《法律分析應當為何?》,李誠予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170頁。哈耶克也指出:“承認每個人都具有我們所應當尊重的他自己的價值等級序列,乃是對個人人格之價值予以承認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對他人進行評價,所依據的就必須是他們的價值等級序列。換言之,信奉自由,意味著我們絕不能將自己視為裁定他人價值的終極法官。”$3[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93頁。
回到反不正當競爭的司法實踐,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以著名的海帶配額為例,該案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說理,“商業道德要按照特定商業領域中市場交易參與者即經濟人的倫理標準來加以評判,它既不同于個人品德,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會公德,所體現的是一種商業倫理。經濟人追名逐利符合商業道德的基本要求,但不一定合于個人品德的高尚標準……”$4[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93頁。
商業道德當然不以圣人的情操和宗教道義去衡量,但是,“經濟人的倫理”是“內涵和外延并不確定的概念”,必須區分具體的法律關系,適用各不相同的法律原則,而不宜相互混用。該案中,馬達慶是山東食品公司長期負責對日海帶出口業務的部門經理,在退休前3個月設立了圣克達誠公司,并在離職之后與山東食品公司開展對日海帶出口業務競爭。合理適用法律原則的前提是,識別和篩選出不同的具體原則,員工在職期間與離職之后,法律原則的就有可能存在差異,不同的原則判斷的主體標準也并不相同。法院按照經濟人的齊一化標準適用山東食品公司和馬達慶,將雇員在在職期間的人格身份視為是經濟人,“用一般的社會觀念衡量,作為一個被企業長期培養和信任的職工,馬達慶的所作所為可能并不合于個人品德的高尚標準,不應該得到鼓勵和提倡,但這并不當然意味著他作為一個經濟人同時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
這一判斷是值得商榷的。本案中,在雇傭關系存續期間,山東食品公司主張的原則是“員工在職期間必須履行合理的忠實義務”,馬達慶主張的原則是“員工有自主參與競爭的自由”;離職之后,山東食品公司主張的原則是“員工應履行競業禁止之義務”,馬達慶主張的原則是“員工有權自由擇業”。就馬達慶而言,其適用的兩條原則都不是“經濟人標準”,離職之后,涉及到企業保密利益與員工謀生權的平衡,這一原則的判斷就是典型的勞動者標準。而在職期間,勞動者的謀生權沒有受到影響,雇員的判斷標準應當是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而不是外部市場中的經濟人標準。科斯已降的企業理論將企業視為關系契約,是市場的替代,以降低交易成本,雇主與雇員的關系區別于市場的個別契約,雇主享有對雇員的剩余索取權。馬達慶在職期間,尤其是其擔任高管的情況下,其負有更大的忠實義務。將“經濟人”外部市場的經濟人標準去衡量企業內部經理的注意義務,評價系統發生了錯位。
籠統以經濟人標準取代全部商業道德的評價主體是有害的$5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 》(法發[2011]18號),《準確把握當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政策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在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研討班上的講話》(奚曉明,2012年2月8日)都提出了“經濟人倫理標準”的尺度。。商業生活非常復雜,交易的主體、場合、地點、方式、社會背景,倫理標準的設定和評價千差萬別。好的做法是,厘清具體的法律原則,按照其不同的社會角色和法律地位,確定不同的評判標準。原則的證立要防止武斷性帶來的偏差,將一個原則話語體系中的標準作為普適性的標準去推知權利和義務。
三、法律原則的權衡
法律原則的適用是權衡的藝術。反不正當競爭法尤為突出,“實踐中不正當競爭概念日益演變成一種對利益的權衡。”$6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際局:《世界反不公平競爭法的新進展》,鄭友德等譯,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1卷,中國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一)原則權衡的方法
原則篩選出來之后,需權衡其效力層級、價值導向和利益大小,方法多樣:
1.“個案中之法益衡量”。拉倫茨提出的方案是:首先取決于依基本法的價值秩序所涉及的法利益是否有明顯的價值優越感。在位階相同或者歧義難斷時,一方面要取決于應受保護法律的影響程度,另一方面取決于假使某種利益須讓步時,其受害程度如何。最后須適用比例原則、最輕微損害原則或者盡可能微小限制的原則。為保護某種較為優越的法價值須侵及一種法益時,不得逾越達此目的所必要的程度。$7[比]羅伯特·阿列克西:《法:作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111頁。
2.邏輯推理。類推適用是最基本的方法,麥考密克認為,法律原則推理和類推推理之間,實際上并不存在明確的界限$8[比]羅伯特·阿列克西:《法:作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111頁。,胡克認為,“類比解釋不過是未言明的一般法律原則的一種掩飾適用。當使用類比推理時,解釋著將某一法律規則適用于某種情形……換言之,從一種明顯能適用該規則的情形中,人們得到一個更一般的法律原則,并通過下一步驟將該原則適用于該規則原本不適用但被認為是與第一種情形相類似的情形。”$9[比]馬克·范·胡克:《法律的溝通之維》,孫國東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頁。阿列克西提出了“融貫性”、碰撞法則和權衡法則等權利證立理論,融貫性標準包括:證立關系的數量、鏈條的長度、鏈條的聯結、理由的權重、相互證立等,在他看來,原則理論隱含著比例原則,表達了帕累托最優的理念。0[比]羅伯特·阿列克西:《法:作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111頁。
3.司法的累積性經驗。原則的權衡必須求助于過往的司法經驗,拉倫茨認為,“法益衡量”并非單純的法感,當裁判日益累積,比較的可能性日益提高,判斷余地將日益縮小。1[德]卡爾·拉倫茲:《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86頁。黃茂榮也指出,雖然法律原則不被清楚地定義出來,但它們卻可能通過個案慢慢地被澄清,而且也在這些摸索中,凝聚了一些可貴的下位原則,或甚至進一步針對某些案型的處理達到了將其構成要件化的地步;一再地嘗試通過一般條項比較公平地處理個案,卻也豐富并相對精確了原本極不確定之一般條項的內容。2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223頁。
4.社會共識與價值觀。社會的正義感、常識、價值觀、共有知識等能為原則的權衡提供背景性支持。在解決道德沖突的過程中,需要依靠經驗、直覺,以及特定背景中的價值、原則是如何牽連進去的敏感意識。3[美]亨利·馬瑟:《合同法與道德》,戴孟勇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頁。梅迪庫斯也指出,反不正當競爭中法律原則的適用,應在更大程度上考慮有關參與競爭法的各階層的觀點,最有可能考慮適用民意調查的方法。4[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頁。
(二)原則權衡中的論爭程序
原則權衡通常難以獲得實體上的滿意答案。德沃金就坦誠,答案通常不能顯而易見地被證明,“在某些案件中法律問題沒有正確答案。”5[美]羅納德·德沃金:《原則問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頁。原因在于:法律價值是多元的、獨立的、沖突的,價值具有不可通約性,也沒有固定的優先順序,任何價值的重要性都會隨情景的不同而變化。原則的適用雖有“權衡空間”,真要確定是哪項原則占據更大份重,則需要對原則及其背后的利益進行觀察、評估、度量和換算。社會越發達,價值系統越豐富,需要平衡的利益就越多,對原則分量的價值判斷通常是極其困難的。
法律原則的權衡需要一種“問題轉向”,從尋找公正的結果轉向確保結果輸出的正當程序。法律原則多元化的提取、廣泛論證和充分解釋,一方面有利于避免法官自我正當化、過多干預道德演進恣意行為,使“道德價值”轉化為反映社會的慣常性習慣道德而不是法官自己的批判性道德6轉引自布萊恩·比克斯:《法律、語言與法律的確定性》,邱昭繼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頁。。另一方面,法律原則的篩選和論證具有社會聚合功能,社會成員在廣泛的溝通、交涉、論辯中,“通過司法建構了互動的框架和語境,他為訴求和沖突提供了一般性的規則和程序。”7馬克·范·胡克:《法律的溝通之維》,孫國東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頁。這種程序有利于彌合分歧、凝聚共識、達致妥協。科弗認為,法律或許以單個的聲音言說,但這并不是一種得到關于法律材料“融貫一致”解釋的聲音,而是一種通常在各種法律觀妥協基礎上達成共識(或多數意見)的聲音。8轉引自布萊恩·比克斯:《法律、語言與法律的確定性》,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頁。
法律原則的適用盡管飽受爭議,但是,整體上仍能維系其公平合理的結果,沒有實證的研究表明,依照規則比依照原則裁判更為公平、更具確定性。原因既要歸因法律原則、社會道德具有內在的確定性,也要歸因于原則論辯的程序過程,價值因素的判斷與權衡偏好爭論,依仗發現的過程,能消弭社會的紛爭。其實,私法原本就具有程序性的品格,偏愛程序控制而疏離結果控制,廣泛地追求特定結果,既不是私法的志向所,亦超出了其能力范圍。9易軍:《私人自治與私法品性》,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3期。或許,在人類有限的理性和制度選擇中,原則適用中的價值權衡程序就更為重要了。
(三)我國司法實踐中的做法
法律原則需要以適合其自身的技術手段去認識,而不能原則問題規則化處理。以競業禁止為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1]18號)規定,“在既沒有違反競業限制義務,又沒有侵犯商業秘密的情況下,勞動者運用自己在原用人單位學習的知識、經驗與技能為其他與原單位存在競爭關系的單位服務的,不宜簡單地以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原則規定認定構成不正當競爭。”
上述內容隱含著的原則的沖突與協調,好的做法是競業禁止涉及的具體原則進行分解,在此基礎上權衡與判斷。就雇主而言,其主張的原則是“雇員在雇傭期間的勞動創造應當歸屬于雇主”,雇員則會提出“運用一般知識、經驗和技能謀生的權利不容剝奪”。顯然,這兩種權利是沖突的。雇員離職后,哪些知識可以帶走,哪些必須留下?界限并不清晰,需要進行權衡。雇員的勞動就業權,屬于憲法所保護的人權,而雇主只涉及民事權利,前者具有價值優勢性,原則的位序更高,后者不得與之相抵觸。但是,原則的適用并非全有全無,盡管兩條原則的序位存在差異,并非意味著后序位的原則一概不發生作用。在適用中還得權衡,比如:尊重競業禁止的合法約定,免受競業禁止的約束并不影響保密義務的遵守。一些法院在處理這類型案件中,采用的就是法律原則的權衡方法。^0典型的如:易達公司與姚向東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5]湘高法民三終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
原則權衡的關鍵在于,全面而準確地把握多元化的法律價值。價值缺位、證立簡單、方法單一、說理不足,是司法適用中的最大問題。比如:在騰訊公司與奇虎公司QQ案中^1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粵高法民三初字第1號、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終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在該案中,騰訊公司通過開發QQ軟件,采取提供免費即時通訊服務的商業模式。奇虎公司針對性地開發了扣扣保鏢軟件,供用戶下載以“全面保護QQ用戶安全”,該軟件會自動對QQ軟件進行體檢,發出健康警示,提供修復幫助,修復之后會禁用相關插件。,一審法院認為,“由于用戶在享受即時通訊服務的時候沒有支付相關費用,因此花費一定的時間瀏覽廣告和其他推銷增值服務的插件和彈窗,是其必須付出的時間成本。”“必須容忍廣告和其他推銷增值服務的插件和彈窗的存在”。二審法院盡管維持了一審判決結果,卻明確指出:上述“判斷失之準確和有所不妥”。二審法院的結論,其實同樣建立在原則的權衡基礎上。騰訊公司會提出“企業的商業模式應當不受他人侵害”,奇虎公司則認為“有利于消費者的商業行為不應受到禁止”,出于消費者利益保護,還需要考慮的原則是:“有利于消費者利益的競爭行為應受保護”。一審法院將看廣告作為是享受免費品的對價,當然不妥:一是對互聯網環境中免費促銷商業模式缺乏基本的認識^2免費商業模式的的經典作品可參看[美]克里斯·安德森:《免費》,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二是對不同的利益缺乏充分的權衡,消費者利益在許多時候具有價值優先性,其序位較高,將看廣告作為一種義務強加給消費者,不能獲得現行法律、司法做法和社會價值觀的支持。判決的信服力取決于更為細致的權衡,比如:消費者權利的性質、受影響的范圍、損害的即時性、嚴重性、彌補的可能性;奇虎公司對消費者保護的實際作用、替代性維護的可能性、行為的適切性、對競爭秩序的影響;騰訊公司利益的重大程度,等等。二審法院權衡的結果似乎是:消費者利益當然應受到尊重,但是,只要消費者的選擇權沒有受到損害,可以“用腳投票”,其利益就沒有受損;奇虎公司對消費者利益的增進不具有實質性意義,給競爭秩序帶來的危害卻很大。顯然,在消費者存在選擇權、替代性成本不高、轉換成本低的情況下,這一判決有其合理性。
還如:在百度公司訴奇虎公司違反Robots協議案中,奇虎公司推出的搜索引擎沒有遵守百度網站Robots協議,百度公司起訴要求禁止奇虎公司的行為,并賠償損失。法院審理之后支持了賠償,駁回了停止侵害的請求。該案是典型的原則平衡問題,百度公司所持的原則命題可以表述為“搜索引擎頁面的抓取應尊重網站的自愿和行業習慣”;奇虎360的命題為“搜索引擎抓取協議及其行業習慣必須有利于促進互聯網的開放和信息自由”。顯然,兩種主張都有受保護的價值,很難說哪一種具有優先性,法院選擇了平衡。在互聯網發展的現階段,司法應當為創新行為提供更有廣闊空間,這一判決是較為可行的選擇。
四、競爭秩序與規范性質
法律原則有賴于法官高超的解釋技巧和權衡能力,依原則判案在一定意義上有著較高的司法成本,這意味著,法律原則維護的秩序具有更為重大的價值。行文至此,必須追問法律原則與競爭秩序的關系。
(一)為什么需要更多的原則,更少的規則
法律原則蘊含著“確定性悖反”^3陳林林:《基于法律原則的裁判》,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3期。:既確定,又不確定。在反不正當競爭法領域,一些人對其心有疑慮,主張增加立法規則,減少一般條款的司法適用。^4據報道,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司法機關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認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缺少立法的支持和肯定。希望法律修訂過程中,能夠對這一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專家集中“會診”不正當競爭案審判難題》,載《中國知識產權報》2012年11月14日。本文認為,反不正當競爭保護很大意義就是一般條款的保護^5謝曉堯:《競爭秩序的道德解讀:反不正當競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這意味著更多的原則,更少的規則。一般條款的認識,不應僅僅拘泥于填補法律漏洞,法律原則契合了某種市場價值和人性美德,在不確定的商業和競爭環境中,法律必須保持寬容,維系正當性評判的足夠“權衡空間”。
市場秩序在很大程度是耦合秩序,競爭規則并非理性構建主義所能精心創造,而是參與者在長期的利益博弈中,不斷試錯、日益積累艱難獲致的。立法者盡管可以將已然形成于市場的商業道德訴諸于文字,形成規則,但是,這面臨幾方面的問題:有限理性使然,并非所有的秩序都能闡明,并訴諸于文字去表達;闡明的規則未必能真實反映其實際的情況;規則的立法表達難以避免外部權威的干預;經濟生活、道德、價值都處于流變之中,難以固化。
商業精神極其重要地包含著追求創新、挑戰風險,不確定性會給現存的倫理、規則帶來沖突和挑戰。競爭首先是一個市場問題,應當交由市場去解決,尊重其自身試錯、修復和調適性進化的規律。企圖以立法規則取得市場自生自發的秩序,一方面會干預市場,另一方面會阻卻多元化的知識來源,妨礙經驗知識多樣性的探求。外部規則對市場的干預,有立竿見影的政策功效,但是,非即時性的不良后果,卻容易被忽略,難以納入成本的估算之中。如果不保持自由度,予以適當的試錯空間,一些行為極容易誤判,其有可能帶來的好處會為社會所忽略。^6按照哈耶克的觀點,“與那些專做惡事的人相比,那些決定使用強制性權力以消除道德罪惡的人,實在導致了更大的損害及災難。”“私域內部的行動是否屬于道德的問題,并不是國家進行強制性控制的恰當對象。”([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80頁。)競爭的條條框框過多,既加大了交易的制度成本,也會扼殺和阻止一些創新行為,妨礙制度知識的學習與探索。理想的制度安排是,立法既要保持秩序威懾上的適度壓力,又要保持制度的足夠彈性和柔韌度,容許商業生活中的創新和試錯,維系商業道德、價值觀和法律自身演進的規律。
法律原則具有極強的制度彈性,以回應市場的需要。法律原則訴諸于商業倫理規范,與競爭參與者的價值觀和社會共識相一致。原則意味著變通和權衡,“法律原則是用‘應當’來陳述的”^7F·J·戴森著:《全方位的無限:生命為什么如此復雜》,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82頁以下。,具有極大的“議價”空間與回旋余地,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這些道德規范和慣例將在一般意義上被遵守,而不是說一律要遵守,但是這種知識仍將提供有益的指導,而且還能夠減少不確定性。盡管對這類規范的尊重并不能夠完全杜絕人們做一些為這些規范所反對的事情,但是對這些規范的尊重卻會將‘失范’行為限制在下述范圍內,即違反這些規范對于行動者來說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有時候,這些非強制性規范可能只是一種試驗,它們可能會在日后不斷的修正過程中漸漸發展成法律。然而,更為經常的情況是,它們將為那些多少不為人們意識的習慣提供了某種彈性的根據;我們可以說,對于大多數人的行動而言,這些習慣起著一種指南的作用。就整體來講,這些調整社會交往和個人行動的慣例和規范,并不會對個人構成嚴重的侵犯,相反,它們能夠確使行動達致某種最低限度的一致性;無疑,這種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將有助于個人之努力,而不會阻礙個人之努力。”^8[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82頁。
法律彈性的另一面相是寬容,寬容是私法的基本品性。法律原則意味著適切性權衡,為法律禁止的行為,必須是超出了社會共識中能夠容忍的限度。由于按照原則判案具有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盡管理論上可以提取相互并列的經驗命題進行選擇,但是不確定性下的司法決策,實際上對競爭者進行了“無辜假定”:“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的法律必須不時地假定人們是無辜的”。^9[美]亨利·馬瑟:《合同法與道德》,戴孟勇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頁。這非常類似于無罪推定,其實質是對非法的競爭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證明標準和更強的論證理由。這無異于一道“防火墻”,防止外部規則對市場內部秩序的侵入。美國學者戴森在追問“生命為什么如此復雜”時指出,復雜比簡單重要,生理平衡比復制重要,細胞的適應力比基因的獨裁重要,整體容忍誤差的能力比每部分的精確重要,復雜開放的生命更強韌。&0F·J·戴森著:《全方位的無限:生命為什么如此復雜》,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82頁以下。競爭制度同樣如此,競爭秩序需要來自其內部博弈中催生的適應力,社會應當對競爭中出現的問題保持適度的容忍。
(二)為什么是否定性規范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反不正當競爭法似乎成為“權利之母”,創造出新型“權利”和他人作為義務的判決為數眾多&1有關梳理參見謝曉堯:《在經驗與之制度之間:不正當競爭司法案例類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頁以下。。這些做法有失偏頗。
從性質上看,私法具有否定性(消極性)規范的性質,法律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性概念。否定性規范是“避免作惡”的規則,美國學者馬瑟指出,一個正派行為原則的標準是:必須防止一個人對另一個人造成重大傷害,這種禁令構成了道德的精髓,“一部道德法典或者一套法律規則體系,主要是由禁止實施某些有害行為的禁令所構成的,而不是由要求提供某些利益的命令構成的。”“實用主義和正義都要求法律將焦點集中在避免作惡這一更為關鍵的問題上。”&2美]亨利·馬瑟:《合同法與道德》,戴孟勇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頁。萊奧尼也指出:“否定性的自由的黃金規則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這一公式與‘施于人’這樣的肯定性的命令截然相反,它僅僅要求人不要干涉他人的選擇。”&3[意]布魯諾·萊奧尼等:《自由與法律》,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68頁。有學者將否定性視為是私法的“品性”&4易軍:《私人自治與私法品性》,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3期。,只消極地要求行為人不作為,而不積極地要求行為人作為。拉倫茨在談論“善良風俗”時指出:其“只起到了一種消極的作用,即限制當事人的私法自治。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法律要去積極地強制某種道德行為的實施……”&5[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下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03頁。
競爭秩序采取否定性的私法,有其合理性。哈耶克就正義、自由、正當性的否定性內涵有過大量的論述。在他看來,我們并不擁有評斷正義的肯定性標準,但擁有何者是不正義的否定性標準,“正當行為規則一般都是對不正當行為的禁令”,“正當行為規則和檢測它們正義與否的標準都是否定性的”。之所以采取否定的規范方式,理由是:立法者界定肯定行為規則有“不可避免的無知”;肯定行為具有很強的情勢依賴性,取決于與他人的互動的綜合情況,“超出了那種能夠共享甚或能夠意識到的共同生活”;面臨指涉未知的不計其數的未來情形。在采取否定性規范的場合,“正當行為規則界分確受保障的領域的方式,并不是把特定的東西直接分配給特定的人,而是使一種從某些明確的事實當中推知特定的東西究竟屬于誰的努力成為可能。”“這些規則并不賦予特定的人以權利,而只是確立一些人們依據他們便可以獲得這種權利的條件。”&6[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二、三卷)》,鄧正來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8頁。
否定性概念意味著,法律并不輕易預設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利,也不預設他人必須所為,而只有之所為足以影響實現權利時,“缺失的權利”才會凸顯。回到反不正當競爭法,該法并不設定肯定性規則,而是采取消極的、防御的方式,通過設定他人的不作為義務,來界定利益受保護之人免于受侵犯的“權利”空間,權利(法益)是通過明確他人負有不作為義務來“投射”和彰顯的,所保護的法益,無法積極行使,只能被動防衛。&7鄭友德等:《論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對象——兼評“公平競爭權”》,載《知識產權》2008年第5期。
(三)對我國司法的思考
改革開放35年是中國經濟社會強制性變遷的過程,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在一個高度轉型的時代難以自生自發地形成,市場經濟尚未健全,缺乏足夠的時間維度去凝聚共識,各種價值觀的沖突和分歧尤為突出。市場秩序中表現出來的各種無序,是市場價值的凝聚與獲取問題,需要時間的催化,不能急于求成。
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成功極其重要地依賴于法院&8WIPO指出:“它若不由法院推動,也會是無效的。在不斷變化的競爭世界中,就連最有預見力的立法者也無法預測未來不公平市場行為的所有形式,而必須依賴法院對法律的解釋。”。在我國,法院處理這一領域的案件,面臨巨大的困難:道德資源的貧乏成為司法中的瓶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尚無已然形成的“內在規則”下,法官缺乏去發現與闡釋的“讀本”;法官的思維方法、邏輯證立、解釋手段,難以形成釋讀社會道德的知識能力;缺乏案例類群、學理研究、案例引證等技術保障;等等。由此導致了一些較為極端的做法。
一種做法是,原則問題“原則化”處理,大而化之,未經說理和具體化,徑行依法律原則判決&9典型的如烽火聯拓公司訴新華科公司案,全部判決理由如下:“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本案中,新華科公司利用為烽火聯拓公司加工生產TG200電子標簽產品之便,在未經過烽火聯拓公司許可的情況下,擅自使用烽火聯拓公司PCB板的布圖設計,并制作印有其公司LOGO‘HK’標識的TG200電子標簽產品,以自己產品的名義對外公開宣傳推廣,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和商業道德。”(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9792號民事判決書)。即使一些法院有所說理,也多為道德大詞的閃爍,法律游離在虛無縹緲之間,缺乏經驗命題的“深度挖掘”,無法真實探明道德規范的內核和結構。
另一種做法更需要引起警惕:道德問題“典律化”、原則問題“普適化”。在法官缺乏道德釋讀能力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級法院存在做出某些指引的沖動,希望以司法政策、典型案例、指導意見等方式統一尺度。由此會帶來一些隱憂:經驗知識是在試錯和探索中日臻完善的,維系分散知識的競爭性產生,有利于提高裁判水平,統一原則的適用標準,導致了競爭性知識的輸出,導致的糾錯成本會更高,前面有關“模仿”、“經濟人”等問題,就是典型的例子。
較為實際和可行的做法是,回歸司法常態,從解決案件的技術性手段方面下工夫,比如:加強法官法律解釋、邏輯推理和說理論證的訓練,裁判文書的公開,建立案例類群,重視經驗命題的提取和累積,加強專家證人、社會調查、法庭之友、專家輔助人等公共協商機制的完善。
法律原則的司法適用,是尋求商業行為道德論證的過程,既是現有道德資源的利用,也會影響商業倫理的生成格局,前者是解釋性的,后者是干預性的。司法有必要保持最大謹慎和克制,充分顧及不同產業、市場主體的需要,考慮道德生成的博弈主體、時間長度、廣泛性,市場自我修復的可能性和代價,對消費者的影響、社會收益和成本,其他替代性措施。司法保持適度的克制,是對市場的最大尊重,真正的商業道德是在激烈競爭中形成的,各種陣痛是市場正常的生理現象,司法不能過多干預和包辦。競爭越充分,我們吸取商業倫理的可能性就越大。哈耶克告誡我們:“法官的工作乃是在社會對自生自發秩序賴以形成的各種情勢不斷進行調適的過程中展開的,換言之,法官的工作是這個進化過程的一部分。”“法官的任務只有在自生自發的且抽象的行動秩序內部才具有意義,比如市場形成的那種行動秩序。因此,法官肯定是保守的,當然這只是在下述意義上而言的,即他不能致力于任何一種不是個人行為規則決定的而是由權力機構特定目的決定的秩序。”*0[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一卷)》,鄧正來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87頁。
結 論
法律原則的司法適用是一個高度“復雜性”問題。僅就概念系統就涉及到:原則、目的、政策;基本原則、具體原則;上位階原則、下位階原則;一般條款、列舉條款;道德原則、法律原則。就其證立的基礎看,外部證立需要求助于商業道德、民眾意識、社會經濟政策、公共秩序等;內部證立需要獲得習慣、立法制度、司法案例、經驗命題等方面的制度性支持。法律原則是權衡之術,需要動用各種法律推理、利益考量、社會商談、法庭論辯等技藝。本文更愿意將法律原則的證成借用哈耶克使用的“規則的闡明”去表達。人類面臨揮之不去的構造性無知的現實處境中,法律始終是不完備的,法律規則始終存在漏洞,法律原則的適用實則是在個案中那些對未闡明的規則進行闡明和解釋的法律實踐。在實踐中,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法律原則是競爭秩序中主張權利的依據,權利的證成與權衡實際上就是不同法律原則提出、論證、選擇和權衡的過程。法律原則的權衡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權利的證成過程。有趣的是,契合市場競爭的需要,以法律原則為特質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典型的私法,其規范性質是否定性的,權利的證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他人不正當的行為去彰顯的。這或許可以理解為,權利乃是一種社會共識——意味著他人的克制、容忍和尊重,在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中,義務具有邏輯優先性,權利的證立和維系,需要有他人為一定負擔的正當性基礎。
There exists a “tree structure” in legal principles. The Chinese courts face a dilemma when they apply legal principles in unfair competition cases. On one hand, legal principles are overused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being used too casual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urts are short of useful legal principles in the sense that legal principles are not able to offer effective guidance. Legal principles must be justifi ed. They can either be specifi ed from basic principles, or be generalized and abstracted from individual cases. On the process of justifying legal principles, the diversity of legal values should be guaranteed. Adjudicating cases by legal principles is an art of balance. It needs some measures to guarantee its effectiveness, including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nalogy, the grouping of similar cases and the streamlining of the argument procedures, etc. Competitive order needs more principles and fewer rules. Judicial activities should not intervene the market excessively.
legal principles; the justifi cation of principles; the balance of principles; unfair competition; judicial application
謝曉堯,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