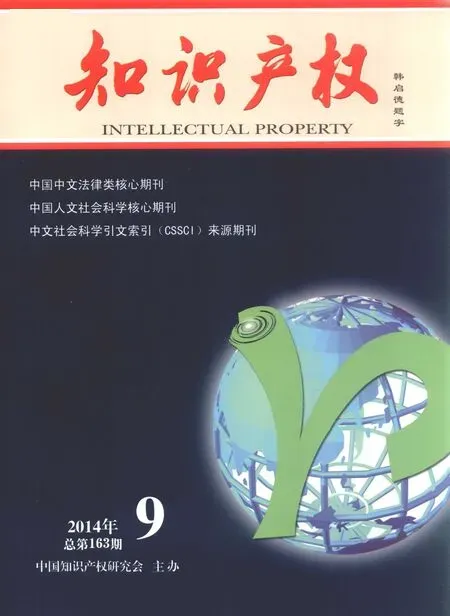美國方法專利拆分侵權認定的最新趨勢
——以Akamai案為視角
劉友華 徐 敏
美國方法專利拆分侵權認定的最新趨勢
——以Akamai案為視角
劉友華 徐 敏
方法專利是由多個有時間過程要素的步驟組成,易為多個主體拆分實施,Akamai案即為典型。該案中,地方法院依實質性侵權的“控制或指揮”標準判定被告不構成侵權;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改變現有規則做出了近乎相反的判決;而聯邦最高法院卻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有回歸現有規則的趨勢。我國多主體專利侵權認定的司法實踐中對直接侵權與共同侵權的界限不明,對“全面覆蓋”原則適用不嚴,不當擴大了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我國應嚴格遵守“全面覆蓋”原則,借鑒“控制或指揮”標準,權利人也可從撰寫技術層面避免拆分侵權。
方法專利 拆分侵權 引誘侵權 直接侵權
專利的權利要求可分為產品權利要求和方法權利要求。前者包括人類技術生產的物(產品、設備);后者包括有時間過程要素的活動(方法、用途)。a《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3.1.1權利要求的類型,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頁。這種含有多個有時間過程要素步驟的方法專利易被多個主體分開實施,在根據全面覆蓋原則(All-Elements Rule)判定侵權時,又沒有任何一個主體單獨實施了權利要求中的所有步驟,此時如何認定這些行為是否構成直接侵權或間接侵權,就成為復雜且亟需厘清的問題。Akamai v. Limelight案(簡稱Akamai案)即為典型。地方法院依據現有規則對該案作出判決,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改變現有規則,作出了近乎相反的決定,2014年6月2日,聯邦最高法院以9比0的絕對性意見撤銷了巡回上訴法院的判決、發回重審。該案判決的反復凸顯了美國對方法專利拆分侵權的態度變遷與發展趨勢,對我國相關實踐有較強的啟示意義。
一、歷時八載的Akamai案判決之反復
Akamai案涉及一個利用內容分發網絡(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 CDN)高效傳輸網頁內容的方法專利,Akamai公司是專利的獨占許可人,該專利包含放置一些內容供應商的內容組件在一組復制服務器上,標記內容服務商的網頁,以此命令瀏覽器檢索服務器內容的步驟。Limelight公司運行著一個類似于Akamai公司方法專利中所述的網絡服務器,通過在其服務器上放置內容組件達到高效傳輸網頁內容的效果,然而Limelight公司沒有自己標記內容服務商的網頁,而是指導他的消費者實施了剩下的標記行為。Akamai公司認為,Limelight公司同時構成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于2006年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2009 年 , 地 方 法 院 依 據 先 前 BMC v. Paymentech案(簡稱BMC案)和Muniauction v.Thomson案(簡稱Muniauction案)確立的“控制或指揮”標準(“control or direction”standard),認為該案中不存在直接侵權,因此也就沒有認定是否構成間接侵權的必要。2012年8月,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對該案作全體法官聯席重審(rehearing en banc),直接依據引誘侵權條款,作出了截然相反的決定。2014年6月2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否決了聯席判決,認為類似Akamai案中的拆分侵權問題并不足以改變現有專利侵權認定規則,撤銷原判決。
(一)地方法院:實質性侵權的“控制或指揮”標準
依聯邦最高法院判例,美國《專利法》第271條(a)款下的直接侵權是指某個單一的主體實施了專利權利要求中的所有技術特征。bAro Manufacturin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1961);Deepsouth Packing Co. v. Laitram Corp.(1972);Joy Technologies, Inc. v. Flakt, Inc(1993);Dynacore Holdings Corp. v. U.S. Philips Corp.(2004).Akamai案中,Limelight公司并未實施涉案專利的“連接”步驟,不符合直接侵權的“全部技術特征”要件,因而不構成直接侵權。法院對間接侵權的認定遵循“間接侵權須建立于直接侵權的基礎上”的“從屬說”。c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336, 341, 81 S.Ct. 599, 5 L.Ed.2d 592 (1961) .在拆分實施行為不構成直接侵權的情形下,Limelight公司也不存在被認定為間接侵權的可能。
2006年,BMC案確立了實質性直接侵權的“控制或指揮”標準,之后Muniauction案對該標準作了進一步澄清和發展。兩案均涉及多個主體對方法專利的拆分實施。BMC案中,法院認為,“多個主體實施某項專利構成拆分侵權(divided infringement)是直接侵權需要某個主體實施權利要求中的全部技術特征的特例。專利拆分侵權的責任劃分理論為:未‘控制或指揮’整個專利實施的主體無須承擔直接侵權責任。”dBMC Resources, Inc., v. Paymentech, L.P., 498 F.3d 1373, 1378-79 (Fed. Cir. 2007).Muniauction案中,法院再次重申,“只有在某個主體‘控制或指揮’了整個專利步驟的情況下,該主體才需要對該方法專利的每一個步驟承擔侵權責任”。eMuniauction, Inc. v. Thomson Corp., 532 F.3d 1318 (Fed. Cir. 2008).
作為“直接侵權需要某個單一主體實施了專利的權利要求全部技術特征”原則的例外,在多個主體拆分實施了某項方法專利的情形下,如某個主體“控制或指揮”了整個專利的實施,則會被視為實施了整個專利,構成實質性直接侵權。BMC案和Muniauction案之后,法院逐漸適用“控制或指揮”標準處理拆分侵權案件。Akamai案判決中引用“控制或指揮”標準,認為消費者并不存在代理關系、替代責任關系或合同上義務實施連接步驟,Limelight公司并不構成對其消費者實施行為“控制或指揮”。同時,由于不存在直接侵權,也沒有必要認定間接侵權。
(二)聯席判決:認定引誘侵權無需以第271條(a)款直接侵權為前提
由于法院傾向嚴格適用“控制或指揮”標準,很少有商事主體僅因與消費者共同實施了某專利(如Limelight公司所做),認定其對顧客的實施行為構成“控制或指揮”而判定其構成直接侵權,這使得權利人直接侵權救濟不能,轉向請求認定間接侵權。然而,間接侵權必須以直接侵權為前提,在無法證明直接侵權的情形下,權利人亦無法從間接侵權規則中獲得救濟。
2012年8月31日,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在聯席判決中認為,“類似Akamai案多主體拆分侵權案件改變了現有的方法專利引誘侵權規則,并且確信國會不會創造使當事人能通過分開實施方法專利的權利要求中的步驟而輕易規避侵權責任的規則”。fAkamai v. Limelight & McKesson v. Epic(Fed. Cir. 2012) (en banc).判決認為:自己實施某些步驟又引誘他人實施構成侵權行為的主要步驟的主體與引誘一個主體單獨實施所有步驟的主體對專利權人的影響是相同的。無論在成文法還是在立法政策層面,均沒有理由區分對待這兩類引誘人,也沒有理由認為后者應負侵權責任而前者不用負責。gAkamai v. Limelight & McKesson v. Epic(Fed. Cir. 2012) (en banc).
判決認為,只有在引誘行為導致實質性直接侵權時,引誘人才需承擔責任。“沒有直接侵權就不存在間接侵權”的原則是確定的,因為并不存在未遂的專利侵權。hAkamai v. Limelight & McKesson v. Epic(Fed. Cir. 2012) (en banc).判決并沒有采用現有間接侵權規則認為的,間接侵權的認定前提必須是有行為人已經實施了《專利法》第271條(a)款規定的侵犯專利的直接侵權行為,但又沒否認“間接侵權必須建立在直接侵權的基礎上”的原則,這里作為間接侵權認定基礎的“直接侵權”并非第271條(a)款中的直接侵權,更多是指侵犯專利權的必要行為,不論其由單個還是多個主體實施。由此,確立的方法專利引誘侵權的新規則為:(1)被控侵權人知曉涉案專利;(2)被控侵權人有引誘他人實施方法專利的步驟的行為(被控侵權人在實施引誘行為時已知被引誘人的行為將產生侵犯專利的后果);(3)方法專利的權利要求中的步驟實質上已被全部實施。
(三)聯邦最高法院:向現有規則回歸的趨勢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類似Akamai案的方法專利拆分侵權并不足以改變現有的侵權認定規則,根據判例法“引誘侵權責任只能建立在直接侵權成立的基礎上”。iLIMELIGHT NETWORKS, INC., Petitioner v.AKAMAI TECHNOLOGIES, INC., et al.No. 12-786.專利權作為國家授予的壟斷權,其保護范圍只能是權利要求中所有技術特征所限定的范圍,任何一個技術特征都不可能被孤立地授權,只有在方法專利的權利要求的所有步驟都被實施的情況下才構成侵權。
判決引用《專利法》案第271條f款(1)項的“專利境外侵權行為認定”對引誘侵權條款進行了解釋,該項規定美國境內的某個主體故意引誘他人在境外組裝部件,該境外主體的組裝行為必須是在美國境內能被認定為專利侵權的行為。最高法院認為,該規定表明國會在為引誘行為施加責任時,該主體自身的行為并不構成直接侵權。在沒有擴張引誘侵權概念的情況下,法院不能對某個非侵權產品施加引誘侵權責任。同時,法院也認為傳統民事侵權規則、刑法上的教唆幫助侵權規則并不能當然類推適用于專利侵權認定中。在傳統的引誘侵權民事規則中,即使第三方無需承擔侵權責任,利用該第三方侵犯他人權利的主體也將被施加侵權責任。判決指出:“Akamai案中關鍵不在于是否存在某個第三方對直接侵權承擔責任,而在于案中根本不存在直接侵權行為。”jLIMELIGHT NETWORKS, INC., Petitioner v.AKAMAI TECHNOLOGIES, INC., et al.No. 12-786.刑法中,即使每個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單獨都不有可訴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對他人造成侵害的也要承擔責任,但該規則中犯罪嫌疑人共同侵犯了被害人的法益,而Akamai案中并不存在專利被侵犯的事實,直接侵權不存在,沒有損害就沒有賠償。
最終,2014年6月2日,聯邦最高法院撤銷了聯席判決,要求以復審意見為參考發回重審,有向傳統規則回歸的趨勢。
二、Akamai案困境之理論反思
在Akamai案中,地方法院堅持間接侵權需以直接侵權的存在為前提的原則,遵循全面覆蓋原則,運用“控制或指揮”標準,判定被告不侵權;而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則從方法專利保護的角度出發,“創造性”解釋間接侵權條款,確立新的引誘侵權規則,以判定被告侵權;聯邦最高法院以技術環境變化不足以改變法律規則,撤銷原判發回重審。這一“不侵權—侵權—駁回”的循環凸顯了方法專利多主體拆分侵權認定的困境,其中對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解釋、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關系等問題典型體現了美國法院在運用司法公共政策影響專利保護力度,直接涉及到司法權的界限,也關切到技術發展與法律規則變化間的辯證關系。
(一)專利權保護力度與司法公共政策
“知識產權制度是一個社會政策的工具”。是否保護知識產權,如何保護知識產權,是一個國家根據現實發展狀況和未來發展需要所作出的制度選擇和安排。k吳漢東:《政府公共政策與知識產權制度》,載《光明日報》2006年10月10日。專利權作為國家授予個人或機構的壟斷權,是實現更大公共利益的手段,其本身并非目的。同樣,專利侵權糾紛中是否給專利權以保護,保護的程度與力度如何,政策上的考量與利益的衡量尤為重要,均具有深厚的公共政策色彩。
在Akamai案中,巡回上訴法院基于功利主義,為強化對方法專利的實質性保護,在法律明確規定了侵權構成要件的情況下,顛倒侵權認定的邏輯,為解決直接侵權認定的不能,“創造性”解釋271條(a)款和(b)款,先入為主地為引誘侵權創設新的直接侵權基礎,典型地體現司法公共政策。
聯席判決直接拋棄《專利法》第271條(a)款的直接侵權,為間接侵權確立了新的“直接侵權”認定基礎。Akamai案中,Limelight公司知曉原告的專利,且實施了在服務器上放置內容組件的步驟,然后指導顧客實施了剩下的步驟,在此過程中,Limelight公司知道自己的行為和用戶的行為合起來構成對原告專利的完整實施,因而其行為構成引誘侵權,引誘侵權的成立必須以直接侵權的存在為前提。基于認定間接侵權的需要,認為Limelight公司及其顧客的拆分實施行為構成直接侵權。lAkamai v. Limelight & McKesson v. Epic(Fed. Cir. 2012) (en banc).
聯席判決認為,第271條(a)款和(b)款是兩個平行條款,(b)款的引誘侵權無需以(a)款直接侵權為前提。這給第271(b)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間接侵權是在直接侵權求償不能的情況下,為適當保護權利人而作出的政策性擴張與強保護,是對直接侵權的補充。從權利人與公眾的利益平衡考量,應該對間接侵權的認定作嚴格限制。間接侵權需以直接侵權為前提就是限制的體現。
相反,地方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從全面覆蓋原則出發,堅守直接侵權的前提性條件,實質上是秉持對方法專利適度保護的司法考量。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引用Muniauction案對侵權認定的解釋,認為只有專利權利要求的所有步驟的實施行為能歸因于某個相同的被告,或者被告確實實施了所有步驟,抑或被告“控制或指揮”他人實施了這些步驟的情況下,才構成對方法專利的完整實施。在Muniauction案確立的規則下,如對專利所有步驟的實施行為不能歸責于任何一個主體,即使被告從實施行為中獲益,也不構成侵權。這實質上是運用司法政策衡量,運用單一主體原則,在直接侵權不成立的情況下,也就沒有引誘侵權的問題。因為如果將第271條(b)款的“侵權”概念從(a)款中孤立出來,引誘侵權規則將不受任何約束,給引誘侵權的認定帶來難度和不確定性,作為間接侵權認定的前提的“直接侵權”不確定,也使得競爭者無法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會被認定為侵權,進而妨礙公眾的自由利用空間。因此,如何運用司法公共政策,在方法專利拆分侵權糾紛的審理中合理的利益考量,確定適度的專利保護力度是值得謹慎考量的問題。
(二)專利權保護范圍與司法權界限理論
要判斷某一具體行為是否構成專利侵權,前提即是判斷和確定專利權的保護范圍,只有在其保護范圍內,權利人才享有禁止權。專利權是國家授予的專有權,權利人在法定期限內享有市場壟斷力。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大小與公眾可自由利用的技術空間具有直接對應關系,對專利保護范圍的合理限定一方面是為專利權人提供適當保護,另一方面也是對公眾自由利用技術提供足夠的法律確定性。各國專利法一般規定,專利權保護范圍以權利要求書為準。只有實施行為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才構成侵權。在方法專利拆分侵權中,被控侵權人并未實施方法專利的所有步驟,其對專利的實施行為并未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對未落入專利保護范圍的實施行為也予以規制顯然是對專利權的一種不合理擴張。
Akamai案爭議的實質并不在侵權規則本身,實際上對構成引誘侵權需要被控侵權人存在主觀過錯、引誘行為、間接侵權需以直接侵權為前提等并沒太大爭議,爭議焦點在于作為引誘侵權基礎的直接侵權的認定不能,導致間接侵權規則根本沒有適用的可能。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強調被控侵權人對專利“所有步驟”的“完整實施”才構成侵權。mm LIMELIGHT NETWORKS, INC., Petitioner v.AKAMAI TECHNOLOGIES, INC., et al.No. 12-786.Akamai案爭議的基礎是直接侵權的存在,即未全面覆蓋專利的實施行為認定為直接侵權。由于直接侵權屬于嚴格責任,無需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意圖,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專利,且實施的技術全面覆蓋了涉案專利,直接侵權就能成立。Limelight公司在其服務器上放置一些內容組件,盡管這屬于對專利技術的實施行為,然而其行為并未全面覆蓋專利的全部技術特征。從侵權構成的一般要件看,能否對一種行為施加以侵權責任,損害后果僅是需考慮的要素之一,行為本身是否具有違法性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不能因為一種行為存在客觀上的損害,單純以彌補損害為目的,改變行為違法性的認定標準。
此外,Limelight公司與其消費者并不存在共同侵犯專利權的意思聯絡,Limelight公司對其消費者的實施行為也不存在“控制或指揮”,正如聯邦法院判決中提到,“用戶并不存在合同關系、代理關系或者替代責任關系下的義務去訪問網站,就如被告雖然給了家庭用戶汽車鑰匙,但家庭用戶并沒有使用鑰匙開走汽車的義務”,nGlobal Patent Holdings, LLC v. Panthers BRHC LLC, 586 F. Supp. 2d 1331, 1332-33 (S.D. Fla. 2008).將用戶的實施行為歸責于Limelight公司也有失公平。
總之,對未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拆分侵權予以控制,客觀上擴張了專利權的保護范圍,超越司法權的職責范圍,對規則作出有悖于國會立法原意的擴大解釋,有違司法權界限原理。
(三)技術環境的變化與法律規則之變遷
為解決類似Akamai案的拆分侵權認定困境,如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所做的,針對云計算與網絡技術革新帶來的技術環境變化,為方法專利的保護“創造性”解釋引誘侵權規則,改變現有規則,實質上擴大了專利權的保護范圍,給公眾自由利用技術帶來不確定性,是對公眾利益的不合理限制。
方法專利的權利要求由多個有時間過程要素的步驟組成,這決定了方法專利易被多個主體拆分實施。這種特點并不是Akamai案所涉及的云計算專利技術所特有的,也不是云計算等網絡技術發展賦予方法專利的新特點。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言:“技術環境的改變并不足以改變現有規則”。oLIMELIGHT NETWORKS, INC., Petitioner v.AKAMAI TECHNOLOGIES, INC., et al.No. 12-786.基于方法專利本身的特點,通過改變侵權認定規則來增加侵權認定的可能,這種做法并不是最佳選擇,侵權規則是對行為和責任的規范,并不涉及專利技術本身,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拆分侵權的認定困境。再者,社會經濟技術總是處于發展變化之中,侵權行為的模式也是層出不窮,如果僅僅是針對某種行為而改變侵權認定規則,將給法律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盡管云計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給方法專利的拆分實施提供了新的便利,給專利法律規則的實施帶來了困境,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專利制度與侵權規則之根基。因此,在方法專利拆分侵權認定實踐中,動輒以技術環境變化或方法專利拆分侵權特殊性為由,“創造性”設置規則的做法值得斟酌。
三、我國處理專利拆分侵權的現實情況
(一)共同侵權與實質性直接侵權的區分不清
方法專利拆分侵權涉及多個主體共同實施一項專利,與美國確立了實質性直接侵權的“控制或指揮”標準相比,我國各級法院基本適用共同侵權規則,但實踐中并未嚴格遵循共同侵權的構成要件。多數情形下,只要被控侵權人為多個且實施行為落入專利保護范圍,多主體即構成共同侵權,而不考慮其意思聯絡,僅關注行為的多主體參與,只要多主體共同實施了某項專利即構成共同侵權,如一些法院認定承攬合同中的承攬人因接受委托實施專利,與定作人構成共同侵權;多個主體間基于正常的買賣關系、購銷合同也會被認定為共同侵權p如“邱則有與長沙航凱建材技術有限公司、湖南順天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參見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湘高法民三終字第39號民事判決書;“上海風某空調設備有限公司與上海某二空調設備有限公司、上海某林電子技術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理論上,共同過錯是共同侵權規則中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的基礎,對類似承攬人這類主體,其與定作人并不存在共同過錯,已盡到基本注意義務且基于正常的商業合作關系而實施專利,判令其承擔連帶責任,有失公平。而強令沒有共同過錯的行為人為他人的行為負責,違背了“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基本法理。
我國《專利法》第11條規定了未經許可實施專利的五種侵權行為,并不意味行為人需親自實施專利的全部技術特征,那些利用他人實施專利并從中獲益的主體,利用他人實施專利的行為本身就屬專利法上實施專利的一種方式,構成直接侵權。由于對專利共同侵權與直接侵權的區別模糊不清,對《專利法》第11條直接侵權的理解過分狹窄,在多主體拆分侵權案件中,我國法院過度適用共同侵權規則,在多個主體不存在共同過錯的情況下,將本質上是由某個主體利用他人實施了專利的情形也認定為共同侵權不符合法理。
(二)未嚴格適用全面覆蓋原則,對間接侵權與直接侵權的關系不明,不當擴大了專利權的保護范圍
從立法上看,我國認定專利侵權并不區分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然而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諸多要求認定間接侵權的訴訟。實踐中,法院未嚴格適用全面覆蓋原則,對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關系不明,將原本不應作為專利保護對象的技術特征作為專利予以保護,不當擴大了專利的保護范圍。
施耐德電氣公司與正泰集團公等侵犯發明專利權糾紛案q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0)一中知初字第26號民事判決書。即為典型。案中雖然正泰公司的產品并不包含與多級斷路器相連的技術特征,但是在其產品說明書中其對顧客告知多級斷路器的型號并指導顧客安裝和使用,一旦顧客將正泰公司漏電斷路器產品和多級斷路器連接使用,連接后的漏電斷路器就會落入涉案專利的保護范圍,正泰公司生產漏電斷路器的行為與顧客的連接行為合起來構成對涉案專利的實施行為。該案與Akamai案十分類似,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正泰集團公司在主觀上有誘導、教唆他人侵犯專利權的故意,客觀上為他人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為由認定其構成間接侵權,對“間接侵權是否要以直接侵權的存在為前提”這一問題表述模糊,未對“直接侵權”作任何考察的情形下,在間接侵權認定時提到構成“間接侵權”的行為為他人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在曾某與重慶市植物保護植物檢疫站、重慶市植保技術服務公司專利侵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植保植檢站在明知原告的專利發明情況下,開發推廣并由植保服務公司生產銷售原告專利發明的藥性肥料中的農藥,且在該產品的使用說明中明示產品使用者使用尿素作載體,導致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故兩被告已構成對原告發明專利的間接侵權”r參見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1999)渝一中經初字第2009號民事判決書。,案中兩被告生產推廣的侵權產品并未落入專利技術的保護范圍,并未實施以尿素為載體這個要素,不構成直接侵權,但法院僅以其行為會導致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為由認定其構成間接侵權,而對“直接侵權”是否存在在所不問。相反,在高某與周某、濟南李斯特環保節能設備有限公司專利侵權案中,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專利“間接侵權行為雖然并非直接實施侵權行為,但應當以第三人完整實施專利技術行為的存在為前提。”s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6)魯民三終字第78號民事判決書。可見,我國法院在多主體專利侵權案中,對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關系不明,做法迥異,客觀上“武斷”地給專利權以不當的保護,值得斟酌。
四、Akamai案對我國方法專利拆分侵權認定的借鑒
我國《專利法》及《專利法實施細則》確立了專利侵權構成的基本標準,無論是相同侵權還是等同侵權均適用“全面覆蓋原則”,即只有被控侵權對象將專利權利要求中記載的技術方案的必要技術特征全部再現才構成侵權,因此,方法專利拆分侵權問題在我國現有法律規則下亦會產生侵權認定的困境。Akamai案判決的變遷對我國有如下啟示:
(一)借鑒“控制或指揮”標準:合理界定共同侵權和直接侵權
我國認定專利拆分侵權通常適用共同侵權規則,然而,方法專利拆分侵權糾紛中,多主體間通常缺乏共同侵權的意思聯絡,不符合共同侵權的構成要件,如不區分主體間的主觀過錯,對所有實施者課以連帶責任有失公平。因此,《侵權責任法》第8條規定的共同侵權規則適用于拆分侵權不合理。其次,《侵權責任法》第9條規定,“教唆、幫助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應當與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該條規定的侵權行為類似美國的間接侵權,在方法專利拆分侵權中,在被教唆、幫助人并未完整實施專利,其行為不構成侵權的情況下,教唆、幫助行為亦不會構成侵權,該條并不能解決方法專利拆分侵權的難題。此外,與美國將間接侵權視為對直接侵權責任的補充相比,《侵權責任法》第9條規定,教唆、幫助行為人與專利實施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然而教唆、幫助行為僅僅是引起直接侵權的發生,其對侵權結果的作用有限,對其施加連帶責任亦有失公平。
相比于美國法院將利用他人拆分實施方法專利視為直接侵權的一種特殊情形,我國認定專利拆分侵權的依據是專利法之外的共同侵權理論,但實踐中直接侵權與共同侵權的界限非常模糊,有濫用共同侵權之嫌,因此,有必要引入“控制或指揮”標準,合理界定直接侵權與共同侵權。將“控制或指揮”他人實施專利的情形從共同侵權中剝離,被控或指揮的人無需承擔責任,控制或指揮第三方的主體構成直接侵權。構成“控制或指揮”的情形可以分為三種:一是代理關系;二是需承擔替代責任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雇主與雇員的關系,關鍵是主體間的控制程度;三是合同關系,如供應商、承包商、融資合同等商業合作主體,以及服務提供商、生產銷售者等商事主體與顧客或產品購買者。對合同關系,應根據合同條款考察是否存在控制或指揮,也可考察下列因素:被控制或指揮的主體(供應商、外包商、承攬人)向其供應的零部件、原材料與專利技術中涉及的技術創新點是否相似或相同。
總之,處理方法專利拆分侵權糾紛應立足于從控制、指揮與協同的關系程度上綜合考慮,其指導思想應是:避免在方法專利中利用第三方的行為,規避專利侵權責任,損害權利人利益,在規避專利侵權責任與有效保護專利間實現平衡。
(二)嚴格遵循全面覆蓋原則,避免不合理擴張專利保護范圍
如前所述,我國法院并未嚴格遵循全面覆蓋原則,在被控侵權人并未完整實施專利的情況下,僅因其行為會導致直接侵權的發生或為侵權提供了必要條件,即認定其構成間接侵權,對行為導致的“直接侵權”是否存在未作嚴格考察,這實質上是將一個并未全面覆蓋專利保護范圍的實施行為納入專利權范圍予以保護,不合理地擴大了專利的保護范圍。
有學者認為,創造性地解讀《侵權責任法》第6條t《侵權責任法》第6條:“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關于過錯責任的原則性規定,可以解決Akamai案困局。該學者指出:“第6條意旨在于,只要行為人有過錯,其行為與他人民事權益損害存在因果關系,就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至于行為人單獨的行為是否構成‘實施侵權行為’,在所不論。只要其過錯行為從整體上致使他人民事權益損害,即可問責。”u何懷文:《方法專利引誘侵權研究——兼評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Akamai Technologie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案全席判決”》,載《知識產權》2013年第3期。該觀點過分強調行為的主觀態度和損害結果,忽略了對行為本身違法性的認定,脫離了知識產權侵權認定的基本邏輯。與傳統民事侵權認定相比,專利侵權認定的前提性問題在于判斷和確定專利權的保護范圍,只有被控侵權技術對涉案專利技術構成全面覆蓋的情況下,被控侵權人才構成對專利技術的實施,才有認定其行為是否侵權的基礎。僅僅考慮行為的主觀態度和損害后果就對其施加專利侵權責任,顯然是“舍本逐末”,不符合專利制度的價值取向。
更重要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Akamai案中所展現的回歸現有規則的趨勢,客觀上收緊了對方法專利的幫助侵權與引誘侵權的認定,實質上放松了對方法專利的保護。連技術領先型的美國,一貫堅持功利主義的司法實踐采用這種思路的背景下,對尚處技術追趕進程中的中國而言,繼續濫用共同侵權理論,不嚴格遵循全面覆蓋原則,不當地擴大專利權的保護范圍,客觀上將保護更多的他國方法專利,更與國際主流趨勢不符。
因此,應合理界定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既要使專利權得到公平保護,又要使公眾對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有穩定的預期。在確定保護范圍時,嚴格堅持全部技術特征原則,避免專利權保護范圍確定的隨意性,防止不當擴大其范圍。對未落入專利保護范圍的,應依法肯定行為人的利用自由,促進技術的傳播和運用,。當然,對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情形,應依法給予嚴格、有效保護。
(三)從撰寫技術層面避免拆分侵權:專利權人的策略選擇
考慮到方法專利拆分侵權的行為模式,從專利權人而言,基于對方法專利拆分侵權的行為模式的考量,在撰寫方法專利的權利要求時應避免將其撰寫成可多方參與的類型,確保該專利只能由某個單一主體實施,在專利保護范圍層面避免拆分侵權認定不能的困境,不失為有效保護其方法專利技術,防范他人通過拆分侵權規避責任的更優策略。正如BMC案中聯邦法院所言:“對于本身需要多主體共同參與實施的專利,專利權人可通過謹慎撰寫專利文獻來避免這些潛在的侵權,法院不能也不應擴張侵權規則來救濟撰寫拙劣的權利要求”。vBMC Resources, Inc., v. Paymentech, L.P., 498 F.3d 1373, 1378-79 (Fed. Cir. 2007).
與Akamai案類似,Level 3 Communications, LL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案(簡稱Level 3案)wL e vel 3 Commc'ns, LL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630 F. Supp. 2d 654 (E.D. Va. 2008).同樣涉及一種使用服務器網絡從高容量網站獲得數據請求,為網絡用戶提供數據的方法,而且兩個案件面對的是同樣的被告。由于Level 3案中原告方法專利權利要求的步驟只需要由單個主體實施,該案中Limelight 公司被認定為侵權。Level 3案中涉案專利的權利要求多次使用了“內容提供者”、“用戶”這樣的表達,這種撰寫方式與在權利要求書中籠統的包含實施系統的所有人有很大差異,權利要求中復制信息的步驟由用戶實施,在遠程中繼服務器中進行信息服務的步驟由系統所有者實施。例如,該案專利的權利要求19:“一種內容交付服務,包含:在廣域網(WAN)的內容服務器中復制一組頁面對象,通過某個非內容提供者的域來實施;給定頁面通常是從內容提供者的域中產生,標記給定頁面的嵌入對象,對于頁面對象的請求是由某個非內容服務提供者的域來實施;在內容提供者的域中接收給定頁面的請求并予以回應,服務于從內容提供者的域中接收的給定頁面而不是用戶的域。”xU.S. Patent No. 6,654,807 col.29 ll.11-37 (filed Dec. 6, 2001) ; see Level 3, 630 F. Supp. 2d at 657-58 n.2 (listing asserted claims).正如權利要求所述,同樣是涉及互聯網的方法專利,該專利的權利要求嚴格區分每個步驟的實施域。Level 案3中,Limelight公司認為用戶的頁面內容是在其個人服務器上運行的,其不應對用戶的行為和設備承擔侵權責任。法院認為,類似源服務器、用戶、客戶端請求這樣的內容是方法專利的外部因素,系統本身并不需要多個主體實施。Muniauction案、BMC案及Akamai案中的事實相區別,該案根本無需要考慮用戶與Limelight公司的關系,甚至無需考慮“控制或指揮”標準,就能得到較好保護。
Method patent is composed of several steps involving elements of time process, which can be splited to implement by multiple legal subjects, such as Akamai case. In this case, the district court verdicted that the defendant's act was not infringement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or command” criterion of substantive tort, which was modifi ed by Federal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in the almost opposite verdict, and might be recovered due to the revocation decision of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Determination of multiple legal subjects infringement of patent in China, the boundary of direct infringement and joint infringement is not clea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 cover” is not strict, which results in the improper expansion of the protective scope of patent right.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 cover” should be observed and the “control or command” criterion sh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hina. Split infringement can be avoided through technical writing by subjects.
method patent; split infringement; lure infringement; direct infringement
劉友華,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法治湖南與區域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徐敏,湘潭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碩士研究生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云計算專利法律問題研究”(12CFX082)的階段性成果、“法治湖南與區域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之“知識產權保護研究平臺”的建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