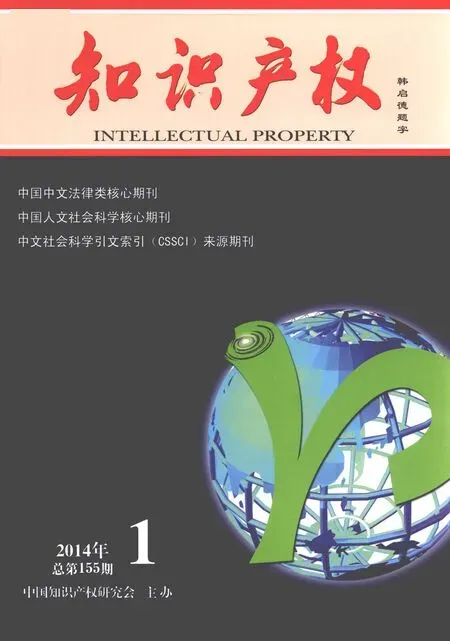Literary Works譯意探源
孫新強 李偉民
Literary Works譯意探源
孫新強 李偉民
現實中,作品千差萬別,《伯爾尼公約》將其分為兩類: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20世紀80年代,美國等國將計算機軟件作為文學作品,納入版權法的保護范圍。隨后,在西方國家的鼓動下,《TRIPS協定》也要求WTO成員將計算機軟件作為《伯爾尼公約》中的文學作品加以保護。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學界未能將“文學作品”理解為一個法律概念,想當然地認為軟件與“文學”無關,將literary works譯成“文字作品”以期涵蓋計算機軟件。此后,在概念法學的驅使下,又推斷出“口述作品”。受此誤導,我國《著作權法》以雙重標準——作品形式和作品內容——對作品進行分類,致使作品各種類之間矛盾、重疊。為了使我國著作權法中作品的分類更加科學,建議將Literary Works譯為“文學作品”。
著作權 文學作品 作品分類
前 言
有民法學者認為,根據《合同法》,民商事領域中訂立的合同可劃分為以下種類:
書面合同;口頭合同;買賣合同;租賃合同;贈與合同;承攬合同;運輸合同;技術合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合同。
上述所謂“民法學者”純系本文杜撰。如果真有民法學者這樣認為,會造成民法學的混亂。然而,我國《著作權法》恰恰是以上述方式對作品進行分類的。誠然,知識產權法不同于傳統民法,具有自己的諸多特點。但不可否認的是,知識產權法仍然屬于民法;民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規則,對于知識產權法仍然適用。具體而言,合同法中關于合同的分類標準完全可以適用于著作權法中的作品分類。《著作權法》卻背離了合同法上的合同分類標準,同時采用不同標準對作品進行分類,導致所分種類之間矛盾、重疊。
著作權法圍繞著作者、作品、著作權等概念而展開,其中,作品的分類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目前,我國《著作權法》正在緊張的修訂中,作品分類亦為修訂內容之一。因此,研究此問題并找出其產生的根源,對于著作權法的立法完善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伯爾尼公約》的漢譯
1886年9月9日,英、法、德、意等10國在瑞士伯爾尼締結了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1條第3款明確表達了這一點:“Industrial property shall be understood in the broadest sense and shall apply not only to industry and commerce proper, but likewise to agricultural and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to all manufactured or natural products, for example, wines, grains, tobacco leaf, fruit, cattle, minerals, mineral waters, beer, flower, and flour.”tion of Litera參見李明山:《中國近代版權史》,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鄧少根:《〈伯爾尼公約〉在中國的傳播》,載《出版史料》2006年第2期。ry and Artistic Works。16年后,1902年3月4日(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外交報》自第3期起以連續三期的版面,全文刊登了《伯爾尼公約》及其相關文件。《外交報》在刊登公約譯文時使用的譯名是《創設萬國同盟保護文學及美術著作條約》。這是國人對《伯爾尼公約》的第一次譯介。a參見李明山:《中國近代版權史》,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鄧少根:《〈伯爾尼公約〉在中國的傳播》,載《出版史料》2006年第2期。
同年,江都于寶軒編纂了《皇朝蓄艾文編》,第73卷——學術部分,收錄了《伯爾尼公約》漢譯正文及其續增條款和改正條款。該書由上海官書局出版,張之洞為之作序。
1909年,《外交報》又刊登了清政府駐德國商務參贊水鈞昭翻譯的《伯爾尼公約》(1908文本)中譯本——《萬國保護文藝美術版權公約》。該譯本與前譯本在內容上基本相同,但略去了前譯本中與《伯爾尼公約》關系不大的一些枝節(如同盟國名單、同盟國全權委員的簽名、各成員國交換文書的情況等),因此,結構更加清晰,文字更加簡潔、準確,而且也更加白話。b雷雁林:《〈外交報〉與〈伯爾尼公約〉在中國的傳播》,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今天看來,早期譯者將公約中的Artistic Works譯成“美術著作”,外延上明顯偏窄,這可能與當時中國的國情有關。我們知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攝影、雕塑等西方藝術形式在我國尚未普及,由“戲子”表演的各種戲劇難以被正統文化當做藝術看待,對于當時的國人來說,所謂藝術無非是指繪畫、書法和篆刻等傳統的中國藝術形式。不過,即使他們對Artistic Works 的理解存在偏差,但對Literary Works的理解卻是非常準確的,譯為“文學著作”則更無不當。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的中文譯名《創設萬國同盟保護文學及美術著作條約》和《萬國保護文藝美術版權公約》后經幾代學者反復推敲、改進,遂通譯為今天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公約名稱雖幾經變化,但學界始終將其中的literary works譯為“文學作品”。對于這一漢譯,鮮有人質疑過。
二、《伯爾尼公約》中的作品分類
現實生活中的作品千差萬別,但《伯爾尼公約》以作品所表達的內容為標準,將不同領域中的作品分為文學作品(Literary Works) 和 藝術作品(Artistic Works),猶如人們依據性別將人分為男人和女人的兩類人一樣。依據《伯爾尼公約》,一部作品如果不能歸入藝術作品之類,便只能歸入文學作品的范疇。毫無疑問,公約中的文學作品乃一法律概念,與文學并無必然聯系,就像《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中的工業產權概念與工業并無必然聯系一樣。c《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1條第3款明確表達了這一點:“Industrial property shall be understood in the broadest sense and shall apply not only to industry and commerce proper, but likewise to agricultural and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to all manufactured or natural products, for example, wines, grains, tobacco leaf, fruit, cattle, minerals, mineral waters, beer, flower, and flour.”依此分類,陳景潤教授關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論文,因不屬于視覺藝術,所以,只能是文學作品。如果將計算機軟件納入《伯爾尼公約》的保護范圍,由于軟件的特點決定它難以歸入藝術作品之類,所以,只能作為公約中的文學作品來保護。
《伯爾尼公約》的上述作品分類為世界各國著作權法所繼受。所不同的是,各國著作權法在保留文學作品分類的同時,將公約中的藝術作品分類分拆為更多的亞種。例如,美國《1976年版權法》第102條(a)款即保留了文學作品的分類,同時,將藝術作品細分為以下7類:
(1)音樂作品,含配詞;
(2)戲劇作品,含配曲;
(3)啞劇和舞蹈作品;
(4)繪畫、圖形和雕塑作品;
(5)電影及其他音像作品;
(6)錄音作品;
(7)建筑作品。d(a) Copyright protection subsi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itle, in 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 fixed in any tangible medium of expression, now known or later developed, from which they can be perceived, reproduced, or otherwise communicated, either directly or withthe aid of a machine or device. Works of authorship include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1) literary works;(2) musical works, including any accompanying words;(3) dramatic works, including any accompanying music;(4) pantomimes and choreographic works;(5) pictorial, graphic, and sculptural works;(6) motion pictures and other audiovisual works;(7) sound recordings; and(8) architectural works.
上述分類使得美國《版權法》上的作品分類邏輯清晰,體系合理。從各國著作權法來看,目前,這是一種被普遍采用的較為成熟的作品法律分類方法。
三、文學作品的“蛻變”
20世紀70年代,隨著計算機軟件業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興起,保護計算機軟件的呼聲日漸高漲。但是,在采用什么法律保護的問題上,人們意見不一。有主張以版權法保護的,可是,軟件作品是否符合美國版權法關于作品必須固定的要求,則不無疑問;也有主張以專利法保護的,但軟件作品是否符合美國專利法對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的要求,則令人生疑。經過激烈的辯論和爭論,最終,以版權法保護的主張占了上風。e自1970年至1979年圍繞著該爭議美國各種學術刊物刊載了上百篇論文。參見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A Study of Copyright in Books, Photocopies, and Computer Programs, 84 Harv. L. Rev. 281 (1970); J. P. Chandler, Proprietary Protec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U. Balt. L. Rev. 195 (1982); Duncan M. Davidson, Protecting Computer Softwar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1983 Ariz. St. L. J. 622; Pamela Samuelson, CONTU Revisited∶ The Case Against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 in Machine-Executable Form, 1984 Duke L. J. 663; Arthur Miller,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 Databases, And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Is Anything New Since CONTU? 106 Harv. L. Rev. 977 (1993); Pamela Samuelson, A Manifesto Concern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Computer Programs, 94 Colum. L. Rev. 2308 (1994); Pamela Samuelson, Why Copyright Law Excludes System and Processes from the Scope of Its Protection, 85 Tex. L. Rev. 1921 (2007); Pamela Samuelson, The Uneasy Case for Software Copyright Revisited, 79 Geo. W. L. Rev. 1746 (2011).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版權修正案》,對《1976年版權法》第101條和第117條進行了修訂,將計算機程序納入到版權法的保護范圍。從此,計算機程序成為一種新的受保護的客體。然而,這種客體究竟屬于版權法上的什么作品類型?鑒于計算機程序的特點,多數學者認為,計算機程序應該作為literary works (文學作品)來保護。f學界的這一觀點也為美國司法實踐所接受。gBrace & World, Inc. v. Graphic Controls Corp., 329 F. Supp. ( S. D. N. Y. 1971); Midway Manufacturing Co. v. Artic International, INC., 547 F. Supp. 999, aff’d, 704 F. 2d 1009 (7th Cir. 1982), cert. denied, 464 U. S. 823 (1983); Apple Computer v. Franklin Computer, 74 F. 2d 1240 (3d. Cir. 1983).
80年代后期,我國較早研究知識產權法的專家密切關注著當時美國的立法動向,在了解到美國有學者主張將計算機程序作為literary works保護時,便將literary works譯成了“文字作品”。h鄭成思:《版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頁。后來,在概念法學的驅使下,又有人推斷出“口述作品”與之呼應。為此,1990年我國制定《著作權法》時規定了“文字作品”和“口述作品”。在“文字作品”和“口述作品”之外,又規定了其他六類作品,外加一兜底條款,以防掛一漏萬。i《著作權法》(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2001年第一次修改,2010年第二次修改,第三次修改正在進行中。)第3條,本法所稱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創作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樂、戲劇、曲藝、舞蹈、雜技藝術作品;(四)美術、建筑作品;(五)攝影作品;(六)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七)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計算機軟件;(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這種作品分類特色鮮明,在世界各國著作權法中獨樹一幟。《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只是在原有基礎上作了微調,《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刪除了“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的規定,增加了“其他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新的兜底性規定,把“計算機軟件”作品改為了“計算機程序”作品,作品類型從8種擴大到15種,接近翻番。j《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2012年7月國家版權局公布,國家版權局官方網站 http∶//www.ncac.gov.cn/ chinacopyright/contents/483/17753.html 。這種作品分類方法仍然繼續重疊,繼續矛盾,繼續邏輯混亂。
顯而易見,“文字作品”和“口述作品”,是以作品的表現形式,即以作品是否固定為標準而劃分的。但是,以此標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劃分出其他6類作品來。顯然,這6類作品的劃分是以作品內容為標準的。可見,在作品分類上,我國《著作權法》采用了雙重標準,即作品的表現形式和作品的表現內容。
由于立法的認可和介入,學界將literary works翻譯為 “文學作品”的百年傳統從此被打破。本文將從語言學和英美立法等不同視角探尋literary works的真實含義,以期正本清源,消除誤解。
四、文學作品“蛻變”的原因
如上所述,《伯爾尼公約》與各國法律中的文學作品是一個法律概念,它與文學本身并無必然聯系。然而,早期學者并未能將其理解為一個法律概念,他們不能想象計算機軟件如何能與文學作品聯系起來。于是,將計算機軟件所屬之作品種類literary works翻譯成“文字作品”。“‘文字作品’中的‘文字’二字,在英語中與‘文學’(literary)相同,但在法語及西班牙等語種中,則與‘文學’不同。這經常使翻譯英文版的版權法專著或法條的人感到棘手。確實,英文中的‘文學作品’,有時應譯為‘文字作品’。”k至于“有時”應為何時,此處,論者并未給出明確答案。這樣,我國著作權理論界便出現了一種新的作品類型——“文字作品”(literary works)。不過,毋庸諱言,這一翻譯的錯誤是明顯的,理由如下。
首先,從語言學上分析,英文literary的含義中沒有相當于漢語“文字的”或“書面的”含義。lLiterary的含義有:1.pertaining to or of the nature of books and writings, esp. those of classed as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2.pertaining to authorship∶ literary style.3.versed in or acquainted with literature∶ well read.4.engaged in or having the profession of literature or writing∶ a literary man.5.preferring books to actual experience∶ bookish. 具體參見Random House Kernerman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K Dictionary Ltd, 2005), p. 1640。
其次,漢語“文字的”對應的是“口頭的”,漢語“文字的”對應的英文是written而不是literary;漢語“口頭的”對應的英文是oral;英文中,written而不是literary對應oral,如英美侵權法中的libel (書面誹謗)對應slander(口頭誹謗),合同法中的written contract (書面合同)對應oral contract(口頭合同)。正因為不了解上述“文字的”來龍去脈,所以,《著作權法》官方譯文便將“文字作品”譯成“written works”。這樣,written works與oral works便真的對應起來。可惜,我國著作權法上的“文字作品”譯自英文literary works而不是written works。可見,一步錯,則步步錯。
再次,將literary works(文學作品)譯成“文字作品”,常常使人陷入邏輯上的矛盾。比如:“有的國家認為,口述作品也屬于文字作品一類,只不過它是以語言形式(而不是文字形式)表達出來的。”mm 鄭成思:《版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頁。但常識告訴我們,口述作品之所以是口述作品,是因為它不屬于文字作品;文字作品之所以是文字作品,是因為它不屬于口述作品。口述作品與文字作品是兩種相互排斥的作品類型。依據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一件作品如果是口述作品,則不可能同時又是文字作品,反之亦然。但是,如果將此處的“文字作品”換成“文學作品”,即“有的國家認為,口述作品也屬于文學作品一類,只不過它是以語言形式(而不是文字形式)表達出來的”,則邏輯矛盾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口述作品與文學作品是根據兩種不同標準劃分的,所以,一件口頭作品完全有可能是一件口述的文學作品。
最后,那些將literary works翻譯成“文字作品”的學者除了不能想象“冷冰冰的”n王遷:《知識產權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版,第66頁。計算機軟件可以是文學作品以外,并未給出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更未提及過英美是如何理解或者解釋這一英文術語的。因此,從英美版權法和《伯爾尼公約》的角度來考察其真實含義,更具可信度和權威性。
美國《1976年版權法》第102條將作品分為文學作品等8類。在該條的立法史和說明中,美國國會特別解釋了literary works一術語。“文學作品”一術語不意味著衡量文學價值或質量的任何標準。它既包括價目表、電話簿和類似的事實作品、參考資料或說明書及數據匯編,也包括計算機數據庫和計算機程序,但因計算機數據庫和計算機程序,不同于程序員的原創思想本身,構成對其原創思想的原創性表達者為限。oRobert A. Gorman, Jane C. Ginsburg, Copyright for the Nineties, The Michie Company, 1993, p. 92; NO. 94-1476, 94th cong., 2nd sess. (1976).
與美國《1976年版權法》一樣,英國《1988年版權法》也有literary works(文學作品)的分類。該法給出的定義是:文學作品被界定為以文字、說、唱形式體現的除戲劇或音樂作品以外的任何作品。pTina Hart & Linda Fazzani,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nd ed.), p.142. “A literary work is defined in the 1988 Act as any work, other than a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which is written, spoken or sung.”很明顯,這里的literary works指文學作品,原因很簡單,以說、唱形式是不可能創作出“文字作品”來的,但說、唱產生文學作品,卻絲毫不令人意外。
1993年以前,在《TRIPS協定》制定過程中,已經修改國內著作權法保護計算機軟件的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要求將計算機軟件作為《伯爾尼公約》所保護的一種作品,納入《TRIPS協定》的保護范圍(原因是《伯爾尼公約》是版權領域中最重要一個公約,其1971年文本是公約各文本中參加國最多的一個)。可是,計算機軟件作為公約中的何種作品保護呢?根據軟件作品的特點,很難將其列為“藝術作品”。于是,只能歸入“文學作品”范疇。因此,《TRIPS協定》第10條明確要求WTO成員將計算機程序,無論源碼還是代碼,作為《伯爾尼公約》(1971年文本)中的“文學作品” (literary works)來保護。q參見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與中國 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編:《 知識產權國際條約集成》,清華大學 出版社2011年版。“Computer programs ,whether in source or object code ,shall be protected as literary works under the Berne Convention(1971).
由以上分析可見,將literary works翻譯為“文字作品”,實是受“常識”之誤導,將這一法律概念與日常生活中人們所談論的“文學作品”不加區分,混為一談。
結 語
受將literary works(文學作品)翻譯成“文字作品”的,不少學者將英美國家版權法中的literary works也翻譯成“文字作品”。r參見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編:《十二國版權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更有學者以此類推,將《TRIPS協定》所援引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中的literary works翻譯成“文字作品”。ss 參見馮曉青:《著作權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編:《知識產權國際條約集成》,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這一翻譯徹底顛覆了學界在此問題上的百年學術傳統。假如將literary works(文學作品)誤譯為“文字作品”,只是在學界流傳,也只是一個學術問題,如今,情況不同了,它已深深影響到我國《著作權法》立法。為了學術的求真和立法的完善,建議:
1.將literary works譯為“文學作品”;
2.廢除《著作權法》中“文字作品”與“口述作品”的分類;
3.以文學作品取代“文字作品”,這樣,諸多口述作品和計算機軟件等便可納入其中;
4.在作品分類條款中,增加“本法所保護的作品不以固定為條件(前提)”;
5.以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的表述代替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表述,以避免陷入先有三類作品后又出現多類作品的矛盾和尷尬。t《著作權法》的模糊規定導致我國學界在作品分類問題的認識上出現嚴重分歧,有持“三類說”的,參見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也有持“八類說”的,參見王遷著:《知識產權法教程》,中國人民法學出版社2011年第3版;還有持“九類說”的,參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甚至認為作品分類不止九類的也有,參見李明德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經過以上修改,由于有了文學作品的分類,許多作品類型便可歸入其中,著作權法上的作品分類將大大瘦身,同時還可遏制作品種類在修訂草案中不斷擴張的不良勢頭。這樣,我國著作權法上的作品分類標準便趨于統一,從而條理清晰,邏輯順暢,體系合理,這完全符合國際上作品法律分類的通行做法。
The Berne Convention classifies works into two categories: literary works and artistic works, although works differ in thouands of ways in reality. In1980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incorporated computer programs as literary works into their respective copyright law. During the Uruguay Round trade negotiation, the TRIPS agreement, insis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requires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WTO protect computer programs as literary works under the Berne Convention. Disappointingly, academia in China did not understand the term “literary work” as a legal term, and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a “literary work” had nothing to do with literature. Accordingly, they intentionally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 as “written work” to include computer programs. Subsequently, driven by the mechanic jurisprudence, “oral works” was inferred from the translation. Misled by this, the Chinese Copyright Law classifi ed works by applying two different criteria: the form and the content. As a result, the classifi ed categories are overlapped and contravene with each other. No logic or rule can be discerned from the classifi cation.
copyright; literary works; classifi cation of works
孫新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李偉民,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