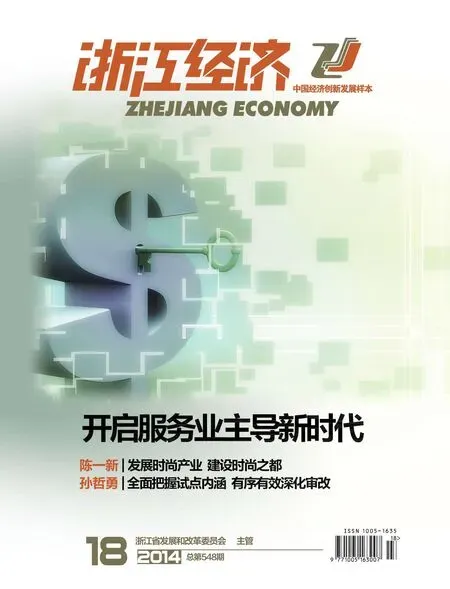現實而無奈的選擇
作為一種妥協和過渡,所謂的“三不變”,正是一種無奈的卻又是現實的明智之舉
8月28日下午,杭州市召開專題工作會議,調整大江東產業集聚區體制,正式設立大江東黨工委、管委會,作為杭州市委、市政府的一個派出機構,托管蕭山區河莊、義蓬、新灣、臨江、前進5個街道的行政管轄區域,對大江東區域統一履行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各項管理職能,負責域內各派出機構、分支機構的協調管理。即便是已經決定大江東的財政權、人事管理權獨立于蕭山區,但還是重申了蕭山區對其原有的行政區劃不變、司法管轄不變、匯總統計也不變(“三不變”)。這顯然是一個帶有漸進意義的體制變動,但也是一個現實而無奈的選擇。
類似的體制變動,從歷史和宏觀的角度來看,其實無非為兩種選擇:一種是在傳統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上頭一聲令下,說變就變了,平調就平調了,“歸大堆”也沒啥了不起的。既沒有這么多的利益考量,也沒有那么多的討價還價。既然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系,由得你來說三道四、推三阻四的嗎?那個時代,也不是沒有管理體制上的變動,但有的話,也是無條件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
一種是在現代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政府已轉型為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型的政府,抓經濟建設特別是抓GDP,并不是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務和政府官員的主要政績所在。老百姓只要宜業宜居、生態良好、社會安全,其他的并不要求更多。官員在那種情況下,或許也會對由行政區劃調整帶來的產值、稅收之類的排名下降,表現得坦然淡定。
但尷尬的是,我們正好處在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期中,或謂搞了市場經濟但還未建成現代市場經濟。既然經濟建設是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又通行了物質利益原則,那行政管轄權和GDP就非同小可。經濟總量大小多少,總是和一級組織的管轄權乃至官員的行政級別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因此,調整體制和區劃帶來的影響,也就比較敏感。作為一種妥協和過渡,所謂的“三不變”,正是一種無奈的卻又是現實的明智之舉。
在人類社會的城市化進程中,大量的農村人口變成城市人口,必然伴隨著大量的農業用地轉為城市用地,由此城市的面積增多、空間擴大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從城市化發展的經驗來看,攤大餅式的城市擴張,也會帶來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空氣污濁、生態惡化等一系列城市病,對此也不可不察,更不可不防。因此,中央也提出來單個城市的發展要有邊界,而城市群才是城市化發展的主體形態。這也就意味著,大城市可以是由多個大中小城市,類似葡萄串那樣結合在一起的城市集合,而不一定都非要把傳統主城區以外的其他衛星城市,統統一網打盡,劃定為我的一個主城區。這種情況,就像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很多大城市,其實就是由大大小小幾十個乃至上百個市組成的城市群。只要你核心城市、首位城市有足夠的輻射力、影響力、帶動力和凝聚力,人家照樣會把自己榮幸地叫作大紐約、大巴黎。
一般意義上說,既然財權和人事權已經“獨立”,所謂的“三不變”終歸是要變的。盡管不能一蹴而就,“一鍬挖成一口井”,但過渡的時間也不可拖得太久。早在上世紀末杭州的發展由西湖時代邁入錢塘江時代之際,我們就不但新設了濱江區,還同時將蕭山和余杭由兩市改成了杭州市的兩區。結果十來年過去了,蕭余兩區還是和杭州市的老城區并非同一體制。這個過渡期,恐怕也就過長了。如果當初就想到消化不了這么大的一塊總量(無論是國土空間還是經濟社會),那就不要簡單地把整個區域統統劃入,需要多少就劃定多少。而被調整的區域,也不必總是糾結于“吃肉要搭骨頭”的心態,非要扳牢“一個都不能少”,不是整體進入就干脆“免談”。
說一千道一萬,上層建筑都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或許正是覺得大江東原有平臺過多、主體過多,憑空生出來諸多無謂的同質競爭和過度競爭,領導層才下決心動體制以促成空間連片、產業相近的427平方公里一體化發展的。我們樂見“一個平臺、一個主體”的新體制,能夠充分展現出其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格外的積極作用,從而促成有關各方的心悅誠服、互利共贏。
——《篳路藍縷:計劃經濟在中國》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