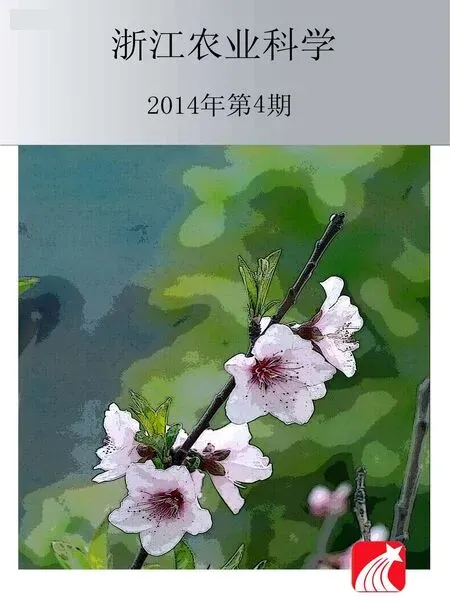宿州市家庭農場發展的探討
柳建國,徐志連,王崇志,梁西陳
(1.宿州職業技術學院,安徽 宿州 234010;2.安徽省宿州市現代農業辦公室,安徽宿州 234010)
宿州市家庭農場發展的探討
柳建國1,徐志連2,王崇志1,梁西陳1
(1.宿州職業技術學院,安徽 宿州 234010;2.安徽省宿州市現代農業辦公室,安徽宿州 234010)
家庭農場是未來我國現代農業主要形式之一。通過對宿州市家庭農場發展的分析,提出家庭農場家庭土地規模閾值、家庭農場準入條件和政府角色定位。
家庭農場;規模閾值;準入條件;政府角色定位;宿州
家庭農場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美國由于土地可以私有化,在開發西部過程中,許多淘金者紛紛加入了西部土地的購買與經營活動,這是美國家庭農場形成的基礎和雛形[1-2]。我國家庭農場最早出現在20個世紀80年代[3],建立了以家庭農場為基礎, “大農場套小農場” “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4]。我國最早出現的農場,確切地說是農墾區的民營農場,21世紀初家庭農場才真正出現,我國民營農場或家庭農場與國外家庭農場的根本區別在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我國的民營農場在土地性質上仍然屬于國家或集體所有,而西方國家的土地則歸私人所有。這一差別決定了我國家庭農場與國外家庭農場要走不同的發展道路。2010年8月,宿州市埇橋區被農業部批準為第1批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宿州市委、市政府決定,按照埇橋區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要求在全市同步推進。2011年11月,宿州市被農業部批準為第1批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側重于生產力的發展,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側重于生產關系方面的探索創新,試驗重點為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因此探討適合宿州發展的家庭農場道路十分有意義。
l 現狀
家庭農場是宿州市培育三大經營主體的創新點,2012年9月市委市政府制定下發了 《宿州市家庭農場認定管理暫行辦法》,對家庭農場進行了定義,對不同產業的大型、中型、小型家庭農場設定了標準,對家庭農場認定程序進行了規定,選擇條件較好的各類專業大戶,扶持建立家庭農場。《宿州市家庭農場認定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家庭農場根據類型分為種植業和養殖業 (種植業包含糧油生產、設施農業、特色種植,養殖業包含家畜和家禽養殖以及水產養殖、特種養殖),每種類型分為小型、中型、大型家庭農場。明確了 “家庭常年在農場勞動人員須在2人以上,土地集中連片,規模適度,使用機械化、標準化操作,從事養殖的家庭農場須取得 《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土地流轉年限不得低于5年”的準入條件。市政府出臺扶持意見,加大家庭農場土地流轉獎補。優先安排承擔各類農業項目,優先安排國家各類支農補貼,市、縣區級財政及各類資源予以傾斜扶持。對實行標準化種植的聯合體家庭農場連片流轉土地在6.67 hm2以上的,每0.067 hm2獎補200元,連補3年,分年度兌現。對從事設施農業、養殖、特色種植等產業被認定為中小型和大型家庭農場的,分別給予一次性獎補3萬元和5萬元。對每年評選出的“十佳家庭農場”給予一定的資金獎勵。
截至2013年10月,宿州市已認定種植、養殖及特色農業家庭農場1 247家,其中大型74家、中型613家、小型560家 (圖1)。碭山、蕭縣、靈璧和泗縣4個縣大型農場較少,中、小型農場較多,大中小農場數量比例接近;埇橋區則為中型農場較多,大型和小型農場較少,顯然是受現代農業核心區有關政策的影響,因埇橋區是現代農業核心區,這也從另一角度反映政策對家庭農場發展的影響。

圖1 縣區家庭農場數量分布
2 面臨挑戰
2.1 科技含量不高,管理水平低
宿州市家庭農場經營管理科技含量不高,突出表現在2個方面,一是經營品種科技含量不高,家庭農場多為常規品種的種植或養殖,特色種植養殖品種少;二是經營理念缺乏先進性和創新性。據不完全統計,家庭農場經營者95%以上為農民,極少數為大學生,文化水平不高,專業知識缺乏,使農場的管理理念和經營理念都很難做到與時俱進。據對613家中型農場申報資料統計,高中以上(含高中)文化水平者為63人,只占經營者的10%,系統學習過農業專業知識的人更少。
2.2 規模經營風險大,啟動資金缺乏
規模經營主體生產成本中包含了土地流轉費用,成本一般在每季1.2萬元·hm-2,從事糧食生產的家庭農場及專業大戶正常年景在支付土地租金以后利潤在0.3萬~0.6萬元·hm-2,遇到大災年可能導致家庭農場破產。糧食生產的政策性保險保額低,小麥、玉米、大豆絕收的情況下只能賠付0.405萬、0.375萬和0.255萬元·hm-2,其他農作物尚未納入政策性保險范圍。
宿州市是農業地區,農民惜地心理重,流轉價格偏高,一般以每年13.5~15.0 t·hm-2小麥折價。家庭農場需要先付土地租金才能種地,如果流轉33.3 hm2土地,連同購買生產資料就需要80萬元流動資金,一般農戶家庭難以承擔。
2.3 基礎設施薄弱,抗風險能力差
傳統一家一戶經營模式導致土地分散,土地連片流轉后,種植農場缺少水利、曬場、倉庫等基礎設施。現在的農田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設計規模較大,一般要求萬畝連片,一般家庭農場達不到。由于家庭農場達不到項目設計的規模,就使得家庭農場的基礎設施失去項目資金資助的機會。養殖農場初期投入巨大,資金不足,配套基礎設施就很難到位。農場的抗風險能力差。
3 問題探討
3.1 家庭農場規模
家庭農場具有適度規模經濟效應,它能實現生產力釋放與風險控制的相對平衡[5]。
適度規模體現在2個方面,一是區域內家庭農場要有適當的數量,太少不好,太多也不好,一個區域內需要多少家庭農場,與區域土地面積和經濟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二是家庭農場規模要適度,我國的家庭農場和西方的家庭農場經營模式有所不同,在我國不可能出現經營上萬公頃土地的家庭農場,這是由我國人多地少及土地公有制的國情所決定的。我國的人地關系不適合發展過大規模的家庭農場,要兼顧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產出率,把握好土地經營規模 “適度”,農場規模的大小與從業者素質、業務知識、所在區域人口密度密切相關。
羅艷等[6]對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區的家庭農場運用模型計算出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面積為2.30 hm2,戶均8.40 hm2時,達到較合理的家庭農場規模。袁賽男[5]提出 “根據我國農業部對當前條件下種糧大戶或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模劃分,一般是北方一季種植的適度規模為80 hm2,南方兩季種植的適度規模為40 hm2”。
據農業部中國家庭農場2012年現狀報告,全國家庭農場平均經營規模13.347 hm2,是全國承包農戶平均經營耕地面積0.500 hm2的近27倍。其中,經營規模3.333 hm2以下的有48.42萬個,占家庭農場總數的55.2%;3.333~6.667 hm2的有18.98萬個,占21.6%;6.667~33.33 hm2的有17.07萬個,占19.5%;33.33~66.67 hm2的有1.58萬個,占1.8%。
土地經營的規模和期限影響家庭農場的發展。家庭農場大部分土地是通過流轉得來的,流轉土地的穩定性就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家庭農場每年經營的土地規模變動太大,顯然是對農場經營極端不利的。土地的流轉如果是短期的,家庭農場就難有專心經營的積極性,也很難做長期的投資,這對于農業生產是不利的。家庭農場在流轉土地時,需要戶戶做工作,戶戶簽合同,一旦遇到一戶不愿意流轉的,就會前功盡棄,成本很高。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家庭農場只有通過適度規模經營,才能靈活應用先進機械設備、信息技術和生產手段,才能夠大幅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就現階段而言,宿州市應以發展中小型家庭農場為主,隨著城鎮化的進程推進,農民越來越多地轉移到城市,那時再大力發展大型家庭農場。
3.2 農場準入制度
現在各地對家庭農場的理解很混亂,有些地方的家庭農場動不動就是幾千上萬畝的土地規模,實際上這些都是資本雇工農業,真正的家庭農場反而沒有注冊登記。
各地家庭農場的準入條件不同,全國缺乏統一準入標準,《宿州市家庭農場認定管理暫行辦法》規定 “家庭常年在農場勞動人員須在2人以上,土地集中連片,規模適度,使用機械化、標準化操作,從事養殖的家庭農場須取得 《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土地流轉年限不得低于5年”。準入制度中對經營者的學歷、業務能力均未做要求,從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家庭農場經營方式和可持續發展。倪坤曉等[7]認為農場文化層次 (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5年)、技術水平低,雇工的勞動處于簡單的重復操作階段,無法提高生產效率是當前家庭農場存在的突出問題。建議對家庭農場主資格在學歷、專業知識方面設置門檻,現階段設置初中以上學歷,取得職業農民資格,以后逐步提高對學歷的要求,并且建立業務知識培訓提升制度。準入制度中對土地流轉的年限要求也偏低,5年時間一晃而過,影響經營者對土地的投入,導致短期行為,加之土地重新流轉難度很大,主體成本增加,挫傷家庭農場主的積極性。建議土地流轉年限增加到8~10年。
3.3 市場主導作用
一些地方,親戚朋友之間搞個假流轉協議,也申報了家庭農場,目的就是能得到政策扶持。這反映一個很大的問題,一方面家庭農場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另一方面規范認證和管理亟待加強。政府對家庭農場的培育不能操之過急,定指標定任務十分有害家庭農場的培育,中、大型家庭農場必須有自己的產品品牌,而且是質量、口碑很好的品牌,充分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過分強調政府補貼或者采用行政手段推銷家庭農場的產品不利于家庭農場的健康發展,是政府不明智的做法。
對家庭農場而言,政府要做的是加大資金扶持的力度、引導考核的力度、公平公正的信譽度、政策保障的力度。
[1] 李志遠,李向紅.美國的家庭農場制給予的啟示與我國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創新 [J].經濟問題探索,2006(9):64-68.
[2] 何多奇.19世紀美國西部家庭農場制度與傳統農業轉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9(4):26-30.
[3] 郭亞萍,羅勇.關于新疆地區家庭農場的思考 [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9,30(2):199-202.
[4] 王景盛,劉巧英.長治市家庭農場 (種植大戶)發展狀況調查 [J].山西農業科學,2013,41(9):995-998.
[5] 袁賽男.家庭農場: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路徑選擇[J].南方農村,2014(4):4-9.
[6] 羅艷,王青.基于小農戶制現狀探索家庭農場制及其規模[J].湖北農業科學,2012,51(6):1281-1283.
[7] 倪坤曉,沈月琴.浙江省慈溪市家庭農場發展現狀的調查分析 [J].浙江農業科學,2012(11):1583-1586.
(責任編輯:張才德)
F 306.1
:A
:0528-9017(2014)04-0604-03
文獻著錄格式:柳建國,徐志連,王崇志,等.宿州市家庭農場發展的探討 [J].浙江農業科學,2014(4):604-606.
2014-02-12
安徽省宿州市政府重點項目 (13SZXDNY02)
柳建國 (1962-),男,安徽宿州人,副教授,博士,從事三農問題和區域經濟發展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