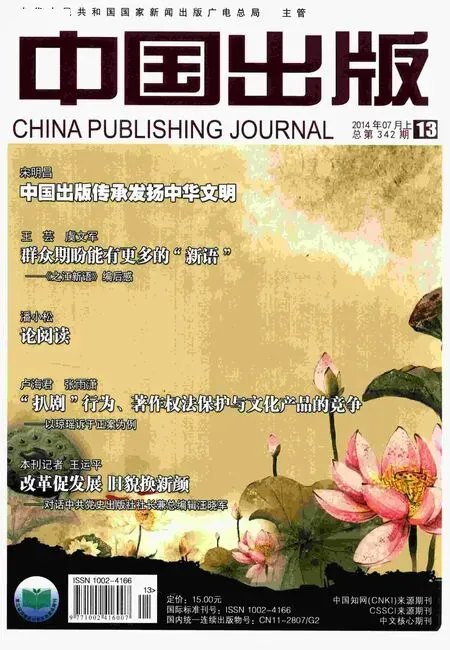民族文化文本形態探究與出版創新
文/曹維瓊 張忠蘭
民族文化文本形態研究,是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出版的核心內容。收集、整理、判斷、選擇民族文化文本,是做好民族文化出版的基礎工作,也是做好民族文化出版的重要環節。民族文化文本形態探究的目的,是梳理民族文化的各種文本形態,摸清民族文化的出版資源,分析民族文化文本的讀者對象,思考民族文化文本的呈現形式,實現民族文化出版內容的深化和表現形態的創新,推進民族文化走出去。本文嘗試探究民族文化文本形態與出版創新。
一、民族文化文本形態的探究
文本,一般是指語言文字的書面表現形式,或各種材質記載的文字材料,即任何由書寫所固定下來的話語。本文探討的文本,不是文體學所指的“作品的表層結構,一系列語句串聯而成的連貫序列”,也不是語言學所說的“語言符號以及由它們所組成的詞、句子和段落章節”,而是從出版學的角度討論文本形態。具體地說,是從出版學的角度探討我國少數民族中有語言而無本民族傳統文字的文本形態。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燦爛的文化,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對民族精神的延續、族群的凝聚、國家的和諧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各種文本形態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對民族文化的傳播和傳承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長期的民族文化出版實踐過程中,民族文化文本形態大致可以分為3 類。
其一,民族民間口傳文體文本,主要指在民間流傳的歌謠、傳奇、故事等,這是民族文化文本的基本形態,這種文本傳播范圍較廣,但是顯得較為零散。在我國各少數民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有自己的民族語言而沒有本民族的傳統文字,在較長的一個時期內,主要是民族文化工作者通過田野調查、收集各種口傳文體文本。在少數民族聚居的省區,都已整理出版過大量的民族民間口傳文體的文集和調查報告。通過多年的收集、整理、研究,民族民間口傳文體文本整理取得豐碩的成果。這些珍貴的資料,是民族文化傳承的寶貴財富,是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們進行民族文化文本出版的主要資源。
其二,民族口傳文化元典,主要指在少數民族上層和知識分子中傳播傳承的史詩、巫辭、祭辭、理辭等,這是民族文化文本的主體形態,這一文本形態相對系統和完整。口傳文化元典,由于長期只為少數民族的一定階層所掌握,只在一些特定的重大節慶活動或儀式上誦唱,口傳文化元典的傳承人的選擇、傳授地點和傳授方式有相當嚴格的規定,其傳播、傳承具有濃厚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因此不為大眾所知。語言阻隔也是人們對民族口傳文化元典了解不多、研究不深的一大障礙。掌握民族口傳文化元典的歌師、寨老、巫師們,有相當一部分不識漢字,但是,他們對民族口傳文化元典的掌握卻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民族口傳文化元典是民族文化源頭性、母體性、衍生性的經典,是民族文化的根,是民族精神的基元。民族口傳文化元典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其中所蘊含的哲學意識、道德觀念、生活準則和藝術修養,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的源泉,是生命的創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對民族文化的接續,對人文精神的弘揚有著重要影響,對培育民族的優秀精神品質有非常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民族口傳文化元典中蘊含的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的過去,也孕育著民族的未來,起著族群識別、認同、凝聚作用。由于各種原因,民族口傳文化元典的整理研究長期被忽略。
其三,少數民族的各種表意文化事相,主要指民族服飾、紋樣、歌舞、圖案、建筑等,這是民族文化文本的重要形態。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服飾、建筑、歌舞等文化藝術形式。我們常說“服飾是穿在身上的史書”“舞蹈是形體展演的史詩”“建筑是凝固的史詩”“儀式是流動的史詩”等就是指這些文化藝術形式具有表意敘事的功能。但是,在民族文化研究中,我們很少把各種表意文化事相當作文化文本形態來看待。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特殊文本需要轉換形式,必須有行家進行解讀,一般人才能看得懂。《說文解字敘》說:“文者,物象之本。”古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說的就是物象敘事功能。古人的文本概念是寬泛的。其實,生活中具有表意敘事功能的物象語言符號,或類語言符號都是文本。一組符號、一組圖案、一組動作,有序地組合排列,就可以稱其為文本敘事。轉換探索民族文化文本形態的視角,這類文本必須重視。
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不是用一種或幾種文本形態就可以概括的,民族文化內容無窮,文本記載也可以形態無窮。文本的含義豐富而不易界定,如果能夠正確對待、合理利用,將為出版的選題來源和內容拓展提供廣闊的空間。
二、民族文化文本內容的分層釋讀
民族文化文本的整理,是為了更有效地對少數民族文化進行研究、傳承和傳播。民族文化是通過各種渠道傳播、各種手段傳承的。出版人應該根據文本的內容,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當代釋讀,為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讀物。
民族文化文本的收集整理,是服務于民族文化研究的。民族文化文本的整理研究成果大多是以漢語表達,其整理者的民族語言能力和釋讀能力是一大難題。新中國成立后,一批民族學者的培養,特別是一批既懂民族語言文字,又經過較好的漢語訓練,具備民族文化研究能力的學者隊伍的形成,為民族文化文本的系統整理提供了可能,為民族文化文本出版創造了條件,為民族文化文本精品打造搭建了平臺。
民族文化文本的收集整理,是服務于民族文化傳承的。民族文化的傳承,要從青少年抓起,幫助他們從小就學習民族文化,熟悉民族文化,最終能夠掌握民族文化,傳承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教育是有別于知識教育、品德教育、技能教育的一種教育形式,具有特殊的價值。民族文化傳承的主體是廣大的青少年。文本整理時,要選擇適宜青少年學習的文本內容,將它改編、改寫成青少年喜歡的文本形式。民族歷史和民族英雄成長的故事,以動漫形式展示最為青少年喜愛。
民族文化文本的收集整理,是為了服務于民族大眾的。民族文化起源于民間,其整理研究,必須滿足人民大眾的民族精神文化需求。民族文化如果不被大眾知曉,不為大眾喜愛,這種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能長久地傳播的,民族文化的通俗化和普及尤其重要。
民族文化文本的收集整理,是為了將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作現代性的釋讀和轉化。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釋讀,古人有古人的訴求,今人有今人的意境,我們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去偽存真,讓優秀的民族文化傳承于現代,服務于當代。
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基元。保護民族文化,就是保持民族的發展,凝聚民族的團結,維護國家的穩定。民族文化文本的現代性釋讀,對養成民族精神會起到非常直接的、深刻的作用。各民族都有豐富的文化積淀和文化內涵。民族文化是豐富多彩的,我們總能從每一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形態中,找出其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主題;民族文化的文本表現形態多種多樣的,同一主題,特別是具有母體性、典型性、衍生性特征的主題,我們總能從多種文本形態中找到共同的表達;民族文化的接受者是多種層次的,同一主題內容會有多重釋讀的需求。針對不同的讀者群體需求,出版人可以對同一主題的不同文本形態進行有機整合釋讀,還可以對同一主題的同一文本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釋讀。民族口傳文化元典的整理尤其應該如此。
圍繞民族文化文本可進行多種研究,多層釋讀,多重利用。民族文化元典文本,是民族核心價值的根基,承載著民族的精神。對民族文化元典性作品的整理保護利用,應形成合力,對同一主題多層次釋讀,多媒體形態呈現,用重大主題引導精品生產,打造多形態、多層次精品叢書,形成多個文本精品簇擁主題,烘托主題,擴大影響。
通過對民族歷史上形成的哲學的、道德的、政治的觀念,或者是社會風俗習慣,或者是音樂的、舞蹈的、繪畫的藝術形象,或者是凝結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審美觀念現代性釋讀,使之內化為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精神,成為民族持續發展的動力。
三、民族文化文本出版形式的創新
民族文化傳播傳承需要有一個物的載體,需要用一個有形的平臺來展示。民族文化能夠廣為傳播和持續傳承的載體和平臺,就是各種文本形式。
早在文字誕生以前,人們就已經有了各種文本記載形態。在不同文明時期,伴隨著文明進步,人類創造了多種文本形態。從用形體動作交流,到聲音語言溝通,再到符號文字發明,各種質地材料的文字文本出現,人們的思想、情感、認識和智慧得以用文字文本的形式傳播傳承,文明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程。
文字文本使人們得以根據文本反復揣摩、反復研讀、反復體會文本作者的文外之意。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文字文本主要有石刻文本、甲骨文本、金屬文本、竹簡文本、木簡文本、布帛文本、紙質文本。中華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體現在民族文化資源的豐富,體現在民族文化文本形態的多樣。
造紙術的出現,印刷術的發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大進步。印刷術使文字文本的復制變得容易了,文化可以在更大的范圍,以更快的速度傳播傳遞,更多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分享文明成果,人們的交流有了更好的平臺,同時也為文化積淀和傳承奠定堅實的基礎。
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數字技術飛速的發展,人們對文本形態的認識發生了顛覆性改變。今天,出版人既肩負著探究傳統文本形態的責任,又面臨著創新當代文本形態的挑戰。
新技術的發展使新形態文本層出不窮。但是,無論文化如何發展,民族文化出版的文本形式,仍然可以用文字文本、圖文文本和視聽文本等來歸類。
文字文本是民族文化出版的基本形式。這是最傳統的,也是主體的文本形式,民族文化出版主要采用這種文本形式。為便于民族文化的傳播傳承,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文字文本常采用民族語言和漢語雙語讀本的呈現形式。
圖文文本是民族文化出版的重要形式。在無本民族傳統文字的少數民族中,各種表意文化事相是民族文化的主要文本形態。音樂、繪畫、服飾、建筑是最富于民族特征的表意文化形式,是民族審美意識、審美情趣、審美觀念的集中體現,圖文文本出版物是釋讀民族文化的重要呈現形式,它可以文圖互動,圖文互補,提供了民族文化的直觀圖像,為瀕危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文化生態記錄的空間,容納了大量的文化生態學信息,保存了文化生態學的現實內容,為民族文化的復原提供了基本素材。有利于人們對民族文化進行文化生態的觀察,有利于我們觀察和認識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
視聽文本是數字出版形態的文本轉換。視聽文本使文字實現可聽,圖像變為可視。特別是多媒體印刷讀物(MPR)技術的廣泛應用,使民族文化圖書出版,既保留傳統紙質圖書的優點,照顧了人們傳統的閱讀習慣,又創新民族文化傳播模式,構建民族文化傳承體系。可視聽圖書的出現,將會使民族文化出版跨上一個新臺階。
民族文化文本還可以有其他各種形態。可以采取設計師用民族審美設計最鄉土特色的藝術作品,手藝人用傳統技藝做精美的工藝物件,研究者用田野調查做最真實細致的文本敘事,出版家用技術手段做綜合立體的文本形式,充分吸納民族工藝中的審美結構樣式,融合利用民族文化中的物象圖案元素,交流互動,創新文本形態,尋找傳統文化、傳統工藝、傳統審美和現代出版結合的傳播路徑,實現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發展的有機鏈接。
四、出版人應該自覺承擔民族文化出版的責任
民族文化文本形態的探究,是做好民族文化出版的前提;民族文化內容的分層歸類,是拓展民族文化出版資源的路徑;民族文化文本出版形式,是出版創意的結果,是出版新技術使用的成果,亦是民族文化文本形態創新的前提。
民族文化文本形態的創新,是要滿足不同讀者群體對民族文化的閱讀需求,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內化于心,提高傳播傳承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覺和自立意識,形成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培養民族傳統文化的欣賞力。
民族文化文本形態的創新,要求出版人有廣闊的視野和獨特的視角,要勇于探索各種民族文化文本的深邃表達,在民族文化文本內容和民族傳統文化精髓中尋求創意。探討在現代化語境下的民族傳統文化出版轉型,從而探索更適應民族文化出版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弘揚民族精神,創新與時俱進的民族文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