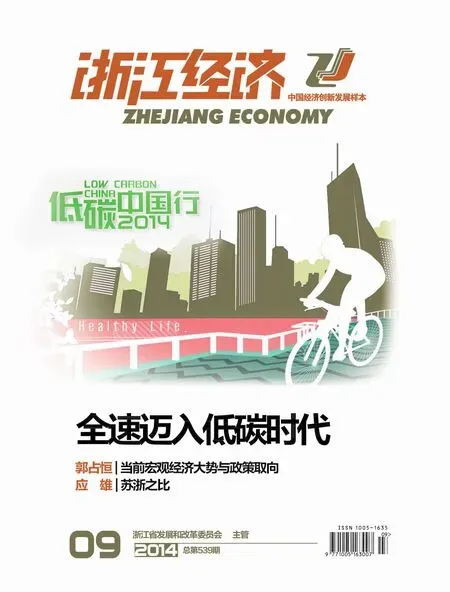換個視角看公司社會責任
金輝
換個視角看公司社會責任
金輝
對于相關利益者利益所負擔的強制性責任,在公司的視角下是一個偽概念,因為義務性的社會責任都已經被具象化的法律責任。倡導性的社會責任實質上是公司的一種經營理念,與其稱之為倡導性社會責任,不如稱之為一種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觀
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賺錢作為唯一的存在目的,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權尤其是社會權,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權利和利益。廣義的公司社會責任只不過是法定義務(責任)而已,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就已考慮了這些要素,公司遵守法律就是承擔了社會責任。至于那些法律沒有規定的事項例如公益捐贈等,純粹是一種道德倡導。換言之,公司沒有義務承擔法律法規以外的事項,但承擔法律責任外的“社會責任”可以提高社會對公司的道德評價,而承擔更高層次的自覺社會責任還能夠有效提高公司的社會競爭力,這在一定程度上能視為一種公司戰略發展手段。
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
公司社會責任包含了對相關利益者責任的考量。筆者認為,所謂對相關利益者的責任承擔其實在我國的部門法體系中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定,這可以將消費者、雇員、環境、產品質量、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置于私法、公法與社會法構成的法律框架內,從法律責任的分類出發說明這一觀點。
(一)私法責任
侵權責任——對環境、產品質量承擔的“社會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八章專章規定了環境污染責任,連同《環境保護法》、《民事訴訟法》中新加入的公益訴訟規則,對環境污染的責任與救濟已成體系。在環境污染損害與結果的因果關系證明責任移轉于污染者,且在免責事由上嚴格限定為不可抗力與受害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考慮到環境污染案件的影響廣泛性,又加入公益訴訟在救濟模式上加以改良。社會責任中要求公司考慮環境利益,其實一旦公司忽視環境利益,那么等待它的將是嚴格的法律責任。《侵權責任法》第五章專章規定了產品責任,同時產品責任是我國私法責任中為數不多的有懲罰性賠償的一種責任,且我國對產品責任中的法定責任較為嚴苛,公司對社會承擔的產品責任的要求幾乎不可能高過這些法律規定。
違約責任——對債權人承擔的“社會責任”。隨著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發展,債權人也被納入了利益相關者的范疇。筆者認為,債權人保護有自己獨有的制度,不應籠統地納入“社會責任”加以保護。債權人與公司的關系只是單純的合同關系,公司對債權人的義務也只是單純的到期還本付息,若未履行則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很難想象公司在做一項運營決策時應當如何單獨考慮債權人的利益。有學者認為,應當讓債權人列席董事會參與決策;筆者認為,股東與債權人的風險是不同的,債權人即使不能被即時清償,但企業破產時受償順序也較股東優先,既然風險不同,那么緣何又要賦予其與股東相似的權利地位呢?換一個思路考慮,在有限合伙企業中,有限合伙人尚且不能參與企業經營管理事項,讓債權人參與顯然是過猶不及。美國學者將債權人列入利益相關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的法律較為保護債權人。我國《公司法》、《破產法》在保護債權人方面已存在相應制度,力度相較美國不可謂不大,這種情況下片面學習美國以“社會責任”保護債權人頗似畫蛇添足。
(二)公法責任——對政府、社區的“社會責任”
美國企業所得稅采用的是超額累進制,在2012年調整稅率后最高稅率為28%,實際稅率一般在15%—28%之間,我國企業所得稅除政策支持等特殊情況外統一為25%,在這個數據上似乎中美并無較大差異。但因我國不采用超額累進制且私人公司以中小規模居多,而大公司一般以國企居多,如此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我國中小型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率必然高于美國。但不能忽略的是,為了避稅,美國有大量公司注冊地并不在美國,而設在如巴哈馬、百慕大等低稅率或零稅率地區,作為跨國公司其承擔的稅率僅為15%左右。對于那些因稅制不完善而逃避法定繳稅責任的公司,也只能通過“社會責任”這一道德概念期冀其承擔相應責任。但這并非一種好的方法,福利經濟學認為通過所得稅制度實現分配公平都比其他社會政策要好,與其讓公司承擔一些內涵模糊的“社會責任”,不如通過稅收直接由政府統一調配。即使反對福利經濟學的觀點,至少有兩點是無可非議的:一是公司在交稅的過程中已經承擔了對政府、社會的責任,這種責任也是法定的,而非“社會”的;二是中國的公司通過多繳納稅款(相對于美國)已經履行部分的公益性責任,因為政府財政總有一部分是投入公益的。
(三)社會法責任——對雇員、消費者、中小競爭者的“社會責任”
對于雇員的責任,《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等作出了細致的規定,這些規定往往具有保護勞動者的立法傾向,而對于消費者責任也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加以規制。在對于中小競爭者方面亦有《反不當競爭法》、《反壟斷法》加以保障,違反這些法律,公司將承擔法律責任,這些規范均是公司運營中不可逾越的紅線。
公司無形資產投資與社會責任
美國有一種工具性觀點認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長久盈利之間具有聯系。Roman(1999)等人在對Griffin Mahon(1997)研究結論分析的基礎上,發現51個實證結果中有32個是正相關、14個不顯著、5個負相關,結論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于實現企業常青意義重大。這種觀點試圖從公司自身出發考慮社會責任的必要性,但在筆者看來,履行一項責任如果能為公司長期發展帶來好處,那么它就不是一項責任,而是一筆投資。為說明筆者觀點,試從人力資源與商譽兩個角度予以論證。
——人力資源。雖然人力資源的價值難以有效計量,但是即便如此,還是不能忽略人力資源對于公司發展的巨大作用。從鎖定人力資源來看,僅僅履行勞動法上的各類法定義務遠遠不夠,公司一方面通過類似股權激勵等人力福利鞏固內部人力,另一方面通過提高自身形象宣傳內部福利來吸引優秀人才。公司履行這些超出法定責任的部分,被定義為社會責任,但是正是因為人力資源能夠為公司帶來盈利,公司才會進行這種投入,從對價上來說給予公司職員福利與投資一項有形資產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從反例考慮,富士康因員工自殺事件為社會詬病,但在沒有違反相關勞動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社會也只能是道德譴責。富士康選擇了看似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模式,但仍連續8年進入《財富》500強。對于法定范圍外的“社會責任”不過是一種無形資產投資,而不是每個公司都有實力和必要進行該項投資的。
——商譽。商譽是指能在未來期間為企業經營帶來超額利潤的潛在經濟價值,或一家企業預期的獲利能力超過可辨認資產正常獲利能力(如社會平均投資回報率)的資本化價值。如果說人力資源的支出被視為無形資產的投資還存在異議,那商譽是一種無形資產可以說已成定論,商譽甚至需要適用《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進行減值測試。而遵從法定義務之外的道德倡導無疑會增加一個公司的社會好感,而這種社會好感就能轉化為商譽,形成無形資產。從這個角度講,所謂社會責任根本不滿足責任的定義。以公益捐贈為例,考慮到我國稅法規定公益捐贈的12%可以在稅前扣除,本質上公司僅需投資88%的捐贈額,就可以換回一定的商譽價值。當然,這種投資并不是等價的,但是不可否認,這種“社會責任”中商業因素的考量是巨大的。
法人的特殊種類與社會責任
我國民法通則將法人分為了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與社團法人,這種分類方法迥然于英美法和大陸傳統,尤其是事業單位法人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專門從事社會公益活動的組織。我國事業單位法人幾乎為“官辦”性質,也不同于大陸法意義上的公益法人。從理論上說,這些法人不以營利為目的,偶為營利,也不為惠及其成員之用,而專為發展壯大公益事業之用。在擁有這類特殊法人的基礎上是否還需要像美國一般擴大公司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值得討論。
我國企業根據所有制的不同還有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這些特殊種類。國有企業作為全民所有的企業當然要考慮社會利益問題,或者說其承擔社會責任問題不過是內部利潤的分配問題。集體企業則要充分考量該群體的利益,即區域性集團的社會利益,這點又頗似美國社會責任中要求對社區成員的責任承擔。可以說,公有制企業因為戴上了“公”的帽子,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問題上與追求利潤不僅沒有矛盾,而且是同一的。即公有制企業賺取的利潤本身就將用于承擔社會責任,而在賺取利潤的過程中承擔社會責任完全可以看作是利潤的提前支取。
在事業單位和公有制企業等社會利益優位的法人大量存在的情況下,我國私企包括小規模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甚至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似乎并不需要如同美國一般嚴格。對要求一般公司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不僅是對公司本身的苛責,也是對公益機關的放縱。
綜上所述,對于相關利益者利益所負擔的強制性責任,在公司的視角下是一個偽概念,因為立法的綜合利益考量,義務性的社會責任都已經被具象化的法律責任。正如弗里德曼所言:“企業僅僅具有一種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法規許可范圍內,利用企業資源從事旨在增加企業利潤的活動,唯一對股東負責。”雖然他的觀點遭致批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利潤是公司最為重要的指標,一些被稱之為“社會責任”的指標事實上就很少能展現。倡導性的社會責任實質上是公司的一種經營理念,如在環境指標達標的情況下節能減排、在符合勞動法規的情況下增加職工待遇福利、在依法納稅的前提下投資公益事業等。這些超越法律高度的行為絕不是一種強制性責任,而是公司發展的一種戰略定位與導向。這與其稱之為倡導性社會責任,不如稱之為一種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觀。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