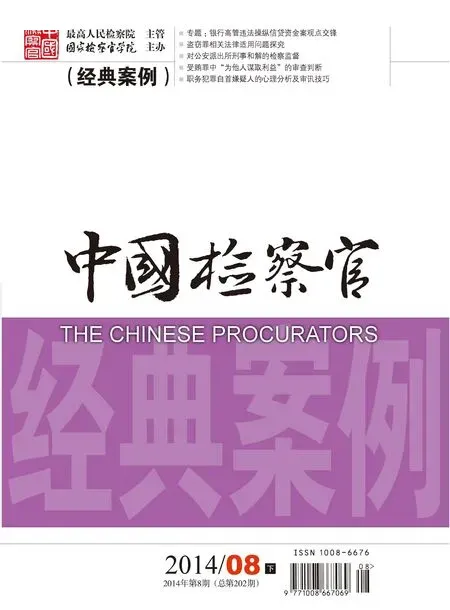盜竊罪相關法律適用問題探究
文◎代科
盜竊罪相關法律適用問題探究
文◎代科*
本文案例啟示:2013年盜竊罪司法解釋第2條(一)中的“盜竊”應作實質理解,同時需根據前行為的案情綜合判斷是否有刑事處罰必要性而加以適用。有盜竊前科的未成年人不能適用減半情形的規定。對多次盜竊中“次”的認定,僅需進行形式審查。多次盜竊同樣存在未遂。行為人多次盜竊,只要有一次既遂,即可認定為既遂。
[基本案情]2014年5月的一天晚上11時至次日凌晨3時,犯罪嫌疑人陳某(17周歲)從某城區濱江路至四環路連續盜竊多輛車內現金,共計人民幣1500余元,其中只有2次盜竊到財物,其余多次均盜竊未果。經查,陳某曾因破壞電力設施罪被判處刑罰。
本案在辦理過程中,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本案犯罪嫌疑人是否適用盜竊數額較大標準減半情形?二是本案是否為多次盜竊?是盜竊既遂還是未遂?
一、對盜竊數額較大的標準減半情形的理解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2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數額較大”的標準可以按照前條規定標準的百分之五十確定:(一)曾因盜竊受過刑事處罰的;(二)一年內曾因盜竊受過行政處罰的;?......(八)因盜竊造成嚴重后果的。”筆者認為,該條款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兩個問題,影響罪與非罪的認定。
(一)如何理解《解釋》第2條(一)中的“盜竊”
對于《解釋》第2條(一)中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前行為構成盜竊罪,但根據刑法或相關司法解釋規定應轉化為其他犯罪,如轉化型搶劫;二是因法條競合或想象競合的原因,依照法律規定或從一重罪處罰的原則,對該盜竊行為認定為其他罪名,如故意破壞電力設施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
對盜竊數額較大的標準降低百分之五十,在沒有符合盜竊罪入罪標準的其他情形時,會涉及到罪與非罪的情況,實踐中分歧較大。一種觀點認為,根據罪刑法定原則,該條款中的“盜竊”只能是前行為依法被人民法院認定為盜竊罪的行為才適用該款,不能擴張解釋。如轉化型搶劫中,其盜竊行為已被更為嚴重的罪名吸收,再次犯罪時不能對其重復評價;另一種觀點認為,對該條款中的“盜竊”不能機械、簡單的理解,應根據前行為是否構成符合盜竊罪名的構成要件進行綜合判斷,即前行為只要符合盜竊罪的犯罪構成,無論是否因法律規定或刑法理論而定為他罪的,應當然適用本條款的規定。
第一種觀點的問題,在于僅從形式上對“盜竊”進行理解,對原本符合盜竊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因法條競合或刑法理論的原因被認定他罪的行為沒有進行實質考慮,如故意破壞電力設施罪中,其行為本質就是盜竊,若只因罪名不同而否定其屬于盜竊行為,以此排除適用該條款有失妥當。
因此,筆者傾向同意對此條款中關于“盜竊”的理解,應對前行為進行實質審查的觀點。但在具體適用時還應當根據前行為的案情綜合判斷是否可能被判處刑罰,不能僅以符合犯罪構成為由,而不考慮刑事處罰必要性,一律適用該條款,如前行為是在盜竊近親屬財物時被人發現,為抗拒抓捕采取暴力行為,根據法律規定應認定為轉化型搶劫,若僅對盜竊行為評價,有可能免予刑事處罰,此種情況就不能適用《解釋》第2條(一)的規定。
(二)有盜竊前科的未成年人是否適用減半情形的規定
司法實踐中,對于有盜竊前科的未成年人再次實施盜竊犯罪時能否適用《解釋》第2條(一)、(二)項的規定,爭議較大。一種觀點認為,未成年人仍應適用該條款的規定,因為之所以對有盜竊前科的人降低入罪標準,是為了打擊盜竊慣犯,其人身危險性較高,且法律對未成年人犯罪已經規定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未成年人不能適用的前提下,根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均應一律適用;另一種觀點認為《刑訴法》對未成年人犯罪制定了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對于其之前的犯罪行為已不作評價,據此未成年人不應適用該條款的規定。
筆者認為,對于有盜竊前科的未成年人,包括因盜竊受過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不能適用盜竊數額較大標準降低百分之五十的規定。該條款降低了盜竊罪的入罪標準,立法本意是為了打擊盜竊慣犯,若未成年人也適用該條款,不利于教育與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同時《刑訴法》明確規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這是對犯罪前科消滅的另一種表述,據此也不應該適用該條款。
二、對多次盜竊的理解
多次盜竊與數額較大、入戶盜竊等行為并列作為盜竊罪的構罪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對其爭議較大,如次數的認定、是否存在未遂等。
(一)關于“次”的理解
多次盜竊作為盜竊罪的構罪標準之一,其中關于“次”的理解尤其重要。單從字面上理解,只要每次實施了一次獨立的盜竊行為,就應當認定為一次盜竊,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對于“多次搶劫”的認定,提出了“對于行為人基于一個犯意實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同時對在場的多人實施搶劫的;或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點實施連續搶劫犯罪的,一般應認定為一次犯罪”的觀點,據此,司法實踐中對多次盜竊中次數的認定也產生了較大分歧,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基于一個犯罪故意,在相對集中的時間、地點、連續實施盜竊行為的,應當認定為一次。另一種觀點認為,應從形式上對多次盜竊進行認定,即無論行為人是否基于一個犯罪故意,只要針對不同對象實施盜竊行為,就應認定為多次行為。
第一種觀點的缺陷有兩點:一是如何確定相對集中的標準?相對集中的時間段標準,有人提出應限定在同一天較短的時間內,那么對于從第一天凌晨前至第二天凌晨后不久的時間段是否認定為相對集中?相對集中的地點,在多大范圍內是相對集中?法律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標準,而司法實踐中由于司法人員的認知水平不同,可能會給出不同的解答,就會造成法律適用標準不統一的情形;二是如何評價行為人是否基于一個主觀故意?因為主觀故意的證據通常只有行為人的供述,鮮有其他證據證實,司法人員對此進行實質判斷時,也會出現偏差,有主觀斷案之嫌,此種觀點不具操作性。
因此,筆者同意對多次盜竊中“次”的認定,僅進行形式審查即可。首先,多次盜竊次數的認定標準不應參照多次搶劫的認定標準:一是多次搶劫是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劫行為均已構成犯罪為前提,而多次盜竊并不以每次盜竊行為構成犯罪為前提,二者適用的前提不同;二是多次搶劫是搶劫罪中法定刑升格情形之一,而多次盜竊是盜竊罪的入罪標準之一,二者的地位不同;其次,從形式上認定多次盜竊的次數,更能體現對多次盜竊的刑法評價。多次盜竊之所以和入戶盜竊、扒竊等行為并列為盜竊犯罪的構罪標準之一,一是多次盜竊的行為社會危害性大,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高,應從重打擊;二是從社會一般觀念看,行為人產生犯意后,實施一次行為、造成一次結果就應視為一個完整行為,不能人為地提高多次盜竊的認定標準。
(二)多次盜竊的既遂認定
盜竊未遂的,除了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盜竊目標的、以珍貴文物為盜竊目標的和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外,一律不追究刑事責任。多次盜竊是否存在未遂,在司法實踐中有較大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多次盜竊和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一樣,不以數額較大為入罪標準,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盜竊行為,就應認定為既遂。多次盜竊也一樣,只要實施完盜竊,無論是否取得財物就應認定為盜竊既遂。但筆者認為,盜竊罪作為傳統的財產型犯罪,不能脫離其侵財的本質,在考慮其盜竊行為的同時,還要考慮被害人是否因盜竊遭受財產損失。對于被害人沒有受損的盜竊行為,仍應認定為未遂。因此多次盜竊也存在未遂的情形。
對于多次盜竊,既有盜竊既遂又有盜竊未遂的,如何認定其犯罪形態,實踐中爭議較大。一種觀點認為多次盜竊,只要有一次既遂,多次盜竊即認定為既遂;另一種觀點認為多次盜竊,無論是否既遂,只要實施了多次盜竊的行為,一概認定為既遂;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多次盜竊必須全部既遂,才能認定為盜竊既遂。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多次盜竊的既遂,可以從多次盜竊未遂的認定進行分析。如前所述,多次盜竊中,對于沒有造成被害人任何損失的情形,應當認定為盜竊未遂,即每一次都沒有盜竊成功的情形才認定為盜竊未遂,因此只要造成被害人一定損失,均認定為多次盜竊既遂。
*重慶市豐都縣人民檢察院[408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