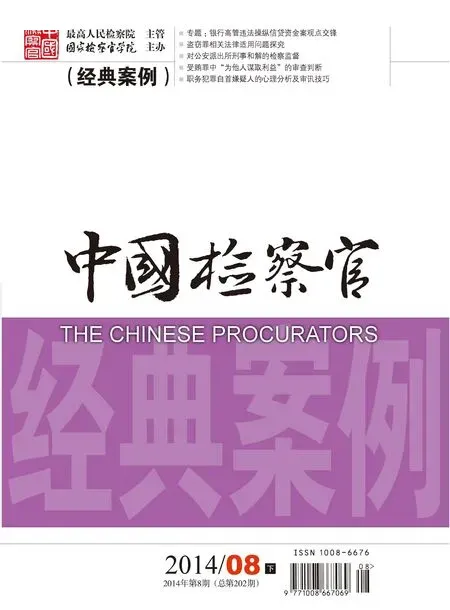私分國有資產罪與貪污共犯辨析
文◎宗雨
私分國有資產罪與貪污共犯辨析
文◎宗雨*
本文案例啟示:區分私分國有資產罪與共同貪污犯罪,應從發放資金手段的合理性、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和款項的違規程度來進行,如果單位有發放工資、獎金、福利等資金的資格,且參與分配人不知曉私分資金的性質、來源,發放款項主要違反財務制度和紀律的,一般應認定為私分國有資產罪,否則,可考慮構成貪污罪的共犯。
[案例一]劉某某,某市煙草分公司副經理兼該市煙葉復烤廠廠長、法定代表人。劉某某上任后授意廠財務通過收取呆帳不入帳、收取欠款不入帳、假列支出的方式,套出單位資金共計670余萬元,設立了“小金庫”(經司法會計鑒定,均屬國有資產),部分用于應對不規范的業務開支,部分用于給職工發放獎金。2001年至2003年間,該廠以風險獎、學習獎、出勤獎、加班費、開業費、公休工資、崗效工資、誤餐費、開工點火費、家屬慰問費等各種形式發放給全廠職工的款項共計499萬余元。
[案例二]倪某某,某市公共汽車公司(國有)經理。倪某某任某市公共汽車公司(以下簡稱公汽公司)法定代表人、經理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欺騙主管部門及國資部門,非法將本屬公汽公司的國有資產共計440萬元及8畝土地使用權轉移至由其控股的出租車公司(私營)名下,用于股東分紅及個人投資。
[案例三]徐某,某縣煤炭調節基金某征收驗票點負責人。王某、肖某、胡某、朱某、姚某、彭某,均為該征收驗票點工作人員。某縣煤炭調節基金管理委員會規定由鄉鎮政府在縣境內設立售票點,對運輸出省煤炭征收煤炭價格調節基金。該鎮政府遂在該縣的鐵路站口設立了一煤炭調節基金驗票點征收煤炭調節基金,并抽調鎮政府的徐某等上述七人到驗票點工作,指定徐某為該驗票點負責人。徐某等七人在該征收驗票點對從該點經過的運輸出省的煤車從事攔車、登記、收款、開票驗票等征收煤炭價格調節基金的工作。在征收過程中,徐某等七人相商,擅自決定降低收費標準,少收取煤炭價格調節基金,并將收取的基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開票后上繳基金專戶,剩余未開票部分七人以加班費的名義共十一次私分截留煤炭調節基金共計23萬元,人均分得贓款3萬至4萬元不等。
一、司法實務分歧
對案例一,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該市煙葉復烤廠構成私分國有資產罪,應追究廠法定代表人劉某某的刑事責任。理由是:第一,劉某某具有犯罪故意。劉作為復烤廠的一廠之長、法定代表人,為了逃避財務監管,在明知違反相關法規的前提下,仍授意設立“小金庫”,用于“部分業務開支和發放職工的獎金福利”。該意志通過劉某得以實現,足以代表單位。第二,從客體、客觀要件上看,復烤廠違反了《會計法》,將應納入企業核算的國有資產單列,設立帳外帳,同時還違反了勞動部的相關文件規定,在工資總額外另列支了工資性項目,造成了應該進入財務監管的國有資金被企業以獎金的形式發放給了個人,導致了國有資產的流失。第二種意見認為,復烤廠不構成犯罪,進而不應對劉某某進行刑事處罰。理由是:該廠從獎勵辦法的出臺至發放人員名單造冊、審簽、按冊發放均是按單位的操作流程進行的,手續相對規范,只是沒有從正規財務帳上列支發放,而是從“小金庫”列支,這違反了財經紀律,并不構成犯罪。
對案例二,也存在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是,倪某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理由是:倪某某在任該市公汽公司法定代表人、經理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欺騙主管部門及國資部門,非法將本屬公汽公司的國有資產共計440萬元及8畝土地使用權轉移至由其控股的出租車公司(私營)名下,用于股東分紅及個人投資。其打著經營股份公司的合法外衣,將國有資產套出占有并支配,符合貪污罪的手段特征。第二種意見認為,倪某某將國有公汽公司的資產轉移至私營公司名下,是用于多數職工(入股的公汽公司職工)分紅,并未個人占為己有,其行為僅構成私分國有資產罪,而不構成貪污罪。
關于案例三,仍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是,徐某某等七人的行為構成貪污罪。理由是:徐某某等七人共謀后,將應征收的煤炭調節基金截留后在小團體內部分配是典型的共同貪污犯罪。第二種意見是,該驗票點構成私分國有資產罪,只處罰徐某某。理由是:徐某某等七人對公款的分配行為是按相對公平的加班規定在部門內公開進行的,該驗票點雖是鎮政府的內設部門,但仍可成立單位犯罪,主客觀方面符合私分國有資產的犯罪構成。
綜上所述,以上案件的爭議焦點在于:1.發放行為具有一定的名目,是否符合私分國有資產犯罪手段的“公開性”特征?2.在全體成員內部分配是否就只能成立私分國有資產犯罪而不能成立共同貪污犯罪?
二、法理評析
一般情況下,只要從犯罪主體、犯罪對象、犯罪客觀方面分析判斷,私分國有資產罪與貪污罪的界限是清楚的。但由于私分國有資產犯罪與共同貪污犯罪在客觀上具有一些相同點,如:在一定的集團內部分配;有一定名目的“公開”分配等,故在實際認定時還是容易混淆。要正確區分私分國有資產犯罪與共同貪污犯罪,筆者認為還應從發放手段的合理性、行為人的主觀故意指向和款項的違規程度來加以辨析,具體如下。
(一)從發放資金資格來判斷私分國有資產罪中手段的“公開性”特征
在97年《刑法》以前,公然對國有資產進行違規分配的行為一般是按共同貪污犯罪來處罰的,但這樣處理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由于是公然進行,公平分配,單位負責人具“法不責眾”的思想,助漲了此類行為盛行,造成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第二,一方面,單位負責人并未將全部國有資產占為己有,而是以獎金形式分配給了大多數職工;另一方面,對大多數職工而言,其無權決定分配與否,只能被動接受,如按共同貪污定罪處罰,如何確定二者的犯罪金額、如何認定共同犯罪故意都成問題。為了準確做到罪當其罰,97年《刑法》增設了私分國有資產罪,并把私分國有資產罪規定為單位犯罪,就是為了有效、準確地打擊單位決定違規發放國有資產的行為。因此,私分國有資產犯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的方式是公開的。這種“公開”具有兩個特征,第一,對內公開。即單位內部發放有公開的形式、標準、手續、規程和帳務;第二,對外公開。即單位具有發放工資、獎金、福利的資格,參加分配的人員不會有顧慮,外部門的人員知曉后亦不會產生質疑。
案例一中,復烤廠自身具有向職工發放工資、獎金、福利的資格,因此該廠發放的各類獎金,對職工來說,在情理之中,感覺并無異常。而案例二中,入股參與分紅的職工如果知道其所分得的紅利源于倪某某的一系列轉移國有資產的情況,仍參與其中的,應構成貪污共犯;如果對股份出租車公司的經營業務、資金運行、營利情況確不知情,這部分參股人員實則是在倪某某的利誘下(還本付息)成為了倪發起成立名為股份公司實為個人所有的掩飾外衣,因此,此部份參股人員在主觀上與倪某某既無貪污、私分國有資產的共謀,亦不是私分國有資產的直接責任人員,對此部分人員則不宜當罪處理。案例三中,該驗票點是鎮政府的一個下屬部門,工作人員均隸屬于鄉鎮,其工資、獎金、福利的領取都在鄉級財政。一旦驗票點發放福利,對于發放的行為,驗票點工作的眾人是不敢聲張和公開的,因為,驗票點自身不具有發放工資、獎金、福利的資格,對于發放行為,眾人均可推知款項來源為非法。徐某某等七人在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積極隱匿公款后在內部“公開”、“公平”分配贓款,此行為實質是秘密的,是犯罪集團內部對犯罪贓款進行分配的一種形式,而非私分國有資產犯罪手段上的公開。
(二)從參與分配人對私分的資金性質、來源是否知曉來判斷其主觀故意
私分國有資產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外化的形式一般表現為“以單位名義”,即“私分”是由單位領導共同研究決定或者有決策權的負責人決定的,最后上升為單位決議,體現了單位意志。在私分國有資產犯罪中,私分的款項、來源,只有單位決策層或單位有決策權的負責人知曉,廣大職工只知道領獎,并不知道領獎的原因及項款的來源,因此,廣大職工主觀上并無犯罪故意,客觀上無權決定、操作。私分國有資產罪一旦成立,一般對分到資產的職工只是要求退清贓款,并不予以刑事處罰。這也是《刑法》規定私分國有資產罪只處罰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的立法原意所在。如果所有參與分配的人員均知曉分配款項的來源、性質,就可判定其主觀上形成了共同犯罪的故意,根據故意的指向,結合客觀行為,進而判定其所構成的具體犯罪性質。
案例一中,復烤廠所發放的獎金、福利等款項的資金來源只有劉某某及其經辦的財務人員知曉,廣大職工并不知道款項的來源渠道,雖然客觀上領到了獎項,但主觀上與劉某某沒有共同的私分故意,所以不能對該部分職工進行刑事處罰。案例二中,分得紅利的股東應視具體情節而定,如果知道倪某某一系列的轉移、隱匿國有資金的行為而參與分配,性質上構成共同貪污;如果確不知情,只是受倪某某的利誘,成為了倪某某股份公司外衣中的一種掩飾的話,不宜作為犯罪處理;案例三中,徐某某等七人均知道分配款項的性質屬公款,是通過隱匿截留而來的,且積極實施、共同參與,是典型的共同貪污犯罪。
(三)從發放款項的違規程度來區分犯罪性質
私分國有資產罪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具有貪污罪的危害后果,但在手段上不同于貪污犯罪。貪污罪的手段一般是利用職務便利,侵吞、盜竊、騙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而私分國有資產罪除逃避上級的監督檢查外,對內是公然對國有資產進行濫發濫放。其形式上往往表現為:發放標準有文字依據、發放范圍有造冊名單、領取有簽字手續、人員變動有賬本交接。私分的款項在單位內部是有據可查的,其本質是違反財務制度和紀律,是一種行政違規。而共同貪污則不然,分配的款項,在單位內部賬上已經通過各種手段填平,永遠無據可查,在形式上具體表現為:涂改賬目、隱匿截留;分配上即領即消,不敢留有簽字,既便當時有,事后也要短期內銷毀(當事人除出于某種考慮保留的除外);人員變動,手續交接中絕口不提。款項的違規程度已不僅僅是一般行政違規,其實質具有明顯的刑事違法性。
案例一中,“小金庫”的設立在該廠具有歷史沿襲性,“小金庫”內的款項只是逃避上級部門的監管,對內有據可查;福利的發放,均由財務造冊,劉某某審簽后發放;職工依次到財務領取簽字,以上均符合典型的私分國有資產罪的特征。案例二中,倪某某發給入股職工的紅利,實質是從國有公汽公司轉移到股份公司的國有資產,只是被倪某某披上了一層股份制的外衣而已,該資產在國有公汽公司的帳上已消失殆盡,不再體現,倪某某用股份公司作掩護,其貪污的犯罪實質很難發現。案例三中,驗票點本身沒有財務,但其經手的收款收續和上繳手續已被徐某某等七人通過收大頭開小尾的方式填平,國家流失的煤炭調節基金在上交的財務手續中再難發現,具有明顯的刑事違法性。
三、案例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在案例一中,劉某某作為復烤廠法定代表人,為了逃避財務監管,違反《會計法》,授意設立“小金庫”,違反了勞動部的相關文件規定,在工資總額外另列支了工資性項目并從小金庫中發放,造成了應該進入財務監管的國有資金被企業以獎金的形式發放給了個人,導致了國有資產的流失。故應認定復烤廠構成私分國有資產罪,對該廠的法定代表人劉某某進行處罰。另,關于復烤廠不構成犯罪的觀點,我們還要從復烤廠發放獎金的數額、套取國有資產的手段等情節來分析,其數額之大,主觀故意之明確已不僅是一般的違規行為,其設立“小金庫”的初衷就是為了逃避監管,違規發放獎金,符合私分國有資產罪的犯罪構成。
案例二中,倪某某利用職務便利,欺騙主管部門及國資部門,非法將本屬國有公司的國有資產共計440萬元及8畝土地使用權通過一系列的非法手段轉移至由其控股的股份公司(私營)名下,其打著經營股份公司的合法外衣,將國有資產套出占有并支配,符合貪污犯罪的手段特征,應對倪某某以貪污罪定罪處罰;對于分得紅利的人員,不宜當罪處理,因為從案情來看,該部分人員對經營、決策均無權決定和參與,不過是被利誘成為了倪合法經營的掩飾。
案例三中,徐某某等七人主觀上都希望通過不開票或少開票的方式將煤炭調節基金隱匿截留下來占為己有,在主觀故意上已形成了共同的犯意聯絡;客觀上七人積極行為,隱匿截留公款,秘密分配,構成共同貪污,均應定罪處罰。
*貴州省安順市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56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