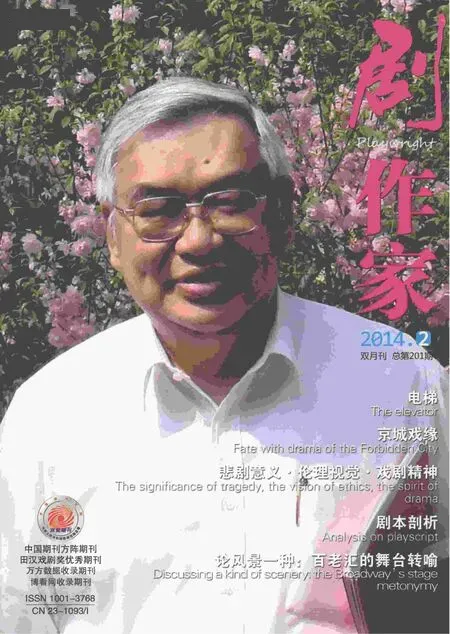論風景一種:百老匯的舞臺轉喻
濮 波
音樂劇的景觀化和倫理真空地帶
當今的舞臺,是一種情境主義者德波所言無奈的景觀,劇場化已經滲透了我們整個社會生活,而生活的實質漏洞百出,離希望的空間渺遠。舞臺,或者像舞臺戲劇一樣的景觀,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經驗和視覺記憶。舞臺,它再現或者表現社會的真實圖景。所謂舞臺空間和社會空間的轉喻,就是指這種內在的邏輯關系。(而日常生活的劇場化,則是另一種生活對應于舞臺的轉喻系統。)
這里所說的是前一種舞臺轉喻,舞臺空間和社會空間的轉喻。它可以分成幾種類型:(1)、一個瞬間轉喻一段社會時間的(比如薩特的《禁閉》、品特的《生日晚會》、布魯斯·諾里斯的《克萊伯恩公園》);(2)一個相對較小的時空轉喻另一個相對較大的時空的(比如老舍的《茶館》);(3)兩個空間完全對等的置換(比如標榜在時空結構上等同的自然主義實驗作品。這些作品在理論中存在,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完全做到。一個理由是,百分之百的即興創作和在場,以及取消再現的努力幾乎都是不成立的)等等。相對于轉喻的修辭,舞臺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一粒沙中見到的世界”,或者一個片斷(橫剖面)中獲取的社會全景。這種嘗試的審美基礎就是“舞臺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或者“舞臺是社會的轉喻”。
舞臺轉喻本質上是一種典型化的或者非典型化的再現,它與另一種修辭:“表現”的模式不同。表現類戲劇幾乎認為戲劇可以是完全創造自舞臺上的,藝術高于現實和社會。社會又可能模仿戲劇。而當代被表現的戲劇,不是從社會風景中截取的。
這種舞臺修辭的不同,使得當今的劇場依然呈現出幻覺和反幻覺的兩種圖形和風景。比如說,選秀是表現,游戲式的、開放式的先鋒戲劇是表現,它不模仿現實。而通過排演的戲劇,無論荒誕劇還是經典的莎士比亞戲劇,都應該是再現劇,它的審美對應就是幻覺劇場。今天,在百老匯演劇區,幻覺劇場和反幻覺劇場的爭執,遠沒有到蓋棺定論的階段。盡管阿爾托和布萊希特的戲劇理論吸引了一大批實踐者,但是在劇場上,那些最能獲得票房的依然是幻覺的劇場。如在最近的《紐約時報》戲劇版里所上榜的最熱門戲劇中,除了品特的《背叛》等少數幾部話劇之外,幾乎清一色都是音樂劇的天下:這十大熱門是《女巫前傳》(Wicked)、《獅子王》(The Lion King)、《魔門經》(The Book of Mormon)、《蜘蛛俠》(Spider-Man: Turn Off the Dark)、《長靴妖姬》(Kinky Boots)、《瑪蒂爾達》(Matilda the Musical)、《安妮》(Annie)、《背叛》(Betrayal)、《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和《摩城》(Motown: The Musical)。可見以具有普世價值的主題和盛大的舞臺景觀為吸引觀眾手段的音樂劇,其本質上就是一種幻覺劇場的模式。
這些以炫耀場景效果的劇作,與阿爾托的殘酷戲劇之觀念和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戲劇觀格格不入,相差甚遠,然而這就是當今百老匯的現實。全球化導致時空的分延和景觀化效果的加強。于是,在這種景觀化的舞臺倫理下,道德屈服于景觀。雖然這些音樂劇最后都通向一種光明的主題,然而為了達到這樣的主題,在舞臺上需要營造巨大的光影工程。而且,這種工程是時間性和空間性相結合的。
因此,雖然過去的舞臺革命,用劇場性去對傳統以模仿和劇情再現的戲劇性進行顛覆的實踐做得非常到位。比如在外百老匯、外外百老匯劇場上演的實驗作品所昭示的。這些作品不再依附于文本,不再召喚“不在場”的現實,而是直接訴諸感官,表現動態思想的深厚潛力,并與進行當中的個別而具體的生命經驗同步。它取消觀演間的界限,讓演員和觀眾在每個戲劇當下融為一體,體驗共同的精神焦慮。通過在場,反對一切再現的手段,也反對斯坦尼、契訶夫、亞里斯多德。
可是,實際情況是,幻覺劇場不可能消失。因為我們稱為戲劇的每一個關注的框架都是虛構的,沒有純粹或真正的“在場”。任何一次排演和演出都是一種“再現”,一次“再生產”和“復制”。因此,它導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戲劇和表演觀念:所有的表演都是幻覺。這個世界上只要有舞臺存在,就不外乎是再現劇場和幻覺劇場。它依靠一遍遍的重復來獲取市場和觀眾。因為,過去的幾十年劇場實驗在很多情況下,它們不但沒能呈現人類強烈情感的精髓,實現觀眾和戲劇的交流,反而陷入形式主義、自我重復和極端混亂的狀態。阿爾托殘酷戲劇理論的失敗之說,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才成立的。
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延續了劇場的幻覺性這種姿勢,雖然它也在內部支持像阿爾托的叛變和革命,也支持像隨后的布魯克(戲劇導演)、特納(人類學家)和謝克納(環境戲劇倡導者)的綜合和妥協(儀式)觀念,可是,在百老匯的劇場里,真正獲取大量票房,維持資本主義江山的是那種大型的感官秀。借助劇情的舊亞里斯多德戲劇觀的痕跡,當代的票房冠軍們都知道,要讓觀眾掏錢來觀看戲劇,話劇儼然是一種權宜之計,斷然不是重頭戲。所以,這里的策略是那種巨型化的演出:《獅子王》、《歌劇魅影》、《媽媽咪呀》、《魔門經》、《貓》,在這些音樂劇里,道德和倫理被開放至一個接近極限的程度。在這些以德波所言的“景觀”——而不是一個道德故事,一個生命經歷給人的沖擊的——劇場里,一切都是有著詭秘的內在邏輯的。
當代百老匯或者倫敦西區、芝加哥、東京、首爾、溫哥華、多倫多劇場區域,一條可見的邏輯就是:一切大型的演出必須將道德的寬容度提高到最大。全球化時代幻覺劇場在倫理道德領域一個最大的挑戰是,這些大型秀需要克服一個矛盾,自由、性欲、身體的展示和陽光主題的巧妙統一。比如說《歌劇魅影》的主題,是對光明戰勝邪惡力量必然性的謳歌,和對純真愛情的提倡……因此,這個戲劇中,女演員投身于以歌劇演員的事業作為維持生計手段的劇情(其中的場景顯然是歷史性的,有不道德成分,女性身體的展示成為了一個時期劇場的噱頭。劇情要再現歷史,就得盡可能再現這樣的壯大色情場面)就顯得為廣大觀眾接受了。觀眾還順理成章得以窺見到劇院的后臺——那些演員們隨便更換衣服的地方,暴露著身體的隱秘之處。這樣的場景設置,舞臺的艷舞和虛幻的景觀,就這樣與正在上演的音樂劇的聲光效果,統一了起來。觀眾以在投入劇情的方法參與了舞臺景觀的營造,成為了現場的一個元素。虛幻景觀的流行,還與一種劇場的分裂行為有關。在視覺上,觀眾包攬聲色舞蹈(劇情空間所展示的);外表上,又以在“觀看一臺人道主義的戲劇和音樂劇為名”的偽裝下正襟危坐,甚至還可以風度翩翩、紳士味道、批判味道十足。
身體和幻覺構成了當今百老匯劇場時空的主要元素。在劇間休息的時候,觀眾們紛紛涌出劇場,去設在劇場十米開外(或者緊鄰的地方)的酒吧痛飲一杯,儀態萬方、道貌岸然地與同性或者異性朋友寒暄、交際。大多數時候,男士們為了遇見一個心儀的異性這樣的目的去酒吧。休息時間一般為20分鐘,中場休息時間過后,劇院進入下半場。你再次回歸到一個安全的觀演地帶。這樣的倫理真空地帶,其實就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空間本質上身體和精神斷裂的事實,正如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一書里強調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斷裂”的癥候。也許,資本主義劇場讓你掏腰包的伎倆就在這里:讓你充滿幻覺,既沉浸在故事中的幻覺,又希望自己獲得超越庸常生活的能量的幻覺。
劇場裸露,作為一種百老匯景觀,與好萊塢的電影制作遙相呼應。它也與資本主義的戲劇制作方式,觀演契約的達成,都有關系。它顯然廣為流行。如在外外百老匯劇場的一個代表性LA MAMA劇院(這個劇院上演過紐約著名的先鋒戲劇家杰?蘇倫(John Jesurun)的作品《空月亮里的張》(Chang In A Void Moon)系列[1]),正在上演《黑場淡出》(Black Out),它的觀演極為典型,是觀眾從高處的黑匣子四周邊框,看籠子般的黑匣子里的三個只穿著內衣的演員的表演。在2013年,倫敦西區的約克公爵劇院里,我第一次欣賞表現大文豪奧斯卡?王爾德同性戀題材的話劇《猶大之吻》(大衛?哈爾作品),其中男性的裸體在舞臺上持續良久。

《黑場淡出》(Black Out)之劇場效果
這樣,當代音樂劇的幻覺看見,與全球化時代的景觀效應是統一在一起的。景觀的流行背后,揭示的是當代人一種對待劇場的態度——它是建構道德同時又是身體和道德不可通覽的場所,一句話,即是道德訴求明顯,又是道德倫理的混沌之地。它背后的邏輯是這樣的,身體的快速來不及修正道德的措辭和話語。
策略和話語
身體和道德的速度感的問題,引發出另外的思考:即不管在百老匯,還是在國內的劇場,策略在戲劇制作中的位置突出了。這是社會的時空演變對應人的精神面貌的另一種修辭轉換。
比如,在當代戲劇越來越頻繁地表現了一種話語的策略而不是對話的策略。對話在戲劇中的位置,越來越渺小,而將主旨讓位給了話語。如上海話劇中心寧財神改編的金庸作品《鹿鼎記》,就是以話語策略代替了對話的豐富和文采。寧財神在原著劇情框架不變的基礎上,進行了大幅度的加料和重構。而對話,卻被評論家批評為這個戲的弱項。[2]這個戲劇,經過與原著寫作時間幾十年的跨度,在當下要表達的是一種超越狹隘社群和政治劃分的那種機械性給人的窒息,它要表現社會階層的第三空間(一種模糊空間)而不是界限非常明確的一種空間。這個戲劇的改編者順著金庸的路子,其實想要達到的是對政治的一種瓦解和救贖,對于我們當代人壓抑人生的一種痛快的宣泄。它這樣的策略,帶起的情感結構是被觀眾認同的。因此,劉劍梅這樣評價:“在這個戲劇里,韋小寶是好人還是壞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身便是一個雜體,而他又能輕易地平衡社會上的所有雜體。這雜體不僅對所謂的男性‘理想人格’提出質疑,也對任何固定的本質化的寫作立場提出質疑。”[3]《鹿鼎記》的改編,說明在全球化時代進程和與之相關的話語系統里,一些超越二元體系(現代性體系)通則的強調。對介于事物邊界之間的雜體的正面表現,對于邊界模糊這種主題的呈現,證實了戲劇策略的存在,而對話的作用在淡化。
當代幾乎所有的劇場觀眾,都非常熟悉當代的戲劇更多的是關于話語的。它的背景是對話的表演性的普遍,以及對主題和題材捆綁的無意識的反抗。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過去,我們看到的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主題,正如黑格爾所言,是兩股理性力量(不分上下的原則)的交鋒與對峙導致的悲劇性。它折射一種不能兩全的高尚法則。而在臺灣戲劇家王墨林參加澳門藝術節的《安蒂岡妮》中,其戲劇的策略又有所不同,表現如下:
舞美:傾斜的坡臺,看似穩固,卻也象征著傾斜的正義,可以倒向國王Creon,也可以倒向安蒂岡妮;
劇情:再經過重新詮釋之后,正義之神阿波羅在這個劇本里已經隱隱退位了,少卻了神性色彩,甚至連盲眼先知Tiresias都不是太明顯,更少了宿命論的成份;與此相反,Creon轉為絕對的主角,掌握此空間的權力,也掌握了權力的空間。
演員表演:白大鉉經常以高亢、清亮、嚴厲的說話口氣,來強調此一王者印象;相形之下,洪承伊所飾演的安蒂岡妮,身形雖然稍微柔弱,但卻表現出堅毅、據理抗衡的神情與態度。兩人用韓語吵起架來,各自顯得正氣凜然,目光炯炯有神。
舞美燈光:紅光、白霧、黑背營造劇場空間氛圍。
幾個劇場的元素,讓王墨林版的《安蒂岡妮》充滿了戲劇能量。這出戲的策略之一便是主題當代化的轉移。重新編寫與詮釋的劇本,除了引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原著臺詞之外,還引用韓國木刻畫家洪成潭關于光州5.18民眾抗暴事件的詩作,以及小說家黃晢日英《悠悠家園》段落,最主要還是回應東亞的戒嚴歷史,更為古希臘悲劇的經典女性形象與當代亞洲的情境建立起具體的連結(這一直都是王墨林多年來的主題關心與批判堅持有關,在其《軍史館殺人事件》、《荒原》中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控訴)。《安蒂岡妮》則是更融入了這些年與韓國戲劇交流后的東亞戒嚴觀,不再只是往內鉆探戒嚴的國家暴力體制之核,而是往外連結亞際(inter-Asia)文化的批判之網;倘若解嚴初期是重新閱讀與認識臺灣的開始,那么千禧以來應該是重新閱讀與認識亞洲的開始,至少我所感受的知識界與文化界,是有這么一個趨向的。[4]
德國戲劇理論家漢斯?雷曼在其《后戲劇劇場》這本書里點明了在當代的后現代的某些劇場作品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戲劇策略,就是類似路易?阿爾都塞把社會辯證時間和主觀經驗時間之間不可或缺的“相異性”轉化成了每件“唯物主義”批判性劇場作品的基本模式,皆在動搖在那種主體中心接受和現實誤讀意義上的“意識形態”。
我理解所謂“批判性劇場作品的基本模式”,即資本主義的空間里,有一種技術時空的增強,對于傳統的時空,就產生了一種擠壓和淘汰。這也可以從以“速度學”著稱的法國思想家保羅?魏瑞利奧指出的“技術速度代替機械速度,是后現代景觀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后現代的景觀沖突在本質上體現為一種時間的沖突”[5]之論斷中得到應征。同樣,兩者速度的差異,與斯叢狄認為的“傳統劇場和當代劇場,在本質的上沖突——所謂的戲劇危機是一種時間危機”[6]的邏輯一致。經驗時間和社會時間的分野,還體現在:“傳統的觀劇時間概念是分離的,而當代的劇場作品打造了精巧的合金。”[7]異質性的時間層匯合在劇場經驗的唯一時間之中。因此,自然科學創造了新的世界圖像——相對論、量子理論、空間時間理論相繼出現。在大都市中,混亂的經驗以不同的速度和節奏發生。對于這種早已產生的經驗,和那些無意識的復雜時間結構,自然科學的新進展造成了一種新的認識。柏格森把經驗時間作為一種“綿延”,從而將其余客觀時間區分開來。社會過程時間與主觀經驗時間的區分越來越清晰。
在田納西的《欲望號街車》里,女主角白蘭琪的主觀經驗時間是綿延著南方種植園氣息的那種帶有巴洛克、封建腐朽色彩,然而又是在內在呼喚著紳士風格的那種老時間,它與現代社會的時間格調(以斯坦利為代表)格格不入。于是,兩種時間在戲劇中產生了沖突。相比之下,斯坦利的時間觀念就比較符合社會的進程:資本主義的機械化進程,具體表現在碎片、斷裂、道德的淡化和不相關的不可通覽的事實增多。這些不斷以合法名義出現的事件碎片(體育、勞動、社會休閑、社區暴力、家庭維護)以資本主義賦予的平等化的形式一股腦兒出現在斯坦利的時間經驗里,產生一種與南方種植園文化不相容的叢林法則經驗。這樣,戲劇的沖突就是兩種時間經驗的沖突。
在一般被認為適合表現“三一律”時空感的劇場中,營造時間速度的非常規化或電影化,則是紐約的波多黎各裔藝術家、劇場實驗者杰?蘇倫作品《空月亮里的張》的策略。漢斯?雷曼指出,他的這個系列作品中充滿了冷靜與意義中純幾何的結構,舞臺空間往往是這樣的:多不設布景,因為燈光層次已經結構得非常精細,這一類別的劇場作品可以說是體現了劇場藝術與電影之間的聯系。電影對話在稍加改造之后,引入到了劇場之中。剪接的原則被加以極端化地應用。雖然一個故事的芽端和片斷在作品中不斷閃爍,但如想找出亦條情節主線,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杰?蘇倫的舞臺空間中,技術時間(社會性的時間),替代了人們過去的經驗時間,使得這個戲劇先鋒作品對應了后現代社會的視覺特征。包括它的臺詞——完全超越了幻覺劇場的再現原則,而是“以一種近乎機械性的、急促、快速的言語方式使得個人性、性格、寓言等戲劇概念都蕩然無存。這就像一個深不可測的視覺、語詞所組成的多棱鏡。觀眾首先感知的是拼貼、剪輯組合而成的影像畫面、電影、敘事印象,而并非戲劇邏輯”。[8]
從戲劇時間的角度上理解杰蘇倫,他建構的是與觀眾的觀賞同步的時間體驗,一切都在這個劇場中屬于原生態。而沒有經過演員“先經驗一遍”—再“通過重復的彩排和訓練”—再“一次次重復地展現在舞臺”上的過程。
這種人物的內心沖動直接可視地展示給觀眾,達到了劇場時間和表演時間的同步。
時間危機的延伸
劇場體現了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經驗的沖突,它恰如其分地用劇場轉喻的形式表達了這種圖形。這就是當代劇場審美的來源。在反映諸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性問題:經濟問題(危機)的時候,劇場依然大有可為,并樂意用再現的手法,并試圖抓住這樣的經濟問題之于人物精神的對應關系。比如,2012年普利策獎、托尼獎和2011年奧利弗獎的三料冠軍《克萊伯恩公園》,便是在老房子的周轉和經濟問題之間展現,繼而帶出社區的其他問題:種族、意識、家庭、國家。家、國家、天下在這部戲劇里有著另一層“轉喻”的修辭對應。可以說,《克萊伯恩公園》里的社區,對應了五十年美國社區的變遷。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有類似之功效,它以男女(家庭)的經濟關系折射了社會本質和時代圖像。易卜生的作品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在運行初期或者還遠未達到一種令人滿意的狀態的時候,那種對于資源的利用和競爭,導致的人際關系的緊張。戲里,海爾茂為了獲得職位,必須非常精明,而且勢利,才能保住江山。而恰巧妻子諾拉做了一件看起來有點傻的事情,一件受制于人的事情。諾拉沒有與海爾茂商量與人交易的事情。易卜生沒有交代這是屬于家庭內海爾茂的默許還是假如知道可能會拼命阻止的道德性。似乎看來海爾茂是會拼命阻止諾拉干這件事情的。諾拉與海爾茂在這件事情上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易卜生似乎贊成諾拉的仗義的做法,于是他站在諾拉的角度來替她打抱不平。而事實上,海爾茂可能會有另外的辦法——如果他知道諾拉為治愈他的疾病鋌而走險,將自己置于非常不利的形勢的話。
海爾茂老成、對于社會的殘酷比較領悟透徹。諾拉則親信別人,顯然屬于浪漫主義類型的女性。這導致家庭被人敲詐的風險。在江山和美人之間,海爾茂很自然地先選擇了自己的江山。而不顧諾拉在自己經濟危機的時候,曾經做過仗義的事情。這也是資本主義的制度造成的(資本主義的負心郎形象,不同于古希臘時期的《美狄亞》的丈夫所表現出來的為了顯赫的王位而不顧倫理道德底線,可以隨意踐踏自己的婚姻和自己生活的伴侶。《美狄亞》表現了王位的那種反人倫的特征)。相對《美狄亞》來講,海爾茂是真實的。這么一件小事,然而它牽動了當時北歐的觀眾,繼而在二十世紀獲得了世界性的成功。這其中的奧秘在哪兒呢?
在海爾茂的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北歐時期,資本主義的制度對于成功人士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海爾茂潛意識里非常清晰,如果江山保住,不怕沒有像諾拉一樣體貼的女人來到身邊。而假如失去自己的職位,則在這個險惡的社會里,有可能什么都失去,甚至最后也會失去諾拉的愛。這是從男性的想象和經驗出發的對于海爾茂這個角色的合理性思考。海爾茂是一個事業成功者的典型。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幾乎都會如此干的角色。這樣,這個戲劇的問題其實不是家庭倫理的事情,不是男女平等的事情,而是社會倫理強加于家庭倫理的那種對應關系。資本主義導致了社會關系的務實,浪漫主義和情義已經退居到了第二線。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權力。易卜生沒有講到即將來臨的欲望和性的巨大的能量。在這部戲劇里,資本主義的紳士風度,好像都已經失去。不僅海爾茂看起來像一個從牟取利息差的銀行生意里剛剛脫身的疲憊男人,諾拉也從浪漫和怡然,慢慢地走向了焦慮。
在寫作這篇文章的同時,剛好美國的電影全球獎揭曉,澳大利亞演員布蘭切特憑借《藍色茉莉》中的表演獲得了最佳女主角。她由于在電影中演一個類似白蘭琪的女子,被封為影后。《藍色茉莉》改編了田納西的《欲望號街車》,但是它的語境和主題則完全變了。用路易?阿爾都塞的原理,我們將這種改編中攜帶的主題性轉喻應用到當今許多領域,就會發現,操作、運用、消費經典杰作中的劇情和主題,已經是當下編劇和導演一個十分不錯的權宜之計——在一個全球化對景觀的控制社會中。因為某種程度上,社會就是劇場,對經典的主題改編就是時間性的一次舞臺轉喻。我們再來回顧田納西的《欲望號街車》中的轉喻:它呈現了一個沖突的社會風景。符號化的人物和對話的轉喻,支撐起了劇情發展的邏輯。在田納西的這個戲劇作品里,白蘭琪是欲望的符號。她擁有一段被資本主義規范和所謂的歷史意識指認為淫蕩的歷史。因此,她被描寫成舉步維艱,沒有出路。她的特異性在于欲望的控制體系與別人不一樣,別人聽從庸常社會的建議,按照今天的科學術語來講,今天的大部分人不會與一個“性取向異常的異性”談戀愛,這表明風險和未來的不確定。然而,白蘭琪天真的地方在于,她突破規范去做了;別人在現代社會里迅速獲得生存的基本伎倆(技巧),她沒有,無論是戀人的選擇,還是在選擇以后的處理,都沒有什么生活的經驗可言。在那個時代,相信社會的公共性信息平臺是缺乏的,社會上也沒有現在這么多的性學指南機構,讓白蘭琪可以去傾述和咨詢一下。她的天真還在于,失去了丈夫之后,開始在小城鎮墮落,與非常多的男子發生了性關系。請記住,這是田納西對女性墮落的標志性指認——他沒有去責怪那些不負責任的男性,與白蘭琪一夜風流之后消失無蹤的那些男人。他的劇場修辭停留在機械轉喻的階段,時代局限性比較明顯。田納西的劇作里,也沒有標明在美國社會,與多名男子保持性關系到底觸犯了什么樣的法律。這就非常令人疑惑。難道與多名男子發生性關系會遭遇驅逐?這是講究人權的美國啊。唯一一個可以想得到的事實是,白蘭琪遭到學校的除名,可能為了維持生計,在酒店與人隨便發生性關系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取金錢。這等于是賣淫。于是,在掌握了一些證據的前提下,小鎮的司法機構,將白蘭琪的繼承一處房產的權利也剝奪了?這好像也說不過去。劇作里沒有說白蘭琪遭到判刑之類。于是,最好的解讀本劇的辦法只能將之讀成一個現代寓言或者現代儀式戲劇。在被家鄉剝奪了繼承權和幾乎是驅逐之后,白蘭琪保持著過去被當下人指認為非常不合時宜的生活和言語方式。
情況也確實如此,在許多的戲劇理論和歷史書籍里,都將這個戲劇的主題界定為南方情調的破落。所以,白蘭琪的性格是封閉的,也就是在戲劇里她不得不走向崩潰。這既是主題決定的人物命運,也是田納西的戲劇觀念(觀念圖形)。
然而,時過境遷,今天我們再來看《欲望號街車》,發現里面的結局是單一的,就是它沒有升華為兩套語言的沖突這樣的戲劇主題。比如,今天我們會認同白蘭琪的遭遇是通過兩套語言系統(阿爾都塞所言的兩個時間的相異性)的沖突造成的。戲劇應該關注這兩套語言法則的沖突和后果,構建一種關系式的戲劇模式。而不再是一個單一的神話和寓言模式。寓言模式屏蔽了某些真實。今天,我們假如再改寫《欲望號街車》,那么主題其實就會集中在兩套生活和意識形態的不相容。而不會局限在讓白蘭琪無路可走,而是在批判過白蘭琪之后要批判斯坦利。這個戲劇在今天可以寫成喜劇。相反,斯坦利代表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叢林法則里生機勃勃的強盜,雖然還沒有獲得成功,但是野心十足,十分活躍;白蘭琪代表了南方的破敗、南方的失落。她的那些語言方式和行為模式既是南方的種植園社會模式的:寄生特征明顯。由于時代和經濟模式造就的局限,那個地域的女性在經濟上從屬于男性,交際花圍繞著男性的富翁轉悠,天經地義。而浪漫主義色彩的幻覺組成了女性生活的全部心理圖景。
在改編的《藍色茉莉》中,女性的困境依然存在,源自于性格和歷史的雙重影響。但是《藍色茉莉》的主題卻是自強不息和寄生生活兩種生活方式和態度的沖突。《欲望號街車》揭示了白蘭琪和斯坦利的時間經驗沖突,而《藍色茉莉》則對比了姐妹之間的生活方式之沖突。相似的人物故事和命運,但是主題完全不同。這就是今日藝術家消費經典巨作的秘密所在。改編法則還有一個潛臺詞,那就是不改變原作品的主題,何以成立?不轉喻其內涵,怎樣在今天成為著作權的主人?
相比之下,電影《安娜?卡列寧娜》的改編是一個反向例子。安娜在電影中,是一個直率的女性,她按照自己的欲望法則生活,而不是婚姻法。不過按照當今人的觀念來看,她事先應該與丈夫有這方面的契約會比較好。安娜在今天可以生活得很好。原則是必須在結婚之前與未婚夫進行雙方權利的溝通:是不是可以在結婚后有另外的性生活?這是很重要的部分。相信如果做到了這一點,他們兩個人的觀念和事實之間就不會分裂。婚姻的要害之處在于,雙方都期待從中得到好處。而雙方都不愿意將這種好處和利害關系事先說明白。另外一點詭秘的地方在于,婚姻和欲望的關系問題。婚姻不可能消除完全消化欲望——對于大多數人來講。一般需要超乎物質的力量才能將這種欲望控制得恰到好處,不傷及脾胃。雙方的欲望機制的達成也需要事先溝通。這都說明在一百多年前的俄國社會,這種“通奸和婚姻”的二元對立,既缺乏溝通,又缺乏透明性和疏導性。言下之意,這個戲劇在俄國背景里除了悲劇式結尾就別無他法。單向度的社會,導致關系的破裂和愈演愈烈的懲罰游戲。這出戲在當代應該停寫了。而湯姆?斯托拍改編的電影則依然在老舊的主題套路里折騰,所以這個電影最后的升華部分不精彩。一個老掉牙的故事,如果不改掉故事的結尾(主題),怎么可以成功呢?
注釋:
[1]《空月亮里的張》(Chang In A Void Moon),首演于1982年的Pyramid Club,2003年10月曾到LA MAMA劇院上演其中的第53、54、55集。
[2]楊申,《教授明星盛贊〈鹿鼎記〉 豐富想象受肯定》,新浪娛樂,網絡資料,網址:
http://ent.sina.com.cn/j/2009-04-09/01512462311.shtml,登入時間2014年1月10日。
[3]劉劍梅,《狂歡的女神》,北京,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2007,第266頁。
[4]于善祿,《〈安蒂岡妮〉的當代轉喻》,《牯嶺街小劇場·文化報》 2009年第9期。
[5]楊子博士論文《家園的蹤跡:全球化上海的劇場與藝術空間初探》,華東師范大學,2011年,第5頁。
[6](德)漢斯·蒂斯·雷曼,《后戲劇劇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99頁。
[7]同上,第198頁。
[8]同上,第142-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