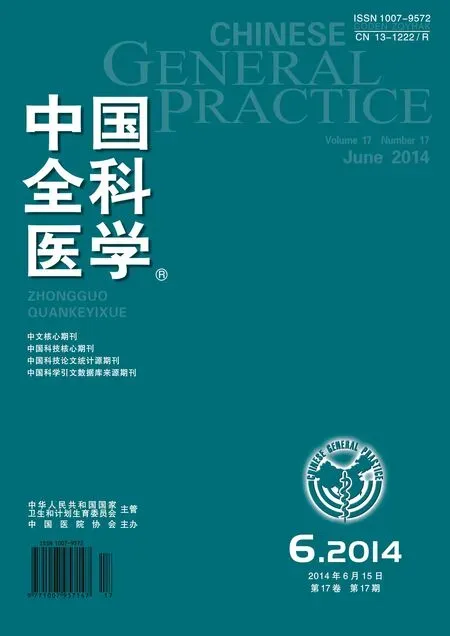2014年ADA糖尿病醫學診療標準選登
糖尿病是一種復雜的慢性疾病,除了需要控制血糖,還需要在多因素風險降低策略的指導下進行不間斷的持續治療。正在進行的患者自我管理教育及其相關基礎工作在預防急性并發癥以及降低遠期并發癥風險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已有證據表明,許多干預措施均可改善糖尿病的治療效果。
美國糖尿病協會(ADA)糖尿病醫學診療標準旨在為臨床醫師、患者、研究人員、納稅人和其他與糖尿病診療工作有關的個人提供總體治療目標和評估治療效果的工具。診療標準提供的建議并不妨礙臨床判斷,而是必須在接受良好的臨床治療,并針對個體傾向性、發病情況及其他患者因素做出調整的前提下應用。
診療標準提供的建議包括篩查以及已知(或確定)對糖尿病患者健康有利的診療行為。許多干預經證明具備較好的成本效益。ADA采用現行方法對作為上述建議基礎的證據進行澄清和編纂、建模,制定出分級系統(見表1)。字母A、B、C或E用來表示支持每項建議的證據等級。診療標準在考慮證據及各項建議的基礎上,總結出改進糖尿病診療流程的策略。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為了改善患者的生活水平,單憑臨床證據和專家建議是不夠的,還必須將其有效地轉換為臨床管理辦法與措施。
1 分類與診斷
1.1 糖尿病的分類 糖尿病在臨床上可以分為四種類型:(1)1型糖尿病(由于β細胞受損所致,通常會引起胰島素分泌絕對不足);(2)2型糖尿病(在胰島素抵抗的基礎上,胰島素分泌功能逐漸喪失);(3)其他原因所致的特殊類型糖尿病,例如:β細胞基因缺陷、遺傳性胰島素作用缺陷、胰腺外分泌疾病(如囊性纖維化)、化學物或藥物(如艾滋病治療或器官移植術后治療)導致的糖尿病;(4)妊娠期糖尿病(GDM,妊娠期間診斷出的癥狀表現并不十分明顯的糖尿病)。

表1 ADA臨床證據分級系統建議
某些患者無法明確劃入1型或2型糖尿病的范圍。這兩種類型糖尿病的臨床表現與病程發展明顯不同。被診斷為2型糖尿病的患者有時也可能出現酮癥酸中毒。患有1型糖尿病的兒童表現較為典型,可出現多尿、煩渴的特征性癥狀,偶發糖尿病酮癥酸中毒。只有隨著時間推移真實診斷才顯現出來,兒童、青少年、成人糖尿病的診斷中都存在一定困難。
1.2 糖尿病的診斷 通常選取血清葡萄糖水平作為糖尿病診斷的依據,可以測定空腹血糖(FPG),也可以測定口服75 g葡萄糖后2 h血清血糖〔餐后2 h血糖(2 hPG)〕及糖耐量試驗(OGTT)。近來,某國際專家委員會已將糖化血紅蛋白(HbA1c≥6.5%視為異常)作為診斷糖尿病的第3項標準。 糖尿病診斷標準:(1)HbA1c≥6.5%,應在實驗室中采取美國國家HbA1c標準化計劃(NGSP)認可的方法,按照糖尿病控制與并發癥試驗(DCCT)規定的標準進行檢測(若無明顯高血糖表現,應重復檢測以驗證結果)。(2)FPG≥126 mg/dl(7.0 mmol/L)。至少禁食8 h方為空腹(若無明顯高血糖表現,應重復檢測以驗證結果)。(3)OGTT中2 hPG≥200 mg/dl(11.1 mmol/L)。應按照WHO描述的方式,使用與75 g無水葡萄糖水溶液相當的制劑作為負荷量。(4)有典型高血糖表現或出現高血糖危象的患者,隨機血糖≥200 mg/dl(11.1 mmol/L)。
1.2.1 HbA1c測定 HbA1c測定應采取NGSP認可的方法進行,并須完全符合DCCT規定的檢測標準。雖然NGSP可能認可床旁HbA1c測定的結果,但由于測定操作熟練度并未進行強制考核,所以這類測定結果用作診斷依據時可能會出現問題。
流行病學數據顯示,HbA1c水平與視網膜病變風險的關聯性與FPG和2 hPG相似。與FPG及OGTT相比,HbA1c測定有以下優點:更加便捷(不必空腹),可能會提高分析前穩定性,并減少日常生活中壓力與疾病引發的不安情緒。同時也必須綜合考慮到這些優點所導致的成本上升,在某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推行HbA1c檢測受到的限制,以及某些個體表現出的HbA1c水平與平均血糖水平不完全相關。
HbA1c水平可能因患者人種/種族不同而出現變化。糖化比率可能因人種不同而不同。舉例來說,雖然還存在爭議,但非洲裔美國人糖化比率可能會較高。一項近期開展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與FPG水平相比較,非洲裔美國人(不論是否患有糖尿病)的HbA1c水平要高于非西班牙裔白人,同時其果糖胺及HbA1c水平亦較高,而脫水葡糖醇水平則較低,提示其血糖負擔(特別是餐后血糖負擔)較重。采用HbA1c測定診斷糖尿病的建議所依據的流行病學研究目前僅限于成年人。同樣的HbA1c水平界定標準是否可用于兒童或青少年糖尿病的診斷尚不明確。
某些貧血和血紅蛋白病患者的HbA1c測定水平解讀顯得特別困難。對于血紅蛋白異常但紅細胞更新正常的患者,如鐮狀細胞貧血,應進行排除異常血紅蛋白干擾的HbA1c測定。請參見www.ngsp. org/interf.asp網站更新列表。紅細胞更新異常的情況下,如妊娠、近期失血或輸液,或某些類型的貧血,只能依靠血糖標準來診斷糖尿病。
1.2.2 FPG與2 hPG測定 除了HbA1c檢測, FPG和2 hPG也可以用來診斷糖尿病。FPG與2 hPG檢測的一致性并非100%。HbA1c測定結果與血糖檢測的結果(FPG或2 hPG)也并不完全一致。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研究(NHANES)數據顯示,按照HbA1c≥6.5%的診斷標準比按照FPG≥126 mg/dl(7.0 mmol/L)的標準少檢出的糖尿病占漏檢糖尿病患者的1/3。許多研究已經證實,在這些診斷標準中,2 h OGTT在人群篩查中的糖尿病檢出率最高。實際上,糖尿病患病人群中很大一部分還沒有被診斷出來。要注意雖然HbA1c診斷標準的敏感性不強,但穩定性很高,這一點亦可有助于確立糖尿病的診斷。
與大多數診斷性檢測一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進行重復檢測以除外實驗室誤差(例如,HbA1c升高時如條件允許應在3個月后復查)。由于碰巧一致的可能性較高,除非已有明確臨床診斷〔如患者出現高血糖危象或典型高血糖癥狀,且隨機血糖≥200 mg/dl(11.1 mmol/L)〕,最好重復相同檢測進行確認。例如,若HbA1c初次檢測結果7.0%,復查結果6.8%,則糖尿病診斷成立。若兩種不同檢測結果(如HbA1c與FPG)同時高于診斷標準水平,亦可確診糖尿病。
另一方面,如果患者兩種檢測結果不一致,則應重復其中結果高于診斷標準界限值的那項檢測,再根據復查結果做出診斷。例如,如果患者的HbA1c結果滿足糖尿病診斷標準(兩次檢測結果均≥6.5%),但FPG不符合糖尿病診斷標準〔<126 mg/dl(7.0 mmol/L)〕,或與此相反,該患者仍應診斷為糖尿病。
由于一切檢測分析前及其過程當中都存在不確實因素,即使初次檢測異常(高于診斷臨界值),復查后也有可能會出現低于診斷臨界值的情況。這種情況在HbA1c檢測中不很常見,但在FPG檢測中相對較為常見,在2 hPG檢測中最常見到。除去實驗室誤差的情況外,上述患者的檢測結果常常處于診斷臨界值邊緣。醫療衛生人員可對這類患者進行密切隨訪觀察,并囑其3~6個月后復查。
1.3 糖尿病風險升高的種類(前驅糖尿病) 在1997年和2003年時,糖尿病診斷與分類專家委員會注意到有部分患者尚不足以診斷為糖尿病,但血糖水平已經遠高于正常。這種情況被稱為空腹血糖受損(IFG)〔FPG 100~125 mg/dl(5.6~6.9 mmol/L)〕,或糖耐量受損(IGT)〔2 hPG或OGTT 140~199 mg/dl(7.8~11.0 mmol/L)〕。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其他一些糖尿病組織將IFG的下限設定為110 mg/dl(6.1 mmol/L)。
“前驅糖尿病”是指存在IFG和/或IGT的情況,將來發展為糖尿病的風險相對較高的一些患者。IFG和IGT本身只是罹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CVD)的風險因素,不應作為診斷的實際依據。IFG與IGT均與肥胖有關(尤其是腹型肥胖或內臟型肥胖),同時還與血脂異常(TG升高和/或HDL膽固醇降低)以及高血壓有關。
一些采用HbA1c測定對是否會進展為糖尿病進行預測的前瞻性研究表明,與血糖檢測一樣,HbA1c測定水平與后來發生糖尿病之間存在強烈而持續的關聯性。對來自16項隊列研究的44 203名個體(隨訪平均間隔5.6年,為期2.8~12.0年)進行的系統回顧表明,HbA1c處于5.5%與6.0%之間者患糖尿病的風險明顯升高(5年發病率9%~25%)。HbA1c處于6.0%~6.5%之間者5年內發展為糖尿病的風險為25%~50%,相對風險(RR)較HbA1c為5.0%者高出20倍。一項在社區開展的以無糖尿病的非洲裔美國人及非西班牙裔白人為對象的研究表明,與FPG相比,HbA1c基線水平是對未來發生糖尿病及心血管事件進行預測的更好指標。其他分析指出,以HbA1c達到5.7%作為患糖尿病的風險因素與糖尿病預防計劃中提到的高危風險因素相似。
因此,將HbA1c處于5.7%與6.4%之間作為判斷個體存在前驅糖尿病的標準較為合理。與存在IFG與IGT的個體一樣,應使HbA1c處于5.7%與6.4%之間的個體了解其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風險升高的情況,并由此主動采取有效策略降低相應風險。另外與血糖檢測的情況類似,風險的持續變化呈現曲線形式,因此HbA1c水平的升高與糖尿病風險升高間并不成比例。對于風險較高的患者,應進行更加積極的干預與密切隨訪觀察。
2 1型糖尿病篩查
推薦標準:1型糖尿病患者經常表現出糖尿病的急性癥狀,血糖水平急劇升高,有些患者還會出現危及生命的酮癥酸中毒。1型糖尿病的發病率和普遍程度也在上升。一些研究提示,測定與1型糖尿病相關的胰島自體抗原可以識別出存在發展為1型糖尿病較高風險的個體。通過這一測定,加上在觀察性臨床研究中對糖尿病癥狀的宣傳教育以及密切隨訪,就可以較早識別出會發生1型糖尿病的個體。根據3項分別來自芬蘭、德國和美國的兒科隊列研究,最近一則研究報道指出,從血清轉化到自體抗原呈現陽性過程中存在進展為1型糖尿病的風險。兩項以上自體抗原陽性的585名受試兒童中,有近70%在10年內發展為1型糖尿病,84%在15年內發展為1型糖尿病。由于德國受試組的兒童均為1型糖尿病患者后代,而芬蘭與科羅拉多組受試兒童則來自一般人群,上述發現的意義十分重大。3組研究的發現明顯一致,這意味著導致臨床發病的這種先后因果聯系同時存在于“散發性”和遺傳性1型糖尿病當中。有證據提示,早期診斷可以減少急性并發癥,同時增加遠期內源性胰島素生成。在缺乏普遍篩查的當下,應考慮使1型糖尿病患者的親屬參與到臨床研究中來,接受自體抗原檢測,進行風險評估(http://www2.diabetestrialnet.org)。
3 GDM的檢測與診斷
推薦標準:(1)對未診斷為2型糖尿病但存在發病風險因素的患者,在初次產前訪視時按糖尿病診斷標準進行篩查;(2)對已知無糖尿病病史的孕婦于妊娠24~28周時進行GDM篩查;(3)對診斷為GDM的婦女在產后6~12周時,進行OGTT測定并按照非孕期診斷標準進行產后持續性糖尿病篩查;(4)有GDM病史的婦女應進行終生篩查,至少每3年1次,以了解糖尿病或前驅糖尿病的進展情況;(5)有GDM病史的婦女出現前驅糖尿病的表現,應接受生活方式干預或二甲雙胍治療以防止發展為糖尿病;(6)還需要開展進一步研究,以建立標準統一的GDM診斷方法。
多年以來,GDM被定義為妊娠期間發生或初次出現的任何程度的葡萄糖耐受不良,不論妊娠結束后情況是否持續,也不排除妊娠之前或妊娠期間可能未檢出的葡萄糖耐受不良。這一定義便于制定標準一致的GDM檢測與分類策略,但許多年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顯。隨著肥胖與糖尿病持續高發,越來越多的育齡婦女被診斷出2型糖尿病,未診斷出的2型糖尿病妊娠期婦女人數也大為增加。因此,有必要對存在2型糖尿病危險因素的婦女在首次孕前訪視時按糖尿病診斷標準進行篩查。患有糖尿病、在孕期前3個月內的婦女應診斷為顯性非GDM。
GDM會同時危及母親與新生兒,但并非其所有不良影響在臨床上都同樣重要。高血糖與孕期不良影響(HAPO)研究是一項大型(約有25 000名孕婦參與)跨國流行病學研究,其結果表明,孕24~28周時,由于母親血糖升高(即使之前在孕期容許范圍以內)引發母親、胎兒及新生兒不良影響的風險持續升高。且對于大多數并發癥而言,風險并不一定要達到臨界值才有意義。所有這些使得我們必須謹慎考慮GDM的診斷標準。可從下列兩種方式中任選其一進行GDM篩查: (1)口服75 g葡萄糖2 h OGTT“一步法”檢測;(2)口服50 g葡萄糖(不必空腹)1 h后血糖篩查,陽性者再進行口服100 g葡萄糖3 h OGTT的“兩步法”檢測(見表2)。不同的診斷標準可以反映不同程度的母親高血糖及母親/胎兒風險。

表2 GDM的篩查與診斷
4 糖尿病治療
4.1 初次評估 對糖尿病患者應進行完整的醫學評估,確定糖尿病的分型以及是否存在并發癥。已明確糖尿病診斷的患者應對既往治療與風險因素控制情況進行回顧,以幫助制定管理計劃,并作為繼續治療的基礎。為評估患者個體的身體狀況,應完善相應實驗室檢查。注重綜合治療(見表3)可使醫療衛生團隊實現對糖尿病患者的最佳管理。
4.2 患者管理 糖尿病患者應接受來自包括醫生、執業護士、醫生助理、護士、營養師、藥劑師和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在內的,具備糖尿病診療專業資質的團隊提供的醫療服務。在這樣的綜合性團隊協作解決方案里,糖尿病患者個體也必須在治療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應通過制定管理計劃,使患者及其家庭,與醫生及醫療衛生團隊的其他成員之間形成合作治療的同盟。應采取多種策略與技術手段,從糖尿病管理的各個角度,為患者提供豐富的宣傳教育,以及解決問題技能的培訓。治療目標與治療計劃應個體化,并考慮到患者的偏好與意愿。管理計劃應將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DSME)與持續性糖尿病支持作為整體治療的組成部分。制定計劃時要考慮到患者的年齡、學習與工作日程及其相應情況、身體活動、飲食習慣、社會情境與文化因素、是否存在糖尿病并發癥、首要健康問題及其他健康問題。

表3 糖尿病綜合評估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