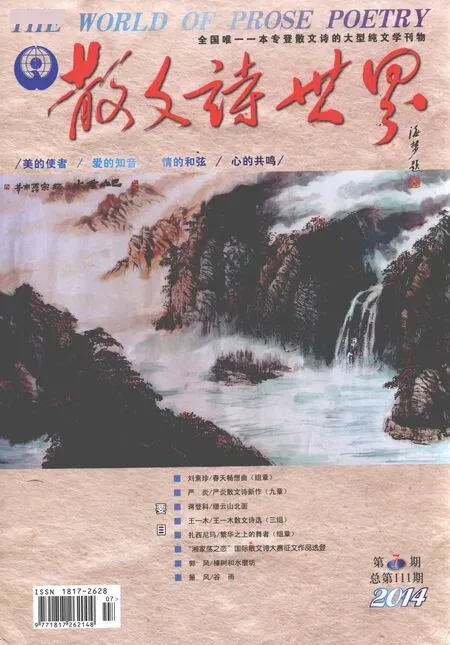拷問失落棱角的溫柔刀—宓月散文詩《魯迅銅像》研讀
黃艷映
散文詩研究
拷問失落棱角的溫柔刀—宓月散文詩《魯迅銅像》研讀
黃艷映

作為女性散文詩作家杰出代表的宓月,曾出版散文詩集《夜雨瀟瀟》《人在他鄉(xiāng)》《明天的背后》、長篇小說《一江春水》、詩集《早春二月》。這位出生江南水鄉(xiāng)的才女與魯迅是同鄉(xiāng),向來以溫婉、恬靜、柔媚的抒情小品見長。但收錄在《明天的背后》的懷古散文詩《魯迅銅像(外一章)》卻鮮有地向我們展示出硬朗的思辨、沉郁的審視和凝重的人文關(guān)懷,使我們看到了這位女性散文詩作家身上強大的理性力量。
縱觀全篇散文詩,拷問與反思分別是作品的外顯和蘊藉。宓月借助在魯迅銅像面前的所見所想,以女性特有的溫柔細(xì)膩,帶領(lǐng)讀者一路拷問自己,拷問這個時代,拷問這個民族已經(jīng)腐化的靈魂,一路反思自己的過去,反思現(xiàn)代人的人生歷程,反思這個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如果說,魯迅以筆為劍,直刺黑暗的心臟。那么宓月的這篇《魯迅銅像》便是散發(fā)著寒光的溫柔一刀,正所謂鈍刀慢剮,將這些麻木的現(xiàn)代橡皮人逐漸肢解。
拷問與反思一直貫穿于整篇散文詩中。開篇就出現(xiàn)極具震撼力的設(shè)問:“不再需要投槍和匕首了,在這個并不平靜的和平年代?/頭發(fā)像刷子一樣豎起來,僅僅是為了時尚?”兩個設(shè)問感情色彩濃烈,對比鮮明。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和平年代里有著許多不平靜,但每個人卻慣于安逸與享受,選擇忽略這些不平靜,甚至是對罪惡與黑暗視而不見。過去直刺黑暗心臟的武器都統(tǒng)統(tǒng)被丟棄。而“像刷子一樣豎起來的頭發(fā)”是魯迅冷峻形象的一大特色,現(xiàn)在卻僅僅把它當(dāng)做為了時尚,這樣帶有幾分不敢相信和近似諷刺的質(zhì)問,給人以巨大的反差,如一面穿透內(nèi)心的照妖鏡,讓你我他都自動對號入座。同時奠定了全文沉重悲痛的情感基調(diào)。緊接著就是一連串的自我反思:“人們把你塑成雕像,以此證明,你依然和我們在一起。/只是,你的目光總是投向遠(yuǎn)處,那個我們看不見的世界。/慕名而來的人們,爭搶著與你合影,仿佛自己真的與偉人站在了一起。/憂憤、彷徨和吶喊,隨著一個時代的足音遠(yuǎn)去了。”人們紀(jì)念這位偉人,把他塑成了雕像,爭相與他合影,以為這便是與他同行,殊不知自己已經(jīng)與偉人的精神境地相去甚遠(yuǎn)。我相信,那個我們看不見的世界,除了有遠(yuǎn)去的憂憤、彷徨、吶喊,一定也存在著詩人對正身處的這個時代的憂患感與責(zé)任感。
“嚼著口香糖的年輕人,用手機從不同的角度自拍著,他在告訴遠(yuǎn)方的朋友,他正在你身邊。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走來,表情肅穆地在你旁邊站了兩秒,就挽著一個女子消失在了人群中……”這么一段富有畫面感的描寫應(yīng)該是全首散文詩中最具有思辨色彩和藝術(shù)特色的工筆描寫,頗有魯迅洞悉人性之風(fēng)。嚼著口香糖自拍的年輕人并非不懂得對偉人心懷敬意,而將偉人形象散播到遠(yuǎn)方去;西裝革履的男子也未必就是在肅立致敬,也只是為在伊人面前舉止瀟灑。這種鮮明的對比是詩人對人情世事的冷靜審視,運用了辨證法思維揭開了現(xiàn)代人慣于偽裝的面紗。
隨后,詩人筆鋒一轉(zhuǎn),用小侄女與魯迅的淵源為過渡,筆觸立即引到“我”的身上。共同的故鄉(xiāng),熟悉的人和景,相似的童年記憶都讓詩人倍感親切。百草園、三味書屋、魯迅路、玩蟋蟀、聽故事,這都是“我”與偉人實實在在的交集,而“我”也曾經(jīng)想把自己提升到“民族魂”的高度。散文詩的第一部分到這里結(jié)束。而引領(lǐng)全詩的第二個拷問出現(xiàn):“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對這個世界,我再也沒有了任何的驚奇?”作者從這里開始帶領(lǐng)讀者開辟一個嶄新的視野,以上文呈現(xiàn)的現(xiàn)實為依托,又不拘于現(xiàn)實的束縛,一步一步走進反思的國度。“支離破碎的現(xiàn)實,只是心上閃過的剎那光影。/世界永遠(yuǎn)不完美,成為我們不愿揭露丑陋的美妙借口。/沒有鋒芒的思想,灰霾一樣在我們頭頂飄蕩。/我們步履匆匆,日復(fù)一日地追逐忙碌,卻不知為了什么。”從“我”到“我們”,從個體到集體,尖銳地指出現(xiàn)代人麻木冷漠,對真善美缺乏追求,同時也不愿揭露假惡丑的共同時代特性。這與當(dāng)初那個“吃人”的舊社會有何區(qū)別?詩人是在反思中提醒我們?nèi)缃袢孕枰斞赴恪皺M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豪情哲思,提醒我們不能自欺欺人,庸庸碌碌地度過一生。
“有時候,我的心口會莫名奇妙地在半夜里疼痛不止。沒有陽光的時刻,黑暗就會在心上堆積。選擇一條灰色地帶讓自己坦然茍活,哪怕成為橡皮人,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許多時候,我總是羞于說:‘紹興,我的故鄉(xiāng)……’我已習(xí)慣了喧囂,習(xí)慣了綿軟的吟唱,習(xí)慣了自己的聲音消失在紛繁嘈雜之中……”詩人這把溫柔刀不單單向著時代,向著現(xiàn)代社會的“橡皮人”,更向著自己灰霾堆積的心臟,細(xì)細(xì)的削磨。這種近乎自虐的自我剖析,大大地增強了自我反思的表現(xiàn)力。雖然作者說即使坦然茍活在灰色地帶上,成為無知無覺的橡皮人也沒什么關(guān)系。有人覺得這里會表現(xiàn)出一點點的無奈與頹廢。如果我們是這樣理解的話,就從根本地與整篇散文詩要表達的情感相悖了。因為在“哪怕成為橡皮人”之前,作者別出心裁地插入一個情感的前提:“有時候,我的心口莫名其妙地疼痛不止。”如果真如作者說成為了“橡皮人”,心口又怎么會疼痛不止呢?實際上,作者是在以“我手寫他心”,每一個麻木冷漠、自欺欺人的現(xiàn)代人都可以成為那個“哪怕成為橡皮人都沒關(guān)系”的“我”。作者以俯瞰的姿態(tài),讓讀者自動代入那個茍活的“我”,極富有感染力,也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鳴,是全篇散文詩沉重的情感的進一步加深和強調(diào)。連說的三個“習(xí)慣了”更是突顯了對現(xiàn)代社會這些不良現(xiàn)象淡淡的失落感。
最后一節(jié)的抒情是整篇散文詩情感的高潮,對魯迅的隔空喊話具有濃重的警醒意味:“為了讓自己的脊椎挺直,你不拒絕苦難和多舛的命運。即使只有一條逼仄的路可走,你也要走出一個有棱有角的人生。/我們在妥協(xié)中變得珠圓玉潤,讓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偶爾也會聲嘶力竭,謾罵一堆堆垃圾讓我們嗅不到生活的馨香。/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只是濺起的一粒塵埃。在自大與謙卑之間,我們往往站錯了位置。”魯迅選擇一條逼仄的路,活出一個有棱有角的人生,我們卻習(xí)慣了妥協(xié),對真理和正義缺乏追求,甚至用雙手蒙蔽自己的眼睛,欺騙自己一切都很美。沒有了該有的棱角,也沒有感知人生的覺悟,對歷史對社會更是起不到推動的作用,這便是作者最為失望最為痛心的事。散文詩的最后采用虛實相生的手法,凝造了一個悲涼又沉郁的氛圍:“唯有大陸新村9號傳出的一聲聲咳嗽,還在震顫著午夜的空氣。仿佛正在喚醒那些沉睡的靈魂,起來做些什么,做些什么……”這富有詩意的句子,讓我們仿佛看到魯迅抽著煙仍在他的居所細(xì)細(xì)看著這個世界,偶爾會發(fā)出一聲聲低沉的咳嗽聲,他正在用沉重的生命喚醒國民沉睡的靈魂,喚醒已經(jīng)失落的棱角。也許不僅是魯迅,還有作者,作者也在盡自己的力量喚醒這些沉睡的靈魂。
《魯迅銅像》是一篇富有現(xiàn)代意識的懷古散文詩,它的出彩之處在于:一是視野開闊,從現(xiàn)實寫到歷史再回歸現(xiàn)實,從身邊的人寫到自己再寫到整個社會的人,內(nèi)容與思想充實,意境廣闊;二是抒情主體的變換自然含蓄,富有深意。抒情的筆調(diào)往往隨著抒情的主體“我”、“魯迅”、“我們”的轉(zhuǎn)換而靈活變動,或沉郁或靈動或冷峻,使得抒情主體立體化,增強散文詩感情的層次感;三是思辨色彩濃厚,彰顯理性的光輝。全篇散文詩雖然透露出作者的悲憤感,但在失落中卻處處閃動著希望的靈光——有把魯迅銅像介紹到遠(yuǎn)方朋友處的年輕人,有像“我”一樣懂得反思現(xiàn)實的人,還有一直在喚醒沉睡靈魂的人。歷史給予我們的還沒有完全磨滅。四是以現(xiàn)代意識“懷古”、“化古”的新穎手法。在歷史的遺跡里注入時代氣息,引發(fā)一些新的思考。開頭的兩節(jié)便是最具代表性:“不再需要投槍和匕首了,在這個并不平靜的和平年代?/頭發(fā)像刷子一樣豎起來,僅僅是為了時尚?”通篇下來,古今融合的地方處處可見,碰撞之處更能激起內(nèi)心的動蕩。正如波德萊爾所說,散文詩,它以幾分柔和,幾分堅硬,和諧于心靈的激情、夢幻的波濤和良知的驚厥。
詩人曾經(jīng)寫道:“歲月的潮音,回蕩在歷史的心壁,唱一路悲歌,穿透日月星辰,留給人類一個沉甸甸的思考。”我想,《魯迅銅像》便是通過拷問與反思,唱一路悲壯的歌,磨刀霍霍,銷魂蝕骨,留給人類關(guān)于精神家園,關(guān)于生命發(fā)聲,關(guān)于追求真理,甚至關(guān)于憂憤、吶喊、彷徨的一個沉甸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