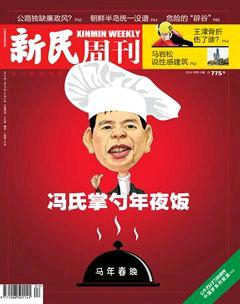探求陶瓷非語言符號的內涵
許國良+吳元浩

觀賞古陶瓷器,就是解讀一部文化史。古陶瓷的器型和器表裝飾上的一些非語言符號,可以給我們明確的斷代提示。其中具象的物體是可以用自然語言和文字表述的,但是表象的變化,絕非用文字描述能夠說得明白。識別這個符號系統需要運用視覺、聽覺、觸覺、嗅覺、指叩、掂量等方法,通過這些識別方法獲得的提示,也是提供給我們作出鑒定結論的客觀依據。如果我們把陶瓷器比喻為一件旗袍的話,那么這陶瓷的胎,就是這件旗袍的面料;器型,就是旗袍的款式;器表裝飾就是旗袍的顏色和圖案花紋。旗袍是從歷史上滿族婦女穿的長袍演變而來,清末以降,隨著西方文明的進入,長袍款式逐漸發生變化,形成了現代的旗袍。這種變化的動力來源于追求時尚的審美觀,而陶瓷器的變化也是如此,受時風影響愈深愈顯。一件陶瓷器就是一個綜合信息載體,承載著一些很難用語言交流說清楚的內容。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入手。一,器型。器型的演變是一門學問,在考古學叫“類型學”。器型的型態變化是可以用語言敘述的,但是它的神態變化,比如豐滿、深厚、古樸、柔和、圓潤等,是對一件器物與其他朝代器型相比較而得出的結論,這就需要經驗的積累和比較。二,裝飾。器表裝飾指的是在成型的瓷胎坯體上采用刻畫、印紋、堆塑等技法或再涂上不同的顏色釉,在“面料”上直接進行的裝飾;一種是“色釉”品種,是指在“面料”成型以后,用含有金屬氧化物呈色劑的釉料,對“面料”表面進行“染色”;一種是“彩繪”品種,是指在成型的瓷胎坯體或經過高溫燒成的瓷器表面上,用含有金屬氧化物的礦物彩料的繪畫裝飾。所有的裝飾必有其含義,意態呈現的,恰恰是文化屬性,是不同歷史階段所表現的文化內容。三,色差。器表都有色,各類器表裝飾顏色會有差異,同一時期的相同產品,都會呈現不同的色差。陶瓷器的呈色是可以用語言來描述的,哪怕是細微的差異,都可以進行化學分析。表象的變化,例如不同的使用環境、不同地區的窯場、出土的、海撈的、外銷回流的商品、家傳的等等,它們各自形成的“色差”,呈現給我們視覺系統的是不同的識別符號,有的就很難用自然語言來說明。四,色澤。色澤的“色”反映的是顏色,“澤”反映的是亮度。色是光作用于物體反射,通過視覺產生的印象;澤是光作用物體的亮度。同一件物體由于擺放的位置不同,都會在顏色和亮度上發生變化。還有缺陷等要素,或帶有偶然性,或帶歷史性,都需要符號的提示才能加以識別。所以我們主動去探察這些非語言符號所提示的內涵,就是要將這些看似獨立但卻相互關聯的信息梳理清楚,熟悉它們之間非語言符號表達的內容,了解它們自己敘述的故事。
掌握陶瓷非語言符號的內涵,會帶給我們三個方面的好處:
一是幫助斷代。一件陶瓷器所反映的非語言符號信息,一經掌握了它們的真實內容,所做出的結論都應該是真實的、靠得住的結論。這些信息的好處在于,已給了你明確的斷代指向。對這些信息必須諳熟于此,嫻熟于心,學習識別非語言符號的過程,就是學會掌握鑒定方法最重要的途徑。二是幫助識貨。識貨就是要“搞明白”,只有“搞明白”,才敢買、敢收藏。這些信息會告訴你一件器物的收藏價值在哪里。三是有助于提高欣賞能力。正因為陶瓷器上的非語言符號,更能反映豐富的歷史文化與完美形式的審美價值,從中體會出并獲得這些豐富多彩的視覺享受,這就是欣賞。而擺在我們面前的關鍵是,要去探察然后讀懂那些符號的真實含義。
我們耗費數年時間撰寫了《陶瓷考辨覽要——742件實樣非語言符號圖解》(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一書,就是希望從陶瓷非語言符號入手,試圖解讀中華文明的未解之謎。
信息
清代皇室琺瑯器杭州首展
15日至春節期間,近百件中國清代皇室及民間琺瑯精品在杭州亮相。琺瑯又稱“佛郎”、“法藍”。在中國,琺瑯器分為兩種:一是源自波斯的銅胎掐絲琺瑯,約在蒙元時期傳至中國,明代開始大量燒制,并于景泰年間達到了一個高峰,后世稱其為“景泰藍”。此后,景泰藍就成了銅胎掐絲琺瑯器的代稱;另一種是來自歐洲的畫琺瑯工藝,它在清康熙年間從廣州口岸傳入中國,并達到頂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