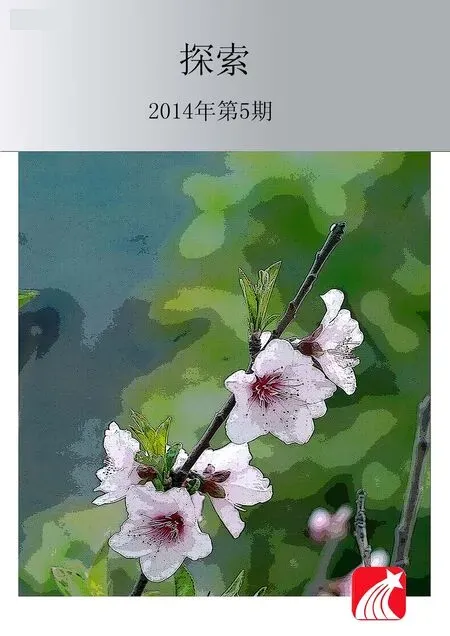試論中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特色
侯保龍,喬耀章
(1.安徽科技學(xué)院思政理論教研部,安徽蚌埠 233100;2.蘇州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江蘇蘇州 215123)
中國社會治理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用“社會治理”取代以前的“社會管理”的提法,并且提出“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制”的重大任務(wù)。這絕非純粹的概念替換,而是立足國情、積極借鑒現(xiàn)代西方社會管理的最新成果作出的戰(zhàn)略抉擇,標(biāo)志著我國開啟了構(gòu)建中國特色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歷史進(jìn)程。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特色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社會管理理論的指導(dǎo)思想特色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管理思想致力于追求社會的平等和解放,致力于消滅剝削和消除階級差別,實現(xiàn)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提出“社會治理”的概念,但是其社會管理的基本理論意蘊卻與現(xiàn)代治理理念高度吻合、甚至達(dá)到“善治”的境界。這條紅線貫穿于社會治理體制改革進(jìn)程。
社會主義社會管理奉行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根本原則。馬克思、恩格斯認(rèn)為,社會管理是政治統(tǒng)治的基礎(chǔ),一切社會管理方式都是政治統(tǒng)治的工具。“一切政治權(quán)利起先總是以某種經(jīng)濟(jì)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chǔ)的。”[1]在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統(tǒng)治總是大量地以維護(hù)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管理的面貌出現(xiàn),而在本質(zhì)上維護(hù)的卻是資產(chǎn)階級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社會實現(xiàn)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當(dāng)家作主,從而為實現(xiàn)社會管理最大程度的公共性提供了基本政治前提。從根本上看,社會主義的社會管理體現(xiàn)“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quán)利的平等……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fù)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fù)活”[2]。在社會主義國家,貫徹社會管理的公共利益至上原則應(yīng)成為人民群眾的自覺遵循。
社會主義社會管理要實現(xiàn)社會服務(wù)對政治統(tǒng)治的超越。國家階級本質(zhì)決定社會管理的性質(zhì)。無產(chǎn)階級國家的建立是實現(xiàn)社會管理服務(wù)性的先決條件。社會主義社會管理本質(zhì)上是無產(chǎn)階級的自我管理,決定其根本性質(zhì)的是社會服務(wù)性而非政治統(tǒng)治。巴黎公社是實踐無產(chǎn)階級社會管理服務(wù)性質(zhì)的一次偉大嘗試。公社把國家政權(quán)重新收回,把它從統(tǒng)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巴黎公社“是終于發(fā)現(xiàn)的可以使勞動在經(jīng)濟(jì)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馬克思指出:“從前有一種錯覺,以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職務(wù),只能委托給一個受過訓(xùn)練的特殊階層,即國家寄生蟲、俸高祿厚的勢利小人和閑職大員,這些人身居高位,收羅人民群眾中的知識分子,把他們放到等級制國家的低級位置上去反對人民群眾自己。現(xiàn)在錯覺已經(jīng)消除。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wù)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責(zé)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zé)任制,因為這些勤務(wù)員是在公眾監(jiān)督下進(jìn)行工作的”[4]。在這里,馬克思揭示了階級社會社會管理根本的政治統(tǒng)治性質(zhì),指出了未來共產(chǎn)主義社會管理的社會服務(wù)性質(zhì)及其實現(xiàn)條件,即社會等級制的消除和真正責(zé)任制的推行。隨著新型的政府與公民平等關(guān)系的確立,以及社會公眾參與下政府責(zé)任制的實現(xiàn),社會管理就可以回歸社會服務(wù)的根本性質(zhì)。
社會主義社會管理主體的變遷應(yīng)尊重社會發(fā)展的客觀實際。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確保人民主體地位是社會管理的最高原則。“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qū)儆谌嗣瘛⒂扇嗣裾茩?quán)的政府的趨勢。”[1]社會主義社會管理主體變遷的基本趨勢是國家的作用在不斷減弱而社會的作用在不斷增強,最終達(dá)到“自由人聯(lián)合體”的自治境界。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群眾參與社會管理成為基本準(zhǔn)則,但社會管理還不能盲目排斥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恩格斯辯證地指出,我們要反對把政府權(quán)威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公民自治原則說成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quán)威與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yīng)用范圍隨著社會發(fā)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1]。我們評價一種社會治理方式或模式的優(yōu)劣,不應(yīng)簡單地看這種治理模式中政府的作用多一點還是社會的作用多一些,而要看這種社會治理模式是否促進(jìn)了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是否促進(jìn)了社會公平正義,是否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hù)。
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總依據(jù)特色
社會治理體制總是與一定社會性質(zhì)和發(fā)展?fàn)顟B(tài)相適應(yīng)。一般來說,有什么樣的社會,就需要什么樣的社會治理體制。十三大以來,我們黨和政府不斷強調(diào)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八大首次明確: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jù)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社會治理體制改革也必須從這個最大實際出發(fā)。
中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應(yīng)適合現(xiàn)階段我國農(nóng)業(yè)社會和工業(yè)社會相混合的特征。美國著名的行政學(xué)家弗雷德·W·里格斯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稱為“棱柱型社會”,認(rèn)為它是一種由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變遷中的過渡社會。在我國現(xiàn)階段,新舊體制的交匯和轉(zhuǎn)化、社會結(jié)構(gòu)、價值系統(tǒng)、行為模式的巨大變化都使我國社會具有明顯的棱柱型社會特征。這是我國社會變遷必須和正在經(jīng)歷的一個相當(dāng)長的社會大過渡、大變遷的階段。在棱柱型社會的社會管理中,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較為明顯的人治型社會管理的痕跡;同時,改革開放的中國已經(jīng)走上了工業(yè)化的軌道,工業(yè)社會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占主導(dǎo)地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也表現(xiàn)了較高的管理效能,但國家機(jī)構(gòu)和制度的建設(shè)還不完善,社會組織的發(fā)展則較為脆弱,社會還存在較為濃厚的國家依賴思維。政府對社會治理承擔(dān)了更多的責(zé)任。
中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應(yīng)兼顧現(xiàn)階段我國多質(zhì)態(tài)社會的特征。在我國,傳統(tǒng)社會遺跡、現(xiàn)代社會基礎(chǔ)和后現(xiàn)代萌芽同時并存,有學(xué)者把這種復(fù)合社會稱為典型的“多質(zhì)態(tài)社會”或“差異性社會”。“如果從歷時態(tài)和共時態(tài)同時考究我國的社會,就會發(fā)現(xiàn)我國社會呈現(xiàn)著由過去的遺跡、現(xiàn)實的基礎(chǔ)和未來的萌芽三種社會質(zhì)態(tài)共存或并存的局面”,“尤其是社會主義質(zhì)態(tài)和資本主義質(zhì)態(tài)共生并存”[5]。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從封建社會繼承下來的包袱很重,經(jīng)濟(jì)社會文化很不發(fā)達(dá),需要在相當(dāng)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去完成經(jīng)濟(jì)社會轉(zhuǎn)型,從而使社會主義建立在較堅實的經(jīng)濟(jì)社會基礎(chǔ)之上。然而,由于諸多復(fù)雜的歷史因素,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僅僅存在七年時間便匆匆進(jìn)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lǐng)域仍然要繼續(xù)完成新民主主義社會應(yīng)該完成而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wù)。那么,這種特殊的社會現(xiàn)實,必然反映到我國的社會治理體制中來。因此,我國的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現(xiàn)實依據(jù)就在于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狀況的具體分析。在某些區(qū)域和領(lǐng)域,社會治理還不能告別政治統(tǒng)治方式,但對于總體上處于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廣大中國社會而言,政府主導(dǎo)、社會參與應(yīng)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基本模式。只有全面地抓住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多面相特征,才可以防止出現(xiàn)社會治理體制改革中滯后于中國社會發(fā)展實際的保守主義傾向,又可以抵制社會治理體制改革中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社會治理模式的教條主義傾向。
三、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歷史使命特色
中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目標(biāo)如何定位,其歷史使命是什么,這是中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關(guān)于這個問題,《決定》中做出了實事求是的回答,即“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維護(hù)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fā)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jìn)平安中國建設(shè),維護(hù)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yè)、社會安定有序”。這個界定,包含了實現(xiàn)社會穩(wěn)定的一般目標(biāo),還內(nèi)含著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歷史使命。正是后者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與資本主義社會治理體制的本質(zhì)區(qū)別之一。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wù)是實現(xiàn)民族復(fù)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為此,我國需要長期的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環(huán)境,這是我國最基本的社會治理目標(biāo),我國一切社會治理都要有利于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這也是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根本出發(fā)點和基本前提。同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社會治理目標(biāo)不能僅僅滿足于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而應(yīng)該在此基礎(chǔ)上追求更加高遠(yuǎn)的社會治理目標(biāo):我國應(yīng)把維護(hù)社會公平正義作為社會治理的崇高目標(biāo)和歷史使命,即通過有效的社會治理,激發(fā)社會活力,實現(xiàn)社會的公平和公正,保持社會和諧。如果說共產(chǎn)主義是一個人人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社會,是一個真正實現(xiàn)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那么,作為共產(chǎn)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其社會治理就應(yīng)當(dāng)自覺地把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崇高的歷史任務(wù),以期不斷地為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高級階段的宏偉社會理想而積極準(zhǔn)備條件。從我國社會治理的現(xiàn)實要求來說,在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中應(yīng)特別注意處理好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與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兩者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只有把維護(hù)社會公平正義作為社會治理不懈追求的目標(biāo),才能從根本上持久地實現(xiàn)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
維護(hù)社會的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治理的根本追求,是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區(qū)別于資本主義社會治理的本質(zhì)特征。從根本上說,我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歷史使命根源于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zhì)。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nèi)在要求。”[6]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zhì)最終要體現(xiàn)在無產(chǎn)階級的人類關(guān)懷、社會關(guān)懷和人民利益關(guān)懷上。胡鞍鋼等認(rèn)為,“從社會來看,公平是人類社會穩(wěn)定和秩序的基石,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和效率的源泉。從個體來看,公平是人的首要利益和首要價值,是人自由全面發(fā)展的最大動力”[7]。因此,只有努力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才有真正的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才能逼真地體現(xiàn)出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才能讓人民群眾真切地看到社會主義的光輝前景。社會公平正義呼喚著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而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也把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當(dāng)做自己的歷史使命。
四、“政府主導(dǎo)+社會參與”的模式特色
一定的社會治理模式總是一定國家社會實踐的產(chǎn)物。西方國家的社會主導(dǎo)、弱化政府作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在西方,國家與社會之間權(quán)能分立的歷史傳統(tǒng)源遠(yuǎn)流長。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以及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地位的確立,資本主義的公民社會從一開始就以對立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國家或政府的面前。在西方的社會管理理念中,作為“無賴”道德預(yù)設(shè)的國家和政府總是難以擺脫社會懷疑、對立的目光。當(dāng)然,這種尊重社會自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既反映了人類社會治理中心下移的一般趨勢,又是西方特定的國家-社會傳統(tǒng)長期發(fā)展的歷史產(chǎn)物。近年,我國學(xué)者對多中心治理模式基礎(chǔ)的公民社會理論進(jìn)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認(rèn)為“公民社會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編造出來的一個粗糙神話,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國人追求的是構(gòu)筑一個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人民社會”[8]。“人民社會”概念的提出,是對西方“公民社會”概念的挑戰(zhàn)和超越,是一種新型的社會與國家關(guān)系的闡釋。胡鞍鋼等認(rèn)為:“人民社會是一種源于中國文化、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全體人民所構(gòu)成的社會主義社會。”[9]
與西方濃郁的政社對立思維不同,中國是一個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府與社會協(xié)同的“人民社會”。因此,“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的主體至少應(yīng)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國家中心主義視域下的政府,二是人本主義視域下的現(xiàn)代公民社會”[10]。如果離開黨和政府的核心領(lǐng)導(dǎo)而盲目地照搬西方社會治理模式,就會出現(xiàn)群龍無首、利益失衡和“公地悲劇”的治理亂象。實際上,中國社會治理模式深深扎根于中國豐厚的歷史文化之中,源源不斷地從中汲取養(yǎng)分。希爾斯認(rèn)為,人們總能在傳統(tǒng)中找到解決現(xiàn)代問題的方法,盡管傳統(tǒng)的東西并不都具有有益于人類的價值[11]。我國社會向來有依賴和相信政府的社會傳統(tǒng),政府官員也有根深蒂固的“父母官”情結(jié)。從歷史上看,凡是政府強大時社會往往穩(wěn)定繁榮,而政府弱小時社會往往會動蕩不安。所以,我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不能不尊重這一中央政府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的歷史傳統(tǒng),充分尊重和發(fā)揮黨和政府在中國社會治理體制中的領(lǐng)導(dǎo)核心和中流砥柱作用。其實,“在任何社會中,政府有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即使在網(wǎng)絡(luò)化治理體系成熟完善的制度條件下,政府依然是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的中樞,是發(fā)動、引導(dǎo)、激勵和監(jiān)管各種社會組織合作的重要力量”[12]。
另一方面,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是社會治理民主化的必然趨勢。在我國,政府與社會民眾和社會組織不是對立的關(guān)系,而是一體化的關(guān)系;不是相互沖突的關(guān)系,而是和諧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政府應(yīng)堅定地實行政社有序分開,完成政府社會管理職能的真正轉(zhuǎn)變。黨和政府應(yīng)以向歷史負(fù)責(zé)的態(tài)度,采取切實有效的舉措盡力培育和發(fā)展社會組織,促進(jìn)“人民社會”自治能力的成長,努力塑造政府與社會的良性合作關(guān)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政府要“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xiàn)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diào)節(jié)、居民自治良性互動”[13],充分尊重和發(fā)揮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中的巨大作用。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總效應(yīng)是形成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優(yōu)勢互補的社會治理關(guān)系和社會治理格局,這就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的巨大優(yōu)勢和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顯著特色。“政府與公民、社會組織的良好合作關(guān)系,不僅有利于對公民權(quán)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更有利于社會治理活動的順利開展,更有利于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使社會建設(shè)和治理活動達(dá)到和實現(xiàn)良性發(fā)展的目的。”[14]如果遵照該模式,就會形成“黨委領(lǐng)導(dǎo)、政府負(fù)責(zé)、社會協(xié)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格局。其中,黨委領(lǐng)導(dǎo)是核心,政府負(fù)責(zé)是關(guān)鍵,社會協(xié)同是依托,公眾參與是基礎(chǔ),法治保障是基石。五位一體,有機(jī)聯(lián)系,密不可分。有學(xué)者也稱之為“混合治理模式”,是介于政府管制與公民自治之間的一種治理模式[15]。這種治理模式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大變遷、大過渡的基本特征相適應(yīng),與我國悠久的社會管理傳統(tǒng)相傳承,與當(dāng)今世界社會治理大勢相呼應(yīng)。總之,我國的社會治理模式既不是片面強調(diào)黨的領(lǐng)導(dǎo)與政府管理而一味排斥社會參與,也不是片面強調(diào)社會自治而否定黨和政府的有力領(lǐng)導(dǎo),而應(yīng)成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黨政主導(dǎo)的、尊重社會參與的社會治理模式。
參考文獻(xiàn):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喬耀章.多質(zhì)態(tài)社會管理中的共同性與差異性[J].甘肅社會科學(xué),2012(4).
[6]本報評論員.圍繞“兩個關(guān)系”加強黨的領(lǐng)導(dǎo)——論學(xué)習(xí)貫徹習(xí)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重要講話[N].人民日報,2014-01-10.
[7]胡聯(lián)合,胡鞍鋼.中國夢:中國每一個人的公平發(fā)展夢[J].探索,2013(3).
[8]王紹光.“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J].人民論壇,2013(22).
[9]胡鞍鋼,王洪川.人民社會是“中國夢”最大動力[J].人民論壇·學(xué)術(shù)前沿,2013(13).
[10]林世選.論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中的公民意識自覺[J].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3(4).
[11]希爾斯.論傳統(tǒng)[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2]藍(lán)志勇,魏明.中國現(xiàn)代化治理體系的方向和策略[J].新華文摘,2014(9).
[13]本書編寫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dǎo)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4]周曉麗,黨秀云.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機(jī)制、理念及其啟示[J].南京社會科學(xué),2013(10).
[15]王學(xué)杰.從政府主導(dǎo)到公民自治:我國社會治理工具發(fā)展的基本取向[J].理論探討,2014(1).
——關(guān)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