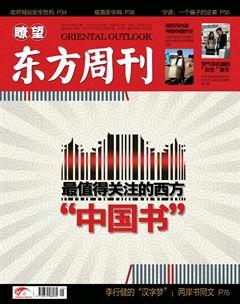闡釋時代和“時代的闡釋”
劉伊曼

2013年,一個特別的公益廣告席卷了整個中國。從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屏幕,到成都地鐵里的大燈箱,以及天津、南京、青島、西安……幾乎所有中國城市的工地圍擋板上,都可以看到一組以“中國夢”為主題,以“泥人張”彩塑、楊柳青年畫、豐子愷漫畫等傳統藝術為表達方式的宣傳畫。
那個一襲紅衣、小手托著下巴、圓圓滾滾的胖女娃,伴著“中國夢,我的夢”的大主題,獲得了覆蓋大江南北的出鏡率。她的創作者—天津“泥人張彩塑工作室”的林鋼,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自己都沒有想到,這個被自己命名為“憧憬”的彩塑作品,會被這樣“發現并升華”。
傳統藝術何以安身立命
清朝末年,擅長捏泥人的窮孩子張明山將泥塑做成了遠近聞名的家族生意,開創了中國民間工藝美術的著名流派,并得名“泥人張”。歷經近半個世紀的內憂外患,在天津這個商業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城市,“泥人張”的絕活不僅傳承了下來,還成為了這座城市的一張名片。
1949年之后,張氏的幾位傳人有的做了天津市文史館館長,有的受聘到中央美院等高校任教。而對保存“泥人張”流派的彩塑工藝最為重要的是,1959年天津成立了“泥人張彩塑工作室”,歸天津市文化局下屬,并招收了第一批學員。“泥人張”正式成為一個事業單位。
“按現在的話來說,這其實就是搶救。”“泥人張彩塑工作室”高級工藝美術師林鋼告訴本刊記者,其實當時張家的后人已經沒有幾個在做泥人了,如果當時不成立這個工作室,不招收學員,“泥人張”很可能早就瀕臨失傳的境地。
“泥人張彩塑工作室”一直不斷從美院招收畢業生,教給他們這一傳統工藝,培養出的幾代學徒有的陸續轉行,有的留下鉆研精進。許多優秀的學徒在學習掌握“泥人張”傳統技法的同時,開創出各自不同的風格。
“雖然說藝術有它的生命力,但是傳統的東西與現在畢竟是有隔膜的。就比如說京劇,現在的人如果不是從小長期接觸,很難對它有興趣。所以,傳統藝術有沒有國家的重視和保護,差別會很大。”與林鋼同時期進入“泥人張彩塑工作室”的高級工藝美術師張玉生對本刊記者說。
張玉生所說的“差別”,在天津三大民間藝術的不同命運上就能體現。半個世紀前,“泥人張”成立了工作室,楊柳青年畫成立了畫社,都歸文化局管,不僅搜集、留存了很多珍貴的老作品,也都開枝散葉,培養出了幾代傳人。然而,一百多年前同樣出名,和“泥人張”一樣獲得過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的天津“風箏魏”卻逐漸式微。
1949年以后,“風箏魏”沒有像“泥人張”那樣成立工作室,一直局限于家族內部傳承。今天,雖然還有魏氏后人以“風箏魏”為名開風箏店,但一些古法手藝已經失傳,作為一門工藝流派,它面臨著傳承和發展的困境。
鮮明的時代特色
在計劃經濟時代,“事業編制”為搞工藝美術的人們提供了重要平臺。他們不僅有相對穩定的收入和相對充裕的創作時間,也獲得了“采風”的合法身份。民間的彩塑藝術靈感源于生活,“泥人張”的工藝美術師和學徒們每年都會外出“體驗生活”以獲取靈感和素材,作品也因此記錄見證闡釋著時代精神。
1978年,第五代“泥人張”的代表人物楊志忠創作了一件佤族少年跟幾只鵝“打架”的泥塑,被選入了人教社小學二年級語文課本,課文名叫《顆粒歸公》,講述的是“弟弟”為了保護公家的糧食跟自家的鵝對峙,被路過的“泥人張”看見并表揚,然后為他塑像的故事。佤族少年雙手高高托舉著麥穗,睜大圓圓的眼睛瞪著幾只跟他搶糧食的鵝,這個藝術形象以及“大公無私”的教育闡釋,一起留存在許多70后、80后的記憶里。
“現在我們也會下鄉采風,但是跟那個年代是完全不一樣的。”張玉生告訴本刊記者。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一個春天,他和林鋼一起到河北興隆的鄉村體驗生活,出發前,先要拿本地糧票換全國糧票,到單位開介紹信、蓋章。到了河北之后,要先到當地縣里交介紹信,然后讓縣里的文化局或者宣傳部再開一個介紹信到鄉鎮,鄉鎮里再給安排一個接待他們的村子,在老鄉家里吃住。白天,大人們下地干活去了,他們就跟村子里的小孩一起玩,給他們捏泥人。
正因如此,從“泥人張彩塑工作室”陳列在櫥窗里的成千上萬件作品中,人們可以清晰地找到不同時期,不同民族和地區的記憶。而這些有著鮮明時代特色的作品,又被一代代的欣賞者發掘、闡釋,賦予新的意義,投射進現實中去,表達人們新的想法和價值觀。
2013年,被選中進入“中國夢”系列宣傳畫的還有高級工藝美術師孫永升的一套作品─《村官》。一個女大學生村官,背著背包,戴著鴨舌帽,蹲在地上跟老鄉一面交談,一面用本子做筆記。其形象與村官的傳統形象迥然不同。
有趣的是,因為那位女大學生村官的形象太像記者,所以在“中國夢”系列宣傳畫里,這組作品被改名為“新聞戰線走轉改,基層采訪中國夢”。
面臨考驗的楊柳青
與“泥人張”的作品一同入選“中國夢”系列宣傳畫的,還有很多天津楊柳青畫社的年畫作品。
在楊柳青畫社的博物館里,收藏著6400多塊畫板和1300多種畫樣。博物館一位工作人員向本刊記者介紹,歷史上,天津楊柳青有很多家年畫店,創作出了大量畫式和雕版。即便是在很艱難的歷史時期,楊柳青年畫依然充滿了蓬勃的生機和創造力。
傳統的楊柳青年畫作品里,有大量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話宣傳優良民風的作品。這些作品多由當時的官方出畫樣,委托畫店制版印刷,然后張貼在鄉間市集,成為早期的“公益廣告”。比如一幅講述愛說謊話的“王大謊”真遇到麻煩時沒人再相信他的老年畫,這次就被“中國夢”系列公益廣告發掘出來,以“誠信”為題再次展現在世人面前。
在大半個世紀的戰爭動蕩中,大量畫版曾被八國聯軍、侵華日軍、國軍等部隊征集了去當柴燒,還有很多畫版流落民間,變成雞窩棚、搓衣板。近年來,因為出版業本身的變遷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雕版印刷的楊柳青年畫工藝正漸漸失去市場。
而最為核心的,是藝術的創新能力面臨嚴峻考驗。
和“泥人張工作室”一路“事業”到底不同的是,楊柳青畫社在改革開放之后改制,開始了企業化管理。雖然依舊歸屬于文化局,但財政上開始獨立,對藝人們而言,績效和考核變得非常重要,潛心搞創作的空間變小了。現在,重復生產更多,有影響力的創新的畫式作品較少,出售的年畫商品和延伸產品,也都是以老的畫式為主。
“年畫不能空洞無物,得有意義。”一位不愿具名的楊柳青畫師告訴本刊記者,對楊柳青來說,需要繼承和保護的不僅是雕版印刷的這種形式和藝術風格,更重要的是其精神內核,和不斷創新的審美表達能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