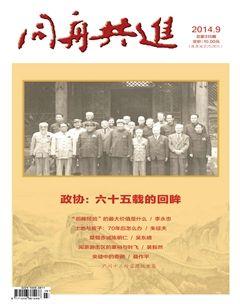紅塵冷眼,有“統”有“戰”
劉統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出席開幕式的各黨派、團體代表634人,來賓300人。這是決定新中國誕生的重要會議,也是中國歷史步入新時代的象征。
但這次會議是否完全如同電影《建國大業》表現的,中共領袖和民主人士濟濟一堂,親切握手,把酒同樂,一派普天同慶的氣象呢?當年政協代表宋云彬先生的日記《紅塵冷眼》,記載了許多有意思的細節。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回顧當年新政協會議前后發生的故事。
來到北平,如何與共產黨相處
新政協的召開,是中共中央發起和策劃的。
當時,由于蔣介石的迫害,大批民主人士寓居香港。周恩來煞費苦心,精心策劃如何把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運送到解放區,同時也要設法將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轉移到解放區來,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周密詳細的計劃。
這個秘密計劃的實施,驚心動魄,可以寫一部書。一批批的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登上輪船,前往解放區。宋云彬是與陳叔通、柳亞子、葉圣陶、鄭振鐸、王蕓生等20人安排在第三批北上的。1949年2月28日上船之后,他們莫不歡欣鼓舞,仿佛從地獄奔向天堂。葉圣陶興奮地賦詩一首:“南運經時又北游,最欣同氣與同舟。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這代表了他們的愿望:參與籌備新中國的建立。
3月5日,船到煙臺,大家終于踏上了解放區的土地。中共當地負責干部紛紛前來慰問,表示熱烈歡迎,使民主人士倍感溫暖。從煙臺去北平,鐵路尚未恢復正常,華東解放區組織了車隊,用轎車、吉普一站站護送,并組織他們沿途參觀。行至萊陽,安排在鄉村借宿。宋云彬解衣欲睡,“忽招待員又來,謂頃悉此間屋主系一肺病患者,故已為另覓借宿處,請即遷往云云,足見招待之周到也。”
11日,到華東局和華東軍區所在地濰坊郊區孟村。華東局設宴招待。“有一司令官名許世友者,發聲宏大,措辭簡潔。”宋笑謂同座:“此莽張飛也。”隨后,參觀國民黨戰俘營,會見濟南戰役被俘的王耀武等將領。王自稱被俘以來已讀書20余冊,頗有領悟。還自撰對聯:“早進來,晚進來,早晚要進來。先出去,后出去,先后都出去。”橫批:“你也來了”。又見剛從淮海戰場押來的杜聿明,“杜為戰犯,故不得與王耀武等同受訓練。足加鐐,狀至狼狽。(鄭)振鐸等均向之質問,彼答詞狡猾。”
經濟南、德州、滄州,汽車顛簸不堪,并時有故障。到東光“沿途見軍民趕修鐵路,至為緊張。一牛車載鐵軌一條,絡繹不絕。”天津開來專列,鄧穎超、楊之華親切迎接。18日列車到北平,葉劍英市長及沈鈞儒、郭沫若等先期到達的民主人士到車站迎接,并安排下榻六國飯店。“六國飯店陳設仿西洋式,被褥軟且厚,頗感過分溫暖”。
雖然旅途艱辛,但宋云彬等人體會到解放區干部群眾對他們的熱情和關心,感受是溫暖和幸福的。一路上,他們也體驗了解放區的生活,對共產黨有了初步的認識。但是到北平后,這些民主人士就面臨一個新問題:他們如何與共產黨相處。
由于國民黨長期的污蔑宣傳,民主人士對共產黨還是心存疑慮的。共產黨的政權中,能有民主人士的地位嗎?1948年底,中共的軍事勝利已成定局,號稱“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羅隆基以留滬民盟負責人的名義寫了一份給中共的建議書,請清華教授吳晗帶到河北省平山縣轉交中共中央。主要內容為:“1. 內政上實行議會制度;2. 外交上采取所謂協和外交方針(即對美、蘇采取同樣友好方針);3. 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黨的自由(鑒于民盟被國民黨宣布為‘非法團體失去了這個自由);4. 在盟內的共產黨員應公開身份,黨員和盟員避免交叉。”中共方面認為,這實際上是“同共產黨討價還價,如得不到同意,即不參加政協、不參加聯合政府,要作為在野黨同新政府進行斗爭”。吳晗和民盟的其他負責人都不同意羅隆基的意見,吳晗特別聲明:羅隆基的來信只代表他自己。最終,羅隆基只得放棄這些不切實際的要求。
大批國民黨軍政人員也面臨重大抉擇:是隨蔣介石逃往臺灣,還是留在大陸迎接新中國的成立。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劉斐,是國民政府赴北平和談代表團成員。和談失敗后,解放軍過江占領南京。劉斐思想斗爭十分激烈,是留北平呢?還是回南京?在毛澤東宴請張治中及代表團成員的宴會上,劉斐試探地問:“毛主席打麻將嗎?”毛澤東隨口應道:“曉得些,曉得些。”劉斐又問:“打麻將是清一色好還是平和好?”毛澤東想了想,笑著答道:“清一色難和,還是平和好。”劉斐豁然領悟:“平和好,那么還有我一份。”就這樣,毛澤東的一席話終于使張治中、劉斐下決心留在了北京。
民主人士到北平后,共產黨統戰部門不斷組織他們開報告會和座談會。對這些形式,宋云彬等人感到很不習慣,甚至內心反感。在日記中記載:4月10日,“下午開教育座談會。聽冗長之報告,殊不可耐。凡開會必有報告,報告必冗長,此亦一時風氣也。名為座談會,實則二三人作報告,已將全會時間占盡,我等皆坐而未談也。一笑。”
5月5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飯店作報告,由文管會以座談會名義邀請文化界人士出席,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談何可得也?周報告甚長,主要在闡明新民主主義真義及共產黨政策。然對文化界人士報告,有些淺近的道理大可一筆帶過。而彼乃反復陳說,頗覺辭費矣。”
5月12日,“晚與圣陶小飲,談小資產階級。余近來對于滿臉進步相,張口學習,閉口改造者,頗為反感。將來當撰一文,專談知識分子。”
這些知識分子不喜歡開會,不喜歡聽報告,他們喜歡什么?還是舊文人放蕩不羈的做派,宋的日記中,幾乎無日不喝酒。小酌四五兩,暢飲一二斤,逛書店,聽京劇。與民國的生活,沒什么不同。這些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擁護共產黨,在思想和行動上卻與新社會還有很大的距離。共產黨怎樣和民主人士共處?怎樣共同建立一個新政權?中共對他們一是團結,二是改造,雙方經歷了一個磨合的過程。
善意的批評
1949年3月25日,宋云彬“上午得通知,下午一時羅邁(李維漢)召開座談會,討論統戰問題。并謂為鄭重起見,特發入場券,將憑券入場云。下午二時許,座談會開始,羅邁宣布毛主席將于四時許到北平,請同人前往西郊歡迎云云,始知所謂座談會者,設辭也。”
組織民主人士迎接毛澤東,是中央統戰部的精心安排。發入場券,說明人選是精心挑選的。借座談會組織大家去西郊機場,既達到保密目的,也避免某些民主人士因去不了而鬧脾氣。可惜宋云彬沒體會到這是一種特殊待遇,陪著毛澤東閱兵也沒表現出什么特殊的感覺。
有一位則是激動不已,他就是柳亞子。柳亞子得以列為“鵠立”迎接的民主人士代表,覺得毛澤東對他是推重的。在起身赴北平時,柳亞子期待在新政府中獲得高位。2月22日他在給上海友人毛嘯岑信中寫道:“弟此次押貨內渡,平安到達,已與此間主顧接洽,估計有利可賺,甚為高興。”
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柳亞子與毛澤東唱和詩詞,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沁園春·雪》,豪邁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震動了國統區,也為柳亞子增色不少。柳亞子自視甚高,他認為共產黨人中能與自己相提并論的只有毛澤東,其他人都不足道。到北平后,這樣的狂語不斷升級。在《為韋江凡題〈故都緣法〉冊子二首》中,有句曰:“除卻毛公便柳公,紛紛馀子虎龍從。”意思是說,毛澤東與柳亞子,是一虎一龍,其他人都只配跟在后面。在《次韻和平江四首》中,又寫道:“留得故人遺句在,北毛南柳兩英雄。”
但柳亞子的自我感覺良好很快遇到挫折,產生了“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和詩插曲。因這段故事已廣為人知,不再贅述,且看另外幾個片段:
據曾彥修回憶:田家英給柳亞子送詩時,柳直接提出了安排職務的要求,而且級別還不低。面對柳亞子的情緒,毛澤東還是要安撫他。5月1日下午,毛澤東偕夫人江青和女兒李訥來頤和園,看望柳亞子。在園中散步、劃船,傍晚才離去。在日理萬機之時抽半天陪柳亞子閑聊,毛澤東也確實不易。但攜家人同來,也在暗示柳:拜訪純屬私人友誼,沒有政治意義。換句話說,毛澤東要讓大家明白:對柳亞子的拜訪,并不意味著在政治上對他的特別信任和重用。
毛澤東來訪使柳亞子欣喜不已,他頭腦中又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寫了《偕毛主席游頤和園有作》,最后兩句是:“名園真許長相借,金粉樓臺勝渡江。”聯系到前幾天他給毛澤東的詩中有“倘遣名園長屬我,躬耕原不戀吳江”的句子,讀者的理解是:柳亞子要毛澤東把頤和園賞給他。盡管柳的后人極力否認,但也難以自圓其說。
這期間,柳亞子多次給毛寄信呈詩,提出了明確的任職要求。5月21日,毛澤東復信曰:“國史館事尚未與諸友商量,惟在聯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難提前設立。弟個人亦不甚贊成先生從事此項工作,蓋恐費力不討好。江蘇虛銜,亦似以不掛為宜,掛了于己于人不見得有好處。此兩事我都在潑冷水,好在夏天,不覺得太冷否?”可見,柳亞子先要江蘇省領導職務,后要擔任國史館負責人,都被毛婉言拒絕了。
其后,柳亞子又演出了一場自立門戶的鬧劇。他拉一些人成立了一個“北平市文獻研究會”,自封主席。柳6月19日日記中寫道:“十一時許,偕赴聽鸝館開文研會籌備會議,通過舉余為主席,儼然黃袍加身,擬推老毛為名譽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脫離共產黨自行張羅這樣的組織,是不是另起爐灶?在自己搞的組織中被選為主席,竟也得意地稱為“黃袍加身”,豈不可笑?至于要延攬“老毛”“入我彀中”,給他當名譽主席,就讓人哭笑不得了。在新政協即將召開的北平,怎么可能允許柳亞子自行成立組織?這不但說明了柳亞子在政治上的幼稚,也說明共產黨不給他重要職務,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的規勸,柳亞子顯然沒聽進去,仍動輒沖動、易怒,歸根到底是因為沒當上大官。6月27日,宋云彬給柳亞子寫了一封長信,直言:“我覺得亞老這次發起文研會是一樁不必要的事情,同時覺得做得有點過火了。”“這樣發展下去,有幾種不好的結果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評、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亞老接近了。而一些來歷不夠明白、心里頗懷鬼胎的人,倒多圍集到亞老的周圍來了。他們不會對亞老有所規箴,只是阿諛順旨,起哄頭,掉花槍,非把亞老置之爐火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亞老的抗議書或介紹信的領袖們,覺得亞老實在太難服侍了,或者覺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復,后來漸漸懶于作復了。這樣自然會引起亞老的不快,增多亞老的牢騷。”“我的愚見,以為像亞老那樣有光榮的革命歷史的人,有崇高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講話,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應該由亞老站出來講話的時候才來講話。”最后宋云彬寫道:“率直陳詞,不避冒瀆,死罪死罪。”柳亞子回信說“事之委曲不盡然者”,但仍接受了宋的勸告:“辱荷惠箋,深感厚愛,昔稱諍友,于兄見之矣。”
宋云彬勸告柳亞子要顧全大局,自己也難免發些書生脾氣。他們對共產黨的一些組織行為感到不舒服。4月20日,招待處干部李女士拿著登記表,請葉圣陶夫婦和宋云彬填寫,上有學歷、家庭情況和將來志愿等內容。宋“聞言大不快。余等此來,先有周恩來電邀,復經香港中共人士催請,到(北)平已匝月,彼等豈不知余等之情況,而尚須加以調查研究乎?”招待處同志解釋說:如果自己不愿意填寫,就請別人代填。宋云彬要過表格一看,別人代他填的學歷是“浙江法政大學畢業”,說這是國民黨時期官僚機關重出身,所以虛報的,現在解放區,大可不必自欺欺人,于是改為“中學未畢業”。這是實話,也是氣話。宋云彬不懂得,共產黨是要進行政治審查和建立檔案的,任何人都要填寫自己的經歷。而且讓他們填志愿,也是為了發揮專長,合理使用。但宋云彬感覺這是共產黨不信任他,未免太幼稚了。
共產黨人對民主人士并非縱容遷就。對他們的缺點,也會提出善意的批評。6月9日,宋云彬又喝了五兩白干,在遠東飯店高談闊論起來。夏衍批評宋喝酒有三階段:一、說話漸多,二、聲音漸高,三、倫次漸少。宋自己反思,亦頗慚愧,記在日記里。經過在北平與共產黨的接觸,宋也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缺點,作詩自嘲曰:
結習未忘可奈何,白干四兩佐燒鵝。
長袍短褂夸京派,小米高粱吃大鍋。
避席畏聞談學習,出門怕見扭秧歌。
中產階級壞脾氣,藥救良方恐不多。
新政協里有“統”有“戰”
民主人士的情況是復雜的。如何改造這些知識分子,如何量才使用,共同搭起新政權的架子,確實不是容易的事。毛澤東、周恩來、李維漢等領導人在籌備新政協會議期間,在統戰工作和組織工作方面,發揮了高超的智慧和策略。既有聯合,又有斗爭;既有熱情友好,又有原則和立場。最后終于把形形色色的民主人士團結在共產黨周圍,共同實現建國大業。
周恩來在籌備新政協過程中,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原則。首先要盡可能地團結最大多數人,要劃“最大的圈子”,不要劃“小圈子”。“要在觀念上,把黨外凡是能夠爭取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士,當成黨內干部來看待。”在代表人選上,他強調政協委員的人選不能搞“清一色”。他說:“政協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沒有意思了。政協就是要團結各個方面的人,只要擁護憲法,立場站過來,我們就歡迎。”政協內部要求同存異。他說:“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求大同存小異,這并沒有壞處。”求同存異,就必須有適當的妥協和讓步。他指出:“除非最原則的問題不會妥協外,凡是有極大可能采納的問題,最終可以取得妥協。”
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代表,需要包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國內各民族、海外華僑及其他愛國人士。取舍十分不易,可謂整個籌備工作中最敏感、最復雜的工作。代表名單,一般先由單位提名,聽取各方意見,反復磋商,再確定下來。在這個過程中,常常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斟酌再三,費時達數周之久。這方面的問題既復雜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周恩來親自處理的。
這個過程,宋云彬在日記中有持續記錄。既然來了北京,誰都希望能參加新中國的籌建工作,在代表推選上競爭十分激烈,有些民主黨派達到明爭暗斗的地步。宋云彬是在沈鈞儒為首的救國會中。7月4日救國會在北京飯店開會,沈鈞儒報告出席政協的代表名單已提出。上邊給名額10人,但救國會提出14人,史良說今天出席會議諸君,都在名單之列。“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當矣”。11日再開會,沈鈞儒再次公布名單,12位代表中宋排名第8。沒想到好事多磨,名單傳到上海,王造時來信非要當代表不可。說當年“七君子”中有他,當不上政協代表太沒面子。龐藎青也大發牢騷,說自己代表北方救國會,竟不得提名,太不公平。宋云彬心想:“此公好名不亞于余,然自知之明則不逮余遠甚矣。”沈鈞儒擺不平,只能與統戰部反復磋商。到8月11日,救國會政協代表名單仍未定。宋云彬心里很忐忑,日記寫道:“看來統戰部還想安排一些人進來,我的大名恐終被擠出耳。近來想法又有點不同,覺得做不做新政協代表也無所謂。難道我真正進步了嗎?”宋能有這種心理準備,說明他真進步了,懂得顧全大局了。9月3日,宋云彬終于收到出席新政協會議通知,并為制作代辦證件照相,糾結的心終于放下了。
為了爭取各方面人士都來參與新政協,中共中央在代表分配上不僅考慮到民主黨派,還按專業劃分了社會科學界、新聞界、工商界等,以便吸納更多的知名人士。宋云彬見到了上海《文匯報》原總編輯徐鑄成,“此次新聞工作者出席政協代表十人,又候補二人。徐鑄成名列候補,殊為委屈。各單位代表名次,統戰部極為重視。聞事前曾再三斟酌,鄭重商討。”中共中央非常重視與民主人士的協商,反復斟酌,務求各方滿意。徐后來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協,中共工作作風的細致和嚴肅認真,給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處理復雜的黨派問題同時,新政協還特設“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以盡量照顧到各個方面。周恩來說:“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形成的。由于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嚴重壓迫,許多志士仁人雖然沒有組織起來,但卻在領導著、聯系著很大一批民主人士從事民主運動。因此,嚴格和正確地說,無黨派民主人士是沒有黨派組織有黨派性的民主人士。”
中共中央在代表的分配上,已經非常細致了,但還有一些特殊人物不好安排。宋慶齡以什么名義參加政協會議?周恩來和李維漢征詢宋慶齡本人的意見,宋表示“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任何團體的業務,也不愿參加任何團體,只愿以個人旁聽的資格列席新政協會議。”為此,新政協又設了“特邀代表”一類。一些國民黨元老和前軍政要員、重要人物如宋慶齡、張元濟、張治中、邵力子、程潛、傅作義等位列其中。“特邀代表”由中共中央直接邀請,不必經民主黨派討論。這使新政協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也體現了中共中央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真誠。
在確定政協代表的過程中,中共中央是心中有數的。有人看起來非常積極,但共產黨自有看法。救國會代表沈志遠(1902~1965),浙江蕭山人。上海讀書期間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2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曾參與《列寧全集》中文版翻譯。1931年12月回國,不久脫黨,從事教學和翻譯。1936年在上海參加救國會。抗戰期間任生活書店總編輯。1944年參加民盟。1948年1月到香港,1948年10月隨沈鈞儒北上到東北解放區。沈到北平比宋云彬等人早,又參加《共同綱領》起草,自我感覺良好。5月27日,周恩來、李維漢在北京飯店邀請救國會同人晚餐,“李維漢報告政局,沈志遠發言,涉及私人,為李糾正,失態之極。”宋所謂“涉及私人”應該是沈談起自己早年革命經歷,被李維漢制止。6月25日,周恩來召集籌備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協會座談會,“沈志遠竟明言此會之召集,主要目的在產生新政協代表云云,頗失態。”沈的這種自我表現,喧賓奪主的做法,并不為中共欣賞,也為宋云彬等民主人士鄙夷。
還有一些著名人士,被拒于政協之外。到北平不久,3月25日胡愈之來拜訪柳亞子和宋云彬,談起張申府。“謂張之大病在不肯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彼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有同事之雅,周恩來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紹,遂以革命先進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實為一沉重之包袱,不將包袱丟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張申府于政協失敗后,不惜與國民黨特務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處捐款,以飽其私囊。彼茍不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豈肯如此。”
張申府(1893~1986),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1921年底旅歐期間,他和夫人劉清揚創建中共旅歐支部,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1925年1月上海中共四大期間,張申府與蔡和森、張太雷等發生爭執,負氣退黨 。以后成為民主人士,參加民盟。1948年底,在共產黨與國民黨舉行戰略決戰,勝利在望時,張申府在儲安平的《觀察》上發表了《呼吁和平》一文,號召雙方停戰。這篇不合時宜的文章遭到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譴責,張本人被民盟開除,劉清揚也與其離婚,張被徹底趕下政治舞臺。千家駒作為民主人士代表到西柏坡拜訪毛澤東。自我介紹時千說“我是在大學教書的”,沒想到毛澤東說:“哦,大學教授呵!我連大學都沒有上過,我只是中學畢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一個小職員,一個月八塊大洋,張申府就是我的頂頭上司。”提起張申府,毛澤東馬上來了氣,說:“你們看到他發表的文章了嗎?我們快勝利了,人家就勸我們講和平,可我們倒霉時就沒人幫我們講話,這不大公平!”后來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真不明白:這么有學問的人為什么會講這樣糊涂的話?” 周恩來說:“也許是想成名吧,這恐怕是研究羅素過了頭,那套和平主義舊的東西又重現了。”毛澤東點點頭:“新中國的建設需要知識分子,可知識分子的立場是個關鍵的問題。立場站不穩,再有學問也不能用啊!”所以新政協把張申府排除在外,也是必然。
劉清揚當時作為婦女界代表進入新政協。沈鈞儒告訴宋云彬:“全國婦代會開會時,統戰部已為劉清揚做布置,選舉委員時劉可得百票以上。劉不知其事,自向代表們商請。選舉結果,劉得一百數十票,在被選委員中名次頗高。然至復選時,統戰部將前為劉布置之百票全部抽去,結果僅得數十票,降為候補委員。”自己私下拉票,屬于非組織活動,也是不能允許的。對劉清揚的微妙態度,也是統戰部堅持原則的體現。
從以上情節可以看出,統戰統戰,不是只“統”不“戰”,而是有“統”有“戰”。共產黨是講原則的,對民主人士也是具體分析的。誰是真朋友,誰是團結對象,可謂內外有別,連宋云彬也看得清清楚楚。
9月21日,新政協在中南海隆重開幕了。各界代表相繼登臺,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宋云彬以獨特的視角,在日記里對發言者一一點評,如9月21日大會開幕當天記:“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陳毅的最簡單,也很得體。”“程潛之講詞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23日記:“傅作義發言最坦率,謂此次赴綏遠,蔣介石曾來電邀赴重慶,有‘足下此次脫險,頗與十年前余自西安脫險相似,深可慶幸之語,然余決不為所動,今日得參加大會,站在講臺上發言,真是既慚愧,又榮幸,更無限興奮云云。”24日記:“陳嘉庚平時頗善講話,今天照發言稿一個字一個字念,像過去私塾學生念書,聽起來頗有滑稽之感。梅蘭芳善唱戲,但上臺演講詞可不成,張難先發言不落窠臼。”25日記:“以陳明仁言辭最誠摯,大可欽佩。錢昌照根據事實發議論,頗不空泛。”宋云彬的點評固然是個人感受,尖銳中帶些刻薄,但他真實記錄了新政協誕生的場景: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4年第9期,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