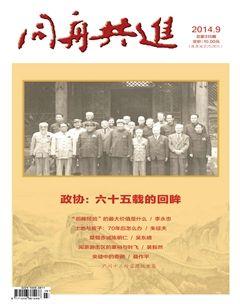胡喬木不討好的序言
楊建民
從許多回憶文章及一些私下口述、日記等看,胡喬木實在是一個復雜的人物。在這些文章里,胡喬木是具有相當閱歷和充分學養,同時又對文藝有著敏銳觸角的政治人物;在眾人的議論里,他的面目有點含混不清,或者有大家厭煩的“左”的腔調,或可跟隨政治風云改變自己的原有觀點……這些使得他即便有著深厚的文字底蘊(這方面他的功夫過硬,是可以引以自得的),卻得不到討好的結果。哪怕是政治大人物,也不能改變這樣的尷尬,這種現象讓人深思。
【聶紺弩不愿攀附“權貴”,出言不遜】
先說一件頗為著名的胡喬木寫序不討好的往事。1982年夏天,胡喬木正帶領一批“秀才”為“十二大”準備文件,寫作大文章時,讀到了學者胡繩帶來的一本香港出版的聶紺弩舊體詩集《三草》(即“北荒草”“贈答草”“南山草”的合集)。翻閱后,對文學有頗高領悟力的胡喬木立即贊其為“奇詩”。聽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該書的修訂版《散宜生詩》,胡喬木立刻表示自己要給這部詩集寫一篇序言。對整天忙于起草各種文件的胡喬木,這確實顯得有點特別。當然,他喜愛這部詩集的心情,卻是一目了然的。
也許是怕讀后心得日久失散,幾天后的7月14日,胡喬木寫出了一篇精粹同時頗具識見的序言:“在我讀到他的這部舊體詩集的時候,心情很是感動和振奮。”并概括道:“我認為他的詩集特別寶貴的有以下三點:一、用詩記錄了他本人以及與他相關的同志二十多年來真實的歷史,這段歷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們認真紀念的。二、作者雖然生活在難以想象的苦境中,卻從未表現頹唐悲觀,對生活始終保有樂趣甚至詼諧感,對革命前途始終抱有信心。這確實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三、作者所寫的詩雖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詩,詩中雜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從頭到尾卻又是用新的感情寫成的。他還用了不少新穎的句法,那是從來的舊體詩人所不會用或不敢用的。這就形成了這部詩集在藝術上很難達到的新的風格和新的水平。”這樣的評價,確實把握了這批詩作的價值,也充分體現了胡喬木的思考和文字能力。
胡喬木是文章大家,他的結尾也頗為精彩:“我不是詩人,但是熱烈希望一切舊體詩新體詩的愛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熱血和微笑留給我們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閱讀聶紺弩的這些作品,人們能夠感到胡喬木的評價是內行而非虛空和過譽的。
照一般人看來,這篇序言由高官、黨內大才子,曾經的毛澤東秘書寫出,受序之人總該感激不盡吧?可惜事實并不如此。盼望自己詩集能早日出版的聶紺弩,聽說了胡喬木想給詩集寫序的事,他擔心大人物雜事繁多,過幾天忘了,會耽擱作品問世,就在胡喬木寫出序言后的7月21日,不知情的聶紺弩竟給胡喬木寄去一函,言語并不客氣地催促道:“頃聞人民文學出版社人言,您要為拙詩寫一序,該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圖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謂‘丈夫不死誰能料也。惟年事既高,且復多病,朝不慮夕,深以能親見此序為快耳。”
此前聶紺弩并未讀到胡喬木的序言,讀后他不由得緊張起來。據詩人牛漢回憶,一天聶紺弩的老婆周穎來電話,大呼:“不好了,大禍臨頭了”,催促牛漢趕快去他們家。牛漢從東中街騎車四十分鐘趕到聶紺弩在勁松區的家,推開門,只見聶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抽煙,頭都不回地說:“胡喬木作序……這就壞了,他知道我內心想什么。”接下來,聶紺弩列舉了胡喬木從馮雪峰送給他的文集里發現“反黨文章”之事,并說:“他看了我的詩并主動寫序,遲早會處理我。”牛漢描述:“那天聶紺弩談得非常動情,我表示理解,相信他的判斷。”(《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三聯書店2008年版)不管胡喬木多么懂這批詩作的意義價值,寫出的文字多么精到,但他先前的一些言論作為,在聶紺弩等知識分子心目中留下的形象,通過這段對話可見一斑。
此時的胡喬木,完全為聶紺弩的詩篇折服,百忙中還給聶寫信說要去看他。不幾天,長年斜躺臥床的聶紺弩便接待了冒著盛夏酷暑前來拜訪的胡喬木,胡不但當面贊揚詩作,還夸獎聶紺弩“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有著數十年豐富閱歷并歷經磨難的聶紺弩,雖然一生中見過并與許多大人物共過事,可此時胡喬木的突然來訪,還是讓他有些“不明白”。這時,中國社科院的李慎之正與胡喬木在玉泉山寫文章,聶紺弩通過他人給李慎之帶話,問胡喬木來訪到底有何用意?李慎之回答:放心吧!喬公(胡喬木)嘴上說的就是他心里想的。胡喬木看望了聶紺弩后,回來還批評李慎之:你看紺弩的詩,多么樂觀,多么詼諧;你的就不行——太蕭瑟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
身份地位的懸殊,對苦難的實際體嘗不一,盡管對詩作有好感,還是有一定的隔膜和敏感。對胡喬木的序言,從大的方面看,聶紺弩是認可的,他在詩集后記中也說:“胡喬木同志的序說我對生活有詼諧感……是內行話,不僅知詩,而且知人。”(《散宜生詩·后記》)可序言中的個別字眼,還是讓他心有戚戚。譬如序言中說:“紺弩同志大我十歲,雖然也有過幾次工作上的接觸,對他的生平卻并不熟悉,因而難以向讀者作什么介紹。”這話一般看去并沒有什么,可聶紺弩對此頗為不滿。他在當年10月25日給舒蕪去函說:“喬序說對我的生平不熟,其意極明:‘此人如有歷史問題,我不負責!否則何必提此?”數十年密致的政治斗爭,一字一句,榮譽后患,均不可知。在胡喬木,也許并無深意,可在聶紺弩,因為多年的底層生活經驗,卻讀出了寫序人自保的潛臺詞。這般讀來,就難以產生好印象——這當然不是主動寫序的胡喬木所能料到的。
當年章詒和在她那本著名的《往事并不如煙》中有這樣的描述:“一天,某知名度頗高的作家讀了詩集(按:《散宜生詩》)后,登門拜訪。寒暄了幾句,便談起了‘散宜生,遂問:‘老聶,拜讀大作,佩服之至。不過我還想問問,你是怎么找到喬木,請他作序的?霎時間急雨驟至,黑云飛揚。忿極的聶紺弩倚案而立,厲聲切齒道:‘媽的個B,我的書本來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壞了!”即使有看法,聶紺弩在先前的抱怨中,還只是停留在“不理解,不高興”的程度,這里突然大爆粗口,似乎又突顯了另一層意思。來客顯然按照常理認為,詩集前面的序言是聶紺弩“求”來的,這是聶紺弩“爆粗”的直接原因。在聶紺弩看來,攀附“權貴”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最不愿不齒的作為,憤激下出言不遜,實在是情景湊合,不得不發也。此事后來一些人多有辯解,認為此乃傳聞,似乎不值得為此認真。可讀了前面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及考慮當時背景,以聶紺弩從《散宜生詩》透露出的個性,這樣的激烈回應,是不難想象的。
【為師陀小說作序,
反使作者“遭受歧視壓抑”】
胡喬木還在給另一位作家寫序后引發了不良后果。不過相比前一篇,此次的影響要小很多。
師陀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較為知名的作家,一生寫過中長篇小說、散文、戲劇等多種式樣的文學作品,較為著名的有長篇小說《結婚》、小說集《谷》(該書曾獲得1936年《大公報》文學獎金),1949年后曾任上海出版公司總編輯,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副主席等。1984年,師陀想再版自己以前的一部中篇小說《無望村的館主》,托人找到胡喬木,胡喬木為之寫了一篇不錯的新版序言。
師陀當時并沒有擔任較高職務,與胡喬木似乎沒有過直接聯系,可他為何尋到胡為自己小說寫序言呢?1983年6月,上海文藝出版社為組織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派丁景唐、郝銘鑒前往約請胡喬木為該“大系”撰寫“總序言”。為此,胡喬木與丁、郝兩位有過一次談話。談話涉及許多作家當時的創作情況,其中也談到了師陀:“師陀當時也是左翼作家,卻不是以左翼作品見長。他在左聯的《文學月報》上發過作品,文字上很下功夫。作品形式也是多方面的,散文、小說、劇本都有,劇本主要是改編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這是否為師陀求助胡喬木寫序的起因,不得而知。不過師陀后來曾與胡喬木通過幾次信,他通過小說家沙汀帶話,希望胡喬木能寫個新的序言。不久,胡便滿足了他的要求。據師陀介紹,《序新版〈無望村的館主〉》一文胡喬木寫得很認真,曾三易其稿,其中說道:“《無望村的館主》是原用筆名蘆焚的老作家師陀同志在1939年上海淪陷期間寫的一部中篇小說。最近作者作了不少的修改,并對一些為現在的青年讀者和南方讀者所不易了解的故實和詞語作了很多注釋,使這部描寫北方(可以假定是作者的故鄉河南一帶)一戶大地主在四代之中怎么由暴發為巨富敗落而為朝不保夕的乞丐的浪漫故事,以新的面貌出現在讀書界……”一個簡短開頭,將小說創作體裁、時間、新意甚至作品梗概盡數寫出。
作為一位懂文學的政治家,胡喬木首先談及的是作品的認識價值:“這部書對于認識中國近代地主社會有一定的價值……這部中篇小說也是這類作品的一種,但是它既有自己的鄉土色彩,而敘述的事件又相當奇特,所以又有獨自的貢獻。”胡喬木到底不隔行,他隨即轉入到小說的評價:“這是一部小說,當然首先要從小說來評價。它篇幅不長,人物不多,但是舞臺面的變化卻很劇烈,有時簡直近于暴風式的瘋狂。讀者可以從這里看出舊社會能把一些人的人性變得怎樣兇殘、丑惡、卑鄙和麻木,而善良的人們又在遭受怎樣可怕的蹂躪……故事的進行是快速的,但作者對人物和場景的描寫卻一絲不茍,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許多幅精雕細刻的肖像畫和風俗畫。一個好的小說家未必是一個好的文章家,作者卻把這兩者都做到了。這是這部中篇的另一個可貴之處。”首先從小說讀出人性,再讀出作者的“手法”“技法”等。說“一個好的小說家未必是一個好的文章家”,這倒別有見地。不是研究深入,談不出這樣一般人不易具有的識見。
為什么要再版,意義何在呢?胡喬木回答:“這本書最初出版時由于當時的環境發行有限,現在重印,希望它能得到全國文藝愛好者的注意。我不是文學評論家,對于作者的人和作品都缺乏研究……當然不致糊涂到說這是什么偉大的杰作。我只想說,讀者看了這本書會喜歡它,會跟我一樣感謝作者用優美的文字敘述了一段悲慘、荒唐而又真實可信的歷史,這段歷史就產生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離開現在不過半個多世紀。”略略咂摸一下,這段文字一方面指出了作品的優長精彩處,同時用“不致糊涂到說這是什么偉大的杰作”來范圍該小說的限度,這比今天許多“抬轎子”的所謂評論家說得有分寸許多。
這當然是一篇好的序言,但如同給聶紺弩寫的那篇序言一樣,它給小說作者帶去了不利。這一次,不利并非來自作者本人,而是來自他人。
據當時《人民日報》副刊的編輯姜德明回憶,這篇胡喬木寫的序言,是師陀本人于1984年7月15日寄給《人民日報》的。他在給姜德明的信中說:“現寄上喬木同志給拙作《無望村的館主》寫的序的復印本,請足下考慮,無論發表在《人民日報》哪一版都行,稿費請直接致送喬木同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胡喬木直接管轄《人民日報》,他的文章當然都最早安排刊出。可姜德明回憶:“我已忘記由于什么原因,未能馬上見報,喬木同志在北戴河還讓秘書打電話來催詢過。”胡喬木的文章寫于當年7月,拖延了一個多月,到9月5日才在副刊發表,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胡喬木有一次來到上海,臨走時接待了師陀。師陀曾當面向胡喬木提出希望能幫助解決住房困難問題。當時上海正經歷“學潮”,胡喬木答應回北京后相機提醒上海的有關方面。回京后不久,胡喬木又接到師陀的信,再次提出房子問題。此時正值1987年春節期間,胡喬木沒有耽擱,立即給上海市委一位姓譚的副秘書長寫信,專門談到此問題:“春節好!離上海前曾接待上海作協副主席、著名老作家師陀同志,他在談話中表示希望能幫助他解決全家三代僅有住房兩間的迫切困難,以便繼續寫作。”接下來還有這樣幾句話:“頃接師陀同志來信,再次要求增配一套房子。師陀同志在作協四大以后只因我為他的小說寫了一篇短序,即無端遭受歧視和壓抑。”因為胡喬木寫的序,竟然使小說家無端“遭受歧視和壓抑”?顯然,雖沒有見諸公開文字,可師陀本人定然有直接感受;胡喬木也一定知道,不然他不會使用“無端遭受歧視和壓抑”這樣嚴重的字眼。
對于師陀,胡喬木還略略作了一點介紹:“實際上他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參加左翼文學的創作活動,在短、中、長篇小說方面造詣很高,后來除繼續寫散文外也寫過劇本,晚年轉入文學史的研究,成績都很可觀。”這樣順下來,就可以再次強調師陀的實際情況了:“他年邁而精力旺盛,為人正派,從不介入派別活動。對這樣一位老作家的嚴重生活困難,似宜盡快設法。上海解決住房問題當然很不容易,但望先給他打個招呼。我早想寫這封信,近日因事忙拖延了,很覺抱歉。以上都是個人的意見,只供市委辦公廳參考。”從這封信可以看出,胡喬木對于師陀的實際困難,的確很是上心。
【“天下世界,最苦惱的人是胡喬木”】
前面主動為聶紺弩詩集寫序,詩集作者不滿意。這其中有詩人不愿獲得“攀附權貴”名聲的原因。這次為師陀小說作序,是小說家自己求來,可一些人大約仍從這樣一點出發,給了小說家“無端遭受歧視和壓抑”的待遇。這里的內情,或許不像表象看起來這么簡單。其他一些作者,也有獲得過官員的文字,雖然可能不及胡喬木對文藝這么內行,寫得不如胡喬木那樣精到,可對于作者,并沒有因此感覺不滿或受到“歧視”“壓抑”。是否胡喬木當時對文藝界發表的言論引起了文化人的不滿?對于胡喬木的一個“徽號”,他的老友季羨林在紀念文章中說:“在他‘胡喬木生前,大陸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稱為‘左后。我覺得,喬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種有意害人的人呢?”這一點,胡喬木自己是知道的。季羨林在同一篇紀念文章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1986年冬天,北大的學生有一些愛國的活動,有一點‘不穩。喬木大概有點著急。有一天他讓我的兒子告訴我,他想找我談一談,了解一下真實的情況。但他不敢到北大來,怕學生對他有什么行動,甚至包圍他的汽車,問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應了。”這是否為人們不滿意他寫序,甚至給求序者以“歧視”“壓抑”的背景和更主要原因?
胡喬木長期愛好讀書,受優秀文化熏陶,使得他保有文化人的基本良知、情懷,這些成分內化,甚至成為性情。這就使他看到好的詩作,便不管不顧,主動操筆寫序,譬如為聶紺弩的《散宜生詩》;讀到好的作品,不顧官高位重,要去見見作者,譬如因為老作家施蟄存寫出一本《唐詩百話》,雖然先前不認識,也要讓當地文化官員陪著去家里看望;見到女詩人舒婷的詩寫得好,也大張旗鼓地上門拜訪;認同報上讀到的好文章,便以普通讀者身份給作者去信。譬如1980年讀到《祖國高于一切》一文,給作者陳祖芬寫信,并給文章中的主人公以實際幫助……此時的胡喬木回歸文人風范,寫精粹文字,率性而為,讓人可喜 。
在中國,有些意識沉冗至極。譬如你“官員”了,就只能接受一種認知方式,而不管這多么抑制才智,扭曲性情。身在其中者,倘情緒所致,偶爾“出位”,就可能影響自己的形象甚至位置。可官員也是人,是文化滋潤的受益者,角色一旦偏于單一甚或僵硬,精神上便難以忍受,就得尋找更高層面呼吸的通道,獲得生命中的別一種樂趣。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一書中說起胡喬木常常愛去錢鐘書家的理由:“我覺得他到我家來,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會兒。他是給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年版)
說起胡喬木的不得不“復雜”,楊絳在《我們仨》中,也引了他人的一段話來描述:“有一位喬木的朋友說:‘天下世界,最苦惱的人是胡喬木。因為他想問題,總是從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對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惱不堪。”一方面,有獨到認知,另一方面,必須保有官員立場,兩方面都得做好或表現好,這就很難了。在此情景下,說胡喬木“復雜”,其中有不得不為的方面,也有自作主張的情緒。倘不簡單地看,這其實是人性多個層面在不同場合、不同時段不由自主的表現,這是我們認識如胡喬木這樣“復雜”的人物應當特別關注的——雖然我們還是希望角色有層次可不必分裂,人性在一些最基本的層面,狀態應當趨于正常才合適。
(作者系文史學者)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4年第9期,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