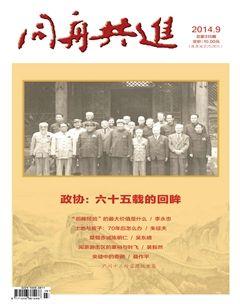閩浙游擊區的粟裕與葉飛
裴毅然
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大將(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葉飛上將(1914—1999),聲名赫赫,誰料兩位大功臣差點死于1936年閩浙游擊區的內部裂爭。
閩浙邊“臨時省委”
1934年7至8月,中革軍委派遣尋淮洲、粟裕的紅七軍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前往浙贛邊界,與方志敏、劉疇西的紅十軍會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隊”在開化、婺源、德興遭到極大損失,方志敏、王如癡、劉疇西等被捕。1935年1月底,新敗的抗日先遣隊殘部到達閩浙贛根據地。中央分局根據政治局1月15日電令,責成閩浙贛省委迅速組成“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委,全師538人共擁有長槍445條、重機槍4挺、輕機槍8挺。“挺進師”隨即進入浙江,開展游擊戰,創建蘇區根據地。這支紅軍在閩浙邊界進進出出,來回作戰。同年4月,開辟出以仙霞嶺為中心的浙西南游擊根據地。
10月,劉英、粟裕的浙南“挺進師”與葉飛的閩東“獨立師”在閩東北壽寧縣境不期而遇會師。聯席會議上,針對國民黨組建“閩贛浙皖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四省國民黨軍力對付紅軍游擊隊,而各紅色游擊區自失去與中央分局及閩浙贛省委的聯系后,各自為戰、互不聯系,形勢很為不利的情況(《劉英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大家認為如果浙江、閩東、閩西三區取得密切聯系,哪怕只在戰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應,也會有利得多。劉英提議由閩北的黃道同志擔任三塊根據地的書記,黃道乃1923年入黨的“老資格”。但因一時聯系不上黃道,先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共11人),來自中央蘇區的劉英任書記,粟裕任組織部長,葉飛任宣傳部長;并相應成立“閩浙邊臨時省軍區”,粟裕為司令員,劉英為政委。由于各游擊隊電臺都已破壞,失去與中央及上級的聯系,甚至都不知道遵義會議,“臨時省委”只能日后再報中央與上級核準。
臨時省委成立后,立即著手開辟新的游擊根據地,重點放在開辟浙南游擊區。葉飛看到劉英、粟裕離開浙南根據地沒有后方,回旋余地太小,主動將閩東四塊游擊根據地中的鼎平根據地讓給劉英;同時見突圍后的“挺進師”僅剩200余人,再將鼎平獨立團劃給“挺進師”。可以說,“臨時省委”初期的合作相當愉快。
分歧是如何產生的
此前,浙閩兩地紅軍游擊隊基本沿用中央蘇區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公開建黨建政。這套蘇維埃運動策略,雖然有利于發動群眾,迅速打開局面,但從長遠看,“打土豪、分田地,打擊面大,不利于團結和爭取其它社會階層。”(粟裕《回憶浙南三年游擊戰爭》,1983年8月22日《黨史研究資料》第8期)此外,浙西南紅區距鐵路不過數十里,白軍以幾十倍力量壓下來,一塊小小紅區,目標非常突出,難以經受白軍反復持久的打擊。為此,粟裕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劇的形勢下,從實際出發,適當調整政策,團結中間階層,對上層也要根據不同情況予以區別對待,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以增加對敵斗爭力量。當粟裕向劉英提出上述意見,劉英認為這些意見是對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十分反感,從此與粟裕產生思想認識上的分歧。
1936年3月,國軍羅卓英部經過幾個月圍剿,將主力集結于城市與交通干線。劉英判斷國軍“圍剿”已結束,要求粟裕率“挺進師”返回浙西南以恢復游擊區。粟裕則認為國軍主力雖集結于城市與交通干線,但僅憑這一情況還不能判斷“圍剿”結束,“挺進師”主力仍應堅持在廣泛區域內打游擊,何時進入浙西南中心區,應在進一步了解情況后相機行事。因與粟裕意見不一,劉英即以省委名義作出主力進入浙西南的決定,并派許信焜任“挺進師”政委。
“挺進師”抵達浙西南外圍,了解到經過幾個月“圍剿”,浙西南根據地主要領導人黃富武已犧牲,其他領導干部除個別人走失,也先后犧牲,保留下來的少數基層干部與部隊,已化整為零隱蔽起來。白軍堡壘工事布得像圍棋子一樣,保安團隊及地主武裝仍在繼續“圍剿”,敵情仍很嚴重。這種形勢下,“挺進師”如主動鉆進敵人包圍圈,正是對方求之不得的。“挺進師”政委許信焜堅持執行劉英的決定,但粟裕只進入浙西南地區進行幾次奇襲,隨即轉入更廣大地區打游擊,未“堅決執行”劉英指示。如此這般,更加深了劉、粟之間的裂痕,并在臨時省委及部隊領導層傳揚開來。
在與閩東領導人葉飛的關系上,劉英希望借重閩東獨立師恢復浙南根據地,葉飛則認為獨立師的首要目標是堅持閩東各區斗爭,逐步恢復閩東根據地,再向外發展。此外,劉英提出內部肅反,派政治保衛局到閩東各根據地。葉飛最初不明白“肅反”是怎么一回事,很高興政治保衛局前來幫助工作。但肅反很快擴大化,一些深受當地民眾擁護的積極分子,甚至表現比較突出的共產黨員都被殺了,閩東群眾一片憤怒。葉飛這才緊急叫停肅反,但許多鄉村還是爆發了追殺政治保衛局人員的行為。劉英與葉飛的關系出現重大裂縫。〔《葉飛與閩東六變》(下),《檔案春秋》2014年第6期〕
“吃掉”葉飛與粟裕被捕
在失去與中央及上級聯系的情況下,浙南、閩東兩個游擊區自行成立臨時省委,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浙南方面還以“主力”自居。同時,因不知道遵義會議精神,受左傾肅反擴大化影響,互相都有抓錯人、殺錯人等誤會之事,因此雙方都有氣。臨時省委本應妥善處理矛盾,但劉英卻幾次提出葉飛留在臨時省委工作,藉以調虎離山,使葉飛脫離閩東。粟裕不贊成,認為這樣不利于堅持閩東游擊根據地,亦不利于協調兩個地區的關系,而且也不符合成立臨時省委之初衷。同時,對劉英派員出任閩東獨立師政委,粟裕認為人選失當,不利于團結。但劉英拒絕粟裕的意見。
臨時省委成立后,因劉、粟、葉三位主要領導經常分開活動,省委實際工作由劉英一人主持。劉英常常將個人意見強壓下來,不僅引起閩東方面的疑慮與反感,亦使粟裕很為難,“我是經常在外面打游擊的,對于這些問題只做了一些調解工作,也沒能收到什么效果。” (粟裕《回憶浙南三年游擊戰爭》)1936年2月間,粟裕正轉戰浙閩邊境,碰到閩北軍分區政治部主任,便手寫一信,托他帶給很有威望的黃道同志,希望黃道能出面召集會議,商討三地游擊區的協調配合。黃道為北京高師生,曾參與南昌起義,歷任贛東北蘇維埃主席團秘書長、贛東北特區委組織部長、閩贛省委主要領導。劉英也曾給黃道寫信聯系過,但對粟裕此信十分不滿,并引起恐慌。3月,劉英致信葉飛,宣布臨時省委決定調葉飛兼組織部長,閩東特委設副書記一人,再次要葉飛來省委。此時粟裕是組織部長,他日后談及此事時說:“這個決定無論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說明劉英同志既想把葉飛同志調離閩東,又想撤掉我這個組織部長。”
1936年2月,葉飛也在福建政和縣見到閩北領導人黃道,向他介紹了閩東、浙南的情況,也談到閩浙臨時省委的分歧。葉飛提議成立閩浙贛省委,請黃道任書記,統一領導閩北、閩東、浙南三塊游擊區。黃道對采取統一行動表示贊賞,但提出一項條件:閩浙臨時省委必須對前期工作做出總結,并恢復浙地根據地,然后才能成立聯合的閩浙贛臨時省委。葉飛回來后,在劉英召集的閩浙臨時省委上,直率匯報了與黃道會面的經過,并毫無心機地將黃道的意見擺上桌面。這無疑是對劉英的打擊。一直謀求建立三地省委的劉英此時改口:“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已經建立了閩浙臨時省委,又何必去建什么閩浙贛省委?有錯誤我們自己會糾正。如果你們有意見,那葉飛來當書記吧。”葉飛很驚愕,他促成三塊根據地的聯合,絕不是為了個人權力。他生氣地回絕了劉英的嘲笑,臨時省委會議不歡而散。
1936年6月,劉英以省委名義取消閩東特委,將閩東特委屬下的三個辦事處上升為特委,調葉飛到省委工作。這一決定遭到閩東特委的一致反對,決定不執行,葉飛仍實際領導閩東特委。劉英越來越感到葉飛對他領導地位的威脅,終于下決心除去葉飛。
1936年秋,活動于浙南慶元縣境內的粟裕,接到劉英以臨時省委名義發來的信,要粟裕趁與葉飛見面之機,將葉飛押送省委,并派來一支武裝監督執行。劉英手令:
你要借會面的機會將葉飛逮捕,派專人押解鼎平。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響命令執行的任務,都將視為對抗和分裂省委。監督執行的部隊隨后就到,望速決。
粟裕十分震驚,不知發生什么事,但認為矛盾應在會議桌上解決,不應采取對敵斗爭手段,但不得不執行劉英命令。深秋之夜,葉飛帶一個連上浙江慶興南陽村與粟裕見面,遭到“挺進師”的重兵圍捕,即發生了紅軍火并的“南陽事件”。粟裕擲杯為號,捉拿省委宣傳部長兼團省委書記葉飛。
粟裕深知此時如將葉飛押至劉英處,已負槍傷的葉飛將很危險。“幸喜在途中遇到敵人伏擊,葉飛同志乘機脫險。閩東同志隨即宣布退出閩浙臨時省委”,“南陽事件”導致閩浙臨時省委的解體,被認為是我軍重大損失之一。
當粟裕未能押解葉飛到達省委所在地,劉英立即召開缺少閩東特委的閩浙臨時省委緊急會議,宣布開除葉飛、邵英平的黨籍,同時提出“分裂省委”的問題,指斥葉飛、黃道反對劉英,粟裕參與其事。會上,劉英還將轉戰浙閩邊境、致信黃道、放掉葉飛,一一說成是粟裕“分裂省委”的具體行為。此前浙西南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也是“全盤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對恢復浙西南喪失信心”。粟裕成為主要斗爭對象,派一個班將他看押起來。
經過一周的反復思考,粟裕從“不能分裂”的大局出發,被迫違心做了“聲明”,斗爭才算結束,獲釋出獄。此后,粟裕與劉英分開活動,各干各的,各打各的游擊。
劉英遺文引發爭議
抗戰爆發后,“挺進師”編入新四軍,閩浙邊游擊隊編入新四軍三支隊。劉英留在浙江,任省委書記,并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團團長。1938年12月,再任閩浙贛三省特派員。1942年2月,因叛徒出賣,劉英在溫州被捕。5月17日,蔣介石自重慶發往浙江急電:“飭速處決劉英。”18日拂曉,劉英犧牲于永康方巖馬頭山。原本人逝事遠,何況還是“省部級”烈士,這場人民內部矛盾也就塵封于歷史的褶皺里。偏偏劉英對這一段內訌耿耿于懷,1940年夏在皖南涇縣新四軍軍部撰文《北上抗日與堅持浙閩邊三年斗爭的回憶》,對這場“路線斗爭”做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陳述。該文1954年8月載《閩浙皖贛邊區史料》,再挑事端,引起浙南游擊區一些老同志的不滿。《回憶閩浙皖贛的革命斗爭》一書收入劉文(節錄),內有一段:
閩浙邊臨時省委第十次擴大會議……討論了對××(按:應為粟裕)問題的處理……討論了××同志三次聲明書,并通過了省委給×同志的一封信……解決了許多無原則的糾紛,開展了反××為首的取消總的領導機關,破壞黨內團結,取消浙江工作的錯誤的斗爭,使挺進師及閩浙邊全黨的同志更加團結和鞏固。
粟裕直到1980年才讀到此文,12月28日,他致信總政、中宣部、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陳述意見:
我認為其中一些重要情節與當時實際情況不符,有一些重要觀點也不能同意,而且里面違反實事求是地點了好多人的名。這篇文章的題目雖似個人回憶錄,其內容卻是對那一地區黨的工作和斗爭做總結性的闡述。劉英同志寫這篇文章時沒有同當時的主要負責同志交談過,事后也沒有送給我們看過,因而只能代表他的個人意見。為免研究黨史的同志把這篇文章作為組織文件來對待,我要求將我的這封信列入有關檔案。(粟裕《回憶浙南三年游擊戰爭》)
南方三年游擊戰,鉆山林、宿野外,強敵環伺,每天拎著腦袋革命,如此弱小還鬧不團結,猜疑爭權,甚至差點“你死我活”。既要防外面的“國”,還要防內部的“共”,革命確實相當不易。用今天的眼光,這場起于末的內部裂爭,完全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只因還沒有建立對待不同意見的民主機制,這才一遇“不同意見”,便會滑向暴力解決。
那會兒若真“解決”了粟裕,那么此后還會有“七戰七捷”“孟良崮戰役”“淮海戰役”嗎?從這一角度看,歷史確有相當的偶然性。
這場省部級以下的“路線斗爭”,一直屬“負面新聞”,直至1980年代才一點點被“回憶”出來。類似的事件不止一起,如張聞天的遺孀劉英在回憶錄中也記述:1934年4到5月,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被抽調出來,任楊殷縣擴紅隊長。楊殷縣乃紅區邊境縣,紅白往來,擴紅困難很大。潘漢年向中央局組織部長李維漢反映實況:不少壯丁跑到白區去了。李維漢一聽,就說潘漢年“右傾”,把他的“擴紅突擊隊長”給撤了。1935年2月10日,紅軍在貴州扎西傳達遵義會議精神,誰都可以上臺去控訴左傾了,“右傾”的潘漢年仍不敢上臺,只在臺下捅捅劉英的膀子,攛掇她上去“放炮”。(《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講真話難,從那會兒就開始了。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政治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解決內部異見的程序設置,實在是必須完成的人文進步。
最近,陳毅之子陳丹淮少將對“南陽事件”的實質有一段分析:這里重要的問題是劉英把個人當成了黨,這種錯誤的觀點已經危害了中國共產黨多年了。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4年第9期,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