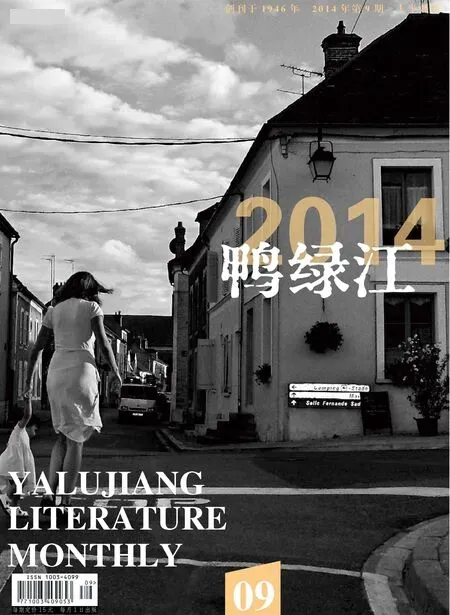平衡術內外的風景
——論夏雨的詩
張立群 孫榕璐
【理論·本省聚焦】
平衡術內外的風景——論夏雨的詩
PINGHENGSHUNEIWAIDEFENGJING
張立群 孫榕璐
歷經多年的實踐,夏雨的詩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她的詩沉穩、克制,講究細節的分寸感。三本詩集《夏之書》《平衡術》《去春天》不但記錄了夏雨詩歌的成長歷程,還標志著一次身份蛻變的過程——從一個普通寫作者到一個詩人。這自然使她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平衡術”的自我展開
很難想象北方詩人夏雨會有如此講究均衡、勻稱的觀念:平衡術。在那首同名的短詩中,夏雨呈現了她對于“平衡術”的理解——
有一架天平
我想知道它是不是很平衡
就用刀或利斧自己從上到下
劈成兩半
左半頭、右手,左身軀、右腿放在了左邊
右半頭、左手,右身軀、左腿放在了右邊
可天平并不平衡
我用余下的人生來思考
發現口腔右下側有一顆蛀牙
——《平衡術》
“平衡術”顯然是保持平衡狀態的思維與方法。它是一種測量標準,同時也是一種生存狀態。在類似“刑天舞干戚”的行為之后,我驚異于夏雨如何在抵達平衡時想到一顆蛀牙。按照現代醫學觀點,人的左右兩部分往往并不平衡,或是臉龐的大小、或是手指的長度……但人們依然存在甚至渴望一種平衡的狀態。以此讀解夏雨的《平衡術》:它并未超越東方人傳統的美學風范,像那些園林中左右對稱的老式建筑,“平衡術”無處不在并切分出一道中軸線。為此,“天平并不平衡”當然是一個問題,尤其在將自己的身體作為實驗品之后。“我用余下的人生來思考”,不過只是因為一顆蛀牙的出現……夏雨以其準確的判斷,講述了人生的不完整性甚至不確定性;她的“平衡術”是一種觀念,同樣也是一種思考人生的態度;她的思考使這首詩上升到了近乎存在哲學的高度。
既然無法保持實際的平衡,那么,道出解構平衡的狀態就很容易成為繼續演繹“平衡術”的重要路向之一。夏雨曾通過“常感左眼濕熱,右眼清爽”說出來右眼是好眼、左眼近視的事實,不過兩只眼是同時視物的,因而在實際生活中,“我”能夠看到正常視力范圍內的“所有大小動靜之物”,為此,我很困惑:“是我的右眼立了頭功/還是左眼在濫竽充數”(《常感左眼濕熱》)。顯然,這是一首“反平衡術”的平衡之詩,從實際上的不平衡到感覺上的平衡,這次夏雨講述的是誤差甚至自欺欺人。結合“平衡術”的正反兩面,我們可以看到“平衡術”加重了一個詩人的思考并由此提升了詩本身的層次與深度。正如詩人要求“有些東西是必須分清的”,關于理念、經驗的剖析與質疑都源自現實的人生狀態。然而,即使將其作為一種哲理詩,夏雨在具體呈現過程中也毫無澀重感和說教意識。她不過是以具體生活式的描繪,形象地說出抽象的原理,并將上述觀念灌注于具體的寫作之中。由此閱讀夏雨的詩,一種對應的結構、敘述過程中良好的平衡力和細節的準確拿捏,都是充分體現詩人敏銳感受力及創造力的前提條件。她當然會對“平衡術”樂此不疲。在后來一首名為《新平衡術》的作品中,詩人依舊重復了之前的過程——這次,為了再次檢測那個天平,“我”再次使用了將自己從上到下劈成兩半的做法:
奇跡出現了
天平竟無比平衡。只有那顆蛀牙
在微微地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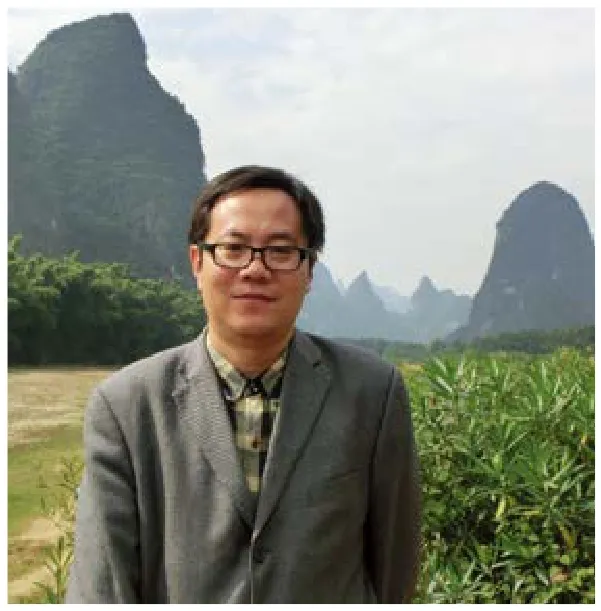
張立群,1973年生于沈陽,漢族。文學博士。現為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山東師范大學博士后流動人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方向研究,具體包括中國新詩與新詩理論,先鋒派文學與后現代文學思潮等。已出版《先鋒的魅惑》《中國后現代文學現象研究》等專著五部,在各種中文核心期刊發表論文20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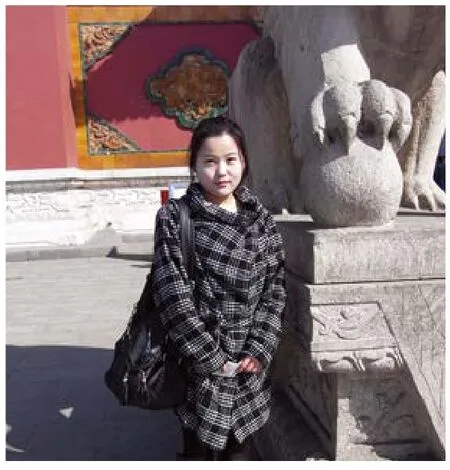
孫榕璐,遼寧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想來,在經歷一年時間蛀牙殘留的不完整狀態之后,“我”已經改換了自己的心境:盡管,這種心境可以在不同時期內交替出現,但一切書寫絕非簡單的重復,詩人在時間的推移中盡管重復了曾經的動作,但得到的結果卻并不一樣。物是人非、終于平衡,唯有蛀牙疼痛……捉取蛀牙的感受既是一種思維的掘進與深化,同時也不乏時間可以改變人生態度的生動寫照。《新平衡術》結尾處的“奇跡”既是一種隱喻,也是一種心境的自喻:讓一切都走進內心,讓思考更為深入并展開想象。“平衡術”在某種時刻就是“生活”本身:當“我”從平衡木上摔倒后,“它用剛剛發生的變故/增強我的信念/并企圖為我的行為/重新命名”(《生活》)。在經歷冥想與實踐之后,夏雨將精神的歷險和寫作之間的奇遇結合起來,她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平衡術》,正表明了她對這一狀態的偏愛與執著!
二、一個清河、小鎮的棲居者
按照“詩歌與地理”關系的說法,“對于任何一個詩人而言,無論接受怎樣的教育或是寫作上的限制,總會在反映他熟悉的地域生活以及故鄉記憶時顯得得心應手”;“對于那種深深植根于地域文化、歷史風情并偏于一隅的詩人而言,或許只有進行獨特的地域式創作,才會使其的位置和風格凸現出來……”[1]夏雨的詩歌首先應當屬于一種“地域寫作”,爾后才是自我觀念和內心世界的呈現。縱覽詩集《夏之雨》《平衡術》《去春天》,夏雨對故鄉清河、小鎮的描寫,堪稱一道亮麗而又持久的風景,在那里,不但有東北的地域風情,更有一位女詩人成長的歷史。
在我看來:“清河與小鎮”極有可能已經耗盡了夏雨的青春并融入其生命之中,因而,描述“清河與小鎮”就是詩人嘔心瀝血式的行為。詩人曾以抒情的方式歌唱過清河:“小清河,他很帥/很多事情與他有關/比如:詩,比如:溫暖”(《唱清河》)。顯然,清河是詩人心中的“美麗的異性”,它激發過詩人無數詩的靈感,因而,即使是北方的隆冬季節“雪漫清河”,詩人仍然在矢志不渝地歌唱“我早已融入清河/被己所迫(《雪漫清河》)”。沒有什么比源自清河的抒情更能讓詩人感到激動不已,這樣,我們至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棲居的記錄”。
夏雨屬于北方小城中成長起來的詩人,這種“先天成長”并不優越的客觀條件使其更容易留下一個詩人最初的本真。然而,即使是本真,若能長久地堅持,也必將會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個性——
清清的水在一個溫柔的聲音里
而聲音在別處
正是世界被歸置的同盟之都
吹著北方的風
那里的燈火又溫馨又明亮
——《清河,清河》

還有什么會比最簡單、樸素的詩句更能打動讀者的心靈?夏雨在書寫自己熟悉的清河時總是那樣自然而然、得心應手。清河的棲居當然會隱含日常生活中的煩惱與波折:清河曾“替我迎接”那個走近你的人,但如今,他卻要成為“遠離你的年輕人”(《清河,替我迎接那個走近你的人》),但在更多時刻,清河之居能夠帶來寧靜、祥和的“幸福生活”——
把清河當圓心
懷念當半徑
那些遠方的所有,及近處的街道、水流、親人
和午后
都在我的圓周上
我用圓周率來暴露我的幸福
——《我在清河的幸福生活》
而在一個又一個季節輪回之始,夏雨則寫道:“綠了清河的水/也綠了清河的岸/我在岸上,我也綠了//但不是我泄露了清河的秘密/保持沉默的三月,作為風景/不能被忽略,但可以被忘記”(《清河的風》)。清河的棲居會滋養詩人的生命,懷著一種“三月的秘密”,詩人從岸上走過,那種從屬于生命和情感的東西讓人久久難忘,它從不帶有斧鑿的痕跡,它只是自然天成、從心中流淌,即使清河最終也要面臨著現代文明的侵襲和浸染。
與清河相比,水畔的小鎮如何在夏雨的詩中浮現呢?
小鎮很小
小鎮叫清河
小鎮的落日多渾圓
小鎮的鑰匙在手里
你的手就是我的手
打開的房子
卻不是你的房子
狂野的心抵不上
小鎮的緩慢和過渡
——《小鎮的落日多渾圓》
小鎮在清河之側,與清河唇齒相依、稱謂相同。然而,只有清河,才有小鎮的邏輯,才能說明夏雨的摯愛。從那些總是通過自然景物抵達社會風物的句子中:“在夏日,沖動的大樹生長著/一棵,兩棵/還有另一棵,和它的伙伴們/極力分割著偌大的天空//那些混亂的枝條/我叫它們小鎮,清河,紅旗街/或逸龍小區//我念及向北的道路/念及夏日成片的荊棘和生活的中心/羞愧便布滿我的臉”(《在夏日》),我們可以感知清河是如此纏綿悱惻地縈繞著小鎮,而唯有目睹那些“老房子”和“街道”,還有“褐色的大壩”,才能喚起我的記憶;小鎮的偏遠和狹小,可以讓任何人留下并不經意的一瞥,但對于我,小鎮卻始終難以被擺脫和離棄。
也許,我應該尋找更多的路
用于走出去。就在那里
生活的技巧和焦慮
帶著重或輕的光芒
抵達。這是我的小鎮
——《我的小鎮》
透過這樣溫馨的句子,小鎮應當是和清河一樣,成為詩人夏雨的“一個人記憶”:無論身在何方,夏雨的靈魂始終在小鎮上游弋、在清河上留居,一如柔軟的清河之水,始終在小鎮的棲居之側且反之亦然。清河和小鎮是夏雨詩歌中現實同時也是靈魂的棲居地,是其詩歌中揮之不去的生活地理。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講述著清河與小鎮的故事,無論外部擴展還是回歸內心,她都走不出清河與小鎮的起點!
三、“我”是“夏天的雨”
如何看待夏雨詩歌中的季節描寫,正如詩人的名字本身就與之相契合——“請記住:/我是夏雨,夏天的夏,細雨的雨”(《蠱蠱——贈》)。“夏天的雨”可以是一次偶然,一場煩悶之后的清洗,它是夏天性格的另一面,并在包含某個特定時空狀態的過程中凝結著季節的故事:
在夏天,以純粹的信仰和純正的血
迎接一場雨,請你
夏天的使者
不要狀告我侵犯了水的意志
一點波光瀲影及音樂
漸漸逼入魂靈,為此我已沉迷太深
——《夏天的秘密》
如果說以上的詩句只是將對夏天的癡迷作為一種詩性的懸疑給讀者留下“秘密”,那么,夏天及其雨意象就在于對自然的向往和季節的崇拜。“夏雨”和它潤澤過的物事,是詩人歌聲中的唱詞,跳動著音符與夢想。如果家鄉的人不幸在此刻“染上某種幸福”,那么,“他”肯定是這個季節中最美麗的風景。這仍然是一個關于家鄉的“寓言”,但更重要的,它又是自我心靈的剖示。“這個夏天,是我同氏家族最甜美的小秘密”,“夏雨”因季節而獲取聲名,又因季節而潛藏秘密,她最終面向清河、小鎮,自然是最為合理的選擇與表達。
當然,就意象本身應有的文化內涵而言,剝開季節的修飾,“雨”依然可以支撐起“象外之景”。“雨”與水同源,既可以暗示詩人的性別,又可以揭示詩人的性格。“下雨之前,再次坐下來/想一首好詩的名字,和它的內涵/那時候我沒在這里/沒在那里/沒在遙遠的北方/沒在那個有名字又沒有名字的小鎮/風吹屋檐/雨打窗臺,多么詩意啊/一個人約好了她/去縫補晚年的白襯衫。現在/天空開始下雨/下在夏日/下在傍晚的前沿/下在她隨手翻開的書頁上”(《下雨》)。沒有過多修飾雨的狀態,比如纏綿、比如狂暴,但舒緩而平淡的敘述,卻可以將陰霾、憂傷同時也是愜意的感受置于其中。沒有更多的色彩,也沒有他者到場,夏雨筆下的雨平和、沖淡,有小鎮的記憶和寧靜,同樣也有一種莫名的安詳:夏天的微雨,即使不是在江南水鄉,依然可以詩意盎然,隱含著少女處子般的純潔感情;雨天最好的事情是聆聽雨滴敲打屋檐和窗臺的聲音,構想一首好詩。生活中的女詩人夏雨也是如此,安靜、純粹,雖言語不多卻從不淺薄。
我們是在時間的推移讓季節發生變遷和輪回中,感受到一種成長的過程:
黃昏終于成熟了
它飽滿的欲望
適合有我這樣一個落寞的女子
——《秋天的黃昏》
沒有什么能夠抗拒蒼老的過程,在時間的檢視下,詩人和她筆下的主人公一起成熟。黃昏、欲望,還有一絲落寞,總之變化會潛含著一系列新的體驗;成長是令人煩惱的,因為成長會帶來一種焦慮,會充斥越來越多的欲望。在“一種暴風雨過后的寧靜與清新”中,詩人感受到“但已沒有什么物事/能妨礙我日益憔悴與不堪”。《我越來越老了》,即使僅從題目去猜測與感受,詩人也進入了另一重心境之中,為此,我們必然要重新認識一個詩人和她此時此刻的詩!
四、“去春天”的轉折
如果強行將夏雨的詩歌通過女性的體驗甚至女性意識等概念進行扭結,或許會產生一種新的視角或曰論述方式。女性、“70后”還有滿族,都會為夏雨的詩歌言說帶來種種命題。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慣常的言說方式也許是徒勞的。“回到寫作本身,我想:堅持下去,或就此停止,也許都是一件好事。”[2]當夏雨在其最近一本詩集《去春天》的“后記”寫下這樣的話,我覺得她已成為一位成熟的詩人,而成熟的詩人不僅要書寫自己的內心,還會關注更為廣闊的生活和詩歌本身的整體發展趨勢,以不斷進步的實踐追逐詩神的腳步。

從世紀初十年來詩歌的發展來看,貼近生活、發現生活,通過寫實與想象接生活之“地氣”,已成為詩人共同關注的寫作方式。“我愿意將所有未被發現的事物/想象成美好/我愿意將所有已被人類發現的事物和道路/重歸于美好”。出現于《新生活》中的這幾行詩說出了夏雨生活態度的新,表明了夏雨對待生活的視點降低與視野擴展。及至那些寫電廠作業的詩,《微小的電波》《上夜班的人》《回到發電機旁》《煙囪》《拉電纜》《一座火力發電廠的聲音》、《發電廠的生活》……夏雨的詩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更加切近日常的現實生活,且深入到生活的底層;將情感和記憶的觸角聚集在具體的情境之上,實現一種向內的收縮和經驗的重組,而發電廠、生活和小鎮、清河就這樣凝結在一起,并實現一種創作上的“拓展”和有效的“補充”:
發電廠純凈的生活,像這個春天
暗合著綿延的呼吸
和起伏的愛
隨著以后的歲月向前走去……
——《發電廠的生活》
我的小鎮,我的發電廠
我溫潤的生活,像天邊的滿月
清晰地映在水底
也像轟隆而來的火車
暗藏著起伏有致的激情與光明
——《我的小鎮,我的發電廠》
她將發電廠的生活描繪得如此純凈、生動、富有生命力;又將呼吸、溫潤以及火車等意象共置于詩歌空間內,實現動靜結合、萌生可以感知的質地與觸感;她讓詩歌始終在光明和純凈的道路上前行,這樣的寫作使詩歌始終保持著淡雅的色調,而其背后則是詩人渴求永遠年輕的心!
按照夏雨的說法,《平衡術》出版后,她有很長一段時間與自己“糾結不清”,“寫詩之初那種快樂的心境蕩然無存”。經過與自己反復對抗、和解,再對抗、再和解的過程,夏雨意識到自己已“忽略了生命中很多原本更有意義的東西”[3],所以,詩集《去春天》出現了;我們也因此聽到了發電廠的聲音和退休工人對于電廠的熱愛。像數年前詩歌批評界流行的“底層”之說,夏雨從關注生活而看到了立在身邊已久的形象與面貌,她的創作也隨即走出日常狹窄的空間,呼吸著春天來臨時清新的空氣,夏雨面向了更為廣闊的世界。
“轉折”之后的夏雨還一度將筆觸聚焦于詠物之上。《去春天》中的“第五輯衣·飾之書”,以大量制衣原料和服飾入詩。對于《絲綢》《羽毛》《亞麻》以及《鉆石》《珍珠》、《珊瑚》《水晶》等,夏雨總是選取特定的角度,突出其質地、升華其精神。縱觀夏雨多年的創作道路,詠物之作并不是夏雨最好的作品,但它們的出現卻使夏雨詩歌的題材范圍、想象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夏雨詩歌的視野由此得以擴展,而新的寫作契機也必將蘊含其中。
如果說“平衡術”可以視為夏雨詩歌最初的觀念,那么,在“平衡術”之內,我們看到的是夏雨的內心;在“平衡術”之外,我們讀到的是世界。應當說,作為一個始終保持安靜狀態寫作的詩人,夏雨的詩擁有很高的藝術品位并具有持續發展的可能。為此,我們有必要對其寫作寄予期待,也許,她更為出色的作品就在不久的將來!
責任編輯 陳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