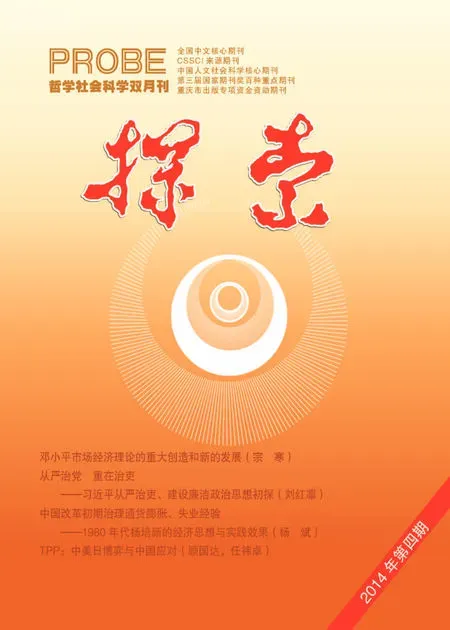社區(qū)社會工作本土化與社區(qū)綜合發(fā)展模式探索
焦若水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甘肅蘭州 730000)
社區(qū)因處于微觀個人/家庭與宏觀環(huán)境的接觸面(interface)而與社會工作推動中國社會轉(zhuǎn)型的訴求最為契合,當代社會工作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解決社區(qū)問題,或?qū)栴}解決于基層的思路而產(chǎn)生,社區(qū)社會工作也因此成為現(xiàn)代社會工作方法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社區(qū)為本的社會工作致力于系統(tǒng)化的雙向改變:作為結(jié)構(gòu)的環(huán)境是透過社區(qū)或日常生活形塑個人/家庭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guī)范,與此同時,個人能動性反過來又深刻地影響社區(qū)氛圍乃至自然社會環(huán)境[1]。我國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展開的特殊社會歷史背景,使得我國社區(qū)社會工作的發(fā)展具有嵌入和競爭化的特點,由此決定了現(xiàn)實的社區(qū)社會工作開展受多個利益相關(guān)方的影響和制約,社區(qū)社會工作的有效展開也就注定有著強烈的本土化特色,基于實踐的社區(qū)為本的社會工作發(fā)展將有別于西方社區(qū)社會工作開展的既定范式,我們以L市一個“三不管”樓院Q社區(qū)的社區(qū)社會工作發(fā)展為案例,提出綜合專業(yè)社會工作和實際社會工作、整合現(xiàn)有社區(qū)社會工作三種模式的社區(qū)綜合發(fā)展模式。
一、社區(qū)變革中的需求與沖突
在當代城市研究將關(guān)注點集中于社區(qū)此起彼伏的維權(quán)運動時,社會工作卻在功能主義的影響下強調(diào)問題的個體化,認為隨著社會交往的碎片化,以及生活空間的封閉化和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趨于個人化、私性化,個人成為原子化的大眾,市民共同體和自發(fā)組織的弱化,使得個人的生活安全越來越依賴于國家的保護[2]。住宅開發(fā)的商品化使得原有的城市空間被分割化,基于社區(qū)團結(jié)基礎(chǔ)上的自主互助也因為物業(yè)公司外包式的服務(wù)而陷于消解,城市居民已經(jīng)習慣于購買服務(wù)而喪失合作提供服務(wù)的能力。在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夾擊下,僅有少數(shù)社區(qū)通過業(yè)主委員會等形式“抗爭化、運動化”地進行自主互助式的服務(wù),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工作服務(wù)的興起試圖通過專業(yè)化方法介入,為中國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的共同體發(fā)展貢獻力量,但許多專業(yè)社會工作者單純強調(diào)用科學知識和方法解決“案主”的問題,往往使社會工作陷入修修補補的境地。特別是城市社區(qū)工作受城市巨量流動人口、老齡化、社會轉(zhuǎn)型帶來的弱勢群體等問題的影響,將大量精力和資源放在源源不斷的“個案”上面,忽視造成社區(qū)問題的社會根源,不但導(dǎo)致有限社會工作資源的浪費和低效率利用,而且造成社會工作的無力感,社區(qū)社會工作改變社會結(jié)構(gòu)與不合理狀況的功能被大大遮蔽,導(dǎo)致表面光鮮的社會工作在街區(qū)權(quán)力體系中逐漸失去影響[3]。實際上,物業(yè)公司規(guī)制體系缺乏導(dǎo)致的物業(yè)糾紛,社區(qū)中業(yè)委會維權(quán)困境迫使社區(qū)成員采取各類集體抗爭行動(上訪、游行、訴訟、訴之媒體乃至暴力手段),居委會工作理念與方法的滯后導(dǎo)致自上而下公共服務(wù)資源與自下而上社區(qū)需求對接錯位,社區(qū)社會組織發(fā)育不全導(dǎo)致社區(qū)公共事務(wù)缺乏居民參與,社區(qū)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都是社區(qū)各利益相關(guān)方缺乏合作機制與能力的表現(xiàn)。在社會工作的實務(wù)中,很少看到社會工作者介入社區(qū)治理結(jié)構(gòu)的創(chuàng)新中,社區(qū)業(yè)主委員會、物業(yè)公司和居委會往往被視為社會工作者進行服務(wù)時的宏觀背景,鮮見社會工作者在實務(wù)中將其納入服務(wù)對象范疇,更遑論社會工作倡導(dǎo)與領(lǐng)導(dǎo)層開發(fā)的體現(xiàn)和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與社會建設(shè)的能力。社會工作正在失去對社區(qū)轉(zhuǎn)型宏觀結(jié)構(gòu)關(guān)注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當代社會學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社會問題范式”的影響,將注意力集中于新建商品房的業(yè)主維權(quán),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城市中不同的、多層級的住宅產(chǎn)權(quán)形態(tài),也就大大制約了社會工作介入社區(qū)發(fā)展回應(yīng)社區(qū)特殊需求的有效性,特別是許多社區(qū)內(nèi)部本身有高度的復(fù)雜性,居民對社區(qū)服務(wù)、社區(qū)管理、社區(qū)參與等方面的需求、能力、意愿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避免一腔熱情的僅僅以一部分社區(qū)居民中積極分子的需求來推動社區(qū)發(fā)展。從社區(qū)內(nèi)部行動主體的角度來看,新型城市社區(qū)經(jīng)歷了從分散的單個房產(chǎn)利益的機械集合到共同房產(chǎn)利益的有機整合的發(fā)展過程。社區(qū)共同體將從地區(qū)性、社會性、群眾性、公益性事業(yè)中日益發(fā)展成為一個中介體和網(wǎng)絡(luò)組織,并在內(nèi)部實現(xiàn)非行政的縱向溝通和橫向聯(lián)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從社區(qū)社會工作的理論僵硬出發(fā),將導(dǎo)致專業(yè)社工被吸納到街道的權(quán)力網(wǎng)絡(luò)過程,導(dǎo)致社會工作外部服務(wù)行政化、內(nèi)部治理官僚化和專業(yè)建制化問題,對復(fù)雜的街區(qū)權(quán)力關(guān)系認識的缺乏大大限制專業(yè)社工嵌入社區(qū)治理的深度[4]。將社會體系理論應(yīng)用于社區(qū)研究,正是把社區(qū)視為集中于某一地方而又比較持久的相互作用的體系,把社區(qū)視為許多個人、群體、機構(gòu)之間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日常生活總是通過社區(qū)里的網(wǎng)絡(luò)來進行的[5]。從社會體系理論來看社會工作的服務(wù)對象,將更加明晰地發(fā)現(xiàn)作為居民個體和社區(qū)的生態(tài)圖,也可以使社會工作介入更為宏觀的社區(qū)治理,推動社會工作發(fā)揮建設(shè)性的作用與價值。
在現(xiàn)行的社區(qū)社會工作模式中,我們一般性地將社區(qū)社會工作分為地區(qū)發(fā)展模式、社會策劃模式、社區(qū)照顧模式等三種類型。不過,這三種模式除了存在調(diào)和不同利益群體的手段不足、居民參與率低和服務(wù)對象依賴性上升、政府責任與角色不清晰、社區(qū)積極分子的激勵不足等問題外,還存在與特定社區(qū)工作展開的時空歷程以及變化契合度不足的問題。實際上,社區(qū)社會工作的有效開展需要整合社區(qū)內(nèi)居委會、物業(yè)公司、業(yè)主委員會等各類組織資源,才能形成合力為社區(qū)提供優(yōu)質(zhì)服務(wù)。而且社區(qū)社會工作具體策略的采用和社區(qū)實踐變化緊密聯(lián)系,如果僵硬地套用社區(qū)社會工作的基本模式,非但不能解決社區(qū)中的實際問題,往往還會起到相反效果。立足中國城市社區(qū)工作的實際狀況,探索形成社區(qū)綜合發(fā)展模式就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二、社區(qū)社會工作介入城市社區(qū)的空間與途徑
(一)社區(qū)問題界定與需要
Q社區(qū)于1998年建成,現(xiàn)有居民104戶,建成伊始就是商品房和單位建房等多種形式混合體制的產(chǎn)物。社區(qū)是臨街的獨棟建筑,除了二樓的平臺以外,社區(qū)本身沒有任何公共空間與場所;社區(qū)業(yè)主的停車通過物業(yè)公司協(xié)調(diào)在L文化館院內(nèi)停放;社區(qū)的供水、供暖管道與設(shè)施都與文化館相連接。由于物業(yè)公司整體承接文化館片區(qū)的物業(yè)服務(wù),因此Q社區(qū)的物業(yè)服務(wù)長期與文化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也為社區(qū)物業(yè)服務(wù)埋下了很多潛在的沖突隱患,伴隨著社區(qū)物業(yè)服務(wù)許多摩擦事件的發(fā)生,社區(qū)與底層商鋪之間在物業(yè)管理上的沖突,社區(qū)停車以及內(nèi)側(cè)樓院與文化館之間的沖突,社區(qū)車位使用的沖突以及社區(qū)樓頂大型廣告牌、移動通訊塔租用費的分配等問題逐漸顯現(xiàn)出來。2012年12月,由于物業(yè)費收繳、物業(yè)管理水平等多個問題,物業(yè)公司在未告知業(yè)主的情況下撤出,社區(qū)在很短時間變得和垃圾場無異。“忍無可忍”的居民自發(fā)組織達成了“平臺協(xié)議”,嘗試進行居民自主性治理樓院。處于困境中的居民在自管初期表現(xiàn)出很大的積極性,四十多位業(yè)主當場交了費用。居民自主性治理樓院的積極分子都是志愿參與的,所以其公信力建立在費用收繳使用的公開透明上,在自管小組的努力下,Q社區(qū)的環(huán)境得到極大改善,新修了保安室彩鋼房,每個單元門口都安置了桌子,平臺上安裝了路燈、花壇。在平臺上安裝路燈,晚上小孩、老人出行更加便捷。Q社區(qū)的物業(yè)自管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許多潛在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Q社區(qū)雖然只有104戶居民,但是社區(qū)居民絕大部分是上班族且收入普遍較高,60歲以上空余時間較多的業(yè)主只有兩個人,且參與動力不足,這就使得自管會在應(yīng)急式地解決了社區(qū)的垃圾問題之后,核心小組成員的穩(wěn)定性和長期發(fā)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七個樓道每個樓道選出來的2名志愿者和1名自管會成員的后續(xù)參加難以得到保障。與樓院自管初期每個樓道2名志愿者完成召集、收費達到社區(qū)102戶的高效率工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后期有關(guān)物業(yè)維護的會議居民參加率不到30%,連志愿者往往最后都聯(lián)系不到。自管會雖然得到大多數(shù)業(yè)主的支持,但也有少數(shù)居民持懷疑態(tài)度,自管會負責人門前甚至出現(xiàn)了侮辱性的張貼,自管會成員的志愿精神和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
Q社區(qū)面臨的問題在于,短期內(nèi)的物業(yè)管理問題雖然得到初步解決,但是如果居民參與率不高,自管的可持續(xù)就難以維系下去,同時居民普遍出現(xiàn)“以繳(費)代管”的情緒,直接結(jié)果是將本應(yīng)屬于自身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社區(qū)管理職責意識極大淡化;自管會成員積極性受挫使得社區(qū)陷入后續(xù)無人敢管、無人能管的挑戰(zhàn)。一旦具有相當熱心和管理能力的第一批居民志愿者工作失敗,將徹底使其他居民再承接和自管的主動性和信心受挫;社區(qū)自管會與利益相關(guān)方之間的溝通合作機制不足,社區(qū)物業(yè)管理出現(xiàn)問題之后,自管會曾經(jīng)和社區(qū)進行接洽,居委會也表現(xiàn)出高度的主動性,但后續(xù)業(yè)主委員會成立等需要大量具體工作,受挫后的自管會產(chǎn)生畏難情緒,對工作分工和人員不足問題有很大顧慮。Q社區(qū)自管小組的探索與問題得到媒體的關(guān)注,媒體通過相關(guān)渠道找到專業(yè)社會工作者,希望通過社會工作專業(yè)方法的介入,幫助Q社區(qū)解決社區(qū)問題。
(二)社會工作者介入的社區(qū)再動員
社會工作者在與自管小組會面之前,通過深訪較為詳細地了解Q社區(qū)面臨的問題和可能機遇,但是與社會工作接案的規(guī)范流程有很大區(qū)別的是,求助者并非社區(qū)居民,而是媒體記者,社會工作者面臨的問題既有社區(qū)內(nèi)部的問題,又有轄區(qū)單位、基層政府、物業(yè)公司等多個利益相關(guān)方。在這種情況下,社區(qū)社會工作通用的社區(qū)策劃、社區(qū)動員、社區(qū)照顧三大模式并不適用。處理社區(qū)志愿居民的受挫情緒,明確自管小組成員的分工以降低工作的壓力感,強調(diào)社區(qū)居民的參與性,提供正面的積極鼓勵與支持成為社會工作者介入Q社區(qū)需要首要處理的問題。
社會工作者商定在自管小組成員全部能參加的時間在Q社區(qū)平臺上進行溝通,自管小組成員全部參加保證了可以全面了解社區(qū)自管的信息,并在會議上討論下一步工作,花園平臺則能夠體現(xiàn)自管小組的工作成效,有效激勵自管小組下一階段的工作。不過,自管小組成員通過報紙看到社會工作者對案例的解讀和建議后,卻普遍期望社會工作者能帶來“專家”式的權(quán)威性指導(dǎo)意見,而非自己做抉擇。社會工作者沒有直接拒絕提供咨詢意見,也沒有直接給出建議,而是通過分享類似案例,通過案例討論激發(fā)自管小組成員的行為動機。自管小組成員在案例的討論中發(fā)現(xiàn),與“H小區(qū)環(huán)境式自管”的成功經(jīng)驗相比較,Q社區(qū)已經(jīng)完成了前面90%的工作,社會工作者積極激勵自管小組成員的熱情,并引導(dǎo)其受挫情緒的處理。運用頭腦風暴方法引導(dǎo)小組進行討論,自管小組成員在案例中找到了更多可借鑒之處和Q社區(qū)可以創(chuàng)新的空間,在大白紙上記錄了下一步工作的規(guī)劃,并設(shè)立了將Q社區(qū)自管案例做成L市社區(qū)物業(yè)自管典型和榜樣的愿景。通過第一次的會面,社會工作者有效激發(fā)了案主的樂觀情緒、希望和動機,并設(shè)立了近期工作計劃和遠景目標。
社會工作者在社區(qū)的角色,可以是引導(dǎo)的角色,幫助居民選擇發(fā)展目標和決定需要,主動發(fā)掘問題并采取合理的行動;可以是促成者的角色,鼓勵社區(qū)討論問題,加強組織,尋求共同目標和改善人際關(guān)系等;也可以是專家的角色,分析社區(qū)問題,提供研究技術(shù)等;還可以是治療的角色,緩和社區(qū)沖突,消除社區(qū)緊張以及調(diào)和社區(qū)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等[6]。在Q社區(qū)的實際工作中,社會工作者“專家權(quán)威式”的單一期待有所改變,但社會工作者深知其在社區(qū)發(fā)展中的角色扮演直接決定著社會工作的功能發(fā)揮,直接影響到社區(qū)發(fā)展的進程。社會工作者在完成第一次會面之后,約定在一周以后自管小組成員對討論所達成的共識作進一步明晰后再次商談。社會工作者將Q社區(qū)下一階段的工作重心轉(zhuǎn)移為資產(chǎn)為本的發(fā)展方向,資產(chǎn)建立模式的核心前設(shè)是每個人都具有能力、潛質(zhì)和天賦等,關(guān)鍵是要發(fā)掘并抓住這些資源,開列出社區(qū)及個人能力清單[7]。社會工作者和Q社區(qū)自管小組成員進一步梳理了Q社區(qū)具有的社區(qū)資產(chǎn)。在后續(xù)的會面中,社會工作者進一步介紹和演練開放空間方法、沖突斡旋方法在解決Q社區(qū)物業(yè)管理中的可能前景,特別是社區(qū)服務(wù)的項目化管理方法,幫助自管小組成員解決分工和人員不足問題。通過幾次小組工作,Q社區(qū)自管小組逐漸明確了工作方向:在社區(qū)召開全體居民參與的開放空間討論會,解決居民參與和物業(yè)管理問題;和居委會聯(lián)合進行社區(qū)服務(wù)項目化管理工作坊,組織成立業(yè)主委員會和志愿者團隊,協(xié)調(diào)利益相關(guān)方解決社區(qū)物業(yè)管理的問題。
第一,我們大學的中文系,特別是國立教育學院的中文系,應(yīng)該考慮開設(shè)比較文學課程,供學生,特別是那些有志于成為華文教師的學生們選讀。比較文學的觀點和研究方法,對學生在大學期間的論文寫作,以及大學畢業(yè)后從事華文教學都頗多助益。
(三)推動社區(qū)組織化與參與式社區(qū)發(fā)展
社會工作者了解到自管小組與居委會一直有聯(lián)系,但并未形成合作關(guān)系,而居委會當年正在著力完成區(qū)政府“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年”的工作任務(wù),樓院長工作正是該居委會工作的亮點。居委會苦于Q社區(qū)居民普遍收入較高,介入社區(qū)公益工作動力不足。居委會曾試圖將Q社區(qū)自管小組朝業(yè)主委員會的方向引導(dǎo),但因工作理念和方法的問題沒有能夠?qū)崿F(xiàn),社會工作者經(jīng)過和居委會溝通,居委會決定在Q社區(qū)設(shè)一個公益崗位,既解決社區(qū)居委會與Q社區(qū)之間的溝通聯(lián)系問題,又大大降低了自管小組的運行成本。在完成政府工作要求的推動下,居委會成為解決Q社區(qū)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力量,社會工作者慢慢開始扮演協(xié)調(diào)者的角色,后期的Q社區(qū)會議都逐漸變?yōu)榫游瘯妥怨苄〗M共同協(xié)調(diào)。在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的協(xié)調(diào)下,自管小組與物業(yè)公司、文化館進行溝通,對樓頂?shù)膹V告牌歸屬與收益問題、前期物業(yè)遺留問題、停車位問題進行了協(xié)商,自管小組開始自覺運用開放空間方法聽取居民和利益相關(guān)方的意見,不再以“問題視角”而是“優(yōu)勢視角”出發(fā)解決問題,大大降低了文化館面對分散業(yè)主和可能矛盾的畏難與推脫心理,也使自管會在社區(qū)居民中的組織協(xié)調(diào)地位逐漸突出。
在Q社區(qū)自管小組的內(nèi)部建設(shè)和外部環(huán)境都得到有效改善的情況下,如何鞏固和延續(xù)前期工作的成果就成為下一階段工作的重點。Q社區(qū)雖然只有104戶居民,但是依然出現(xiàn)了居民依賴自管小組,將自管小組視為第二物業(yè)公司的思維慣性,特別是自管小組提高物業(yè)費收費標準后,許多居民更是認為只要自己付費就是對社區(qū)自管的支持,不參與社區(qū)任何活動。自管小組面臨的社區(qū)居民參與不足和“以交代管”的問題而難以持續(xù)。社會工作者和自管小組的成員反復(fù)進行討論,通過對其他社區(qū)類似問題解決的案例分享和視頻觀看,自管小組成員表現(xiàn)出對“開放空間”的濃厚興趣,104戶居民和經(jīng)過整治的社區(qū)平臺也具備舉行“開放空間”討論社區(qū)物業(yè)管理問題的可行性。自管小組成員經(jīng)過和每個樓道選出來的2名志愿者和居民的廣泛溝通,決定利用周末晚上時間在花園平臺上召開“開放空間討論會”,自管小組在會議召開之前就將花園平臺做了精心布置,將討論會的各項事宜通過形式多樣的粘貼向居民展示,提出居民如果不積極參與到社區(qū)物業(yè)管理中,房產(chǎn)的貶值和生活質(zhì)量的下降將會極大影響居民的切身利益。在前期充分的準備工作下,居民委員會、文化館物業(yè)辦公室、原物業(yè)公司的代表也都參與了會議討論,甚至吸引了附近社區(qū)居民的參加。“開放空間討論會”使居民特別是有抱怨情緒和表達意愿的居民都參與其中,也使自管小組成員更加感受到從獨角戲到同臺演出轉(zhuǎn)變的重要性。各利益相關(guān)方對物業(yè)管理可能的問題和挑戰(zhàn)做了詳細的討論,對前期物業(yè)的遺留問題做了原則性協(xié)定,解決了Q社區(qū)物業(yè)自管的后顧之憂;商定通過自管小組和居委會設(shè)在Q社區(qū)公益崗位人員統(tǒng)籌協(xié)商事務(wù),并在花園平臺公告欄隨時發(fā)布信息的長效機制。
居民討論會召開之后,Q社區(qū)自管小組的成員已經(jīng)習慣于用需求評估方法來化解物業(yè)管理中面臨的各種問題,物業(yè)費的收繳由上門收變?yōu)榫用衤愤^門衛(wèi)室自覺交,信息公開由單向發(fā)布變?yōu)楣鏅诨咏涣?應(yīng)急式的救火員工作方式轉(zhuǎn)變?yōu)楣嫘詬徫怀R?guī)解決,自管小組的成員甚至開始被邀請到相鄰社區(qū)指導(dǎo)解決類似問題。成功解決Q社區(qū)物業(yè)管理問題也使社會工作者得以更為廣泛地介入到當?shù)氐纳鐓^(qū)工作中,社區(qū)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都邀請社會工作者參與當?shù)厣鐓^(qū)建設(shè)工作和相關(guān)培訓(xùn)咨詢工作,原物業(yè)公司在其他社區(qū)中遇到業(yè)主維權(quán)活動時也咨詢社會工作者如何應(yīng)對。社會工作者對Q社區(qū)介入的成功實踐,說明社區(qū)不應(yīng)該只是社會工作的項目地,而應(yīng)該成為社會工作的事業(yè)之根。社會工作應(yīng)該長期深入地扎入某個具體的社區(qū),并根據(jù)社區(qū)的節(jié)奏開展工作,它應(yīng)該推動組織的在地化,同時也應(yīng)該積極進行資源的鏈接,使外部公益網(wǎng)絡(luò)和社區(qū)能夠連接起來,從而在社區(qū)中形成社會力量,參與到社區(qū)治理中去[8]。
三、實踐需求與本土化導(dǎo)向:社區(qū)社會工作綜合模式的形成
20世紀后期以來,西方社會工作實務(wù)被個體化和市場化逐漸侵蝕,社區(qū)和群體的作用大大下降,社區(qū)社會工作也逐漸失去其重要地位。我國的社區(qū)建設(shè)則因一開始被視為國家社會建設(shè)的基礎(chǔ)單元,在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分法中日漸分離化,社區(qū)更多地被視為社會工作開展的場所和空間,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社區(qū)社會工作。我們認為,社區(qū)社會工作在中西方社會中具有很大區(qū)別,不過相通之處并不在于社會工作的專業(yè)性不足,而是社會工作如何真正回應(yīng)來自于社區(qū)的實踐需求,這就需要社會工作者如何更好地回應(yīng)中國社區(qū)建設(shè)和社會工作發(fā)展的結(jié)構(gòu)性要求,運用綜合發(fā)展模式,充分整合多種資源,發(fā)展更加切合社會發(fā)展實踐的本土社區(qū)社會工作經(jīng)驗。同樣,社區(qū)社會工作的本土化,絕非在中西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之間制造人為的對立,真正推進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可行途徑,在于尊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文化,建立以社區(qū)需求為核心的實務(wù),和社區(qū)發(fā)展的利益相關(guān)方一道工作,通過綜合而融入,形成切合實際的社區(qū)社會工作。
(一)實踐需求導(dǎo)向的社區(qū)工作方法綜合運用
社區(qū)社會工作中社區(qū)策劃、社區(qū)動員、社區(qū)照顧三大方法都是社區(qū)社會工作理論和邏輯上的分類,但任何方法的使用必須和社區(qū)發(fā)展的實踐結(jié)合起來。王思斌教授指出,當前社會工作的發(fā)展是專業(yè)和非專業(yè)社會工作的相互嵌入,專業(yè)社會工作在嘗試嵌入到本土社會工作當中尋找并創(chuàng)造自己的發(fā)展模式[9]。從社會工作實務(wù)通用過程模式的接案、預(yù)估、計劃、實施、評估和結(jié)案整個過程中,我國專業(yè)社會工作在服務(wù)介入都異于西方社會工作理論的獨特工作方式及內(nèi)容[10]。中國社區(qū)社會工作的獨特價值還在于社區(qū)社會工作一度在西方成為社會工作實務(wù)的外圍,當今重返社區(qū)成為許多國家社會工作的新選擇,在一個整合社會工作者的部門里,聯(lián)合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產(chǎn)業(yè),聯(lián)合允許重新建立社會關(guān)系,而且也是社區(qū)生活的推動力之一。分享同一行動、為了共同目標而無私合作的快樂不但能夠提高活動服務(wù)人群的福利,而且還能恢復(fù)并提高我們的公民身份、我們的目標環(huán)境,以及我們的人性[11]。
無論是從國家層面2006年以來推進的社區(qū)建設(shè)與社會工作事業(yè)受到的空前重視,還是2013年12月民政部、財政部聯(lián)合下發(fā)的《關(guān)于加快推進社區(qū)社會工作服務(wù)的意見》,都充分表明社區(qū)社會工作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是社會干預(yù)的主要形式。中國的社區(qū)發(fā)展的內(nèi)生力量來自于社區(qū)居民有意愿改變的問題,社區(qū)社會工作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則來自于國家基層社會治理、商品房物業(yè)化管理和居民自治等多個因素的互動。我們的研究表明,在城市社區(qū)開展社區(qū)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的專業(yè)化和“科學程序”等體現(xiàn)社會工作者的專業(yè)能力固然重要,但是通過發(fā)動社區(qū)發(fā)展的各利益相關(guān)方積極參與,建立社區(qū)、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的互動機制,以綜合模式推進社區(qū)治理更符合當下眾多城市社區(qū)發(fā)展的實踐需求。
(二)從無主體的社區(qū)發(fā)展到利益相關(guān)方合作
(三)從社區(qū)社會工作到對“社區(qū)”的社會工作
在我國實施社會建設(shè)與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的新時期,社區(qū)是基礎(chǔ)單元,這就決定了從社會工作本身出發(fā),將社區(qū)社會工作僅僅視為一種工作理念與方法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社會工作者必須站在“黨委領(lǐng)導(dǎo)、政府負責、社會協(xié)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戰(zhàn)略格局,審視社區(qū)在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與意義。社區(qū)社會工作的服務(wù)對象不僅僅是社區(qū)中的弱勢群體和普通居民,而是將社區(qū)中在場的國家——社區(qū)黨組織和社區(qū)居民委員會、市場的社區(qū)化力量——物業(yè)公司、社區(qū)社會組織共同組織起來,在社區(qū)這一層面整合宏觀社會資源,著力改變“社區(qū)是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的現(xiàn)實困境。社會工作介入形成的內(nèi)外合作力量有利于形成能和企業(yè)、政府平等協(xié)商的合作治理格局。這依賴于社會工作者在社區(qū)中長期的工作,在社區(qū)中形成互惠、信任與網(wǎng)絡(luò),從而使得社會工作形成一種社會力量,也才能夠和政府、市場形成真正平等的合作,使權(quán)力得到制衡[8]。在這個意義上,社區(qū)社會工作并不是局限于“社區(qū)的問題”,而是要關(guān)注“社區(qū)問題”,從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的角度重新定位社區(qū)在社會發(fā)展中的地位與價值,建立對社區(qū)發(fā)展的支持體系,推動社區(qū)在社會發(fā)展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張和清.社會轉(zhuǎn)型與社區(qū)為本的社會工作[J].思想戰(zhàn)線,2011,(4).
[2]陳映芳.城市與中國社會研究[J].社會科學,2012,(10).
[3]朱健剛,陳安娜.嵌入中的專業(yè)社會工作與街區(qū)權(quán)力關(guān)系:對一個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的個案分析[J].社會學研究,2013,(1).
[4]趙懷娟,林卡.需求與供給:中國社會工作職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分析[J].山東社會科學,2012,(6).
[5]焦若水.組織、網(wǎng)絡(luò)與社區(qū)治理——基于北京市三個社區(qū)的實證研究[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9.
[6] Morris. “The Role ofthe Agenton Community Development”in Lee G.Cary(ed)[G]//Community Development as A Process.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0.
[7]Snow,L.K.The Organization of Hope:A Work Book for Rural Asset-basedCommunityDevelopment[M].Chicago:ACTA Publications,2001.
[8]朱健剛.轉(zhuǎn)型時代的社會工作轉(zhuǎn)型:一種理論視角[J].思想戰(zhàn)線,2011,(4).
[9]王思斌.中國社會工作的嵌入性發(fā)展[J].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1,(2).
[10]閔學勤,黃燦彪.適度的社區(qū)自治及其路徑選擇——基于香港和內(nèi)地社區(qū)治理模式的比較[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
[11][西班牙]Antonio López Peláez,Sagrario Segado Sánchez-Cabezudo.21世紀社區(qū)社會工作所面臨的新挑戰(zhàn):以西班牙為例[J].社會保障研究,2012,(5).
[12]張和清,楊錫聰,古學斌.優(yōu)勢視角下的農(nóng)村社會工作:以能力建設(shè)和資產(chǎn)建立為核心的農(nóng)村社會工作實踐模式[J].社會學研究,2008,(6).
[13]夏建中.社會學的社區(qū)主義理論[J].學術(shù)交流,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