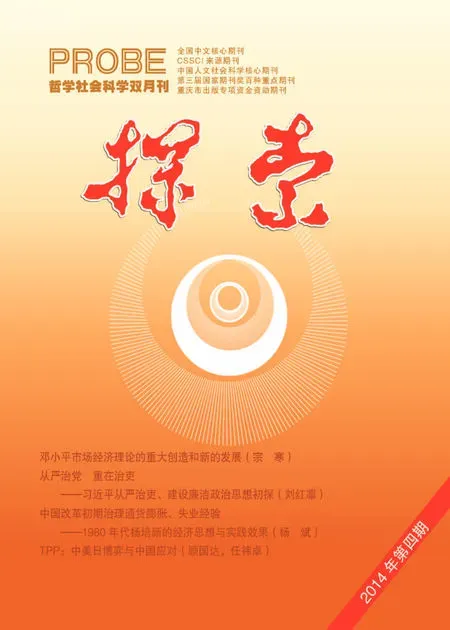中國改革初期治理通貨膨脹、失業經驗
——1980年代楊培新的經濟思想與實踐效果
楊 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北京 100732)

一、楊培新榮獲2014年度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
楊培新,1922年1月生于廣東大埔縣百侯鎮。1938年在武昌中華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國共產黨。1943年進入重慶《商務日報》,先當記者,后任采訪部主任,主要承擔了揭露國民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對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殘酷剝削,國民黨官吏的貪污、腐敗,以及民族工商業的衰敗和掙扎的工作。內戰爆發后,參加上海《文匯報》,任經濟版主編。在這期間,出版了《新貨幣學》、《中國通貨膨脹論》,在香港出版了《C C豪門資本解剖》、《T V宋豪門資本解剖》、《大財閥蔣介石》。上海《文匯報》被封后,赴香港創辦《文匯報》。
1949年,楊培新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的秘書并兼任宣傳處長等職,創辦并主編《中國金融》雜志。1978年三中全會后,擔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著手金融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調查研究,并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建議。1982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此后曾先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首鋼公司顧問。在這期間主要著作有《舊中國通貨膨脹》、《新中國五年來經濟建設成就》、《中國的金融》、《論我國銀行改革》、《我國社會主義銀行》、《我國貨幣政策》、《華俄道勝銀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新思路》、《承包制——企業發達必由之路》、《通貨膨脹——人民的災難》等。
2014年4月19日,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在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舉行。楊培新榮獲2014年度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中國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代表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評獎委員會對楊培新的成就做了充分的肯定和褒獎,指出楊培新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金融學家和教育家,新中國金融制度建立和金融學科發展的重要貢獻者和奠基人之一。認為楊培新從事經濟金融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學科建設工作長達70余年,為推動我國金融、經濟領域的理論研究、經濟金融體制改革、金融教育和人才培養做出了卓越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楊培新為推動中國經濟金融改革傾注了自己的心力。早在1978年,楊培新就提出了推動銀行改革的政策主張,堅持在銀行改革中引入市場機制,并通過銀行體制改革支持全面經濟改革的進程。在金融改革中,楊培新提出了“首先擴大基層行的自主權,發展多元化的金融結構體系和金融市場,改革和完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最終建立現代市場濟和金融體系”的改革路徑。
在20世紀80年代,楊培新撰寫了大量的文章、著作和政策建議,闡述他的貨幣政策、價格改革和金融全面改革的主張,經黨中央國務院采納后,促進了中國改革的平穩推進,取得了兼治通貨膨脹和失業困難的顯著效果,成功克服了治理通貨膨脹與失業不可兼得的“二元悖論”,同時也避免了俄羅斯“休克療法”模式帶來的劇烈社會動蕩。
在經濟領域改革中,提出了先從簡政放權開始,并通過承包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然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主張,并被中央采納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被理論界戲稱為“楊承包”。楊培新提出的貨幣政策、價格改革、金融改革、企業改革、財政改革等主張,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整體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而且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避免市場轉軌過程當中的市場代價,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楊培新在經濟金融理論研究與推進現實改革做出貢獻的同時,在金融教育與人才方面表現也很搶眼,他參與創辦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現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前身)和廣東嘉應大學,并任嘉應大學的首任校長,兼任多所大學的教授,培養了大量的金融專門人才。
二、西方學者承認解釋中國成功具有深遠意義
楊培新獲得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貨幣政策、價格改革和金融革的主張,促進了中國改革的平穩推進,取得了兼治通貨膨脹和失業困難的顯著效果,成功克服了治理通貨膨脹與失業不可兼得的“二元悖論”,避免了俄羅斯“休克療法”帶來的劇烈社會動蕩。楊培新在20世紀80年代與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弗利德曼相識,他們作為中美兩國研究貨幣和通貨膨脹問題的權威專家有過長期學術交流,兩人學術觀點雖然不同,但在嚴格控制通貨膨脹的主張上有相似之處,弗利德曼在交流中對中國治理通貨膨脹與失業的成就表示欽佩,他曾稱誰能解釋中國的成功就能獲得諾貝爾獎。
上述評價出自一位一慣固執地鼓吹自由市場的著名西方學者之口,絕非是討好逢迎,而是遇到了他實在無法理解的客觀事實,承認中國的成功超越了他認為理想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西方貨幣理論的權威人士尚且如此贊揚中國,中國就更不應該自我輕視、自我貶低本國的成功經驗,而應進行深入研究并提煉出超越西方的市場理論和貨幣理論。倘若盲目追隨和崇拜西方經濟學理論,其實并不能贏得西方經濟學家和學術界的尊重,只有從實際出發敢于堅持中國獨有的特色,才能取得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并且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西方學者對中國走“北京共識”道路成功的贊揚,對俄羅斯盲目追隨“華盛頓共識”失敗的批評,以及近年來國際輿論贊揚“中國模式“都說明了這一點。
弗利德曼認為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關鍵是放開價格,無論忍受任何社會痛苦也不能進行干預,政府唯一可以干預、控制的就是貨幣發行量。弗利德曼所主張的“放開物價發揮市場作用、管緊貨幣控制通貨膨脹”政策,20世紀70、80年代在智利、巴西等拉美國家實施后付出了巨大社會代價,當年智利物價上漲位居全球之冠、失業猛增了十倍之多,廣大民眾陷入極度貧困甚至難以承擔公交費用,平均食物開支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從17%猛增到了接近80%,弗利德曼弟子曾撰文揭露許多兒童因營養不良常在學校暈倒的事實[1];即使在美國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實施后也造成嚴重社會后果,導致實體經濟的眾多企業陷入破產、大量工人失業的情況發生;前蘇聯、東歐經濟轉軌國家實施后付出的社會代價更為慘重,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嚴重經濟衰退、失業危機和民眾儲蓄化為烏有的后果。令人擔憂的是,弗利德曼的市場、價格、貨幣理論仍在全球占據主流地位。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做法與世界其他國家普遍的做法迥異,成功克服了嚴重短缺經濟和隱性通貨膨脹,不僅沒有造成嚴重的失業,而且還解決了數千萬知青待業難題,這意味著中國較好地攻克了治理通貨膨脹與失業不可兼得的“弗利德曼悖論”,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在轉軌過程中更好地發揮市場作用,避免了拉美、前蘇聯和東歐甚至美國等發達國家都被迫付出的沉重代價。弗利德曼稱贊誰能解釋中國的成功就能獲諾貝爾獎,不僅意味著解釋中國成功具有深遠的經濟理論意義,更為重要的是還有解決現實難題和避免社會代價的現實意義。顯而易見,美國、拉美等實行市場經濟上百年的國家都一再遇到的難題,今后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還會因種種原因而不得不面對,如濫發美元引發全球輸入通貨膨脹、油價暴漲、爆發戰爭等等。毫無疑問,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探索和積累起來的治理通貨膨脹與失業的成功經驗,將能夠有效地避免大量企業破產、工人失業和民眾收入、儲蓄縮水的代價。
三、中國改革奇跡超越了西方經濟學理論
早在1978年,楊培新就提出了“經濟改革引入市場調節機制,銀行改革擴大自主貸款權支持國企面向市場擴大生產”[2]的思路。楊培新認為當時流行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帶來了誤導,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運作遠比教科書更為錯綜復雜。他在新中國成立前曾經親身體驗過美國顧問推薦類似政策的效果,抗戰勝利后取消統制經濟過程中就曾經“放開物價、管緊貨幣”,但在供求缺口過大時放開價格以后物價立刻就會不停地上漲,而管緊貨幣政策卻有很長時間滯后效應難以發揮效果,緊縮工商業貸款抑制生產供給不利于吸收過多貨幣,直到企業紛紛破產、工人大量失業導致社會有效需求銳減,企業家、民眾手中沒錢之后才會抑制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又會變成通貨緊縮給工商業、民眾帶來新的經濟災難[3]。
楊培新在改革開放時期處理貨幣與物價關系的政策建議,與弗利德曼的貨幣理論相比取得了更好的實踐效果,關鍵在于發現并穩妥處理了一些重要的市場失靈,而這些市場失靈現象在西方經濟學中往往被忽視。楊培新認為,市場供給和需求之間存在很大缺口的情況下,放開市場價格就會導致價格暴漲并嚴重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這時市場價格機制難以發揮有效調節作用并恢復供求均衡。由于企業受固定資產限制價格上漲刺激,供給的作用非常有限,管緊貨幣就會限制銀行支持企業擴大生產的能力,價格暴漲往往還會誘發市場投機導致需求嚴重扭曲,進一步擴大供求缺口、價格猛漲和市場失衡[4]。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需求曲線看似非常科學、合理,其實僅僅適用于價格均衡點附近供求缺口不大的情況。當由于種種原因導致供求出現過大缺口并遠離均衡價格時,供給曲線向上傾斜一段之后就會變成垂直的直線,原因是受企業設備、廠房等限制難以繼續擴大生產,價格暴漲往往導致大量資本涌入追逐投機暴利,導致正常的需求曲線從向下傾斜變成向上傾斜形成嚴重扭曲,生產者也可能被高額利潤吸引加入投機者的行列,惜售、囤積居奇,扭曲供給曲線發生向后逆轉的傾向,這意味著供給停滯、需求猛增導致價格加速上漲甚至失控,市場價格機制出現失靈并難以促使供求恢復均衡。
楊培新認為,上述情況并非偶然發生,其實在許多條件下都有可能發生,如通貨膨脹、爆發戰爭、資本操縱、過度投機,從戰爭統制經濟或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等,都可能出現供給和需求之間過大缺口和價格機制失靈,出現過度投機市場失靈、通貨膨脹市場失靈、戰爭經濟市場失靈、經濟轉軌市場失靈等等,這些市場失靈往往具有相互作用和彼此擴大趨勢,此時政府不應坐視不管而應根據市場失靈的具體原因,靈活采取各種有效的措施幫助市場機制恢復正常運轉,這樣才能促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楊培新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就長期研究各種商品、金融市場的運行,曾經反復親身經歷過惡性通貨膨脹、過度投機等市場失靈情況,當時的政府和美國經濟顧問對民間疾苦視若無睹,表面上不干預經濟而實際上放任外國、豪門大資本掠奪,市場失靈和供求缺口過大恰恰是投機牟利良機,四大家族豪門資本趁機操縱商品、金融市場投機大發橫財,導致廣大民眾和民族資產階級利益蒙受了巨大損失。
楊培新認為,發揮市場機制的關鍵并不是放開價格,而是生產者自主根據市場需求安排生產,消費者根據自身需要在市場上自主選購商品,在供求缺口不大時可以允許價格自由浮動,這樣既能更加準確調節供求關系又不至于傷害消費者。但是,在供求缺口過大時就會出現價格機制失靈,市場就可能將大量資源配置給趁機謀利的投機者,任由價格暴漲暴跌就會嚴重危及消費者或生產者利益,當構成市場主體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受到嚴重的傷害時,就根本談不上發揮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正常作用,特別是涉及重要大宗基礎商品影響到整個經濟時,就可能帶來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導致經濟陷入危機[5]。存在供求缺口過大、過度投機或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關鍵不是放開價格,而是政府應該將社會利益和民眾利益放在首位,靈活采取各種手段如價格管制、穩定基金、國企配合措施,將價格波動維持在消費者、生產者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同時采取財政、金融、產業政策加快經濟結構的調整步伐,待供求缺口縮小、市場穩定之后再放開價格。
改革初期雖然存在政府管制沒有放開市場價格,但是大多數的價格是在生產者、消費者可接受的范圍內,產品的出廠價格高于成本能夠保證企業有適當的盈利,產品的銷售定價較低照顧到了低收入的普通民眾利益。導致商品供應不足、品種單調的主要原因是計劃太死,只要讓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根據市場需求安排生產,銀行改革擴大自主權并根據市場供求情況發放貸款,就能迅速擴大短缺的消費品生產并縮小市場供求缺口。這種通過擴大生產恢復供求平衡方法比放開價格更為優越,能夠更好保護消費者利益并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避免漲價傷害民眾利益造成阻力反而影響改革的穩妥推進。限制漲價雖然在短期內對生產者利益有一定影響,但從長期來看卻為市場容量擴大留下了更大的空間。企業通過提高效率、擴大投資能夠獲得更大的長遠發展。漲價將刺激生產者沿著供給曲線向上移動達到低水平的均衡,而沿著同一價格水平擴大投資平移供給曲線將達到更高水平的均衡,適當條件下限制價格波動有利于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6]
四、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理論
馬克思認為,價值規律有調節社會化大生產的作用,價格受供求狀況影響圍繞價值波動并調節資源配置。資本家追求最大剩余價值限制了工人的收入增長,生產無限擴大與社會有效需求的矛盾導致生產過剩,爆發經濟危機時價值難以實現并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出現過大的供過于求的缺口和市場調節作用失靈。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為西方社會改良緩解這類市場失靈提供了重要啟示。二戰后西方社會改良、改善收入分配、緩和階級矛盾,實施國有化、金融管制化措施限制資本貪欲,實行匯率、利率和資本賬戶管制并嚴厲打擊金融投機,實際上是在冷戰壓力下被迫借鑒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凱恩斯主義,這在美歐上層精英專家智囊的著作中也直言不諱承認這一點。2008年以來,美歐濫用凱恩斯主義挽救金融危機,卻深陷財政赤字、國債膨脹和濫發貨幣等難以自拔的困境,也從反面說明二戰后西方較好經濟增長來自借鑒馬克思主義。
存在過大供不應求缺口、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將會影響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發揮正常的資源配置作用,此時放開價格將會導致物價飛漲并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引起不同產品相對比價的扭曲,妨礙資源在不同領域的配置,促使大量資源從生產領域流出并引發過度市場投機,結果不創造價值的投機者獲取大量資源引起市場失靈,導致商品生產、流通、消費、投資活動難以正常進行,國民經濟將會陷入長期停滯。這一現象絕非是“短期市場闖關陣痛”。楊培新認為,西方倡導的“放開價格、管緊貨幣”政策,難以控制通貨膨脹并且恢復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將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放在首位,不應恪守西方經濟學維護資本利益的不干預市場教條,而應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將價格控制在消費者可接受的范圍內,特別是影響廣泛的大宗商品、匯率、利率等重要價格,有控制價格比放任價格暴漲更有利于發揮市場正常功能,同時應采取積極的財政、貨幣和產業政策加速經濟結構調整。這樣有利于迅速消除過大的供不應求缺口和通貨膨脹,從而更好發揮價值規律、市場調節作用,恢復供求平衡。
楊培新認為,發揮市場經濟作用,關鍵是維護廣大民眾利益,這是馬克思揭示的社會化大生產時代的市場經濟規律。市場經濟將生產、消費、流通連接成了一個有機整體,遵循這一客觀規律才能促使市場經濟為人民發揮配置資源作用,違反這一規律,損害廣大民眾利益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和經濟危機。楊培新關于如何發揮市場經濟作用和推進改革的主張,不僅符合改革初期黨中央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即衡量改革措施是否正確的標準不是看其符合某種理論教條,而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維護社會穩定。
楊培新提出的穩妥的價格改革和貨幣政策主張得到了政府的認同和采納,最終促使中國平穩渡過了短缺經濟轉軌的危險期并形成繁榮的買方市場,沒有像前蘇聯、東歐國家那樣付出了經濟轉軌的慘痛代價。但是,也應預見,今后由于種種原因還可能出現供求缺口過大的情況,如過度投機、自然災害、爆發戰爭、貨幣失控等,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當前美歐國家已進入了虛擬金融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經濟資源正大量流出創造價值的第一、第二產業,以及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第三產業如教育、科研、醫療等,大量流入不創造價值的虛擬金融投機領域。國際金融資本施壓各國敞開大門、開放資本賬戶,促使國際投機熱錢在世界范圍內能夠迅速流動,人為制造過大市場供求缺口、操縱市場價格暴漲暴跌,特別是操縱大宗商品、匯率、匯率等重要價格的劇烈波動,掠奪實體經濟創造的價值并獲取巨額投機暴利。他們打著自由市場的旗號破壞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功能,釀造頻發金融危機打擊國際對手并掠奪全球民眾財富。美歐金融資本曾誤導突尼斯、埃及等中東國家放開價格、取消補貼,進而趁機在糧食豐收情況下,投機炒作國際糧價暴漲,引發中東動蕩;利用民眾強烈不滿煽動鬧事輸出顏色革命和政權更迭,還曾施壓日本實行匯率、利率自由化并釀造泡沫經濟,致使日本爆發金融危機并陷入二十年經濟停滯。國際金融資本還利用自然災害、爆發戰爭等趁火打劫。這種情況下,如果恪守不干預市場教條就會導致物價飛漲。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國家物價失控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動蕩,二次大戰期間西方國家被迫吸取教訓并普遍實行價格管制。歷史事實證明,其實根本不存在讓廣大民眾忍受“市場闖關陣痛”,結果卻讓市場經濟更好發揮配置資源作用的客觀規律。這些其實都是西方為維護大資本利益誤導別國編造出來的神話,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如果損害民眾利益,其結果就會違反馬克思揭示的生產社會化規律,就會破壞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正常作用,引起乘數擴大的連鎖反應,經濟危機甚至整個社會動蕩。當今世界出現了金融動蕩頻發、戰爭危險加劇的復雜形勢,從這個層面上看,楊培新關于如何矯正供求缺口過大導致的市場失靈現象,控制過度投機、通貨膨脹危害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對于維護民眾利益、社會穩定和經濟金融安全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改革不應照搬西方教科書的市場教條,而應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將維護廣大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這樣社會主義才能比資本主義更好地發揮市場經濟的潛力。楊培新既熟悉市場經濟調節供求、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也反復經歷過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等復雜市場失靈,深知必須將民眾利益放在首位并有效矯正各種市場失靈現象,這樣才能發揮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服務廣大人民。他認為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應將維護人民利益放在首要位置,這樣就能創造出優越于西方的市場、價格和貨幣理論。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人曾經盲目崇拜西方經濟理論,將美國向中國推薦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政策,當作規范的系統經濟改革方案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模式,提出了“價格改革一步到位”的“忍受陣痛闖關”激進價格改革主張,并曾一度占據了上風。但是,憑借楊培新等親身經歷過市場經濟的老一輩經濟學家竭力反對,并提出新的穩定價格主張下,中國并沒有像俄羅斯一樣采納世界銀行推薦的政策建議,而是堅持將維護人民利益和社會穩定放在首位的改革方針,成功避免了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所帶來的社會動蕩和經濟下滑,更好地發揮了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方面的積極作用,避免了美國推薦的市場經濟轉軌方式帶來的社會風險代價。
五、穩妥處理貨幣與物價關系兼治通貨膨脹與失業困難
20世紀80年代,美國向中國推薦“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政策舉措,將這種價格改革與貨幣政策稱為規范的配套改革。楊培新則針鋒相對、旗幟鮮明地指出,“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政策是很不穩妥的,主張貨幣政策和價格改革都必須十分慎重穩妥,貨幣增長應適當并經常根據經濟情況變化調整,不應一刀切而應甄別對待以利于結構調整,價格改革應采取謹慎的漸進方式避免損害民眾利益。為此,楊培新撰寫了大量的文章、政策建議和著作,闡述他的貨幣政策和價格改革主張,并最終贏得了政府的認同和采納,有力地促進了中國改革的漸進平穩推進,取得了兼治通貨膨脹和失業困難的顯著成績,避免了美國認為治理通脹和失業不可兼得的負面效應。
楊培新主張的貨幣政策與價格改革思路,從某種意義上與美國推薦的政策恰恰相反。楊培新認為,在物資短缺導致物價上漲壓力較大時,倉促價格改革等于放手漲價,會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而且漲價受固定資產限制難以馬上刺激供給,特別是此時管緊貨幣就更加難以支持企業擴大生產,不如謹慎推進漸進價格改革緩解物價上漲壓力,同時以比較寬松的信貸供給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支持企業投資改造并擴大短缺商品生產,促使短缺商品供求接近平衡后再放開價格。中國改革初期面臨著嚴重的物資匱乏,數千萬知青返城沒有工作,形勢遠比前蘇聯改革初期嚴峻。中國采取同西方規范藥方相反的辦法,一方面進行謹慎、漸進的價格改革,一方面增加銀行貸款支持輕紡工業,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既增加供給抑制了通貨膨脹,又解決了數千萬知青返城后的待業問題。前蘇聯采取西方推薦的“放開價格、管緊貨幣”政策,卻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經濟衰退和失業危機。1979年—1984年間,我國消費品供應從嚴重短缺變得日益豐富,緩解了隱性通貨膨脹壓力,1983年北京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消費品市場繁榮景象,綿延數公里的皇城根鄰街兩側全是擺滿輕工產品的新商鋪和商攤。我國還通過發展生產新安排了4 600萬人就業,其中國企新增就業占50.38%,集體企業新增就業占49.6%。1979年,公開失業率曾高達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5.9%,但是到了1984年,明顯改善并下降到1.9%[6]。
1978年,楊培新提出了銀行改革支持全面經濟改革,由銀行根據市場情況發放中短期設備貸款以擴大短缺商品生產的思路。1980年冬,由于“洋躍進”上馬了過多大建設項目,國民經濟面臨著物資短缺和物價上漲壓力,出現了較多社會不穩定因素。黨中央做出進一步調整和壓縮基本建設戰線的決定,國民經濟進入了重調整、緩改革的時期。當時有些經濟學家認為,調整壓縮基本建設首先就要壓縮銀行中短期貸款,銀行中短期貸款是“信用膨脹的表現,是拉長基建戰線的重要原因之一”。針對這種看法,楊培新撰寫了《關于中短期設備貸款的意見》,上報給黨中央和國務院。楊培新在上報政策建議中指出,發放十幾億中短期設備貸款的實踐證明,這種貸款用于國有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它投資數額小,土建工程不大,投產時間短,發揮作用快,能迅速增加短缺消費品供給平抑物價,有利于通過擴大生產增加就業機會,有利于促進結構調整消除農輕重產業失衡,消化因壓縮基建嚴重過剩的機電產品。中央領導采納了這個意見,在調整期間,不僅沒有停掉銀行中短期貸款,而且還明確指出,要進一步擴大這種貸款額度[2]。
控制通貨膨脹是進行價格改革的前提條件,在沒有消除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進行價格改革,就等于放手讓商品漲價并損害廣大民眾利益。20世紀80年代,曾有人認為,西方一些國家在輕度通貨膨脹的刺激下,可以取得社會經濟的一定發展的做法,“我們不妨也可以采用”。楊培新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當時我國并不存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過剩危機,恰恰相反,我們的貨幣購買力經常是大于商品供應,再加上基建戰線拉得過長,人民生活需要不斷提高,這在客觀上就已存在著自發性的通貨膨脹現象,如果從宏觀上不控制有可能轉化為爆炸性的通貨膨脹,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有些人曾主張價格改革一步到位,據說二戰后西德改革就曾推行了這樣的政策,結果帶來了高速增長的“艾哈德經濟奇跡”。但是,楊培新從長期從事銀行和通貨膨脹的研究出發,質疑這種美國推薦的所謂德國成功經驗,還親自到西德進行經濟考察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986年,楊培新特意訪問了德國賢人委員會主席斯奈德,他說戰后德國價格改革采取了慎重的步驟,影響面大的鋼、煤、電供不應求,價格沒有放開,依靠馬歇爾計劃提供的資金加速鋼、煤、電的生產,供求基本平衡后才放開價格。戰后住宅嚴重短缺,房租、房價都沒放開,二十多年后雖然放開了房租,房價仍有較多管制以遏制投機。[9]
1986年,有關經濟部門原本打算采納價格改革闖關的建議,放開某些重大短缺物資的價格“一步到位”,如鋼材價格準備每噸大幅度提高一倍多。楊培新考察德國回國后,及時向黨中央、國務院遞交了相反意見的調查報告,建議鋼材等重要物資調價緩行,因為基礎性大宗商品的影響面很廣泛,可能通過復雜的經濟連鎖反應引發普遍物價上漲。中央領導專門召集會議聽取匯報,說明這是1986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決定,定于次年的1月1日起實施,中央書記處已通過方案,只等政治局委員劃圈了。但是考慮楊培新提出的建議,決定暫不實施[8]。
20世紀80年代,如何評價中國這段改革歷程,雖然眾說紛紜,但是,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改革卻從反面印證了中國改革初期改革選擇的正確性。俄羅斯改革完整照搬了西方推薦的規范改革方案,“放開價格、管緊貨幣”在俄羅斯有了充分的實踐機會。俄羅斯前總理蓋達爾曾被稱為“市場經濟之父”,他只有書本知識而沒有實際經濟工作的經驗,西方有意選擇許多這樣的學者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培訓,然后當作市場經濟專家推薦給葉利欽政府并委以改革重任。蓋達爾受到西方貌似科學而實則過于簡單的市場供求和價格理論的誤導,采納了美國推薦的“放開價格讓市場發揮作用、管緊貨幣控制通貨膨脹”政策,結果發生惡性通貨膨脹。放開價格之后,市場表面上可以更加自由發揮調節經濟作用,實際上作為市場主體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均遭受沉重打擊,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導致市場規模大幅度縮減一半以上,這根本不是“短期陣痛”,而是持續十年之久的長期災難,直到普京執政并且拋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后才出現經濟復蘇。
美國推薦的“放開價格、管緊貨幣”政策,據說既能刺激生產又能遏制物價,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放開價格導致的物價狂漲,使企業供給和需求均遭受打擊。從供給方面來看,物價上漲使企業資金大大貶值,難以購買變得昂貴的原料和設備,“管緊貨幣”更令企業雪上加霜,無法獲得調整結構的設備貸款,甚至無法獲得維持生存的周轉資金;從需求方面來看,物價猛漲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將廣大居民數十年儲蓄一掃而光,社會需求萎縮導致市場陷入蕭條,企業難以維持生產更談不上擴大投資,原來短缺的彩電、冰箱等消費品,不僅沒有發展反而大幅度滑坡。俄羅斯民眾盼望“經濟奇跡”會降臨至俄羅斯,但他們望眼欲穿迎來的卻是高達2 000% 的惡性通貨膨脹,還有超過20世紀30年代西方大蕭條的嚴重衰退[9]。
參考文獻:
[1][加]那奧米·克萊恩.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2]楊培新.論我國銀行改革[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3]楊培新.中國經濟動向[M].桂林:耕耘出版社,1946.
[4]楊培新.我國貨幣政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7.
[5]楊培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新思路[M].上海:上海三聯書痁,1988.
[6]楊斌.探索解決當前就業矛盾的宏觀治理對策[J].中國工業經濟,1996(6).
[7]楊培新.論我國銀行改革[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8]李向陽.走進中國經濟學家[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99.
[9]楊斌.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