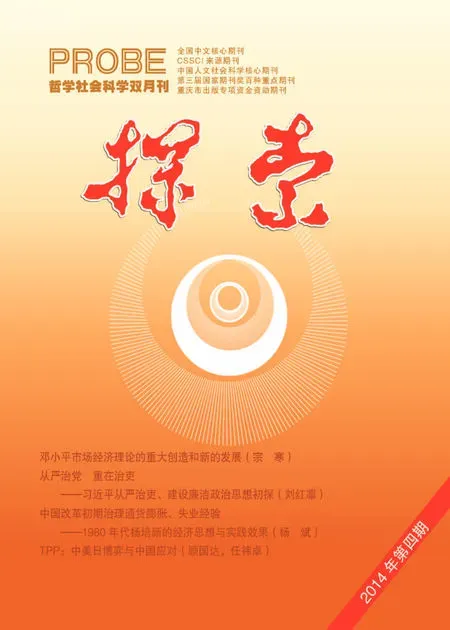存在論的斷裂與馬克思的重建
——馬克思人學存在論革命研究(下)
陳曙光
(武漢大學,湖北武漢 430072)
(接上篇①本文的上篇已在本刊2014年第2期刊發——編者。)費爾巴哈開辟了“回歸感性”的人學存在論道路,昭示了人學發展的未來方向,為西方人學存在論的現代轉向和革命變革拓展出嶄新的平臺,但費氏人本學絕不是這場革命的實現,更不是這場革命的完成。費爾巴哈未竟的事業,是由馬克思來完成的。
三、面向生活:馬克思人學存在論的現代轉向與革命變革
全面克服實體本體論人學所導致的對人的現實生命及其歷史發展的抽象化理解,找回被傳統人學所遺忘的人,尋求開辟一條通達現實的人和人的現實生活的存在論道路,為“無家可歸者安居”,這個任務最終落到了馬克思的肩上。馬克思全面超越了費爾巴哈的局限性,于“存在論”的根基處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重建了關注人的生存際遇的現代人學本體論路向,推動人學范式從實體論人學轉向了生成論人學。
(一)存在論承諾:馬克思人學不可或缺的意義維度
馬克思越出了西方傳統人學無法逾越的“存在論陷阱”,終結了實體本體論的強大傳統,但絕不意味著人學從此放棄了存在論的意義和承諾。從人學的發生邏輯、建構邏輯、演進邏輯來看,存在論承諾始終是馬克思人學不可或缺的意義維度。
其一,從人學發生邏輯來看,本體論追求有始無終
“本體論”的追求源自對人類自身生存本性的自覺表達和形上澄明,有起始無終期。人類思維與生俱來的超越本性、窮根究底的探索精神決定了任何拒斥形而上學(本體論)的企圖都將是徒勞的。康德曾感嘆:“曾經有一段時間,形而上學被稱為一切科學的女王,……現在,時代的流行口吻導致對它表現出一切輕視,這位老婦遭到驅趕和遺棄。”[1](3)不久前,哲學還是萬物之王,因為子嗣眾多而君臨天下,倍受追捧;而今卻被放逐荒野,孤苦零丁,一無所有。但是康德又認為,形而上學是人類理性的自然傾向,我們一定要為形而上學恢復昔日的榮光和地位,建立科學的形而上學已是迫不及待。人類對“精神家園”的追求并沒有隨著實體本體論傳統的終結而結束,人類對“自身完美”的期待,對意義世界的向往,對崇高理想的追尋,絲毫不亞于對物質世界的依賴。人類思維的超越本性決定了任何哲學家都無法走出“形而上學的困惑”——一方面,人們懷疑形而上學,要求終結形而上學;另一方面,人的生存本性決定了人又走不出形而上學。施太格繆勒因此說:“形而上學的欲望和懷疑的基本態度之間的對立,是今天人們精神生活中的一種巨大的分裂”[2](25)。
馬克思終結了傳統形而上學,但并未終結一切形而上學。馬克思完成了對傳統人學本體論的顛覆,但并未實現對整個人學本體論的徹底否定;或者說,馬克思終結的人學本體論只是一種特定的本體論形態,而不是終結了人學本體論的未來發展。“形而上學的終結”只是意味著一種特定的哲學思維方式和解釋原則的終結,而非形而上學本身的終結[3]。即使以往的形而上學之路誤入歧途,形而上學的問題卻依然是有意義的。我們不能以人學史上某種具體形態的“本體論”之誤而否定一切“本體論承諾”的意義。對于馬克思來說,他的使命不是放棄形而上學,而是通過開辟新的道路拯救形而上學。馬克思人學的存在論革命不是為了消滅人學的本體論維度,而是為了開辟本體論發展的嶄新道路。馬克思既是形而上學(本體論)決定性的“終結者”,又是其偉大的“復興者”和“拯救者”。
其二,從人學演進邏輯來看,拒斥本體論欲行未果
眾所周知,反形而上學思潮肇始于近代的經驗論者,他們不承認超驗世界具有實在性。培根認為,超驗的形而上學無助于認識真理,反而堵死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霍布斯則將哲學與科學混為一談,將哲學定義為“關于現象或明顯的結果的知識”。[4](65)康德反對“拒斥”形而上學的做法,他說:“人類精神一勞永逸地放棄形而上學研究,這是一種因噎廢食的辦法”[5](163)。
進入現代以來,實證主義舉起了拒斥形而上學的大旗,形而上學的遭遇愈加艱難。反形而上學一度成為某些時髦思潮標新立異的共識,甚而通過邏輯分析得出結論:形而上學的全部斷言陳述都是無意義的[6](13-14)。羅蒂明確提出,當代哲學的首要任務便是:“擯棄西方特有的那種將萬物萬事歸結為第一原理或在人類活動中尋求一種自然等級秩序的誘惑”[7](15)。以孔德為始祖的實證主義哲學把本體論問題看作既永遠無法得到解決又永遠無法加以證實的思辨哲學而逐出了自己的視野。實證主義這種斷然拒斥和根本否定本體論意義的做法是極端的,它割斷了自己與哲學歷史和哲學傳統的聯系,否定了自己的歷史基礎和理論前提,從而也必然阻礙自身的發展。
其實,形而上學作為對“存在”問題的一種“總的看法”[5](168),它的消亡與否,并不僅僅取決于哲學家們的親近或疏離。也許正是發現了孔德實證主義拒斥本體論、消解形而上學的片面性,對本體論的追求在邏輯實證主義者中又戲劇般地重新崛起,再次展示出本體論問題的永恒魅力。當代最有影響的邏輯實用主義者蒯因提出了自己的“本體論承諾”,蒯因認為,任何理論都存在“存在論的承諾”,“一個理論的存在論承諾問題,就是按照那個理論有何物存在的問題。”[8](204)蒯因把對本體論問題的回答重新看作進一步回答認識論問題的必要前提。他和斯特勞森一起,在分析哲學中“重新恢復作為存在論的形而上學的地位”[9](418)。蒯因在存在論方面所作出的原創性的貢獻無論是對于科學哲學的現代轉向還是對于本體論的當代復興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馬克思是最早發現傳統形而上學的癥結并對之進行批判的現代哲學家之一。正如海德格爾所說,馬克思完成了對形而上學——柏拉圖主義的顛倒,但馬克思并沒有終結哲學發展的一切可能性,相反,馬克思開辟了一條通往未來的哲學之路。在哲學史上,馬克思與孔德幾乎同時舉起了“拒斥形而上學”的旗幟,但是兩人在指向性上有著本質的不同,“孔德把‘拒斥形而上學’局限于經驗、知識以及‘可證實’的范圍內;馬克思提出的是另一條道路,即‘拒斥形而上學’之后,哲學應關注‘現存世界’、‘自己時代的世界’、‘人類世界’,‘把人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10](59)馬克思開辟的生活形而上學不是可有可無的,因為人之為人,總要確立生活的意義,開啟崇高的境界,表達精神的追求,這就賦予了馬克思人學本體論以合法性。“在日趨功利化的‘時尚’里,闡明‘形而上學’的意義,訴說哲學境界之必要,陳述哲學意義之真實,告誡人文精神之可貴,強調終極關懷之重要,提升人的哲學式的精神品位與道德素養”[11]。只有這樣,人才能夠有所追求,精神有所皈依,對未來有所憧憬。
其三,從人學建構邏輯來看,本體論維度欲罷不能
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形而上之學,本體論構成它的基礎和核心,任何真正的哲學是不可能把本體論問題擱置起來的。而人學作為對人的問題的一種哲學沉思,其理論形態注定是一種形而上之學,注定依賴于本體論的支撐。任何缺乏本體論根基的人學都是漂浮的、無根的。試想,馬克思如果不能科學回答“人之為人的存在論根據”這一根本性問題,又如何能夠回答清楚諸如“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和人的發展”等衍生問題?況且,馬克思人學的革命性變革“如果不觸及存在論,所解決的只能是枝節性問題,只有存在論的轉換,才能導致哲學的根本變革”[12]。
馬克思人學具有本體論的維度,但是馬克思究竟秉持什么樣的本體論立場,馬克思本人并沒有直接言說。馬克思只在他的早期著作(《博士論文》和《巴黎手稿》等)中有過“本體論”的提法,在成熟時期的著作中則不再使用這一概念。如果試圖在理論上概括馬克思的本體論,那么這將會使我們處于一種多少有點矛盾的境地。一方面,馬克思沒有直接概括自己的存在論主張,但另一方面,“任何一個馬克思著作的公正讀者都必然會覺察到,……,他的這些論述在最終的意義上都是直接關于存在論的論述,即它們都純粹是本體論的”[13](637)。接下來,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如何立足于當代,合理地闡釋馬克思人學的存在論立場;或者說,哪一種闡釋既契合當下的時代背景,同是又貼近馬克思的本來意義。
(二)感性生活本體論:人學存在論的斷裂與重建
馬克思人學革命是于存在論的根基處發動的。針對西方傳統人學熱衷于從超感性世界來尋找人之存在的本體論根據這一堅硬傳統,馬克思一反傳統人學的思維定勢,以“面向生活”的理論原則瓦解了“我思故我在”的強大傳統,開辟了與傳統人學完全異質的人學存在論道路。在馬克思看來,人生活其中的“感性世界”是唯一真實的意義世界,先于人或外在于人的“自在世界”是存在的,但與人分隔開來的“自在世界”,“只具有應被揚棄的外在性的意義”[14](178);而至于所謂的“超感性世界”或“本體世界”根本上就是思想虛構出來的假想世界,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抽象物。“世界不在‘我’之外,‘我’也不在世界之外”。人之為人的存在論根據不在超驗世界,而在經驗世界;不在人之外,而在人的感性生活之中。“人的感性生活”本身構成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存在論根據,我將其定義為“感性生活本體論”(Perceptual-Life Ontology)。
何謂“感性生活本體論”?是指“人的感性生活”是人之為人的最本原的基礎、最充足的根據、最后的原因,尊重人的生命價值也因此上升為最終的意義承諾。
“感性生活本體論”的確立,首先表征著馬克思與實體本體論原則的決裂,然而,這決不是宣布一個口號那樣的簡單,而是需要做出富有原則高度的理論界劃。馬克思在《提綱》和《形態》中對“感性生活”的本體論地位進行了深刻的(可能并非直接的)論述,對此,我最近發表在《哲學研究》的一篇文章對《提綱》第一條和《形態》中的一段話進行了比較深入細致的分析,在此不再贅述[15]。今天,我想繼續就《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另外幾段話所隱含的本體論意蘊做一補充論述。
第一段話:“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16](67)
在這一段話中,馬克思將“人與動物”的區別提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實體主義人學認為,人有意識、宗教、理性等,而動物沒有,這是實體本體論的基本看法。馬克思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也沒有停留于這一點。馬克思承認“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但如果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那馬克思不過是又一個黑格爾主義者而已了。馬克思超越黑格爾的地方在于,他發現“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了。“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獨特屬性,通過這些屬性,可以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但此時的人仍然是一種動物——長得人模人樣的特殊動物,而沒有成為“人本身”。而只有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人”才成其為人。在這里,“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相比較于意識、宗教、理性而言,具有始基性的地位,是人成其為人的最后的根據,即存在論根據。
第二段話:“這些個人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不在于他們有思想,而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16](67)
在這一段話中,馬克思將“思想意識”與“生產生活”的地位做了一個本體論的區分。馬克思指出,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不在于他們有思想,而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思想”與“生產”之間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究竟是什么,馬克思認為,不是實體本體論人學所謂的“思想觀念的活動”、“理性意識的活動”,或“宗教信仰的活動”,而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在這里,“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相比較于意識、宗教、理性而言,具有優先性的地位,是人成其為人的“第一位的原因”;而觀念的活動、意識的活動、宗教的活動等等不過是人的“第二個歷史活動”,是人成其為人的“第二位的原因”。可見,馬克思從根基處超越了西方傳統人學的知識論立場。
第三段話:“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6](78-79)
在這一段話中,馬克思將“生產”與“生活”的關系做了一個本體論的界定。首先,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不是“生產”,而是“生活”。也就是說,“生產”是手段,“生活”才是目的。“生活”具有更為根本性的地位。其次,結合第一段話“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這一論述來看,“生產”與“生活”具有同一性。“生產”的過程同時也即是“生活”的過程。再次,從馬克思的論述來看,“生活”概念其實可以包容“生產”的內涵,“生產”間接地來看就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因此,“感性生活本體論”是比“生產本體論”更能恰當地表達馬克思存在論立場的一種現代闡釋。
總之,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說,感性生活本體論的出場是一次偉大的革命性變革,是人學史上發生的一場“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它終結了實體本體論人學的強大傳統,瓦解了西方傳統人學的基本建制,摧毀了實體主義人學的堅硬內核,宣示了西方傳統人學的破產,標志著人學存在論傳統的徹底“斷裂”。
(三)人本價值的高度彰顯:感性生活本體論的價值論意蘊
存在論回答“是”的難題,價值論屬于“應該”的范疇。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在于:任何“是”的難題都指向“應該”,任何存在論都內蘊著價值論的意蘊,缺乏價值維度的存在論是無效的。存在論的失誤必然導致并最終體現為價值生活的偏離。回顧人類社會發展史,價值領域的迷誤一直伴隨著人類發展進化的歷史,然而,其原因歸根結底卻不在價值自身。存在論的失誤乃是價值生活迷失的罪魁禍首。因此,意欲解決精神迷失和價值錯位的問題,出路還在于跳出價值論的窠臼,回歸存在論的領地來解決價值生活的難題。
馬克思開辟的存在論境界說明,“人是什么”的問題固然重要,“如何對待人”的問題更為重要。感性生活本體論直接地是解決了“人是什么”的存在論難題,深層地是彰顯了“如何對待人”的價值論意蘊。馬克思對“人是什么”這一存在論難題的回答是:感性生活創造人,人的感性活動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礎;因而對“如何對待人”這一價值論問題的回答理所當然就是:“以人為本。”
馬克思開辟的存在論境界說明,“人的社會”并不是人之外的“實體”的杰作,不能把人類歷史看作是“神律”或“他律”的進程,并不存在超驗的“實體”來擬定歷史進程這一事實。人類歷史就是人自己的作品,是人的感性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展開,是人的意義的生成過程和價值的實現過程。
馬克思開辟的存在論境界說明,“社會的人”并不是“上帝”的作品,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的存在論根據就在于“感性生活”本身,不能再從人的存在之外尋找人之為人的根據,人正是在感性生活中生成為現實的人并向著理想的人邁進,也是在感性生活中確立和實現人自身的價值。
馬克思開辟的存在論境界說明,“人類解放”絕不是訴諸理性邏輯的自我完善,或者訴諸個體的精神啟蒙,或者依靠倫理意義上的個體性世俗化拯救,或者訴諸萬能上帝的救贖,或者訴諸杰出個人的良心發現和偉大行動,而必須通過人的感性活動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乃至整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必須通過人的感性活動,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上力求“改造世界”,在“政治解放”的基礎上追求“人類解放”,在“反思現實”的基礎上力求“超越現實”,才能最終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
馬克思開辟的存在論境界說明,“人的存在”根本不需要人之外的實體來確證,“人的偉大”根本不需要人之外的實體來擔保,“人的意義”根本不需要人之外的實體來賦予,人的偉大與崇高只能歸功于人自身,這就直截了當地說明人的世界應該“以人為本”,而且只能“以人為本”。
馬克思開辟的存在論境界說明,“以人為本”是歷史發展的最終邏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進步,人類終將走向“自由個性”,到那時,踐行“以人為本”就不再是一種奴人之術,一種權宜之計,而是不可僭越的“天命”,是不可踐踏的法則。
馬克思開辟的存在論境界說明,“民生幸福”是當代中國的首要價值,社會生活理應“以民生幸福為價值旨歸”[17],而不是以人之外的物為本,不是以人之上的神為本,也不是以任何別的先驗實體為本,所謂“神本”、“君本”、“官本”、“物本”、“資本”等都不過是一種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表現!
四、“感性生活本體論”在何種意義上超越了“實踐本體論”?
究竟如何概括馬克思人學的存在論立場,學術界眾說紛紜。在這里,我又提出了“感性生活本體論”的概念,有人就會疑惑:這是不是又一個“文字游戲”?為什么要在“實踐本體論”之外又出一個“感性生活本體論”的概念?“感性生活本體論”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突破了實踐本體論的傳統價值?這是本文必須面對的問題。
其一,相對于“實踐”實體化的解釋傾向而言,“感性生活本體論”可以擺脫實體主義的解釋框架。現在,學術界有很多人提出“實踐本體論”。但是,它雖然使“實踐”上升為本體,卻并未真正把握馬克思實踐觀的實質,原因在于實踐本體論不同程度地將“實踐”絕對化了,“實踐”成為了又一種“實體”。也就是說,“實踐絕對化”的解釋傾向尚未跳出實體本體論人學的形而上學窠臼,只不過是把原來的“精神”實體替換為“實踐”[18],把原來的“實體絕對化”替換為“實踐絕對化”。“實踐”似乎擁有無條件的合法權,或者擁有自我闡釋其合法性的“理論力量”。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實踐規定一切,什么規定實踐”[19]。“實踐”仿佛又淪為了一個無所不包、沒有條件限制的“全能”概念,人類走出了“上帝萬能”、“理性萬能”,卻又墮入了“實踐萬能”的深淵。對實踐不作任何價值判斷的絕對化傾向是當今世界飽嘗人類自身實踐之害的重要原因。而“感性生活”則不是一個實體性概念,而是一個生成性概念,這樣可以避免重蹈“實體本體論”的覆轍。
其二,相對于“實踐”經驗化的解釋傾向而言,“感性生活本體論”可以擺脫經驗主義的解釋框架。當前對馬克思實踐概念的闡發存在著兩種經驗常識性的理解框架:一是對實踐觀點的庸俗化理解。或者把“實踐”理解為單純的物質功利性活動,或者理解為工具性、策略性活動,完全忽略了實踐觀點與人的現實生命之間深層的意義關聯。二是對實踐觀點的技術化理解。把“實踐”視為價值無涉的中立性概念,對實踐活動的非理性的、反主體性的、反人類性的層面缺乏識別,造成了對實踐的無批判盲從,這就恰恰抹殺了實踐概念最重要的理論意義[20]。在這些解釋框架中,實踐概念與人的現實生命之間的內在關聯卻被遺忘了,實踐概念在理解人的現實生命及其歷史發展方面所獨具的思想內涵和理論意義被遮蔽了,一句話,實踐概念的精髓和靈魂失落了。“感性生活本體論”正是在此背景下并適應這一要求應運而生的。“感性生活”已完全不是價值無涉的中立性概念,而是包容了深刻的價值論意蘊,體現了實踐與人的現實生命之間的深層意義關聯。
其三,相對于“實踐”單一化的解釋傾向而言,“感性生活本體論”可以開辟更為豐滿的視界。在傳統的解釋框架中,“實踐”主要就是指“物質生產活動”,“物質生產”構成了“實踐”的硬核。其實,將“實踐”等同于“物質生產”的單一化傾向并沒有合法性的支撐。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生產活動”是人的感性生活本身,但不是感性生活的全部。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類所關注的“感性生活”的領域是不同的。馬克思為什么那么關注“物質生產”呢?原因很簡單,馬克思不能離開他所生活的時代來進行任何理論上的言說。馬克思生活在工業社會的初期,為溫飽而掙扎還是人們的主要目標,生存和衣食住行還是人們關切的主要問題,車間和廠房還是人們生活的主要場所,休閑和娛樂還是一種奢望的時候,“實踐”自然就主要是指“物質生產”,而休閑生活、娛樂生活、消費生活則被置于次要的甚至是被遮蔽的地位。而到了毛澤東那個時代就不同了,盡管生存和衣食住行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但更根本的問題——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擺在了突出的位置。在這種條件下,毛澤東把實踐界定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領域就不失為一種洞見,這三個方面依然是人的感性生活本身,只是毛澤東關注的角度與馬克思有了不同,“階級斗爭”已經上升到了首要的地位。今天已經進入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時代,革命與階級斗爭已經或正在淡化,物質匱乏問題、基本生存問題已經解決或不難解決,在人們面前展開的是一個遠比“物質生產”更廣闊的領域,消費社會、休閑社會、虛擬社會的快速成長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能再僅僅從“物質生產”領域來理解人的“感性生活”,而應該去發掘“感性生活”更為豐富的內涵,比如消費生活、休閑生活、娛樂生活、精神文化生活、虛擬生活等。顯然,“感性生活本體論”在現今具有更為鮮明的時代價值。
其四,相對于“實踐”被束于認識論領域的解釋傾向而言,“感性生活”優先開啟的是存在論的境界。受蘇聯模式教科書和近代西方認識論哲學的影響,有學者把“實踐”囿于認識論的解釋框架之內,把“實踐”理解為一個單純的認識論概念,而忽視了其首先是一個本體論的概念;只看到了實踐的認識論維度,而忽視了其首要的維度應該是本體論的維度;只承認實踐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而忽視了其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實踐的地位僅僅體現為對于認識的基礎地位,實踐的功能僅僅表現為聯結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的中介,實踐的作用僅僅在于提供認識的感性材料來源,充當認識的真理性標準。其實,只要我們忠于馬克思的著作,不難發現,我們從馬克思哲學中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一種認識或思維方法,而是關照現實變革現實的實踐態度以及追求自由解放的超越維度。正是基于此,“感性生活”概念躍出了認識論的邊界,優先開啟的是存在論的境界。“感性生活”的性質是屬于前邏輯的、前概念的、前反思的,是現實的人的生活本身,是物質世界和觀念世界最具本源性的基礎。
其五,相對于“實踐”被囿于宏大領域而言,“感性生活本體論”優先觀照的是日常生活領域。過去,人們談論“實踐”往往局限于生產發展、技術革新、制度變革、政治革命等宏大的非日常生活領域,似乎關涉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休閑、娛樂、消費等)和微觀領域(家庭、生活圈、虛擬空間等)根本就不配“實踐”這一偉大的概念。其實,這不僅是對馬克思實踐觀點的誤解,也恰恰把人的生活世界給劈成兩半了。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范式的轉換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傳統的哲學范式只關注宏大領域,采取的是宏大敘事的話語方式,忽視日常生活和微觀領域,因而弱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現實、干預現實、塑造現實的能力。究其原因,不在于我們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精神,而在于我們對“實踐”概念的誤讀。其實,非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自由切換才構成人們的全部生活、全部實踐。在和平年代,在和諧社會中,人們最切近、最緊要的“實踐”正是存在于微觀領域,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現在,人們越來越看重感性的幸福,生活的“感性”化正成為時代發展的趨勢,“幸福指數”、“幸福中國”、“快樂工作”、“快樂生活”等等這些極富時代感的新名詞、新概念日益普及就是最好的證明。鑒于此,我們不能僅僅囿于宏大領域上來理解“實踐”,關注人的生存際遇、建構詩意的感性生活,應當進入到我們對“實踐”概念的理解和重構之中。此外,“感性生活”概念的確立有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從宏大敘事轉向微觀敘事,有助于提升馬克思主義哲學參與現實的理性塑造的功能,有助于扭轉馬克思主義哲學“貧困”和“失語”的境況。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感性生活本體論”概念是對“實踐本體論”概念的一種糾偏和超越。當然,強調微觀領域的感性生活并不意味著拒斥或忽視宏大領域的實踐活動,兩者都屬于人們的感性生活,統一于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之中。
參考文獻:
[1][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德]施太格繆勒.當代哲學主流(上卷)[M].王炳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3]賀來.論馬克思哲學與形而上學的深層關系[J],哲學研究.2009(10).
[4]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16-18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65.
[5][德]康德.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M],龐景仁譯,商務印書館,1978:163.
[6]洪謙,主編.邏輯經驗主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13-14.
[7][美]理查德·羅蒂.哲學和自然之鏡[M].黃宗英,譯.上海:三聯書店,1987:15.
[8]See W.O.Quine.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M].New York,1979:204.
[9][美]M.K.穆尼茨.當代分析哲學[M].吳牟人,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10]肖前等主編.實踐唯物主義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11]陸杰榮,張偉.哲學境界:詮釋馬克思哲學的一個新視角[J].教學與研究,2008,(11).
[12]楊魁森.深化生活世界理論研究[J].長白學刊,2007,(1).
[13][匈]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M].白錫堃,張西平,李秋零,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陳曙光.小同大異:馬克思人學與費爾巴哈人學的存在論分野[J].社會科學輯刊,2014,(2).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夏建國等.唯物史觀價值旨歸的時代意蘊——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民生幸福[J].湖湘論壇,2013,(3).
[18]孫正聿.怎樣理解馬克思的哲學革命[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3).
[19]徐長福.世紀之交若干哲學問題的邏輯清理[J].天津社會科學,1999,(1).
[20]賀來.實踐與人的現實生命——對“生存論本體論”的一點辯護[J].學術研究,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