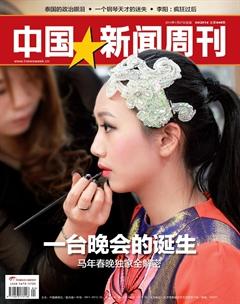治理大城市病宜用市場手段
易鵬
北京兩會上,控制人口規模的信息很多,各界也很關注。應該說,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其承載力的極限點,一個國家人口過于集中在少部分區域,也不利于可持續和均衡發展,對于北京進行人口規模控制有一定必要性。但這種人口規模控制需對癥下藥,遵循市場規律,采用疏而不是堵的方式來控制人口。
2000年到2010年北京每年的常住人口增長超過80萬,2012到2013年也超過50萬。2012年,北京人口已經達到2069萬,遠超之前確定的2020年人口規模2000萬的目標。北京人口聚焦的根本原因,是北京擁有比全國任何城市都好的公共服務能力、產業聚焦能力、低投入高收益的機會能力。對于老百姓而言,選擇在哪個城市生活、工作,最樸素的原因就是看病、教育、工作這三方面。在這三方面,北京在全國城市中處于領先的地位,于是出現這種人口快速進入的局面,就很正常了。
北京能夠在這些方面遙遙領先,是來源于行政級別、政府主導的城市發展模式。這點從北京和上海的發展對比就很清楚,上海按照道理應該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其發展條件和區位也遠好過北京,建國時上海市500多萬人,而北京只有100多萬。到現在北京和上海的人口相差不大,都在2000萬以上,表明北京聚集人口的速度遠超上海。同時,北京擁有的教育、醫療等各種公共服務的水平,現在也超過了上海。
上海對比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對比北京更加不需多言。北京既是直轄市更是首都,于是在行政級別和政府主導資源分配的情況下,在財力、能源、水資源、人才、資金更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特權,最終導致了北京的各種能力明顯超出其他城市。即使北京人口在快速增長,政府還通過對地鐵、公交、供熱等公共服務業補貼、通過行政配置資源,建設南水北調等各種工程來提高北京的水與能源供應能力的方式,抑制成本上漲,而不能將價格作為調節資源分配的工具,最終傳導出錯誤的信號,導致了北京人口聚焦加速、大城市病加劇。
要想破除北京的大城市病,控制住北京的人口規模的增長,必須要回歸到最根本的地方來對癥下藥,也就是必須要深刻認識到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的將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要深刻領會到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基本原則。以市場作為主導力量,市場自然會找到城市人口配置的均衡點;隨著一個城市的人口的增長,各種成本也會上升,自然也引導人口向別的城市去聚焦。
如果繼續采用政府主導的通過拉高進入北京門檻的方式來控制人口,而不是采用市場主導來疏解北京各種資源的方式來控制人口,最終會走入一條老路。畢竟,人往高處走的愿望誰都不能夠阻攔,為此必須要將北京從高處放到平地上來,或者在全國培育更多的高處,將北京和其他的城市之間的差距縮小,才能夠讓人口均衡分布。
為此,應該通過市場方式,將北京過于集中的資源疏散到全國各地,將北京的全方位的功能分解到全國各地。遠之,將北京的功能和資源疏散到包括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等城市群中去;中之,通過京津冀一體化,將北京的資源和功能疏散到京津冀城市群區域中,尤其是環首都的河北地區;近之,將北京四環以內的資源疏散到四環以外,通過混合社區的建設,降低人口流動頻率,減少大城市病。一旦這種市場主導的格局形成,可能會在全國出現更多接近于北京綜合實力的城市,那么分流北京人口的目的自然就水到渠成。
為此,需要通過市場的方式,通過市場購買增加北京的人口承載力,這種購買主要面向石油、天然氣、水等資源,因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大都市都是通過市場的方式來配置這些資源,而非自身就能夠生產這些資源。通過市場競爭,提高規劃、管理、運行、品牌等在內的城市的綜合解決方案的水平,從而通過軟實力的提升提高北京的人口承載力;對比國際大都市,北京市的人口承載力還有空間:大東京3400萬人,城市運行得有條不紊;香港才1000多平方公里,承載了700多萬人,城市壓根不擁堵。1.68萬平方公里的北京,承載了2069萬人就這樣苦不堪言,與其說是逼及承載力上限,還不如說是反映了城市管理運行等軟能力的低下。
畢竟人往高處走是鐵律,之前北京也采取了嚴厲的控制人口的措施,但沒有控制住就是明證。想要控制住北京的人口,必須遵循以市場為主導的方式。不從治本上解決北京人口規模問題,而是靠行政力量來控制人口,不會有太理想的效果。以市場主導,以疏代堵方為治本之策。
(作者系盤古智庫城鎮化首席研究員,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