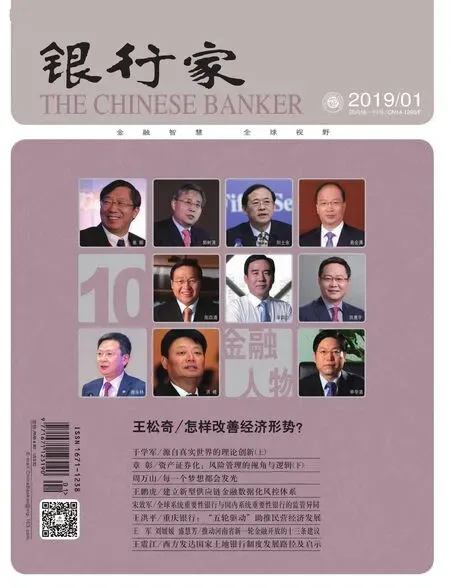抵債資產處置招投標合同糾紛及其啟示
劉楠
基本案情
上訴人A銀行順達分行因與被上訴人鄧某、劉某招投標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一審法院民事判決,向二審提起上訴。
原審查明,2010年2月2日,A銀行順達分行在公告中稱:我單位擬處置以法院裁定收取的位于順達市勝利西路路南的房產一處,共計兩層,面積約800平方米。該房產無產權登記手續和報建審批手續,占用的土地為劃撥地。后鄧某、劉某與張某合伙,以張某的名義報名,參與A銀行順達分行的資產處置,并于2010年4月9日向A銀行順達分行交納了18萬元投標保證金。參與者均與A銀行順達分行簽訂了《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承諾與聲明》及《參加談判確認書》。《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內容顯示,談判背景:由于該資產土地使用性質為劃撥地,不具備處置條件,需完善土地手續,變更土地使用性質。
為盡快落實項目處置條件,A銀行擬選取合作人,代理A銀行完善相關手續,使資產達到處置條件。資產達到處置條件后,A銀行將按競爭性談判價格以協議方式將資產處置給合作人。談判內容:意向合作人已對該項目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和實地勘查,對該項目情況完全了解。合作意向人通過競爭性談判成為擬合作人后,自愿交納履約保證金18萬元,如出現以下事項,擬合作人自愿將履約保證金18萬元作為賠償支付給A銀行:(1)在A銀行上級行批復前退出的;(2)在上級行批準后退出或未在約定期限內完成土地性質變更手續的。同時,若因以上兩項事項給A銀行帶來損失、保證金不足以彌補的,擬合作人將另行賠償,A銀行有權另行選擇其他合作人繼續辦理。談判內容:標的物達到處置條件后,A銀行將協議處置給合作人,對處置價格進行競爭性談判,此價格為提出土地性質變更、房產登記過戶、土地過戶等事宜所有稅費支出后的A銀行凈受益價格。合作人的確定:競爭性談判中報價最高者,A銀行將其作為擬合作人,報上級行審批。如上級行同意該方案,則擬合作人在遞交書面申請后正式成為合作人;如上級行不予批準,則本次談判結果以及上述各條款自動失效,A銀行在上級行駁回方案后三日內退還履約保證金。
2010年4月14日,A銀行順達分行集中采購辦公室出具競爭性談判結果通知書,內容顯示:集中采購辦公室會同公司事業部、辦公室、風險部和監察部于4月13日完成了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合作意向人事宜競爭性談判采購程序。根據競爭性談判結果,報價最高者為張某,報價為242萬元。幾日后A銀行順達分行以本次資產處置上級行未同意為由口頭通知張某談判結果作廢,并退還張某繳納的18萬元投標保證金。
一審法院裁決銀行敗訴,原告鄧某、劉某與被告A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順達分行簽訂的《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有效;被告A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順達分行依法將原告鄧某、劉某確認為處置房產的合作人。二審法院裁決,一是維持一審判決書第一項的內容,即原告鄧某、劉某與被告A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順達分行簽訂的《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有效;二是變更一審法院判決書第二項的內容為:被告A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順達分行依法將原告鄧某、劉某確認為處置房產的擬合作人。
爭議的焦點問題
原告當事人的主體資格問題
銀行認為,一審原告鄧某、劉某不具備主體資格。銀行一方在原審中則堅持認為鄧某、劉某不具備主體資格,二審中仍然堅持主張鄧某、劉某對A銀行順達分行無訴訟權利。A銀行順達分行在處置資產過程中有與張某簽約過一些必要文書,該文書不顯示有本案鄧某、劉某的意思表示。說明張某與鄧某、劉某非合伙關系,鄧某、劉某對A銀行順達分行無訴訟權利。
原告認為,其有相應訴訟權利。公民之間自愿合伙從事民事法律行為,本案不屬必要共同訴訟,張某退伙不影響其他合伙人在本案中相關權利。
原審認為,鄧某、劉某與張某出具的協議書能夠證明三人系合伙關系,合伙人可以推舉負責人,負責人的經營活動由全體合伙人承擔民事責任,鄧某、劉某對合伙人張某的經營活動自愿承擔義務、享有權利,在張某退出合伙時,約定了由鄧某、劉某全權履行相關義務和行使相關權利,鄧某、劉某向A銀行順達分行主張權利并承擔相關義務并無不當,故A銀行順達分行的該辯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二審法院認為,張某依照A銀行順達分行的條件,參與競爭性談判,與A銀行順達分行簽訂了《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等文書。根據《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第四條合作人的確定約定內容,競爭性談判中報價最高者,A銀行將其作為擬合作人,報上級行審批。張某為當場報價最高者,A銀行順達分行應依約將其作為擬合作人。關于鄧某、劉某對A銀行順達分行有無訴訟權利的問題。因鄧某、劉某在原審中提交的與張某出具的協議書證明三人系合伙關系,張某退出合伙時,約定了由鄧某、劉某全權履行相關義務和行使相關權利,鄧某、劉某向A銀行順達分行主張權利并承擔相關義務并無不當。故A銀行順達分行的該項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競爭性談判合同的成立條件
競爭性談判合同是附條件生效合同,是否未經批準不成立。銀行抗辯稱,競爭性談判合同是附條件生效合同,因上級行未批準,該合同不具備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銀行在二審中認為,張某和A銀行順達分行簽署的文書已表明合作是附條件的,只有在條件成立時,處置拍賣才能產生法律效力。而2010年4月13日的拍賣因不符合所約定的條件,A銀行順達分行及時反饋給張某并按約定退回了張某繳納的保證金。在A銀行順達分行進行第二次、第三次處置拍賣時,張某或其公司參加,因競買未成功,退回了相應的保證金。由此說明2010年4月13日第一次處置拍賣無效符合法律規定,也符合雙方的約定,張某是認可并接受的。
原告抗辯,從A銀行順達分行于2010年2月2日在報紙刊登招標公告,到同年4月13日雙方簽訂的《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充分說明A銀行順達分行發出的是明確訂立買賣合同要約,鄧某、劉某的合伙人張某以最高報價242萬元中標,根據《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第四條合作人的確定約定,依約鄧某、劉某成為A銀行順達分行處置資產的合作人,該談判現場說明對A銀行順達分行具有法律約束力。根據《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約定,其性質為附條件履行合同,并非A銀行順達分行所稱的附條件成就合同。另外,A銀行順達分行退回交納的保證金是該行的單方行為,其不能證明附條件履行合同成立,更不能免除A銀行順達分行繼續履行合同義務。另鄧某、劉某及張某從沒有參加A銀行順達分行所稱的第二次、第三次處置拍賣,張某受其他法人單位指派,參加第二次、第三次拍賣是公司職務行為,其行為不影響鄧某、劉某主張的任何權利,也不能當然推定張某個人或鄧某、劉某認可或接受第一次拍賣無效。endprint
原審認為,鄧某、劉某依照A銀行順達分行的條件,參與競爭性談判,并與A銀行順達分行簽訂了《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等文書,《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約定了雙方享有的權利及應當遵循的義務,具有了協議的性質,該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背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為有效協議。鄧某、劉某系競爭性談判中報價最高者,A銀行順達分行應當依據該協議將鄧某、劉某確定為擬合作人。A銀行順達分行口頭向鄧某、劉某答復稱上級行未同意,依據不足。
二審法院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它分別分析了鄧某、劉某的兩個訴訟請求:一是請求確認雙方房產擬合作競爭性談判協議有效,二是將鄧某、劉某確認為A銀行順達分行處置房產的合作人。對第一個訴訟請求中雙方簽訂的《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雙方均無異議。對第二個訴訟請求中鄧某、劉某要求的確認為合作人的問題,經查,雙方簽訂的《A銀行順達分行抵債資產項目確定擬合作人競爭性談判現場說明》第四條中明確約定,競爭性談判中報價最高者,A銀行將其作為擬合作人,報上級行審批。本案中,張某作為擬合作人后,A銀行順達分行依約應繼續進行的程序為:報上級行進行審批,其上級行同意,張某在遞交書面申請后正式成為合作人。原審認定A銀行順達分行將鄧某、劉某確認為處置房產的合作人不當,應予糾正為擬合作人。至于擬合作人確定后,A銀行順達分行是否依約定履行了上報審批義務,A銀行順達分行與鄧某、劉某雙方仍存在較大爭議,應由雙方另行處理,不屬本案審理范圍。對于A銀行順達分行主張的本次交易標的已依法處置完畢的問題,因本案中鄧某、劉某的訴訟請求為確認其合作人的身份,故A銀行順達分行該主張與本案無關。
幾點啟示
從本案審理過程來看,銀行對抵債資產的招投標處理的管理應注意以下事項:
對于欠缺法定手續的抵債資產的處置應在有關公告中明晰銀行和參與合作單位的權利義務。尤其是銀行內部在抵債資產處置管理上有著嚴格的授權審批機制,因此銀行內有關協議文本和相關文書應該清晰地表明有關當事人在各個環節中為何角色,有何權利義務。本案中銀行的對方當事人應為“擬合作人”而不是“合作人”,這對于本案的訴訟有著極為重要意義。
在招投標的內部管理上,應嚴格防范操作風險,防止基層行未經上級行授權而擅自完成抵債資產的處置。銀行基層機構越權處置抵債資產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這一方面源于抵債資產處置的內部管理失控,另一方面也源于基層機構有尋租的利益沖動。銀行內部必須加強抵債資產的授權控制,并應強化越權或者濫用權利的問責機制。從本案銀行內部招投標操作管理來看,基層行在履行相關審批手續方面可能存在某些不足,或者上級行在審批有關申報上未能及時明確地回復,以致本案所涉及的抵債資產發生此次訴訟,并可能由此給銀行帶來一定經濟損失。
銀行應積極抗辯和維護自身權益。本案中,原告已經獲得一審法院的支持,而銀行積極維護其合法權益,積極抗辯并獲得法院的支持。雖然二審法院并沒有完全糾正一審法院判決的內容,但是確立了原告僅為“擬合作人”的資格,這很大程度上為銀行維護其權益留下了空間。尤其是銀行已經將本案爭議涉及的抵債資產已經按照正常程序完成處置,如果不改變一審法院確立的合作人身份,則勢必導致銀行承擔很大的賠償責任,相反如果基于“擬合作人”,則在擬合作人確定后,A銀行順達分行是否依約定履行了上報審批義務,即使銀行有過錯,其法律責任也小于確定為“合作人”的情形。
(作者單位:北京銀行法律合規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