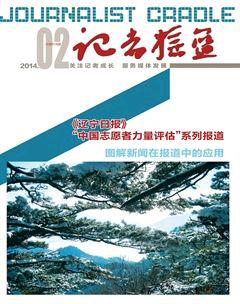網絡傳播中的“沉默螺旋”現象
李函擎
“沉默螺旋”的概念最早由德國傳播學者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提出。諾依曼以人類具有被孤立的恐懼為基礎,指出輿論對個人所具有的社會控制作用。“沉默螺旋”意味著人們一直在觀察他們周圍的世界,當人們表達自己觀點時,如果獲得更多支持,變得有說服力,他們就會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再那么小心翼翼。而當他們發現自己的觀點被眾人所丟棄,他們就會保持沉默。這樣一來,一方意見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
然而當網絡逐漸走入人們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成為人們交流和溝通的主體,很多人認為網絡的特性足以打破“沉默螺旋”賴以生存的基礎,因為持反對意見的受眾不需要再害怕被孤立,可以隨意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沉默螺旋”模式在網絡中逐漸消解。
筆者認為,如果從狹隘意義上去理解諾依曼的“沉默螺旋”理論,它產生的最根本依據確實是壓力。而網絡傳播因為具有開放性、虛擬性和匿名性等特點,導致個人對網絡傳播中的“意見環境”的感知及其帶來的壓力相比于現實中的人際傳播、群體傳播中帶來的壓力自然會小一些。但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當“沉默螺旋”現象放到特定的網絡中去研究時,是不是所有的沉默現象都是來自壓力?有沒有不是由于壓力而產生的沉默?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要判斷沉默的是一種態度還是一種判斷?是由于態度上的不一致我們選擇沉默,還是由于判斷上的不自信導致我們沉默。
態度上的沉默即傳統意義上所說的由于壓力導致“沉默螺旋”現象的產生。但在網絡交流中,與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所傳遞信息的權威性相比,我們經常會質疑自己判斷所依據的事實究竟是否真實存在。我們可以反對傳統媒體所發表的觀點,但我們無法質疑它們報道的事實。而由于網絡中充斥大量的虛假信息,需要我們在網絡交流中不斷地思考,判斷再判斷,隨著跟帖數量的增多,事實呈現出與我們原有認知不同的面貌,結果導致我們不是由于壓力沉默,而是我們的判斷逐漸站在了少數人的隊伍中,或者當我們發現多數人的判斷更符合事實,于是放棄了原來的判斷,加入到多數人的陣營,使得多數人的意見更加強大,從而讓真相浮出水面。因此,即使在網絡傳播中我們對意見環境所感知的壓力減小,但由于調整判斷所產生新的“沉默螺旋”現象依然在繼續。
除此之外,“沉默螺旋”現象在網絡傳播中還有另一種可能,即沉默的是表達還是沉默的是意見。在網絡傳播中,我們正常表達的意見經常會被網絡水軍的聲音所湮沒,網絡水軍就好比現實生活中的托兒,大多是花錢雇來發表聲音的,他們未必了解事情的始末但還是在網絡中大量發表一種聲音,表現為對某一事件的積極響應或嚴厲打擊。他們所發表的言論雖然不產生真正有意義的實質性意見,但發出聲音的強大,也形成了一定的輿論影響力。這樣頻繁發帖只有聲勢卻不產生意見量,和數量上占少數卻生產強勢意見量的雙方,形成了新的螺旋博弈。
通過上面的分析,在網絡傳播中,我們不排除沉默螺旋產生的心理機制仍然存在,“沉默螺旋”現象并沒有也不會消失。網絡傳播中不存在所謂的“反沉默螺旋”現象,但會出現雙螺旋的博弈,這就涉及到“沉默螺旋”表現形式的復雜性問題。當我們從多個角度重新理解網絡傳播中的“沉默螺旋”現象時,可以發現這種“沉默螺旋”是在不斷調整變化的,有壓力的調整,有判斷的調整,有評價的調整,還有意見聲音和零值聲音之間關系的調整。它有時表現為單一型存在模式,有時又表現為復合型的存在模式。如果我們這樣來理解網絡傳播中的“沉默螺旋”現象,而不是僅僅從傳統理論上去理解,我們便打破了固有思維的局限性,網絡傳播中這種擴大化的“沉默螺旋”模式便顯而易見了。同時,“沉默螺旋”機制并不是孤立在網絡中存在的,它與我們現實中的輿論機制發生著復雜的互動。在我國現有體制下,往往會出現社會表層心理和深層心理脫節的現象,這一現象已經在網絡上有所體現,比如流言的泛濫與不同價值觀的傳播。在這種現實的集權體制與網絡空間中的相對自由體制下,沉默螺旋如何在兩個場域中發生作用,也是需要我們思考的新命題。當一個全新的媒介走入我們生活時,我們必須對原有的命題有一個全新的思考和認識過程,才能全面客觀地去判斷這一媒介將對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全新變化。
(作者單位:遼寧廣播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