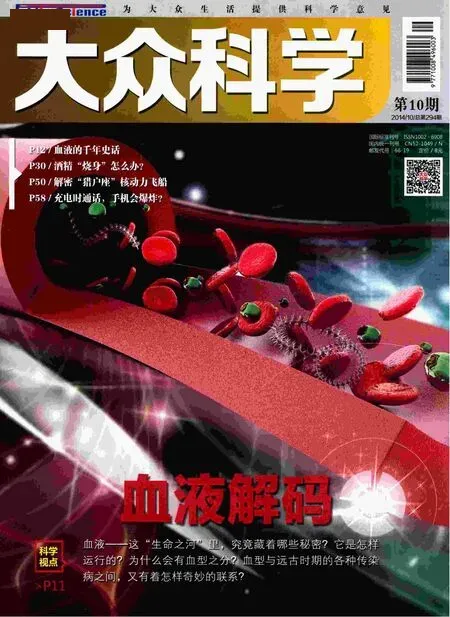血液的千年史話
文- 余 風(fēng)
輸血是近代醫(yī)學(xué)中堪與抗生素媲美的偉大成就。回顧醫(yī)學(xué)史,從放血治療到輸血的嘗試,從輸動(dòng)物血到按成分輸血,人類對血液的認(rèn)識(shí),經(jīng)歷了數(shù)千年的艱難探索
希臘神話中,醫(y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從他的姑姑智慧女神雅典娜那里得到一種威力巨大的藥:蛇發(fā)女妖美杜莎的血。據(jù)說,美杜莎身體右側(cè)血管里的血,有讓人死而復(fù)活的神奇功效;而她身體左側(cè)血管里的血?jiǎng)t是致命毒藥,能讓人瞬間斃命。
神話中的這一描述,似乎暗合了現(xiàn)代人對血液的認(rèn)識(shí)——血液既能傳播埃博拉、艾滋病等疾病,帶來死亡的陰影;但與此同時(shí),通過輸血又能挽救無數(shù)生命。
血液,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生命之河”,它沿著人體內(nèi)總長約96540公里(相當(dāng)于赤道周長的2.4倍)的動(dòng)脈、靜脈和毛細(xì)血管靜靜流淌并潤澤著我們的全身。一般來說,一個(gè)健康成年人體內(nèi)的血液約占其體重的7%~8%,如果人體失去超過血液總量15%的血液,脈搏會(huì)加速跳動(dòng),會(huì)出現(xiàn)暈眩、發(fā)冷癥狀;失血量達(dá)到40%時(shí),血液流回心房將受影響,會(huì)出現(xiàn)心動(dòng)過速癥狀;失血50%時(shí),將危及生命。

醫(y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雕像

阿茲特克的祭司用活人的心臟供奉太陽神。

創(chuàng)作于中世紀(jì)的一幅描述放血療法的繪畫。

美國首任總統(tǒng)華盛頓正是死于放血療法。
血液的原始崇拜
遠(yuǎn)古時(shí)期,人類的祖先以狩獵為生。當(dāng)他們發(fā)現(xiàn)人和動(dòng)物失血后,生命也隨之逐漸虛弱乃至衰竭,便萌發(fā)出對血液的原始崇拜——在他們看來,血液象征著生命和力量。
當(dāng)時(shí),人們常以血液祭祀神靈。比如,古代中美洲的阿茲特克人認(rèn)為,眾神獻(xiàn)出了自己的肢體和鮮血來讓太陽升起,因此只有獻(xiàn)祭才能讓神祗們繼續(xù)維持天地間的正常秩序。因此,供奉太陽神的祭司會(huì)用黑曜石制成的鋒利匕首,從第10根肋骨下的心臟方向插入并剖開犧牲者的胸膛,將還在跳動(dòng)的心臟掏出,高舉過頭頂獻(xiàn)給崇高的太陽神。
公元100年的南美秘魯莫切繪畫中,記錄了莫切人是怎樣用敵方的俘虜獻(xiàn)祭的——祭司割斷犧牲者的頸動(dòng)脈,喝下血液以吸收犧牲者的生命力和精髓。
這種對血液的原始崇拜,引發(fā)出古人種種在今天看來離奇荒誕的行為——古羅馬人會(huì)飲下戰(zhàn)敗的角斗士的血,以使自己強(qiáng)壯;此外,他們還相信喝人血能治療癲癇;古埃及皇后殺死奴隸后用他們的血沐浴,因?yàn)樗嘈胚@會(huì)讓自己變得更美麗。
關(guān)于血液的最早醫(yī)學(xué)記錄
周杰倫有句膾炙人口的歌詞:“我給你的愛寫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達(dá)米亞平原。”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關(guān)于血液的醫(yī)學(xué)記錄,就來自美索不達(dá)米亞平原上的蘇美爾人。
蘇美爾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產(chǎn)生的文明,其開端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蘇美爾人很早便認(rèn)識(shí)到血液是“生命的基石”,并認(rèn)為血液是由肝臟控制的。同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巴比倫祭師,則把人體內(nèi)的血液分為白晝血與黑夜血——這是古人對于動(dòng)脈血與靜脈血的最早認(rèn)識(shí)。
希波克拉底與放血療法
在人類歷史上,放血療法曾被當(dāng)做一種“萬能療法”而延續(xù)了2000多年。
放血療法的理論基礎(chǔ),來自古希臘著名醫(yī)生、“西方醫(yī)學(xué)之父”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7)的“體液學(xué)說”。那時(shí),古希臘人認(rèn)為疾病是神靈對人的懲罰。因此,生病后往往花錢請巫師念咒文、施魔法、祈禱——這自然起不到什么療效,患者還常常因?yàn)檠诱`病情而死去。
為了破除這種“疾病神授”的迷信,希波克拉底通過研究人的肌體特征和疾病成因,提出了對后世影響深遠(yuǎn)的“體液學(xué)說”。他認(rèn)為,人的生命依賴血液、粘液、黑膽汁和黃膽汁四種體液,疾病的發(fā)生是由于體液的失衡,而恢復(fù)平衡的方法就是嘔吐、發(fā)汗、瀉下和放血。在古希臘人看來,血在四種體液中占主導(dǎo)地位,因而放血療法備受推崇。
中世紀(jì)以前,放血療法的主要實(shí)施者是教堂的僧侶,直到1163年,教皇亞歷山大三世才把這權(quán)限下放給民間的理發(fā)師。現(xiàn)在理發(fā)館的招牌——紅藍(lán)白條紋的旋轉(zhuǎn)筒子,就來源于放血療法。其中,紅色代表動(dòng)脈血,藍(lán)色代表靜脈血,白色代表繃帶。理發(fā)師們還發(fā)展出一整套放血操作規(guī)程和工具,比如,切割血管時(shí)用的柳葉刀——英國著名醫(yī)學(xué)雜志《柳葉刀》正是得名于此。
客觀來說,放血療法有其合理性,但它只能治療部分疾病,且放血量有嚴(yán)格限制。然而,由于缺乏正確認(rèn)識(shí),它曾被作為一種“萬能藥方”而風(fēng)靡整個(gè)歐洲。12世紀(jì)的一首歌謠,對此進(jìn)行了形象地描述——“身體放血改新顏,提神醒腦又亮眼;思維清晰無悲愁,運(yùn)動(dòng)內(nèi)臟益睡眠;聽力敏銳精神旺,聲音洪亮每一天。”據(jù)說,就連法國皇帝路易十五患上天花后,也是通過放血來進(jìn)行治療的。
那么,放血療法真的那么神奇,能“改新顏”嗎?
死于放血的華盛頓總統(tǒng)
放血療法從歐洲傳到美洲后,大受歡迎,尤其是得到著名醫(yī)生、同時(shí)也是唯一一個(gè)在美國《獨(dú)立宣言》上簽字的醫(yī)生本杰明·拉什的推崇。
1794~1797年,費(fèi)城流行黃熱病時(shí),本杰明每天至少給100名患者實(shí)施放血治療,以至于他診所后院變成了血海,血里滋生的蒼蠅密如黑云。一位好事的英國記者翻閱當(dāng)時(shí)費(fèi)城的死亡報(bào)告后發(fā)現(xiàn),經(jīng)本杰明治療后的患者,死亡率明顯偏高。

1667年,勞爾將羊血輸入一名年輕男性患者體內(nèi)并獲成功。

“微生物學(xué)之父”列文虎克

布倫道爾把健康丈夫的血輸給產(chǎn)后大出血的妻子,11例實(shí)驗(yàn)中5例成活。

“血型之父”蘭德斯坦納

阿萊西斯·卡雷爾開創(chuàng)了血管吻合術(shù)。
放血療法還曾奪去美國開國總統(tǒng)華盛頓的寶貴生命。1799年12月12日,他在冒雪巡視種植園后出現(xiàn)喉嚨疼痛癥狀,2天后,病情加重。管家和醫(yī)生先后4次為他放血125盎司(約3572毫升,幾乎占了他體內(nèi)血液總量的一半)后,他于14日晚上不幸去世。
華盛頓總統(tǒng)的慘痛教訓(xùn),引發(fā)了人們對放血療法的質(zhì)疑。
10年后,蘇格蘭軍醫(y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把366名病情類似的士兵平均分成3組,進(jìn)行對照實(shí)驗(yàn)。他發(fā)現(xiàn),采用放血療法的一組士兵死了35人,沒采用放血療法的兩組則分別只死亡2人和4人。1819年,法國醫(yī)生皮埃爾·路易發(fā)布了他在長達(dá)7年時(shí)間里對近2000名患者的臨床觀察報(bào)告,結(jié)論同樣是“放血療法的死亡率偏高”。
此后,隨著越來越多的類似報(bào)告的出現(xiàn),這個(gè)流行了2000多年的療法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tái)。
血液循環(huán)理論問世
1616年,現(xiàn)代生理學(xué)奠基人、英國醫(yī)生威廉·哈維從動(dòng)物實(shí)驗(yàn)中觀察到血液在體內(nèi)按一定途徑運(yùn)動(dòng)。這一具有跨時(shí)代意義的偉大發(fā)現(xiàn)為后來的輸血治療奠定了基礎(chǔ),也啟發(fā)了向血管內(nèi)注射藥物治病的設(shè)想。
其實(shí),早在中世紀(jì)就有醫(yī)生提出,將血液從一個(gè)人體內(nèi)輸入另一個(gè)人體內(nèi),也許能治療包括精神錯(cuò)亂在內(nèi)的各種疑難雜癥。有的醫(yī)生甚至認(rèn)為,輸血能改變?nèi)说钠沸校L試將貴族的血液注射給罪犯——這一荒謬的實(shí)驗(yàn)最終當(dāng)然以失敗告終,但輸血時(shí)代到來的曙光,卻已離之不遠(yuǎn)。
勞爾開動(dòng)物輸血先河
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輸血,發(fā)生在兩只狗之間。
1665年,英國生理學(xué)家理查德·勞爾首次進(jìn)行動(dòng)物間輸血實(shí)驗(yàn)。他將一只狗放血至瀕死狀態(tài),再用鵝毛管將健康狗的動(dòng)脈與瀕死狗的靜脈相連接,瀕死狗竟奇跡般地起死回生。這一實(shí)驗(yàn)開創(chuàng)了動(dòng)物輸血成功的先河。
1667年11月23日,勞爾為一名感到自己“腦子有熱、不平衡”的22歲年輕男子輸人少量羊血。他將羊的頸動(dòng)脈與男子的肘靜脈連接,輸血后患者無任何不良反應(yīng),6天后患者向英國皇家協(xié)會(huì)報(bào)告了他的自我感覺,醫(yī)學(xué)界為之震動(dòng)。
同一年,法國御醫(yī)丹尼斯用同樣的方法將羊血輸給一位16歲男孩取得成功。12月19日,丹尼斯再次將280ml的小牛血輸入一位名叫莫里的患者體內(nèi)。不幸的是,莫里在接受第三次輸血后出現(xiàn)發(fā)熱、腰痛等癥狀,伴有黑色尿,不久便死亡。莫里的家人隨即狀告丹尼斯殺人。法庭最終雖然宣告丹尼斯無罪,但同時(shí)判決:自1668年4月17日起,未經(jīng)巴黎醫(yī)學(xué)部批準(zhǔn)不得輸血。1677年,法國議會(huì)、英國皇家學(xué)會(huì)相繼下令禁止人體輸血實(shí)驗(yàn),隨后羅馬也禁止輸血。
此后,一度轟動(dòng)世界的輸血療法被冷落了一個(gè)半世紀(jì)。
列文虎克發(fā)現(xiàn)紅細(xì)胞
1674年,荷蘭顯微鏡學(xué)家、“微生物學(xué)之父”列文虎克借助自己設(shè)計(jì)的顯微鏡,發(fā)現(xiàn)了人類唾液中的微生物、精液中的精子和血液中的紅細(xì)胞。
1674年4月7日,列文虎克在給英國皇家學(xué)會(huì)的書信中寫道:“我發(fā)現(xiàn)血液是由水晶體般的霧狀水組成,其中含有非常小的圓形球狀物。”列文虎克提到的水就是血漿,圓形球狀物則是紅細(xì)胞。
這些微小的紅色球狀物到底有多小?列文虎克希望得出精確結(jié)論,為此,他獨(dú)辟蹊徑,用頭發(fā)和沙子作參照物,最終測量出紅細(xì)胞的直徑大約為7.9375微米,體積是一顆細(xì)沙粒的2.5萬分之一。這和今天測得的紅細(xì)胞平均直徑7.2微米,平均體積83立方微米非常相似。
通過對從鯉魚科的小魚到巨大的鯨魚等各種魚類血液中的紅細(xì)胞進(jìn)行測量,列文虎克發(fā)現(xiàn),它們的紅細(xì)胞的體積是大致一樣的,他還發(fā)現(xiàn)了白細(xì)胞及血液的凝固性(血小板的功能)。
紅細(xì)胞的發(fā)現(xiàn),意義重大——它改變了人們過去把血液看作一種簡單的、蘊(yùn)含著看不見的精神和人性的液體的錯(cuò)誤認(rèn)知,使人們了解到血液是一種快速生長的物質(zhì)。
布倫德爾的人際輸血實(shí)驗(yàn)
1817年,在輸血實(shí)驗(yàn)被“叫停”近150年后,英國婦產(chǎn)科醫(yī)生、“直接輸血的先驅(qū)”詹姆斯·布倫道爾自行設(shè)計(jì)了一套由漏斗、注射器和試管構(gòu)成的輸血裝置。在狗身上測試了這套裝置后,他將幾個(gè)健康的人捐獻(xiàn)的血注射進(jìn)一個(gè)血流不止的垂死患者的手臂,但兩天后,這名患者不幸去世。
不甘心失敗的布倫道爾此后又進(jìn)行了幾次實(shí)驗(yàn),將健康丈夫的血輸給產(chǎn)后大出血、瀕臨死亡的妻子。11例實(shí)驗(yàn)中有5例成活,引發(fā)醫(yī)學(xué)界轟動(dòng)。
布倫道爾認(rèn)為,此前法國御醫(yī)丹尼斯的輸血實(shí)驗(yàn)之所以失敗,是因?yàn)檩數(shù)氖恰靶笊难薄KJ(rèn)為,不應(yīng)該在不同物種之間輸血,因?yàn)椤安煌愋偷难合嗖钌踹h(yuǎn)”。
“血型之父”蘭德斯坦納
1900年,世紀(jì)之初,血液發(fā)展史迎來一次偉大的發(fā)現(xiàn)——奧地利醫(yī)學(xué)家卡爾·蘭德斯坦納通過實(shí)驗(yàn)發(fā)現(xiàn),人的血液有三種不同的類型:A型、B型和O型。這一發(fā)現(xiàn),為蘭德斯坦納摘得了1930年諾貝爾生理學(xué)或醫(yī)學(xué)獎(jiǎng)的桂冠。后人為紀(jì)念這位偉大的醫(yī)學(xué)先驅(qū),尊稱他為“血型之父”,并將他的生日——每年的6月14日定為“世界獻(xiàn)血者日”。
1902,蘭德斯坦納的同事在一次更大規(guī)模的交叉實(shí)驗(yàn)中發(fā)現(xiàn)了AB型血。至此,A、B、O、AB四種血型全部被發(fā)現(xiàn)。
1927年,蘭德斯坦納與美國免疫學(xué)家菲利普·列文共同發(fā)現(xiàn)血液中的M、N和P因子,直接帶動(dòng)了此后MNSS血型系統(tǒng)的發(fā)展。1940年,蘭德斯坦納和另外幾名醫(yī)生共同發(fā)現(xiàn)了血液中的Rh因子——這項(xiàng)發(fā)現(xiàn)拯救了很多從母親那里得到不匹配Rh因子的胎兒的生命。
卡雷爾開創(chuàng)血管吻合術(shù)
輸血治療中的一大難題,是怎樣將血管直接連通,形成血管吻合。
最早進(jìn)行血管重建的是Lambert,1762年,他對一個(gè)肱動(dòng)脈的小破口進(jìn)行了縫合關(guān)閉。這是一個(gè)歷史性的進(jìn)步,此前為防止出血,都是對破裂的血管進(jìn)行結(jié)扎。之后,有許多醫(yī)生都進(jìn)行了類似的實(shí)驗(yàn),但直到法國醫(yī)生阿萊西斯·卡雷爾發(fā)明出“三點(diǎn)法”血管吻合技術(shù),才真正解決了血管吻合的難題。
當(dāng)時(shí),血管吻合術(shù)之所以難以實(shí)施,首先是因?yàn)槿狈线m的縫合材料。其次,破損血管中沒有血液充盈,血管管壁往往貼在一起,很難縫合,且縫合后的血管也容易變狹窄,易導(dǎo)致血流過慢。此外,縫合材料的存在會(huì)破壞血管內(nèi)皮的完整性,導(dǎo)致人體凝血機(jī)制的不恰當(dāng)激活,最終引發(fā)感染或血栓形成,造成血管再次阻塞。
為解決這些難題,卡雷爾冥思苦想。后來,他在一家男子服飾用品商店得到靈感——在這里,他不僅找到了非常纖細(xì)的縫合針及縫合線,還從刺繡女工固定布料邊緣的手法中得到啟發(fā),發(fā)明出著名的“三點(diǎn)法”血管吻合術(shù)——在兩根需要吻合的血管橫截面上取等邊三角形的三個(gè)頂點(diǎn)作為固定,再經(jīng)過稍稍牽拉,原本圓形血管的吻合操作就變成了對三個(gè)吻合平面的操作。

“三點(diǎn)法”血管吻合術(shù)原理圖。
從1894年到1904年,卡雷爾反復(fù)實(shí)驗(yàn),最終成功地將動(dòng)物的靜脈與動(dòng)脈吻合。1908年,他將一名父親的動(dòng)脈與其患病女兒的腿部靜脈吻合,由于二人血型相同,輸血大獲成功。
“三點(diǎn)法”血管吻合術(shù)的問世,意味著離體器官能及時(shí)得到血流灌注,使器官移植成為可能。隨后,卡雷爾成功完成了動(dòng)物腎臟和卵巢移植,并發(fā)現(xiàn)了如何進(jìn)行冠脈血管的操作以保證心臟的供血供氧——這對后來的冠脈搭橋手術(shù)而言十分重要。
卡雷爾還與亨利·大金一起發(fā)明了卡雷爾-大金傷口處理法,在青霉素發(fā)現(xiàn)之前,這一方法一直是標(biāo)準(zhǔn)的傷口處理方法。
1912年,因“三點(diǎn)法”血管吻合術(shù)的發(fā)明以及由此帶來的器官移植的可能性,卡雷爾榮獲諾貝爾生理學(xué)或醫(yī)學(xué)獎(jiǎng)。
血液抗凝與血庫的建立
18世紀(jì)至19世紀(jì)中葉,為解決輸血中血液凝固問題,一些生理學(xué)家和醫(yī)生開始著手進(jìn)行抗凝或去纖維蛋白的嘗試。比如,Hewson發(fā)現(xiàn)了中性鹽的抗凝作用,但最終因毒性過大而未能臨床應(yīng)用。Panum則主張將血清攪拌去除纖維蛋白后輸入人體——也就是將血清分離后輸入人體。
為改進(jìn)輸血,英國產(chǎn)科醫(yī)生布拉克斯頓·希克斯首次使用磷酸鈉抗凝劑。此后,又相繼有生理學(xué)家提出用草酸鹽、檸檬酸鹽以及枸櫞酸加葡萄糖的混合物作為抗凝劑。
1915年,紐約馬爾他西奈山醫(yī)院的外科醫(yī)生理查德·萊文森博士發(fā)現(xiàn)0.2%的檸檬酸既可以防止血液凝固又對人體無害。1943,這種檸檬酸被研制成ACD并沿用至今,為血庫系統(tǒng)的建立奠定了基礎(chǔ)。

布拉克斯頓·希克斯
自體血回輸技術(shù)問世
當(dāng)輸血被應(yīng)用于臨床后,血源不足成為一個(gè)突出矛盾。此外,由輸血引發(fā)的疾病傳播、溶血反應(yīng)等日益受到重視。在這一背景下,自體血回輸技術(shù)宣告問世。
最早的自體血回輸,可以追溯到1818年。當(dāng)時(shí),布倫德爾為1例產(chǎn)后大出血的婦女回輸了從她自己身上收集的血液并獲得手術(shù)成功。但直到1874年,海莫才將自體輸血方法廣泛用于產(chǎn)后出血治療,并首次提出術(shù)中自體血回輸這一輸血新方式。
此后,隨著血液收集裝置的不斷改進(jìn),自體血回輸日益受到青睞。目前,歐美國家有50%以上的輸血為自體輸血,澳大利亞60%的擇期手術(shù)患者選擇自體輸血;日本則有80%的患者術(shù)前備自體血。自體輸血的優(yōu)勢是顯而易見的:不會(huì)因輸血染上AIDS、梅毒、瘧疾、肝炎等傳染性疾病;不會(huì)產(chǎn)生對血液成分的免疫反應(yīng);無溶血、發(fā)熱、過敏等輸血反應(yīng);可解決特殊血型(如Rh陰性)病人的供血問題;不需檢驗(yàn)血型和交叉配血試驗(yàn);對不接受異體輸血的宗教信仰者也能進(jìn)行輸血治療。可惜的是,盡管有這么多優(yōu)點(diǎn),但目前中國自體輸血比率僅為1%,大多數(shù)醫(yī)院尚未開展這項(xiàng)業(yè)務(wù)。
“缺什么補(bǔ)什么”的成分輸血
在輸血治療中,有時(shí)輸全血可能既達(dá)不到治療目的,又會(huì)引起輸血反應(yīng)。例如患血小板減少的或粒細(xì)胞減少癥的患者,輸全血很難提高血小板及白細(xì)胞的數(shù)量,且大量輸血后,還會(huì)因血容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臟負(fù)擔(dān)。
幸運(yùn)的是,20世紀(jì)70年代成分輸血技術(shù)的問世,解決了這一難題。
成分輸血,是根據(jù)血液比重不同,將紅細(xì)胞、白細(xì)胞、血小板等各種血液成分加以分離提純后,依據(jù)病情需要輸注有關(guān)成分的一種輸血方式。
與輸全血相比,成分輸血有著眾多優(yōu)勢——它的針對性更強(qiáng),“缺什么補(bǔ)什么”,且每一種血液成分在制備過程中都要經(jīng)過提純、濃縮,濃度和純度更高,療效更好;全血成分復(fù)雜,而成分血相對單一,因此它引起不良反應(yīng)的幾率要低于輸全血;由于血液中各種成分傳播病毒的危險(xiǎn)性并不一樣,比如,白細(xì)胞傳播病毒的危險(xiǎn)性最大,血漿次之,紅細(xì)胞和血小板則相對較安全,因此,成分輸血能有效減少輸血相關(guān)傳染病的發(fā)生;不同的血液成分有不同的保存條件,分離制成的各種血液成分制劑,能更好地根據(jù)各自適宜條件進(jìn)行保存;每份全血可以制成多種成分血,分別用于不同的患者,可使一人獻(xiàn)血,多人受益。
回望人類醫(yī)學(xué)史,從“體液學(xué)說”的提出到放血治療的盛行,從輸動(dòng)物血到實(shí)現(xiàn)人際輸血,從血型的發(fā)現(xiàn)到按成分輸血,人類對血液的認(rèn)識(shí),經(jīng)歷了數(shù)千年的艱難探索。未來,隨著人類對血液認(rèn)識(shí)的不斷加深,我們必將揭開這一“神奇液體”的更多秘密。
獻(xiàn)血有害健康嗎?
獻(xiàn)血,是救死扶傷,為社會(huì)奉獻(xiàn)愛心的高尚行為。我國從1998年10月1日起,開始實(shí)行無償獻(xiàn)血制度。
通常我們一次獻(xiàn)血量為200毫升,約占全身血液總量的5%左右。對健康人來說,這個(gè)量不足以對身體造成傷害。初次獻(xiàn)血后有人會(huì)感到頭暈惡心,這是由于血壓改變和情緒壓力引起的,很快會(huì)被身體調(diào)整過來。此外,白細(xì)胞、血小板等也會(huì)減少,但血小板的壽命為7~10天,因此幾天后即可恢復(fù);紅細(xì)胞的壽命是100~120天,紅細(xì)胞明顯減少時(shí),骨髓會(huì)用6~8倍的速度造血,1個(gè)月內(nèi)紅細(xì)胞數(shù)量即可恢復(fù)正常。其他大部分因獻(xiàn)血而減少的物質(zhì),2天內(nèi)就能得到補(bǔ)充。
獻(xiàn)血后最好在原地休息10分鐘,不要猛地起身,以防引發(fā)眩暈。2小時(shí)內(nèi)針口不要碰水,24小時(shí)內(nèi)不宜進(jìn)行體力勞動(dòng)或體育運(yùn)動(dòng),2天內(nèi)不宜抽煙喝酒。獻(xiàn)血后要注意補(bǔ)充營養(yǎng),尤其是補(bǔ)充鹽和鐵元素等,因此可以馬上喝一杯淡鹽水。此外,2次獻(xiàn)血的時(shí)間間隔最好不少于6個(g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