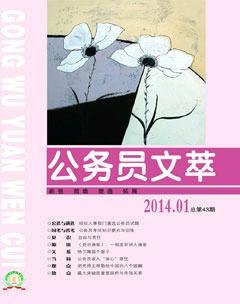罪刑法定“因公”犯罪更不應例外
據《南方周末》梳理,自2000年以來媒體廣泛報道的16起公民在城管執法中死亡的案例,有5起被追究刑責,5起未予追究刑責,個別刑罰情況不明。5起被追究刑責的案件,多以故意傷害罪起訴,未被追責的,尸檢報告多將死因指向被害人自身的疾病等情況。
城管與小販的戰爭,沒有贏家。伴隨著一起又一起沖突乃至傷亡的案件,公眾對這句話的認知得到加深。梳理這些城管致人死亡案件發現,罪與非罪以及量刑的輕重也確實成為社會公眾屢屢討論、熱議的話題。執法者犯法(甚至犯罪),是社會普遍認為應當從重處罰的事由,但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卻又可能很難完全滿足這樣的期待。
“因公”犯罪,并非嚴格的刑法概念,其與刑法意義上的職務犯罪有不小的區別。后者除了強調犯罪嫌疑人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還要求其犯罪本身具有“利用職權實施”的特性,比如刑訊逼供、非法拘禁、暴力取證等。簡言之,所謂利用職權,意味著法律確曾賦予某些機關以人身強制類權力,而此類特殊主體的犯罪行為屬于在行使相關權力時的嚴重越界。相應地,刑法在量刑時對此多會有“加重處罰”的表示,或可視為對“知法犯法”的懲罰。而“因公”犯罪試圖歸納的城管執法過程中致人死亡案件,由于城管本身并不具有法定的人身強制權,其在執法過程中出現致人傷害、死亡等情形,處理時現有法律可能無法將其執法者身份作為某種量刑考慮。
城管執法中致人死亡案件,是否該因特定主體的身份而予以加重量刑,這是一個層面的問題,但在所謂執法過程中出現完全超越其職權的犯罪行為,是否會因為特定主體的身份而有定罪、量刑上的從輕,則可能是另一個層面的憂慮。在現有判例中,城管執法致人死亡,多以故意傷害罪認定,《刑法》第234條對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量刑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三個檔位,但現有案例中卻多未被重判。在城管執法人員“外力”前提下,被害人是否“有病”,成為量刑輕重的關鍵,也成為了外界非議的核心。
盡管并無人身強制權,但因為是從事公職過程中犯罪,就有意無意地得到某種量刑上的考慮,這絕非法治秩序下所能容忍的現象。司法裁判在相關案件處理過程中客觀上是否給公眾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值得深思。從技術層面看,刑事司法裁判文書長期以來較少闡述法理的設置,無論是采納與否均直接套用既有條款,而非詳盡表述相關理由,是造就公眾相關觀感的重要原因。
人們往往用“公平不公平”作為對具體個案結果的評判框架,而司法則義無反顧地擔負著公平正義的使命。奉著社會公職的名義,絕不應該從事違法甚至犯罪的行為,行為一旦越界則司法就絕不應該對其有半點從輕的寬宥與心思。顯然,司法還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與反思,去彌合和緩解公眾在此間已經產生的憂慮。
(摘自《思想理論動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