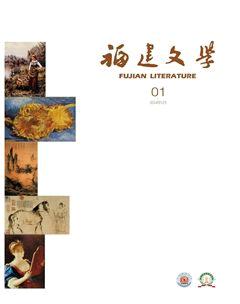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語境
李迎春
鐘兆云在與二姐鐘巧云合作的新著《鄰里》后記里寫道:“這是一個鄉村的傳記,一群村民的傳記,一部鄉親人物的大辭典,大凡傳記和辭典,真實是生命力。”作為《鄉親們》的姊妹篇,時隔兩年之后,鐘兆云、鐘巧云姐弟再度合作,捧出面目一新的66萬字傳記體小說《鄰里》,讓我們再次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廣袤的鄉村。對于大多數作家來說,鄉村是我們的童年記憶,是作家走向人生道路的原點。而對于農家婦女鐘巧云來說,鄉村不僅存在于成長的記憶中,而且是每天鮮活的現實。因此,以正在蛻變中的鄉村生活作為寫作基礎的創作,無疑是《鄰里》最大的特色與優勢。翻開厚厚的小說,我再次跟隨作家來到閩粵邊界的武平小山村,向那片深情的土地和它的鄉親們致敬。
要想歸納小說的特點,至少有四點是值得關注的。一是小說體現了中國鄉村最真實的生存范本,作家所說的“真實”就是這種剝開了鄉村外衣之下的真實境況;二是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傳統鄉村的結構在快速地消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基于人性的探索思考良多;三是小說中客家題材與客家語言的高度融合,向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的鄉村民情風俗畫卷;四是從真實的描摹到藝術手法的使用,使《鄰里》這部作品的小說敘事技巧日傾成熟。
如果要想認識真正的中國鄉村,那么《鄰里》和上一部《鄉親們》一樣,依然是中國鄉村最真實的生存范本。《鄰里》所敘述的美溪村是南中國客家地區的一個普通鄉村,介于閩南金三角和珠江三角洲的中間地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偏僻和貧困成為它的代名詞。美溪因為小說使得它成為讀者眼中美麗而傷感的鄉村,成為作家創作的地域場。《鄰里》不是一種完整的長篇結構,但每一個短篇中的敘事語境大都與作家成長的時期相近,基本囊括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可能毫不夸張地說,相對于大多作家對鄉村的想象描寫,《鄰里》是鄉村小說里最真實的鄉村狀態。鐘巧云在勞作之余將思索的目光投向她身邊的親人、鄰里叔伯,隨時記錄下他們的言行舉止,作為小說的原型。作家在寫作中堅持“踏在生存的地平線上”,“努力透視底層百姓的疾苦和內心世界,由表及里探尋,提示這一生命群體的存在形式”(鐘兆云《后記》)。小說的農村是緩慢流淌的時光河流,它不像城市那么張揚、那么劇烈地變幻,它通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揭示鄉村的變遷;與此同時,通過一件件典型的事例來反映農村的“新”、“奇”。《賭博風云》里的賭博風氣,《養豬及其他》里大規模養殖業的興起,《水牯買“牛”》里婚姻傳統的消失……小說正是以橫的事件,縱的人物成長歷程,構成鄉村變遷的座標。從外表看,鄉村的生活改善了,建起了新房新舍,但垃圾增多了,環境污染了;從內部看,鄉村的善良淳樸依然沿襲,鄉村的愚昧落后也同樣沿襲,再加上賭博風氣的彌漫、鄉村管理的缺失,鄉村的精神生活空虛而迷茫。《鄰里》向我們展示的正是這種矛盾交織下的鄉村生活。
當鄉村的孩子離開鄉村,回頭尋找出發的地方,卻發現鄉村早已不是我們記憶中的模樣。這就是每一個中國人成長的困境。城市化進程帶給我們的是陌生化,鄉村的多樣性正在消失,代替的是千篇一律的所謂城市生活。《鄰里》正是揭示了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人性探索。美溪村的發展中不可阻擋地遇到了這股城市化潮流,一是打工潮,二是賭博風,三是征地拆遷。地處兩省交界的美溪村,經歷了兩次大的經濟轉變,打工使村民們脫離貧困,征地拆遷使村民獲得一筆可觀補償,然而更多的是村民思想和社會風氣的轉變。人性,就在鄉村的變遷中凸顯出來。小說緊緊抓住人性的閃光點和丑陋之處,向讀者訴說鄉村的精神困局。就編排來看,開篇是《天平上的親情》,結尾是《父親在天堂》,向我們講述了一個完整的以子云、子龍家族的親情故事,還有周圍鄰里間的家庭關系,承襲著古老的鄉村傳統,人性中的善良、質樸、無私,恪守家庭、重情重義得以彰顯。《依依婆媳情》、《母和子》、《這樣一個家》、《王桃花們的開心時機》都洋溢著這種溫暖的情懷,讓人留戀與感動。當然,人性中的丑陋也在此粉墨登場。好吃懶做的泥公、自私自利的菊花、守財奴細狗、忤逆媳婦菊招、無理取鬧的菊英、賭博頭子陳發貴、賭虧了的老板娘……甚至還有為一點錢財不惜鋌而走險殺人害命的,上豐一個村的人爭請莊家到自己家賭博。為錢財逐利,失去善良本真,失去親情友情的事例在文中比比皆是。這是觸目驚心的現實,也是人性丑惡的釋放。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正遭遇著這種好與壞、善與惡交織的困境,令人感慨,令人深思。
近幾年,客家題材的寫作漸成風氣,也有不少精品問世。《鄰里》帶給我們的驚喜是,這部作品題材與語言的高度融合,將客家元素做到無縫對接,而不是勉強將客家風俗風情貼上,使內容與表達成為兩張皮。可以說,《鄰里》中的客家民情風俗是滲透到語言里的。翻開全書,我們看不到純粹的客家民俗的描述,而是在人物的敘述中自然展現這種風俗。客家訂親、過生日、葬禮等的風俗并沒有大段大段描寫,更沒有對扛菩薩打蘸之類的濃抹重彩,只有像流水一樣自然流淌,穿插在事件和人物中的講述。而客家語言也在順其自然中寫出,如“酸夾女王”(形容很會說酸話的女人),“雪白的大腳髀”(雪白的大腿)、“鬼喔般”(鬼叫一般),形象而生動。更有那些詼諧的客家語言讓小說增色不少。如說“目珠烏三寸”,“目珠”就是眼睛,意思說看了讓人討厭;“窮人不消多,有兩甲米就會唱歌”,表示容易得到滿足;“爺哩娭哩惜滿子”,表示父母親最疼小兒子。等等這些客家語言俯拾皆是,可以說是客家語言的活詞典。客家題材與客家語言的巧妙結合,形成了《鄰里》這幅美麗的客家鄉村風情畫卷。
作為小說,與第一部《鄉親們》相比,敘事技巧更加成熟。對于創作,鐘兆云說“寫作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過于虛構,或過于現實,往往就不是文學,難以牽引人,因此,這兩者之間的橋梁,還就是文學。”從現實出發的虛構,不是簡單地記錄生活,而是對生活的重新梳理,取到撥開迷霧見真山真水的效果。《鄰里》的小說敘事風格依然是寫實的,但在篇章結構、心理描寫、人物塑造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像《賭博風云》、《養豬及其他》、《泥公的前半生》、《牛腚根》、《逆子》等都是很精彩的短篇。《賭博風云》從不同的人群涌向細狗家開始寫起,先抑后揚,一步步將賭博的興起作了交待,然后通過愛英、玉珍、香玉的親身體驗,細狗家因招攬賭博場地發生的糾紛,兩個老板娘的賭博經歷,最后引出賭王陳發貴,將鄉村的賭博演繹得妙趣橫生、風生水起。在小說中,還插入家庭糾紛、夫妻感情等,使作品更加充實厚重。在人物的篇章里,泥公、牛腚根、胖清等都是通過主人公的成長經歷,抓住幾件事情進行敘述,展示人物的性格及命運。人物個性各有不同,角色塑造立體豐滿,特別是通過對話推動情節發展,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活。整部小說沒有獨立的主人公,鄰里鄉親都是小說中的主人公,以美溪村為中心,人物關系構成一個網狀,慢慢地向讀者娓娓道來,有時看似漫不經心,其實大有深意。這種敘事方式沿襲了我國古代明清以來小說的敘事傳統,往往被很多當代作家所忽視,然而《鄰里》的實踐證明它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鄉親們》和《鄰里》是客家鄉村的大書,也是為千千萬萬個美溪村和它的鄉親們立傳的大書。它們既是小說,更是現實;既是現狀,更是精神探究。《鄰里》這部小說里,我們看到了作家一如既往的努力,看到了他們永遠不變的鄉村情懷。我們期待鐘兆云、鐘巧云姐弟倆的鄉村系列第三部更加精彩、更加有味、更加經典。
責任編輯 石華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