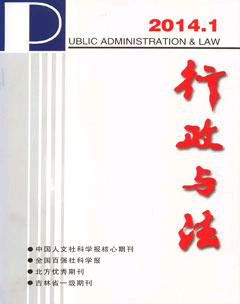網絡暴力言論治理的國際經驗及其借鑒
摘 要:網絡暴力言論是對公眾合法權益、政府公信力、網絡空間與實體社會秩序的挑戰,并已成為產生網絡風險的重要誘因之一。網絡暴力言論的存在不只是利益關系復雜化、網民結構年輕化、道德自律意識薄弱等原因所致,也與當下網絡的商業化運作、公民表達渠道不暢、媒體素養教育缺失等因素有關。發達國家在政府重視保障公民表達自由的前提下,加強了對網絡內容的治理。借鑒發達國家依法治理網絡暴力言論的成熟經驗,引導網民擔當起維護文明與道德的使命,已成為當前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
關 鍵 詞:網絡暴力言論;依法治理;網民
中圖分類號:C91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4)01-0041-06
收稿日期:2013-08-27
作者簡介:王彬彬(1982—),男,山東郯城人,國家行政學院教務部助理研究員,江蘇省行政學院廉政教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政府管理。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領導干部‘網絡執政能力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CZZ036;國家行政學院院級招標課題“公務員網絡參政道德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2ZBKT020。
網絡參與的開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匿名性,在理論上解構了傳統話語的權威,于是,受眾的主體性被最大化,草根力量迅速崛起。也正由于“網絡成了一個去中心、無疆界、主客體交織、富有彈性與不確定性的特殊空間”,[1]使少數網民極易突破理性、客觀、守法的底線,成為網絡暴力言論的發布者或傳播者。網絡暴力言論是社會暴力思維在網絡空間的延續,對社會公共秩序、公民合法權益等都存在著潛在的危害。在發達國家,盡管號稱“言論自由”受到完全保護,但在網絡上散播暴力言論并不在受保護之列。事實一再證明,放任自流、超越秩序的網絡不僅充滿風險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近年來,各國政府都在探索契合國情的網絡內容治理路徑,其成熟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一、網絡暴力言論的分類及其危害
我國目前尚處于復雜的轉型期,階層關系的復雜化、利益分配的懸殊化以及全球化帶來的文化上的劇烈震蕩,反映到網絡這一匿名、開放、管制相對寬松的虛擬空間時,難免會產生輿情激揚、“眾神狂歡”的獨特言論表達現象。網絡暴力言論這種極端表達方式正以其獨有的方式破壞著公共規則、侵蝕著道德底線。在我國,網絡暴力言論開始觸及社會大眾的“興奮點”是始于2006年的“虐貓女”、“銅須門”等熱點網絡事件。由于人人都可能成為網絡暴力言論的受害者,世界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加強了對網絡內容的管理。譬如:美國白宮網站的一篇文章宣稱,“聯邦政府正在謀求更大權力來保護民眾免遭各種網上威脅,其中就包括嚴格監管在網上鼓吹和激化情緒,從而導致暴力的言論”。[2]因此,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加強對網絡暴力言論的關切和治理,本文對三類網絡暴力言論進行了解析,闡述其對無辜個體、社會秩序和政府權威的危害。
一是個體攻擊型,牽動網民盲從,侵犯公民權益。這類網絡暴力言論一般都帶有很強的群體娛樂性,或危言聳聽,或極具爆炸性。簡單說來,這些言論能夠成功吸引網民關注,并引發人們進行辯護或抨擊的強烈興趣,在群情激憤的情況下,使無辜個體的合法權益遭到嚴重踐踏。在2006年4月發生的“銅須門”事件中,某網友自曝其妻子因玩網游“出軌”,這一看點吸引了數以萬計網民的“眼球”,在短短數天之內,大量網民對當事人進行了血腥味十足的謾罵和討伐,甚至有人發表了“以鍵盤為武器砍下奸夫的頭,獻給那位丈夫做祭品”的暴力語言,令當事人名譽和身心受到了嚴重傷害。《人民日報》曾發文總結了網絡暴力言論具有的三大特征,包括“以道德的名義惡意制裁、審判當事人;追查并傳播當事人隱私,煽動和糾集人群以暴力語言進行群體圍攻;在現實生活中使當事人遭到嚴重傷害”。[3]事實上,網上針對公眾個體的暴力言論,多數是以“道德審判”的名義發聲,煽動“良心發現”的網民向毫無還擊之力的個體進行群體性攻擊,結果導致當事人在現實生活中遭到嚴重傷害。盡管多數網民對暴力言論的響應是出于維護正義的目的,但這種群情激憤、口誅筆伐的話語暴力侵害了受害人的名譽權或隱私權,嚴重者還可能構成侮辱、誹謗等刑事犯罪。
二是報復社會型,制造心理恐慌,危害社會秩序。當前,由于局部暫時出現的財富分配不均、社會正義失衡等原因,導致一小部分在現實生活中失意的網民選擇通過在網上發表對社會報復性言論的做法,宣泄對其所遭遇不公的不滿,以暴力言論實現其批評和表達的權益。這類網絡暴力言論容易把社會帶入“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一旦被利用來挑戰社會秩序和規則,就會演變為實現個人不正當目標的工具。此外,網絡正在成為社會心理的“晴雨表”、焦點事件的傳播源,它的傳播效果是傳統的傳單、廣播和電視等所無法比擬的。借助發達的互聯網,一條信息就有可能演變成軒然大波。因此,網上的這類暴力言論及其所形成的共鳴,極易在網絡公共領域的“廣場式狂歡”效應下,迅速演變為可能誘發社會心理恐慌的導火索。一些人(尤其是容易沖動、放縱的年輕網民)借助網絡傳播所具有的身份隱匿性、聯合成本低、殺傷半徑大等特征,自覺或隨波逐流地成為了網絡暴力言論的制造者或傳播者。盡管參與傳播網絡暴力言論的網民中多數是抱著“旁觀”和幸災樂禍的心態而卷入其中的,并以調侃和“惡搞”的態度去理解和對待其行為,但其行為的后果卻是極具負面性的,對社會秩序的威脅不容小覷。
三是解構權威型,引發集體癲狂,制造群體極化。網絡輿論已經成為執政黨、政府獲取政治權威及合法性的重要資源,但網絡所具有的解構權威、去中心化特質。容易為信息傳播中的群體極化現象制造便利。群體集化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認同偏執會對主流權威形成了巨大挑戰。有的網民以攻擊執政黨、政府和其他公共組織的權威為主題發表的暴力言論往往會在網上引發群體極化現象,并帶來“多數人的暴力”,淹沒理性的聲音。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對群體極化現象有著深刻的研究,他指出,在從眾心理的支配下,“群體會表現出一些孤立的個人不可能有的情緒和行為。在群體中,傻瓜、低能兒和心懷妒忌的人,擺脫了自己卑微無能的感覺,會感覺到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巨大的力量”。[4](p33)因此,這類網絡暴力言論更應當引起領導者的警惕。在現實生活中,這類網絡暴力言論的爆發與網絡的商業性炒作、民眾正當表達渠道的缺失有很大關聯。一方面,商業網站為追求點擊率,熱衷于炒作爭議性議題,貫用吸引眼球的圖片、驚心動魄的標題、極盡夸張的細節對相關議題進行解讀,從而為這類負面言論在網民中的“發酵”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從某些“網絡暴民”身上很容易看到公眾缺少有效的表達空間或渠道的影子,為促使與自身利益緊密相關問題的解決,人們會傾向于運用夸張、激進甚至暴力的言論對政府等公共部門施加壓力。
二、外國政府治理網絡暴力言論的經驗
如何在網絡傳播中控制暴力言論的泛濫、蔓延,規范、凈化網絡空間,最大限度地降低網絡暴力言論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發達國家政府和社會組織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互聯網上的暴力言論將摧毀我們的生活!”德國《焦點》周刊近日以此為題報道了該國治理網絡暴力言論的案例:德國一地方警察局依法拘捕了一名在網絡聊天室中吹噓“有一把槍,要殺死每個人”的青年,盡管該青年事后稱當時僅是一句玩笑話,但仍被判監禁并罰款。近兩年來,德國已處罰了60多起類似案件。[5]類似的報道在其他發達國家也屢見不鮮,網上任何“逾越言論自由和煽動犯罪間的那條界限”的暴力言論都會被防范和懲處。目前,發達國家政府對網絡暴力言論的治理普遍采取“政府與社會、企業互動,法律、技術、社會、教育多種手段并用”的綜合治理模式,具體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注重依法治理,健全專項法制。暴力言論破壞網絡生態、顛覆良序公德,首要的舉措就是從立法層面予以約束。1997年6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世界上首部全面規范Internet的法律——《多媒體法》(德文簡稱IUKDG),該法實施的目的在于保護用戶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并以專門篇幅對網絡服務商的責任、義務作出具體規定,還要求服務商不得鏈接或在搜索引擎中出現法律禁止的不良信息,違者最高罰款1.5萬歐元。美國與網絡不良信息治理相關的法律包括《聯邦禁止利用計算機犯罪法》、《計算機安全法》、《域名注冊規則》等。為對上網青少年進行保護,美國在2000年底通過的《兒童互聯網保護法》規定,公共圖書館都必須為聯網計算機安裝信息過濾系統,否則圖書館將無法獲得政府提供的技術補貼。2010年,美國又通過了《將保護網絡作為國家資產法案》,授權給聯邦政府在實施緊急狀態的情況下關閉互聯網。2005年,韓國接連發生一系列網絡暴力事件,促使韓國國會于2006年底通過了《促進使用信息通信網絡及信息保護關聯法》,該法規定各主要網站在網民留言前必須對其身份信息進行記錄,此外,網站如不主動屏蔽有關暴力、違法和涉嫌詆毀他人的文章和影像等,將要對因此而導致的后果負法律責任。
第二,明確責任部門,履行管理職能。早在1992年7月,韓國就成立了信息道德委員會。目前,韓國管理互聯網內容的專門機構是隸屬于信息和通信部的互聯網安全委員會(Internet Safety Commission,KISCOM),該委員會的主要目標就包括阻止有害信息在互聯網和移動網絡上的流通,以促進健康的網絡文化發展。KISCOM的審查范圍包括BBS、聊天室以及其他“侵害公眾道德的公共領域”、可能“傷害國家主權”和“傷害青少年感情、價值判斷能力的有害信息”。在德國,聯邦內政部總體負責網絡監管,其直屬的聯邦刑警局下設機構“數據網絡無嫌疑調查中心”承擔國內俗稱的“網絡警察”的職能。他們無需根據具體的嫌疑指控,有權24小時不間斷地跟蹤和分析網絡信息,以發現可疑的違法行為。目前,德國已有16個州設立了“網絡警察”或類似監管機構。2004年,希臘成立了網絡犯罪部,專門負責處理與互聯網相關的犯罪行為,一旦發現涉及國家安全、欺詐犯罪的暴力信息,馬上就會向法庭申請專門的搜查令,逮捕涉案人。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對不良信息治理負有重要責任,不僅如此,日本還積極號召民間機構和社會團體也加入到治理網絡不良信息的行動中來。2005年4月,日本成立了隸屬于信息技術安全局的“國家信息安全中心”,加強對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
第三,創新技術手段,過濾不良信息。自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來,各國政府都將出現于公共場合、可能被理解為帶有威脅公共安全意味的信息視為潛在危險要素進行嚴肅處理。近期,雖然受美國“斯諾登監控丑聞”影響,人們對政府過度監控網絡表示反感,但鑒于日益猖獗的網絡暴力言論會增添整個社會的緊張氣氛,人們對政府監控和清理網絡暴力言論的舉措表示了理解。據《環球時報》介紹,保守估計,全球幾乎八成以上的國家正在加強對鼓吹暴力等網絡言論的監控。在日本,人們將鼓吹暴力的網絡言論稱為“網絡犯罪預告言論”。在2008年日本“秋葉原殺人事件”后,盡管輿論對身處社會底層的罪犯有不同看法,但日本公眾幾乎都同意對“網絡犯罪預告”進行即時監控和嚴厲懲處。為此,日本警視廳專門委托軟件公司開發了能自動收集“網絡犯罪預告”言論的軟件。法國注重減少網絡暴力信息對青少年的危害,在政府干預下,網絡服務商有義務向用戶推薦“家長監督器”等青少年上網保護軟件,這類軟件可以阻止網絡不良信息對青少年的傷害。美國很多商業網站都與聯邦政府密切合作,并使用針對不良信息的過濾器。例如:SurfControl公司推出的“網絡巡邏”軟件是美國過濾工具的典型代表,近年來,該公司一直在為包括網絡暴力言論在內的不良信息的治理提供解決方案,相關網站的編輯在刪除有關褻瀆種族、民族、宗教和人身攻擊的言論時“從不手軟”。
第四,突出源頭治理,引導行業自律。鑒于網絡的開放性和虛擬性,行業自律就成為了目前各國政府治理網絡暴力言論的普遍做法。發達國家的互聯網企業多在政府引導下建立起行業自律組織,通過制定行業規范、處理社會投訴、進行宣傳教育等路徑,在維護網絡內容健康和保護公眾利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例如:英國在對互聯網內容進行管理時,貫徹堅持的就是一種“監督而非監控”的理念,通過網絡觀察基金會(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IWF)與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協會的合作,共同發表了題為《安全網絡:分級、檢舉、責任》的文件,并以此作為行業自律的基礎,鼓勵業界建立道德及分級標準,便于公眾知曉規避不良信息的方法。再如:法國相繼成立了“互聯網監護會”和“互聯網用戶協會”等組織,以及法國唯一的負責自我調節和協調的獨立機構“互聯網理事會”。德國設立“國際性內容自我規范網絡組織”以確保網絡內容的健康,尤其是對于未成年使用者。日本的行業自律體系更顯完善,Internet行業制定了一系列行業規范,如《網絡事業者倫理準則》強調行業自律與法治相結合,使網絡經營者的自律成為解決網絡問題的重要措施。
三、我國加強網絡暴力言論治理的路徑
在網絡時代,“人人都是麥克風”,任何個體行為都會對他人、社會、國家產生影響,責任無處不在。最大限度地保護網絡參與者的權益,維護網絡的正常秩序,使網絡不斷造福于人類,是現代政府的重要職責。倘若對網絡暴力言論放任自流,“當網絡上越來越多這樣的表現與暴力,理性的聲音就會選擇退場,積極的網絡輿論價值就會被掩蓋,整個社會的表達習慣就會遭到歪曲,中國正在通過網絡平臺蓬勃生長的言論進取就會遭遇挫折”。[6]因此,我國應當充分吸取國際上的成功經驗,以加強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為依托,健全法律體系、改進監管體制、創新技術手段,依法對網絡暴力言論進行治理,逐步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治理模式。
第一,加快專項立法,確保治理的針對性。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網絡內容治理,正在不斷建立健全互聯網監管法制,新世紀以來,我國先后出臺了多部與互聯網內容管理相關的法律、規章,例如:2000年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2000年國務院第31次常務會議通過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12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而早在2009年開展的“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則彰顯了政府在網絡內容治理中的堅定決心。然而,與公眾網絡參與的迅猛發展相比,立法的步伐遠落后于治理網絡暴力言論等新生現象的需要。特別是由于我國相應的法律法規對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行為及其法律責任的界定過于模糊,導致了對網絡暴力言論治理在法律適用上常常遭遇到尷尬。因此,我國應對現有法規進行清理,力爭出臺一部統一的關于互聯網信息傳播的法律并啟動配套法律的制定。同時,通過立法手段實現對網絡暴力言論的分級管理,嚴格事后追懲制度,實現依法治理的目標。目前,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已開始進行相關的探索,例如:杭州市人大常委會于2009年通過的《杭州市計算機信息網絡安全保護管理條例》開創了國內網絡治理的先例,該條例對計算機信息安全實行五級分類管理,并對網絡論壇實名制、嚴禁網上惡意評論、治理暴力言論等做出了明確規定,為我國其他地區對網絡信息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鑒。
第二,完善管理體制,提高治理的科學性。網絡不是孤立的空中樓閣,網絡空間中每一條信息的傳播都能在實體社會找到現實的根據,因而政府對網絡內容管理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網絡空間中暴力言論的頻繁宣泄,在“很大程度上是實體社會中風險要素在網絡空間無序釋放的結果,而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有組織的不負責則是這些風險積聚的主要根源。從這個角度來看,網絡暴力言論具有‘社會晴雨表功能。對此,政府要經常性地反思制度設置的公正性”。[7]因此,各級政府應當不斷加強網絡管理體制建設,提高治理的科學性。一要健全監管機構,理順管理職能。各級政府要把網絡內容管理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和績效考評體系,從戰略全局高度重視、發展、管理網絡,并形成網上信息內容管理部門牽頭,互聯網行業管理和打擊網絡違法犯罪等部門密切配合的高效聯動的工作格局。二要加強風險研判,有效引導輿情。網絡暴力言論的宣泄,在客觀上還具有一定的“社會安全閥”功能。各級政府應將網絡輿情研判作為信息化條件下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不斷提高輿情預警、發現和處置能力,及時開展風險問題評估;滿足公眾的合法表達權,引導網民理性表達意見,堅持網下處置和網上引導相結合,用尊重民意的實際行動贏得民心,把公眾情緒引導到健康理性的軌道上來。
第三,加強道德引領,實現治理的自覺性。治理網絡暴力言論必須在全社會倡導文明、負責的網絡話語表達,做到疏、堵結合。要通過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提高網民的自律意識,增強其對暴力文化的“免疫力”。2013年8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舉辦了“網絡名人社會責任論壇”,網絡“大V”們就網絡名人應堅守的“七條底線”達成共識,即法律法規底線、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公民合法權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和信息真實性底線。專家認為,這是網絡管理方式由“堵”到“疏”的轉變。[8]加強網絡文明的道德引領,一靠政府的政策宣傳與素養教育,二靠網絡意見領袖等公眾人物的示范,三靠互聯網傳媒發揮信息“把關人”作用。在互聯網空間,“把關人”是那些復雜多樣的傳播媒介,“把關”責任的缺失是網絡暴力言論肆虐的重要原因之一。《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網絡服務商對于有害信息承擔停止傳輸、保存記錄并向有關部門報告的責任。早在2003年,國內30余家知名互聯網信息服務媒體就簽署了《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自律公約》,承諾自覺接受管理和公眾監督、堅決抵制有害信息。因此,網絡服務商不僅要依法加強對暴力信息的“把關”,還要承擔網絡素養宣傳、教育的職責,將自身打造成為傳遞正能量的重要平臺和實現“中國夢”的強大推手。
第四,加速技術創新,增強治理的有效性。以技術創新推進“綠色上網”是根治網絡暴力言論的有效方式,目前,世界各國在技術上主要采取限制、過濾、屏蔽等手段對網絡暴力信息加以處置。2009年,我國為保護未成年人健康上網而推廣的“綠壩-花季護航”綠色過濾軟件,采用語義分析技術主動識別、攔截網絡不良信息,盡管這款過濾軟件尚不能做到盡善盡美,但卻邁出了以技術治理網絡暴力言論等不良信息的實質性步伐。因此,在軟件的研發、推廣和管理方式上還要下功夫。推行以技術治理網絡暴力言論,要重點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其一,需要政府為網絡服務商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幫助網絡服務商完善技術監管手段,運用更先進的技術對網絡信息進行分析、篩選、過濾,確保其掌握網絡內容管理的主動權。如德國政府為鼓勵使用不良信息過濾軟件,專門為圖書館、學校、政府等機構提供技術補助資金。其二,推動網站逐步實行網絡后臺實名制,完善對不良信息的追查機制,遏制網絡暴力言論的發布和傳播。作為互聯網普及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雖然美國暫未對網絡實名作出強制規定,但實際上,美國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站“臉譜”和互聯網“大牌”谷歌推出的“Google+”社交服務,都在實行實名制。因此,盡管網絡實名制在世界范圍內仍存爭議,但實施實名制對于治理網絡暴力言論的作用卻不容忽視,降低阻力的關鍵是完善配套政策以消除網民對隱私泄露和權益受損的擔憂。
四、結語
“每一種技術或科學的饋贈都有其黑暗面”,[9](p26)網絡在帶給人類巨大便利的同時,也以其自身的風險特性加劇著社會風險。但網絡技術運用者的行為失范、網絡空間管理者的職責缺位是網絡風險產生和擴散的根本原因。因此,網絡雖然是虛擬空間,但不應成為任意放縱的天堂。無論在何種制度空間,摒棄網絡暴力言論都是社會正常運轉的需要。治理網絡暴力言論不僅是凈化網絡空間的一種文化現象,更是政府加強社會管理、促進和諧穩定的一種行政職能。然而,這項工作顯然不只是政府的“獨角戲”,它與社會各界密切相關,需要各方力量的齊抓共治。我國政府應吸收國外成功經驗,從社會全局統籌謀劃,探索建立以立法為保障、技術手段為主導、行業自律為支撐、網絡素養教育為基礎、國際合作為輔助的綜合治理模式,共謀網絡生態的改善與網絡時代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劉劍敏,李潤權.論網絡的碎片化特征[J].新聞愛好者,2011,(18).
[2][5]紀雙城,柳玉鵬等.網絡暴力玩笑在全球不被寬容[N].環球時報,2013-07-31.
[3]鄧曉霞,王舒懷.網絡輿論暴力來勢兇猛 如何向它說不[N].人民日報,2007-08-10.
[4](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6]珍惜言論權利 杜絕網絡暴力[N].南方都市報,2008-06-02.
[7]姜方炳.“網絡暴力”:概念、根源及其應對——基于風險社會的分析視角[J].浙江學刊,2011,(06).
[8]光明日報評論員.堅守互聯網“七條底線”[N].光明日報,2013-08-19.
[9](美)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M]. 胡泳等譯.海南出版社,1996.
(責任編輯:牟春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