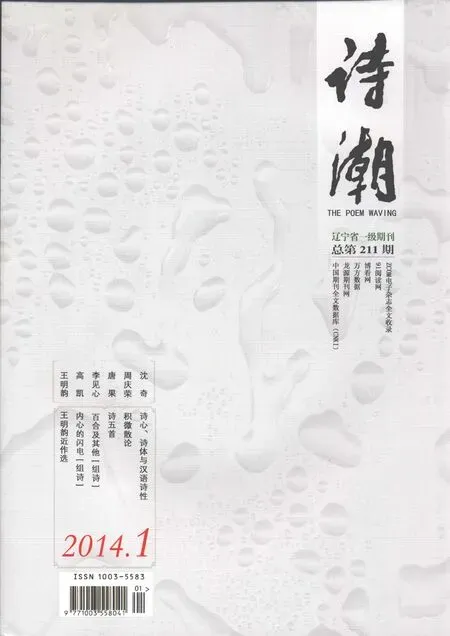遼西特產心靈之果
寧珍志
遼西特產心靈之果
寧珍志
如果不讀作品,我真的感受不到遼西這片貧瘠的土地、苦難的土地、文化積淀深遠厚重且現實發展還很脆弱單薄的土地,一旦與詩人的心靈接壤,會迸發出多少璀璨的生命之光。遼西有山,山并不高;遼西有水,水難豐盈;即使泥土,也會在春天的風沙與夏季的旱情里極不甘心地翻飛漂泊……物質生存條件的竭蹶反倒讓詩人們的精神需求更為渴望,心靈空間的主觀創造情緒恣意生長,語言呈現的世界獨特而富有韻味。生于斯長于斯的詩人們所構建的地域版圖并非是物理般的照相式投射,他們的筆觸也絕不會單純停留在山川景物人文習俗的表象層次,因為那不是詩。詩的表達,即是把它們無限循環地濃縮,化作春夏秋冬節氣的一方天色,化作喜怒哀樂個人的一次表情,化作聲音色彩欲出的一縷清唱,這天色表情清唱經過內心化學反應生發出來的詞語意象,又會被無限地放大,進而洋溢出勃勃的精神能量。
《第三生活區》是高詠志在悟透事物正反兩個方面之后,從中間地帶切開而生成的剖面。脫離母體后它也有兩面,或上下,或左右,或陰陽,或意念中的合而為一。目擊者清晰的一面被稱為“第三”,這是對心靈向度的重新命名,有著多音區、混聲部的含混性,是生活本象的藝術還原。比如《蜜夜》,蘋果、抹布、胡楊林、銅管樂器、舊麻袋、釘子、蘑菇等眾多意象交替登場,是暗夜的富庶豐饒?是人性的暗喻復指?是世界的物質依賴?結尾高潮迭起,以柔軟彰顯力度顯然比描述力度本身更有反彈性。高詠志毅然作別一詩一主題的粗淺表達,跌宕出精神的深層次。這在《春天的第一場雨》《那一夜》《愛的藝術》等詩中都有著透徹的體悟和表達。韓春燕的《秋天是一段別樣的經文》第一次讓遼西納入知識分子詩歌寫作的范疇,時間的哲學內涵與外延深邃精致,知性的旗幟光彩奪目。季節作為時間的具象所在,于遼西的意義不僅僅停留在紙上,而是源自故鄉源自童年的直覺靈光,是以往對現實的一次次深刻打動。果實打點行囊離家,離開枝頭離開土地,成熟的告別,收獲再見,諸多似曾相識的表達,在詩人筆下成為“陌生化”,意境創新,感性而質樸的喻體墜滿形而上的碩果。被哲學化了的花鳥蟲魚草木果蔬則活泛出密匝的精神光澤,有意與無意、醒與醉、生與死、現世與輪回,生命的多義和不可知性,詩人讓遼西涵蓋廣博深遠的人生真諦,鮮明標榜自己的辟入角度。
菁菁幾乎無時不在維護自己的精神“潔癖”,內心語境的澄明透徹繼續創造著女性詩歌的一方天地,構成自己靈魂眷戀的無限汪洋。蔚藍的大海,灼熱的桃花,孤獨的水晶,輕輕的蝴蝶,曼舞的雪花,司空見慣的景物
在詩人筆下,重新煥發出另類光芒。這組詩如同蘭波所言,“綜合了芳香、音響、色彩”,把女性生命活動的閃光點、純情度、思考力很質感地傳遞出來。菁菁的詩,既有琵琶遮面欲言又止的古典詞語含蓄空間,又有直擊心靈短促快捷的現代思想銳度,細膩與開闊融會,婉約和鋒利共存,從容攜深摯并行;而暗示、轉喻、通感等多種手段的運用,也讓菁菁的詩歌有了某種縱深程度的執著。雷子的組詩《沉入海底》應該說是詩人腳踏遼西大地朝向遙遠的一次精神漫游,令我們感受到她內心承載痛苦的寬容與豪氣,生命的滯重感豁然撲面。村莊、河流,成為詩人的精神投影;父輩、童年,深化詩人的精神履歷。“把所有的熟悉走成陌生/——這就是幸福。自由。”故鄉深秋十一月的季節背景,冷色調的客觀物象與內心的情感溫度吻合,但是它們并沒有遮蔽詩人內心向往的熾熱,抒情背后隱含的悲涼與靈魂的自由舞步且緩且急,忽明忽滅。矛盾符合內心的真實,慘烈唱出生命的高音。雷子創造的詩境凝聚遼西的水土遼西的風情,每一朵花都開得不平凡,每一棵苗都長得很艱苦;朝露更多的時候是淚水,晚霞更近的時候是血衣。雷子消亡這一個自己,再生另一個自己,內心釋放的痛苦醇厚而濃重,從遼西一躍而出,定格為女性直面生活的寶貴閱歷。
李見心的《十枝百合》是一個女人的心路歷程,既為情感的數度宣泄,又為生命隱秘的逐層袒露,內心的不可重合性預演著生命風情萬種的可能性。思想穿越,精神高蹈,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互為轉化的抒情敘述,讓生命成色接近于爐火純青。欲望、夢囈、謊言、死亡、記憶、魅力、純潔、甜美等多重意象交織糾葛廝纏,讓愛情婚姻家庭社會充滿變數。這是當下生存的歷險記錄,是人性若干角落的曝光,是女性視角的一線經驗,顯然已超越地理局限輻射周邊世界。李見心的詩歌表達頗具“傷口性”,像刮骨療毒,像岳母刺字,毀滅的同時宣告新生,疼痛的須臾昭示理想,悲劇性的敘述風范令人肝腸寸斷。離原的《一個理想主義者》這組個人主義視角內的遼西生活速寫,摒棄沉重、刻意、委婉的文字風格,讓抒情暫退其后,以口語敘述為主角,讓輕松、歡快、滿足的情緒占領詩人表述的畫面,仿佛是不經意,仿佛是信天游,精致而小巧,具象而生動,以田園之美之樂之和諧為遼西生存辟出另一番景象。但是,總覺得這是作者的人為故意,表面的逃遁,實際的曲筆,精神的階段性勝利掩蓋的正是難以下咽的疼痛與傷痕,社會的某些不端必然是詩人心中塊壘。從《一只母雞產了一枚蛋》《幸運的蟲子》等詩中,我們覺察到了詩人的內心脈動,用它們來參照人的生活,不知是人的悲哀還是人的幸福?透過詩人的溫馨場景,“十年九旱”“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自然主義生態的確在遼西有著根深蒂固的傳承,這也是局囿發展的傳統觀念,或許詩人自覺無力改變而把深深的遺憾和酸楚隱藏在文字背后。人在極度痛苦的時候不是號啕大哭而是無奈微笑,離原的樂觀書寫讓詩歌意義的解讀有必要朝深水區拓展。
王文軍的鄉土詩歌擔當著遼西地域文化的更多內容。《凌河的午后》直接把家鄉的一條河流作為組詩的題目,讀來如在現場,以泥土般的親切、樸素和真誠來完成自己的精神還鄉之旅。《太陽往上升》的驚詫自責,《當我在河邊散步》的復位融入,《回鄉偶記》的追溯懷想,《山村墓地》的感觸頓悟,都讓生命的存在有著確鑿的發祥地。雖然詩人長期工作在鄉鎮,身處遼西,但靈魂與肉體的現實矛盾不可能不在自己的作品中顯現,所謂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說到底還是“隔”,貼近也有距離感。詩人需要做的,即是用鄉音、血脈、祖上的印記,來填補后工業時代物質化給人格給人性給生命帶來的裂痕。王文軍的詩不晦澀,不高深,有時簡單的一句話,便蘊含人生大哲學。即使是遼西人的普通日子,也往往存有這種智慧。現實在古典的韻致里,多了一份含蓄和內斂。楊慶華的《春天里》,無疑是書齋化寫作的遼西版本。唐詩宋詞的營養學盡管無人計量,可是對后人的巨大影響不可言說,特別是在西方現代詩的表現力度逐年趨緩時,能從傳統的國學中“縱向”繼承,其實比“橫向”移植還要艱難。所以說楊慶華詩中的那份典雅、舒緩、柔軟、神韻來之不易,這是詩人內心生活的無數次感動而成,是詩意棲居的文字體現。江河澎湃是氣象,小橋流水也是風韻,生命存在并非一兩個或幾個模式,遠離現世塵囂保持恬靜心態,此處無聲勝有聲。詩人的文字氣質猶如遼西的土地,不以高粱玉米自居,能長出一片茂密的稻菽,也是人生的盛宴。
只要是心靈的必然源于土地。八位遼西詩人的作品,像八棵樹上的累累果實,結實飽滿,折射太陽光芒,散發著陣陣誘人的芳香。
2013年11月28日于沈陽北陵

唐果

艾泥

王單單

艾傈木諾

尹馬

張翔武

胡正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