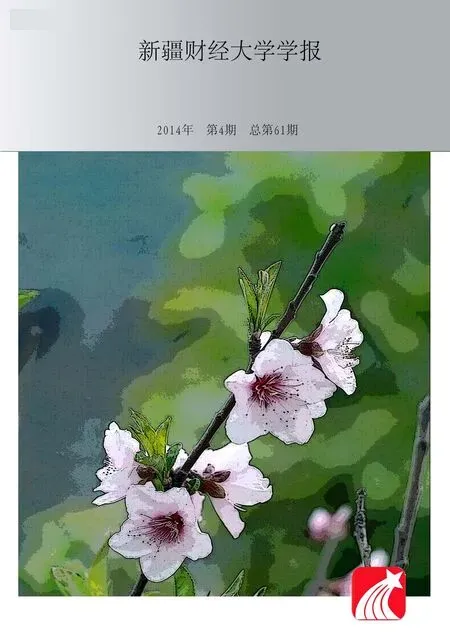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綢之路文化的變遷及啟示
粟迎春
(新疆財經(jīng)大學(xué),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一、歐亞草原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在北緯50度附近有一條“歐亞草原路”,它東起蒙古高原而西至黑海沿岸,是橫貫歐亞北方草原地帶的一條古代交通路線。古希臘著名歷史學(xué)家希羅多德在其巨著《歷史》中,曾對這條道路的方位、經(jīng)過的地區(qū)以及這條路線上的貿(mào)易活動進(jìn)行過描述。他認(rèn)為,約在公元前5世紀(jì),黑海周圍是游牧的斯奇提亞人(斯基泰人)的勢力范圍,黑海沿岸也有不少希臘商人的集居點(diǎn)。他們經(jīng)游牧人斯基泰人而與東方有著貿(mào)易關(guān)系。[注]參見希羅多德著、王嘉雋譯《歷史》(第4卷),商務(wù)印書館1959年版,第439頁。經(jīng)過多年的探討和研究,中外學(xué)者對希羅多德的觀點(diǎn)不少已趨一致。戴禾、張英莉在《先漢時期的歐亞草原絲路》[注]參見張志堯著《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9~21頁。一文中通過大量史料闡明,早在公元前6世紀(jì)至4世紀(jì),中國絲織品就見于南亞(印度)、西亞(古波斯)和東北亞(蘇聯(lián)阿爾泰等地),并且還傳到了遙遠(yuǎn)的歐洲。
在法國人L·布爾努瓦所著的《絲綢之路》一書中,有一段頗具文學(xué)色彩的描述:公元前53年,當(dāng)時的羅馬“三頭政治”之一的執(zhí)政官和敘利亞總督克拉蘇率軍東征,與安息人(波斯人)的軍隊進(jìn)行了一場非常激烈的戰(zhàn)斗。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時候,于正午時分,安息人在陣前突然展開他們鮮艷奪目、令人眼花繚亂的軍旗。由于這些軍旗耀眼刺目,竟使羅馬軍團(tuán)大受驚嚇,最終導(dǎo)致大潰敗。那些在這次戰(zhàn)役中讓羅馬軍團(tuán)眼花繚亂的、繡金的、色彩斑斕的軍旗,歷史學(xué)家弗羅魯斯認(rèn)為就是羅馬人前所未見的絲綢織物。數(shù)年之后,絲綢在羅馬成為最時髦的服裝用料。對于羅馬人來說,這種來自世界之端的異國織品是令人驚奇的高級奢侈品。絲綢成為西方認(rèn)識古代中國的窗口,成為東西方世界溝通的最初媒介,而遠(yuǎn)古時期中國絲綢輸入西方的主要路徑就是歐亞草原絲綢之路。
人類在各個地域產(chǎn)生的物質(zhì)文明,不是長期囿于孤立、封閉狀態(tài),而總是向外尋求聯(lián)系,并在相互交往中得以發(fā)展。草原絲綢之路從本意上看是指一條連接?xùn)|西方貿(mào)易的交通要道,但商品交換的附加效應(yīng)勢必是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草原絲綢之路正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與橋梁。2002年在古城西安舉行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國際研討會上,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李水城教授指出:“許多人把公元前138年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后絲綢之路的開通作為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起點(diǎn)。在官方交流正式確立前,東西方文明之間的民間交流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經(jīng)存在了。”[注]參見馮國、李勇、張澤遠(yuǎn)著《東西方文明交流新發(fā)現(xiàn) 早于絲綢之路開通前3000年》,原載于新華網(wǎng),2002年12月16日。李水城教授以權(quán)杖為例說明東西器具間的“相似”很可能是外來文化因子與本地文化接觸后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現(xiàn)。現(xiàn)在歐亞各國博物館中游牧民族出土器物具有的高度一致性,也說明了這條通道在早期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價值。
二、金山銀水:草原民族文化的搖籃
歐亞草原通道的形成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環(huán)境考古學(xué)資料表明,在北緯40度~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qū),有一條東起蒙古高原,向西經(jīng)過南西伯利亞和中亞北部進(jìn)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達(dá)喀爾巴阡山脈的狹長草原地帶,這里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勢比較平坦,生態(tài)環(huán)境比較一致,適宜游牧民族或部族的生活。[注]參見張景明著《草原絲綢之路與草原文化》,原載于《光明日報》2007年1月26日版。這條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連接中亞和東歐,向東南可以通往中國的中原地區(qū)。北方游牧文明與中原農(nóng)耕文明的經(jīng)濟(jì)互補(bǔ)、相依相生的關(guān)系,成為維系草原絲綢之路的基礎(chǔ)條件。幾十年來的諸多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表明,早在青銅時代,這條通道就已經(jīng)是許多游牧民族或部族往來于東西方之間游牧地的必經(jīng)之路。
在亞歐草原通道中開發(fā)最早的,是由漠北大草原經(jīng)由阿爾泰山向西延伸的路線。它位于蒙古高原、阿爾泰山和天山山脈組成的亞洲草原東段,其中阿爾泰山享有“黃金之路”的美譽(yù)。哈德斯在《中國阿爾泰古代草原絲路》一文中,根據(jù)文獻(xiàn)記載和本人的實(shí)地調(diào)查,對阿勒泰草原絲綢之路各路段(干線)進(jìn)行了頗為詳細(xì)的介紹。[注]參見哈德斯著《中國阿爾泰古代絲綢之路》,原載于《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發(fā)源于阿爾泰山的額爾齊斯河和烏倫古河一路奔流,滋潤著阿勒泰地區(qū)的土地,它們流經(jīng)的地區(qū)被稱為“阿爾泰山脈南麓的兩河流域”。 “金山”和“銀水”分別代表阿爾泰山和額爾齊斯河。“阿爾泰”在蒙古語中意為“黃金”,“額爾齊斯”在突厥語中意為“水流湍急”。獨(dú)特的地理地貌塑造著阿勒泰地區(qū)獨(dú)特的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這里水草豐美,自然條件優(yōu)越,是許多古代游牧民族的發(fā)祥地。
新疆文物考古所專家張平曾經(jīng)考察過這條草原通道,他認(rèn)為地處亞歐草原通道東段的阿勒泰地區(qū)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資源以及歷史文化等因素,自古以來就是草原居民遷徙、角逐、逗留的歷史大舞臺,被稱作草原民族文化的搖籃,蘊(yùn)含著豐富的巖畫、鹿石、墓地石人、石堆墓、石圍墓、石棺墓等古代文化遺跡。[注]參見張平著《大漠讓我們與世界相連——草原絲綢之路 傾聽亞歐草原通道的駝鈴》,原載于《中國國家地理》2007年第10期。生發(fā)在這里的文化,雖然形態(tài)各異,但都以草原為共同載體,并以此為基礎(chǔ)建立起內(nèi)在的聯(lián)系與統(tǒng)一性。生活繁衍在這片土地上的游牧民族是傳承東西方文明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是新疆阿爾泰草原文化的主要締造者,對開通和繁榮草原絲綢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
大量史實(shí)表明,公元前2世紀(jì)以前中國內(nèi)地與中亞以及歐洲之間的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是通過秦國,尤其是趙國與月支等西北游牧民族而建立的。新疆北部的阿爾泰山和額爾齊斯河上游地區(qū)的古代居民在這種東西文化交流關(guān)系中曾起過樞紐作用。[注]參見馬雍、王炳華著《阿爾泰與歐亞草原絲綢之路》,原載于《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9~21頁。從公元前7世紀(jì)起,這條草原之路的脈搏,隨著強(qiáng)有力的游牧民族的變換而搏動。首先是君臨西亞的斯基泰人,然后是公元前3世紀(jì)雄據(jù)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后來出現(xiàn)于蒙古高原的鮮卑、蠕蠕(柔然)、嚈噠、突厥、回鶻、蒙古族等相繼稱霸于草原路上,并據(jù)此同東西文化圈進(jìn)行貿(mào)易和文化交流。季羨林先生說:“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jìn)的重要動力之一。”[注]參見季羨林著《<中外文化交流史叢書>序》,原載于《中外美術(shù)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絲綢之路沉淀著的不僅僅是一種文化,更多的是當(dāng)時社會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絲綢之路的開辟和發(fā)展為古代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它從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方面,影響和推動了沿線各地社會歷史的發(fā)展,進(jìn)而也加速了人類文明的進(jìn)程。
三、碰撞與融合: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路文化的發(fā)展
(一)商貿(mào)往來與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路文化的發(fā)展
如前所述,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路文化的發(fā)展首先得益于歐亞草原通道上的商貿(mào)往來。貿(mào)易是人類自然產(chǎn)生的交換行為,交通則是完成貿(mào)易的一種重要工具。由于居住環(huán)境的不同,物產(chǎn)與運(yùn)用物產(chǎn)的智慧也不同。人類的貿(mào)易行為在歐亞草原通道上透過村落與村落、區(qū)域與區(qū)域之間的相互交換而形成。活躍在歐亞草原絲綢之路上信仰各種宗教的胡人,是東西方貿(mào)易及交流的承擔(dān)者。塞種民族最早開辟了亞歐大陸的草原絲綢之路。他們從中原獲取絲綢,然后通過互市貿(mào)易,賣給前往西方的商人,并從商人手中獲得西方的金銀、陶器、谷物等生活所需。在遠(yuǎn)古時期,絲綢被輾轉(zhuǎn)傳播到四方。然而,雛形期的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馳騁往來于這條通道上的民族紛爭與遷徙,常常阻滯道路的通行。所以,當(dāng)時的東西方之間并沒有深刻的了解,文化上的交流基本處于相互隔絕的狀態(tài)。為了使農(nóng)業(yè)生活不受游牧民族侵?jǐn)_,以絲綢換取馬匹成為漢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于是,在政府的積極管控下,原本或許是區(qū)域與區(qū)域的區(qū)塊貿(mào)易逐漸成為一條穩(wěn)固綿長的交通路線。
(二)王朝興衰與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路文化的發(fā)展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向西方的道路,使得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一直到歐洲的貿(mào)易往來真正建立起來。由此實(shí)現(xiàn)了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綢之路上文化的第一次大跨越——由原始文化進(jìn)入了真正意義上的絲綢文化。
(2)采用活性炭進(jìn)行脫色處理。活性炭吸附被視為最經(jīng)濟(jì)實(shí)用的脫色去雜方法,經(jīng)過反復(fù)試驗,不同類型的活性炭均不能吸附雙乙烯酮中的有色物質(zhì),初步判定雙乙烯酮中的有色物質(zhì)和雙乙烯酮的性質(zhì)極為相似,活性炭對其不具選擇吸附性。因此,該方法并不適用于雙乙烯酮分析的預(yù)處理。
自秦統(tǒng)一六國(公元前221年)至北宋建立(公元960年)的千余年,秦、漢(西漢)、隋、唐諸政權(quán)均建都于西北關(guān)中的長安(今陜西西安),以漢族(即先秦時華夏族)為主體的傳統(tǒng)文化,藉其政治勢力向四周輻射。中央王朝的興衰與草原絲路文化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凡中央王朝強(qiáng)盛之時,亦是草原絲綢之路興盛暢通、草原絲路文化繁榮發(fā)展之時;反之,中央王朝分裂割據(jù)之時,也是絲綢之路相對荒蕪沉寂、絲路文化衰敗蕭條時期。
漢朝采取了一系列增強(qiáng)漢朝與西域聯(lián)系的措施,如漢代的和親、通關(guān)市,鼓勵漢朝人到西域經(jīng)商,推動了草原絲綢之路的開辟;此外還建立了西域都護(hù)府,南匈奴歸漢,北匈奴敗走金山,解除了匈奴對漢朝及西域城國的威脅,打通了前往西方的道路,保證了來往商人與使節(jié)的安全,從而鞏固了草原絲綢之路的地位。西行道路上的駝鈴聲此起彼伏,不同文明之間的人員往來日益頻繁,商品的交換空前繁榮。“在烏孫國同漢朝聯(lián)姻時,設(shè)‘譯官’等官職,烏孫昆莫向漢武帝贈送樂器,出嫁烏孫國的細(xì)君公主作類似哈薩克民歌的歌謠,[注]《細(xì)君公主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yuǎn)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nèi)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xiāng)。”漢朝公主向其夫‘學(xué)烏孫言’等歷史史實(shí),均反映了當(dāng)時的文化交流是何等的密切頻繁。”[注]參見賈合甫·米爾扎汗著、薩恒·松哈泰所譯的《哈薩克草原絲路及其經(jīng)濟(jì)文化》,原載于《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頁。
唐朝貞觀年間,當(dāng)時的統(tǒng)治者借擊破突厥的時機(jī),一舉控制西域各國,并設(shè)立安西四鎮(zhèn)作為控制西域的機(jī)構(gòu)。唐朝還設(shè)立北庭大都護(hù)府,轄天山以北諸部,結(jié)束了分裂割據(jù)的局面,為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通及振興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商貿(mào)基礎(chǔ)。唐朝與回紇的絹馬貿(mào)易與和親使草原絲綢之路達(dá)到鼎盛階段。而此時的絲綢之路所傳播的文化已不僅僅是絲綢文化了,絲綢之路促進(jìn)了中國自漢代至唐代的文化開放政策的形成。受波斯文化影響的粟特人給唐朝的一些都市帶來一種開放的胡風(fēng);來自中原的唐朝旅行家、使節(jié)、學(xué)人、僧人在游記中較詳細(xì)地介紹了哈薩克等西域民族的情況,為我們今天研究哈薩克等游牧民族的歷史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世紀(jì)著名學(xué)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馬赫穆德·喀什噶里等文化名人就是這時代所產(chǎn)生的。[注]參見賈合甫·米爾扎汗著、薩恒·松哈泰所譯的《哈薩克草原絲路及其經(jīng)濟(jì)文化》,原載于《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頁。
安史之亂之后,唐朝國力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jìn),侵占了西域的大部,絲綢之路上失去了往日熙來攘往的人群商隊和川流不息的馬匹車輛。公元10世紀(jì)中葉以后,中國經(jīng)濟(jì)、文化重心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草原絲綢之路逐漸衰落,草原絲路文化漸趨沉寂。
蒙元時期,以上都(今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lán)旗金蓮川)、大都(今北京)為中心,設(shè)置了帖里干、木憐、納憐3條主要驛路,構(gòu)筑了連通漠北至西伯利亞、西經(jīng)中亞達(dá)歐洲、東抵東北、南通中原的發(fā)達(dá)的交通網(wǎng)絡(luò)。東西絲路又復(fù)建立,歐洲、阿拉伯、波斯、中亞的商人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往來中國,商隊不絕于途。清代初期,準(zhǔn)噶爾、哈薩克與清政府的絹馬貿(mào)易仍在進(jìn)行。清代后期,隨著西北疆域中巴爾喀什湖以南、以東,齋桑泊以東與帕米爾等大片國土淪于沙俄之手,加之推行閉關(guān)鎖國政策,這條重要的陸上通道最終走向了蕭條。
(三)民族遷徙與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路文化的發(fā)展
中國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區(qū)。自青銅時代起,在草原絲綢之路上活動的族群先后有卡拉蘇克、斯基泰、狄、匈奴、鮮卑、突厥、回鶻、契丹、蒙古等,他們世代“逐水草而居”。特殊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生產(chǎn)方式,使得游牧民族遷徙最為劇烈、持久,而與農(nóng)業(yè)社會的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也最早、最主動。在與中原漢族長期的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中,草原游牧民族汲取了先進(jìn)的社會文明,促進(jìn)了自身的發(fā)展。以絲綢之路草原路為渠道和橋梁,從公元初南匈奴“內(nèi)附”,到公元13世紀(jì)以后蒙古族和契丹、女真、滿族等陸續(xù)入主中原,民族融合與民族文化發(fā)展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他們與中原漢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了豐富多元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從而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草原民族通過民族遷徙和同農(nóng)業(yè)社會的經(jīng)濟(jì)交流,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dāng)了絲路貿(mào)易的中介民族,對開通和繁榮草原絲綢之路作出了很大貢獻(xiàn)。在中國歷史上每當(dāng)出現(xiàn)統(tǒng)一和強(qiáng)盛的王朝時,北方草原上就會隨即誕生一個強(qiáng)大的游牧帝國,如漢朝與匈奴、唐朝與突厥、宋朝與蒙古、明朝與女真。這些強(qiáng)大起來的民族勢力先后控制北方草原地區(qū),將原先緊緊依靠中原地區(qū)農(nóng)耕經(jīng)濟(jì)而生的民族趕離他們的家園。游牧民族的經(jīng)濟(jì)是不穩(wěn)定的,當(dāng)遭遇內(nèi)困和外來打擊、其勢力逐漸衰退之時,必然另尋適合自己生存的空間。北方草原地區(qū)的東、南、北部都不適宜游牧民族生活,只有沿草原絲綢之路的通道向西遷徙。匈奴、回紇、契丹等民族均屬于這種情況。[注]參見張景明著《草原絲綢之路與草原文化》,原載于《光明日報》2007年1月26日版。匈奴西遷、突厥西遷、契丹耶律大石西遷并建立西遼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率蒙古大軍西征,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政治版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遠(yuǎn)影響。
從秦漢至隋唐,在漠北地區(qū)先后有強(qiáng)大的游牧民族建立政權(quán),與內(nèi)地政權(quán)相抗衡。自匈奴之后,漠北興起的鮮卑、柔然、突厥、回鶻等均不同程度地統(tǒng)治過新疆地區(qū)。他們帶有崇拜山川、日月、河流及英雄祖先的原始薩滿教之游牧文化,不僅影響了內(nèi)地漢族傳統(tǒng)文化,而且對新疆草原游牧民族多元文化的產(chǎn)生影響深遠(yuǎn)。[注]參見周偉洲著《古代西北少數(shù)民族多元文化的發(fā)展與變異》,原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第3期。如西遷的回鶻諸族與新疆當(dāng)?shù)孛褡逯饾u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的維吾爾族。突厥、回鶻各族均系操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之游牧民族,他們與原新疆諸族經(jīng)過長期的交融,逐漸形成了新的新疆少數(shù)民族多元文化。
12世紀(jì),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征,建立了強(qiáng)大的西遼政權(quán),統(tǒng)治中亞近百年。西遼立國中亞后,與占據(jù)東歐的東斯拉夫人及北宋王朝均保持密切聯(lián)系,通使和貿(mào)易十分活躍。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歐陽修、蘇轍、包拯等,都曾出使遼國。西遼王朝施行比較寬容的文化政策,以儒家思想為指導(dǎo),對人民“輕搖薄賦”,對屬國屬部“柔遠(yuǎn)懷來,羈縻安撫”,對宗教信仰“循俗寬容”,形成漢、唐之后漢文化向中亞傳播的又一個新浪潮、新高峰,促進(jìn)了社會的安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
13世紀(jì),興起于漠北蒙古草原的蒙古族西征和南下,對北方草原地區(qū)的政治形勢和民族分布格局影響巨大。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騎兵,沿著草原絲路橫掃歐亞大陸,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從而使得草原絲綢之路的南道和北道,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四川、云貴通向南亞的道路,以及中國東南沿海與波斯灣、地中海及非洲東海岸的海洋絲綢之路聯(lián)系起來,東西方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又一次進(jìn)入繁榮發(fā)展階段。蒙古西征的結(jié)果之一就是中亞、波斯等地信仰伊斯蘭教的軍士、工匠、商人等大量遷入中國西北各地,伊斯蘭教及其文化影響深遠(yuǎn)。早已突厥化了的蒙古貴族統(tǒng)治者,大力推行伊斯蘭教,使該地區(qū)原有佛教文化特征的各族文化發(fā)生了第二次大的變異。今天,新疆阿勒泰地區(qū)主要少數(shù)民族如哈薩克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維吾爾族等均與上述古代民族有直接的淵源關(guān)系。這一區(qū)域的文化內(nèi)涵,既包含著其先民在絲綢之路上的固有文化特征,又凝聚著他們與中原漢族和其他民族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的結(jié)晶。
絲綢之路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文化系統(tǒng),并非一般人誤解的一條商路。它的交通是覆蓋某個區(qū)域社會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的交流渠道,在這個環(huán)境里,各民族的活動造就了其交流的方式,從而也造就了自身民族歷史文化的特色。
(四)城鎮(zhèn)分布與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綢之路文化的發(fā)展
草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換的興旺,往往與草原上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關(guān)系。草原絲綢之路各段路的選擇、形成,與各個地理單元內(nèi)的山川形勢、聚落城鎮(zhèn)的分布有關(guān)。古代草原絲綢之路沿線的城市,如烏孫國的赤谷城,漢代蒲類國、蒲類城(今巴里坤境內(nèi)),突厥汗國、突騎施汗國時期的別失八里、輪臺(今烏魯木齊附近)、伊犁阿力麻里(弓月城)、博爾塔拉境內(nèi)的伊克烏格孜(雙河城)等古城,與當(dāng)時中亞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境內(nèi)的碎葉、怛羅斯、伊斯菲加普、塔勒格孜、石國(今塔什干)、海亞里等古城連成一線,既是當(dāng)時草原絲綢之路的集散地,也是當(dāng)?shù)氐恼巍⑸虡I(yè)和文化中心。[注]參見賈合甫·米爾扎汗著、薩恒·松哈泰譯《哈薩克草原絲路及其經(jīng)濟(jì)文化》,原載于《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頁、87頁。
阿爾泰的古代游牧部落葛邏祿、克馬克人于公元8世紀(jì)至10世紀(jì)分別建立了葛邏祿汗國和克馬克汗國,他們在塔拉斯河與楚河及額爾齊斯河畔興建了許多新的城市,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了阿爾泰與中原、中亞絲綢經(jīng)濟(jì)的密切聯(lián)系。在克馬克汗國的城市中有專門進(jìn)行商品貿(mào)易的巴扎,還有不少學(xué)習(xí)伊斯蘭教的經(jīng)文學(xué)校。伊斯蘭教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中亞及哈薩克草原后,各突厥語民族逐漸放棄了原有的古突厥文和回鶻文,開始使用阿拉伯文,中亞各國同阿拉伯、波斯等東方大國的文化、經(jīng)濟(jì)、政治往來更加密切。遼代和元代時期形成了幾個“國際都市”。遼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寧路等皆為當(dāng)時世界上有名的城市,各國使者、商賈云集于此。西遼建都于今新疆額敏縣境內(nèi)的葉密里。公元1130年后,契丹人征服中亞及哈薩克大部分地區(qū)后,在楚河流域的巴拉薩袞附近建立新的都城,稱虎思斡耳朵。契丹人在征服中亞及哈薩克時,沒有破壞城市和農(nóng)田,相反他們在這些地區(qū)建立了許多新城市。契丹統(tǒng)治者在這些城市里修建了宮殿、佛寺等。這些建筑以中原地區(qū)的建筑風(fēng)格和圖案繪畫為裝飾。[注]參見賈合甫·米爾扎汗著、薩恒·松哈泰譯《哈薩克草原絲路及其經(jīng)濟(jì)文化》,原載于《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頁、87頁。
自漢唐以來,草原絲綢之路上以絲綢、茶葉及畜產(chǎn)羊馬為主的大型綜合貿(mào)易——絹馬貿(mào)易在邊疆民族地區(qū)以固定的形式進(jìn)行著。從事絹馬貿(mào)易的主要民族有匈奴、突厥、回紇、吐蕃、蒙古(包括西蒙古瓦剌部、漠北蒙古)、吐谷渾、西夏、哈薩克等。絹馬互市有固定的互市地點(diǎn),它們都是這一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明清時期茶馬司所在的烏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臺、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地位更為顯著。北方游牧民族依靠絲綢之路貿(mào)易網(wǎng)絡(luò)和封建社會的商品交換機(jī)制與中原漢族交流,形成了農(nóng)業(yè)文明社會和草原游牧社會經(jīng)濟(jì)互利互補(bǔ)的模式。
絲綢之路沿線的城鎮(zhèn)是絲路行旅的依托,為絲路的暢通與秩序安定提供安全保障。絲綢之路自身的發(fā)展,也會大大影響所經(jīng)地區(qū)的人文發(fā)展和環(huán)境變遷。在草原絲綢之路沿線,形成了許多著名的城鎮(zhèn)。直到今天,它們中的大多數(shù)也還是絲綢之路旅游的名勝。
草原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亞歐大陸的貿(mào)易聯(lián)結(jié)者,更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薈萃之地。不同文明傳來的新鮮養(yǎng)分,孕育著新的文化。漢族傳統(tǒng)文化、中亞及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相互滲透、浸潤,促進(jìn)了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綢之路文化的變遷與發(fā)展。這條世界之路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貿(mào)易,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匯集、宗教的傳播、文化的碰撞、民族的融合與經(jīng)濟(jì)社會的發(fā)展。
四、距離與時空的跨越:環(huán)阿勒泰草原絲路文化變遷的啟示
(一)多元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是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精神動力
草原絲綢之路自古以來就是聯(lián)結(jié)中原文明、草原文明、中亞文明、西亞文明、歐洲文明的紐帶。“黃金之路”阿勒泰是草原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碰撞不僅影響了不同文化、區(qū)域和國家的發(fā)展變化,而且也對整個社會的變遷發(fā)展產(chǎn)生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從文化層面來分析區(qū)域經(jīng)濟(jì),其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文化的碰撞、溝通、交融及在此基礎(chǔ)上的整合,這也是推動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精神動力。今天,在著手進(jìn)行區(qū)域經(jīng)濟(jì)開發(fā)建設(shè)時,必須對該區(qū)域的歷史文化資源進(jìn)行認(rèn)真調(diào)查、挖掘,充分考量區(qū)域內(nèi)并存的多元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通過積極有效的引導(dǎo),將多元文化整合成為能夠?qū)^(qū)域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推動作用的文化力。
(二)重視文化對經(jīng)濟(jì)社會的推動和引領(lǐng)作用
在以往時代,文化交流是作為商品交換的附加效應(yīng)而存在的。商業(yè)活動是東西方各民族交流的橋梁,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動力。它所承擔(dān)的媒介作用波及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領(lǐng)域,東西方之間物質(zhì)與精神文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商業(yè)活動這一媒介而進(jìn)行的。信息化時代,文化在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中的地位、作用乃至方式都發(fā)生了變化。以信息、科技等為代表的現(xiàn)代文化對經(jīng)濟(jì)社會的推動和引領(lǐng)作用越來越突出。人們用“人類文明的運(yùn)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動脈”來贊美和評價草原絲綢之路,這顯然包含了對北方古代各民族在絲綢之路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中的貢獻(xiàn)的評價和思考。它不僅涉及經(jīng)濟(jì)史問題,同時也涉及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和宗教史諸問題。如今的絲綢之路所承載的,已不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商品,人們在遙望過去的同時,更關(guān)注對文化變遷的考量,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對東西方文明再次對話與交流的渴望與設(shè)想。
(三)主動參與文化的交往與交流,推動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自古以來,我國北方游牧民族都努力從各方汲取藝術(shù)營養(yǎng)以豐富自身。草原絲綢之路除了傳輸絲綢外,文化的傳播、宗教的傳播、各類發(fā)明創(chuàng)造和技術(shù)的傳播,折射出草原游牧民族寬廣豁達(dá)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阿勒泰地區(qū)豐富的草原文化遺產(chǎn)就是這一偉大歷史進(jìn)程的見證。草原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發(fā)展,使阿勒泰地區(qū)與中原、中亞、西亞連接起來,成為開放的歷史文化區(qū)域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廣闊舞臺。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激烈競爭的今天,文化的交流已經(jīng)不受地域、民族的限制,超越了時空。任何民族的東西通過交往、交流而具有了世界性。主動推進(jìn)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文化更新的一條重要路徑。生活在信息化時代的各民族,應(yīng)有更為積極的交往意識,更加開放的、更加包容的交往心態(tài),主動參與文化交往與交流,推進(jìn)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現(xiàn)代化的新的起點(diǎn)上,我們需要從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實(shí)踐出發(fā),遵循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弘揚(yáng)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把握現(xiàn)代先進(jìn)文化的方向,著眼世界文化前沿,吸收中外文化之精華,不斷發(fā)展、創(chuàng)新,才能煥發(fā)出一個新興大國的軟實(shí)力優(yōu)勢。
文明交往是人類歷史變革和社會進(jìn)步的標(biāo)尺。人類社會歷史不僅僅是各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推動的物質(zhì)運(yùn)動過程,而且也是人類世代累積創(chuàng)造出來的、具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文明形態(tài)及其交往的序列。文明只有在交往之中才能更好地發(fā)展。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大通道,它代表著不同文明之間的無限聯(lián)系及其最大融合。華夏文明五千年的延續(xù)發(fā)展正是借助了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不同文明的交往。今天,這種規(guī)律依然發(fā)揮作用。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千百年來新疆一直充當(dāng)著各種文化交流平臺的角色,其本身就是一個經(jīng)濟(jì)文化的共融區(qū)域,蘊(yùn)藏著巨大的潛力。幾千年來一直是世界各大古代文明頻繁接觸、相互滲透的地區(qū),它們的交融或排斥對這一地域里多元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同時也促進(jìn)了東西方文明各自的發(fā)展。這是一條和平和希望的捷徑,和平和希望的新的絲綢之路。在經(jīng)濟(jì)文化的意義上,新疆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一座橋。[注]參見戴維·戈塞特著《新疆經(jīng)驗與絲綢之路的復(fù)興》,原載于《參考消息》2006年5月31日版。絲綢之路經(jīng)濟(jì)帶,一頭連著繁榮的東亞經(jīng)濟(jì)圈,另一頭系著發(fā)達(dá)的歐洲經(jīng)濟(jì)圈。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與外界的交流。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dāng)今,絲綢之路都是中外文明交往永遠(yuǎn)的通道。
參考文獻(xiàn):
[1]希羅多德.歷史[M].王嘉雋,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9.
[2]張志堯.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M].烏魯木齊: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4.
[3]張平.大漠讓我們與世界相連——草原絲綢之路 傾聽亞歐草原通道的駝鈴[J].中國國家地理,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