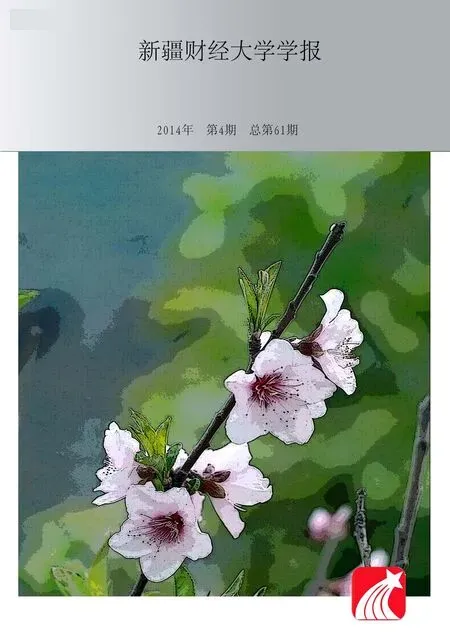抵御境外宗教極端思想滲透與新疆意識形態安全建設
魏 昀
(新疆財經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亞伊斯蘭復興思潮的盛行,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在我國境內特別是新疆地區進行滲透傳播,對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特別是對新疆意識形態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如何有效抵御境外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加強新疆意識形態安全建設,促進新疆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維護祖國統一,已成為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現實而緊迫的課題。
一、抵御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對新疆穩定的危害影響及對策研究對學者而言是一個特殊、重要的問題。特殊性在于,宗教極端主義思想進入新疆后,即與新疆的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合流為“三股勢力”,致使新疆的分裂與反分裂、滲透與反滲透、暴恐與反暴恐斗爭更加尖銳、復雜,有時甚至是相當激烈的;重要性在于,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對新疆的影響廣泛而深入,不但給國家安全帶來威脅,更給新疆的長治久安帶來現實危害,成為當前影響新疆社會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已對一些少數民族群眾造成影響,而且其傳播方式越來越隱蔽。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傳播、危害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誰?來自哪里?對于這些問題如果了解不夠深入,就會造成在打擊措施上無處發力。因此,研究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對新疆穩定的危害和影響具有較高的理論和學術價值。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同時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近年來,新疆周邊安全形勢再趨緊張,主要表現為伊斯蘭極端勢力的生存空間擴大,恐怖事件呈小規模多頻率發展,尤其是宗教極端組織“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以下簡稱“烏伊運”)在阿富汗北部的勢力很大,其“新生代”主張“重返中亞”呼聲高漲,整個組織重返中亞跡象明顯。從目前的情況看,“烏伊運”重返中亞的條件日漸成熟, 如此必會危及新疆地區的穩定。這是因為,中亞是“烏伊運”組織的老巢,又有“伊斯蘭圣戰聯盟”分支力量和眾多秘密聯絡點,“烏伊運”組織重返中亞后,勢必會引發伊斯蘭極端勢力開展報復行動,發動針對政府、軍隊、情報機構和民眾的報復性恐怖襲擊。由此,以“烏伊運”組織為首的宗教極端勢力的報復行動不但會對中亞構成危害,也會對新疆“三股勢力”尤其是宗教極端團伙“伊吉拉特”產生示范效應,刺激新疆暴恐分子出境或在境內開展“遷徙圣戰”活動,從而破壞新疆的社會政治穩定。因此,新疆周邊宗教極端勢力仍是當前影響其非傳統安全的最重要因素。隨著新疆周邊宗教極端勢力問題的復雜化和普遍化,對它的系統研究更加迫切。然而,新疆的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組織、團伙大都來自于境外而作亂于境內,并與周邊的宗教極端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研究這一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研究成果可為有關部門制定相應政策與對策提供參考,從而為中國國家利益和新疆的社會政治安定提供服務。
二、國內外學術界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研究簡述
(一)國外學術界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研究簡述
國外學術界對于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的研究相對較少,針對新疆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的研究幾乎沒有。國外學術界對宗教極端主義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宗教極端勢力產生的歷史淵源、發展過程,以及對本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影響;二是打擊遏制宗教極端勢力的路徑。
國外涉及宗教極端主義問題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有:彼得·曼達威爾[1]在《跨國穆斯林政治》一書中認為,在當今的英國最激進的極端組織是“解放黨”,其在英國傳播極端思想,號召建立伊斯蘭國家。由于其崇尚“圣戰”,因而英國的一些城市如倫敦等可能會成為宗教極端思想的樞紐地。
《伊斯蘭解放黨:伊斯蘭的政治叛亂》是美國尼克松中心對伊斯蘭解放黨進行的一項專題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伊斯蘭解放黨傳播宗教極端思想在數十個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引發了意識形態之戰,成為恐怖主義傳播的載體,并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中亞宗教極端主義——問題與前景》[注]參見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戰略研究所2002年6月在塔什干召開的中亞宗教極端勢力問題研討會相關論文集。一書對宗教極端主義的歷史發展、在中亞的現狀以及如何有效遏制與打擊宗教極端主義等問題進行了闡釋。書中強調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要正確引導青年一代,以避免青年人受極端宗教思想的蠱惑而走向激進;還提出民主與法制建設、社會經濟的良好發展是打擊極端宗教主義的有效途徑。
(二)國內學術界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研究簡述
概括地說,由于與新疆毗鄰的中亞伊斯蘭國家的社會政治穩定對新疆影響度很大,因此國內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重點在“三股勢力”的危害,特別是宗教極端勢力對新疆穩定的負面影響方面見多,且大多為一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和社科項目課題,而以宗教極端主義作為專門研究對象獨立于“三股勢力”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學術成果較少。
目前,國內涉及宗教極端主義問題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有:金宜久[2]在《當代宗教與極端主義》一書中對宗教極端主義進行了詳細論述,對伊斯蘭極端勢力在西亞北非、中亞、南亞等地區發展的歷史線索進行了詳細梳理;對宗教極端主義概念界定、形成的歷史原因、基本特征等進行了詳細論述與分析,并專門對宗教極端組織與極端勢力進行了論述。
許利平[3]在《亞洲極端勢力》一書中從全方位的角度闡述了伊斯蘭極端勢力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特點,并提出極端勢力與宗教和恐怖活動的結合、宗教極端主義的政治化發展趨勢會給國際社會帶來更大的動蕩與危害。
陸忠偉[4]在《非傳統安全論》一書中指出,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已與“東突”分裂勢力合為一體,對非傳統安全中的宗教極端主義的打擊治理需加大對宗教的依法管理,出臺系統的治理方案。
蘇暢[5]在《中亞宗教極端勢力研究》一書中指出,中亞宗教極端勢力與“東突”相勾結,對新疆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以及國家安全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中亞宗教極端組織“伊斯蘭解放黨”對新疆宗教極端組織“伊扎布特”的示范作用提醒我們,打擊宗教極端勢力要與國際社會進行有效合作,建立健全反恐機制。
三、境外宗教極端思想滲透對新疆意識形態安全的危害
(一)嚴重侵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削弱國家認同感和中華民族凝聚力
中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這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識。“國家認同不僅是個人最重要的集體認同,同時也是國家主權合法性的來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與準則,因此,國家認同也是社會行動的驅動力。”[注]參見樊紅敏著《國家認同建構中的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汶川地震后的啟示》,原載于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但是,境外敵對勢力卻積極向我國尤其是新疆輸入宗教極端思想以侵蝕民眾的思想意識,以期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
宗教極端勢力在我國境內進行非法傳教活動,加緊了對新疆社會各層面的滲透,以發展信徒,擴大影響,進而控制信教人群。他們歪曲新疆歷史,煽動狹隘民族情緒,鼓吹民族分裂,宣傳宗教極端意識。蘇東劇變之后,國際反華勢力和境內外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加緊了對新疆各級各類學校的反動宣傳,并通過郵寄和偷運反動書籍、報刊、音像制品,電臺廣播,國際互聯網和人員交往等,收買、策反我國師生,加緊對新疆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非法傳教組織利用一些學校講座講壇和學術沙龍等對學生宣傳宗教教義,混入校園向學生散發宗教宣傳資料。“他們利用舞會社會交友談戀愛等方式廣泛接觸各類學生,向他們免費贈送反動錄音帶和《古蘭經入門》等宗教書刊,在學生中發展教徒。”[注]參見馬大正著《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頁。分裂分子從事傳教活動時形式多樣,不拘泥于宗教規程,更注重思想意識上的滲透。作為一種宗教意識形態,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與發展給民族分裂勢力提供了思想基礎,削弱了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加劇了民族分裂勢力的囂張氣焰,對國家安全、少數民族公民身份、國家認同等造成了極大的現實威脅。
(二)對新疆的社會政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總部在巴基斯坦拉合爾的泛伊斯蘭組織“世界伊斯蘭宗教宣教協會”每年均派宣教人員來新疆布道宣教,其“臺比力克”(伊斯蘭評議會)組織已在我國新疆地區發展成員。新疆周邊國家的宗教極端組織運動成為影響我國邊境安定的極不確定因素。宗教極端勢力在我國境內鼓吹“信仰安拉第一”,鼓動群眾反對所謂的“異教徒”,挑起民族矛盾,煽動開展“圣戰”,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他們打著宗教的旗幟妄圖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宗教極端勢力在新疆建立了“東突伊斯蘭黨”、“東突伊斯蘭真主黨”等極端主義政黨以及一些恐怖主義團伙,形成組織化和互相勾結、跨地區聯合的趨勢;此外,與境外恐怖主義組織緊密勾結,接受“基地”組織的恐怖活動培訓,策劃、實施了一系列爆炸、暗殺、投毒、縱火等暴力恐怖活動,這些活動造成了無辜各族群眾的重大傷亡和財產損失,對新疆的社會政治安全構成直接威脅。
(三)制約新疆少數民族價值觀的現代轉型
境外敵對勢力妄圖利用宗教,通過喚起少數民族的宗教感情與狂熱,逐漸消解少數民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從而損害我國的文化安全。新疆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在歷史演變的長河中,宗教倫理道德已內化為其民族文化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逐漸演化為一種穩定的宗教心理。“這種心理屬性一旦形成便充當起宗教靈魂的角色,既主導著宗教文化本身的性質與演變,也塑造了宗教文化與其他文化的關系模式,推動或限制著對其他社會現象的作用。”[注]參見李利安著《宗教心理與社會和諧》,原載于《中國宗教》2007年第5期。由于伊斯蘭教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特征,加之長期受宗教的影響,信徒可能產生對其他不同文化的排斥心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對新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現代轉型起到的將不是一種積極促進的作用,而是一種深層次的制約作用。此外,西方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 與“三股勢力”的滲透與破壞,弱化了一些群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削弱了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陷入狹隘的本民族文化價值觀認同,這就制約了新疆少數民族價值觀的現代轉型,對我國社會意識形態建設也將帶來不利影響。
四、境外敵對勢力在新疆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的原因
(一)宗教自身的特點
從某種意義上講,宗教具有神秘色彩和權威性。現實生活中,一種外部力量一旦被超現實化,就具有某種神圣的意義,信徒的敬畏之心便會油然而生。同時,宗教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來世觀,信徒由于對來世報有強烈的憂慮感,因此對神靈頂禮膜拜,心懷敬畏,并不準異教徒對神靈不敬,從而建立起神靈的權威性。宗教的神圣性進一步表現為特殊的宗教氛圍,在神的名義下,無論是禮儀服飾還是教義教規,都被染上了神秘和神圣的色彩。
宗教還具有某種盲目狂熱追隨和敏感性。宗教信仰指人對“神圣”或“神圣者”的信仰,反映出人的靈性世界和精神生活,無法通過實踐去映證。由于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其具有鮮明的非理性色彩,也就使其成為信徒精神世界一個高度敏感的區域,如有人觸動它,信徒的宗教感情很容易被激發從而走向狂熱,最終導致群體性的非理性行為的出現。
此外還有宗教與民族交融的一致性。歷史上,對許多基本上全民族同一信仰的民族,宗教的教義教規都已與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融合在一起。千年的歷史傳承中,信徒對宗教信仰所產生的宗教情感已內化為本民族的共認的價值理念,并最終成為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同時,“宗教情感往往與民族情感交織滲透在一起,宗教成為民族自我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維系民族凝聚力的紐帶。”[注]參見王穎、秦裕華著《關于新疆民族文化認同與宗教認同》,原載于《新疆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現代社會中,當宗教作為一個民族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核心部分出現時,如果在宗教信仰問題上產生分歧和沖突,勢必會給社會安定造成不利影響。由于宗教與民族交融的一致性,廣大信徒有時會將他人對他們所信仰宗教的態度等同于對他們所屬民族的態度。
(二)跨國民族的同源性與宗教信仰的同一性相互交織的負面影響
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中亞與我國同源的幾個跨國民族建立了獨立國家,這對新疆的部分同源少數民族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特別是一些維吾爾族人在境外敵對勢力的蠱惑下企圖分裂中國妄圖在新疆建立獨立國家,這對新疆的穩定與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一些中亞國家獨立之后,“雙泛主義”、“三股勢力”十分活躍,給新疆的民族關系以及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國家間關系都帶來了消極影響。新疆有7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毗鄰新疆的8個國家有5個是伊斯蘭國家。新疆有6個少數民族是跨界民族,與新疆接壤的恰是他們的民族同源國,如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羅斯等。“就文化的傾向性而言,如果某一跨國民族的主體部分建立了主權國家,其分屬于不同國家的跨國民族往往會產生‘回歸’的欲望”,[注]參見蔣兆勇著《民族與外交交織的新疆問題》,http://dajun.com.cn,2003年10月24日。從而淡化對本國的國家認同。新疆部分少數民族群眾由于與中亞一些國家存在民族同源性和宗教信仰的同一性,使得他們在民族意識、民族感情、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生活習俗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認同性和相似性。境外敵對勢力把新疆少數民族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以及與毗鄰國的共同宗教信仰作為疏離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政治資源,利用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人為地擴大新疆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間的差異,試圖割斷新疆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緊密聯系。這些跨國民族共同的語言、宗教信仰及文化特征正是境外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分裂與滲透的重要突破口和工具。
(三)地理環境、經濟發展以及新疆的經濟戰略地位等客觀因素
新疆少數民族地區地理上距內地經濟發達地區遙遠,客觀上加大了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難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生產方式制約了整個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新疆特別是南疆的一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落后,有些地區還停留在小農經濟的狀態,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且現代化交通設施建設不足,信息流通渠道欠缺,民眾很容易陷入狹隘的族際小圈子而缺乏與外界溝通的主動性。“在穆斯林社區,伊斯蘭文化往往被社區成員視為主流文化,擁有話語霸權。生活在這種環境的個體,其生活方式和行為規范只有符合伊斯蘭教的要求,才能符合社區規則,并得到社區其他社會成員的認同,實現歸屬,否則,就會出現被孤立的現象。”[注]參見賀萍著《新疆地區穆斯林社會心理的實證分析報告》,原載于《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4期。各種因素的疊加致使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更加突現出宗教的神秘色彩以及信徒對宗教的盲目追隨性,而信徒的宗教情感也容易被激發出來被敵對勢力所利用。
新疆地處亞歐腹部、亞歐大陸橋中心,是我國與中亞、歐洲連接的唯一陸路通道,是繼北美經濟圈、歐盟經濟圈和東亞經濟圈后的全球第四大經濟圈——中西南亞經濟圈的重心區,經濟地位不言而喻。新疆沿邊境線附近擁有17個一類口岸和12個二類口岸,成為我國利用周邊國家資源和市場最為便捷的省區之一。如果我們將向東往太平洋市場方向調整至向西往大西洋歐洲市場,里海、黑海西亞市場,波斯灣中東市場方向,新疆是中國距離西亞、歐洲及中東最近的地區。隨著中亞經濟的發展,新疆可能會成為重要的經濟中心。“新疆對于中國而言,不再僅僅是國防線,更是開放前沿和持續發展的戰略要地,戰略觀察家幾乎一致預言,未來15年,新疆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腹地的地位將得到極大的提升。”[注]參見田磊著《悵望新疆》,原載于《南風窗》2009年第17期。這恰是境外敵對勢力覬覦中國資源、恐懼中國強大從而加大對新疆進行分裂和滲透活動的原因所在,而宗教的自身特點與其產生的負面作用則成為境外敵對勢力對我們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有效渠道。
五、加強新疆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路徑選擇
(一)在新形勢下不斷鞏固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支撐,自身需要具備合法性。主流意識形態合法性建設的基礎在于民眾的認同。塞繆爾·亨廷頓說:“如果政府制度只代表利益集團的利益,只代表社會組織的利益,那么政府行為就只有局部的合法性,而不可能有普遍的合法性。”[注]參見塞繆爾·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在階級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只能是一個,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主流意識形態必然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倡導的價值觀符合并維護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得到了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廣泛認同。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深,社會主體利益訴求日益多樣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由于特殊的地理、歷史和人文環境,境外宗教極端思想滲透對新疆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帶來不小的沖擊與威脅,這需要我們在新的條件下不斷鞏固主流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民眾對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解主要來源于日常生活,通過感受黨和政府實施的政策對自身生活的影響來認知理論。因此,鄧小平提出的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然是今天在新疆抵御境外宗教極端勢力侵蝕的重要物質基礎理念,百姓生活富足安定必然會增強對國家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疏離分裂勢力對其進行的侵蝕與滲透。此外,黨員干部的身體力行是增強執政黨和主流意識形態凝聚力的關鍵。走群眾路線,傾聽群眾的呼聲,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及早消除群眾中的消極情緒和矛盾激化的苗頭,才能真正做到在意識形態領域構筑起抵御宗教極端思想滲透的思想防線。
(二)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加強“四個認同”意識的培養和鞏固
在國際社會中,民族國家的主體地位與民族意識的強弱有密切關系,欠缺民族意識與淡薄民族身份的國家主體在現代民族國家之林不可能成為強者。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國家穩定與發展的重要基礎就是妥善處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民漢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指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注]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自覺地樹立和鞏固中華民族共同的意識、信念、信仰,并以此來聚合、統一、規范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行為,是中國的選擇,更是新疆少數民族地區抵御宗教極端思想滲透和分裂勢力侵蝕的必然選擇。
“認同是一種建構,一個從未完成的過程 —— 總是‘在過程中’。”[注]參見齊格蒙特·鮑受著、鄭莉譯《作為實踐的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頁。“四個認同”是新疆少數民族地區打造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塑造共同心理的特殊功能。在西方加緊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境外宗教極端勢力利用各種途徑對新疆進行滲透的嚴峻形勢下,加強“四個認同”意識培養,尤其是加強對中華文化認同的培養非常重要,這是愛國主義的心理基礎。在“四個認同”基礎上加強愛國主義教育,“要把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主觀認同納入整個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整體系統之中,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維護和實現國家和民族全面、整體性的國家文化安全。”[注]參見胡惠林著《中國國家文化安全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頁。歷史上,愛國主義從來都是凝聚民心、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的旗幟。
(三)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堅決抵御宗教極端思想對青少年的滲透
在堅決遏制傳播極端思想的源頭、嚴厲打擊極端勢力、切斷傳播渠道的同時,還應重視強化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在全疆各地廣泛開展各族群眾共同參與的文化活動,利用伊斯蘭教的積極因素,并把其“嵌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流意識中,引導廣大穆斯林群眾把思想融入到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中去,從而凈化意識形態領域,瓦解極端思想傳播繁衍和極端化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針對宗教極端勢力對教育領域滲透和對青少年思想侵蝕的嚴峻形勢,當前的重點應是引導和幫助青少年認清宗教極端勢力的本質和危害,加強對學校青少年學生的反滲透思想教育,建立健全教育領域抵御極端思想滲透的長效機制;及時發現抵御滲透的薄弱環節,明確不同時期及相關單位反滲透的具體任務,制定相應的政策和策略,采取得力措施抵御滲透和防止滲透的擴散;充分發揮教師特別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輔導員和班主任隊伍在抵御極端勢力滲透方面的作用;重視編寫和整合具有新疆特色的政治理論課教材,使正面的、積極的思想占領學校的思想文化陣地,嚴厲打擊宗教極端勢力在學校的滲透活動,引導青少年理性地對待宗教信仰上的盲從心理和主觀情緒,樹立正確的宗教觀,抵制宗教極端思想的侵蝕,消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利用的社會土壤。
參考文獻:
[1]彼得·曼達威爾.跨國穆斯林政治[M].英國勞特利奇出版社,2001.
[2]金宜久.當代宗教與極端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3]許利平.亞洲極端勢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4]陸忠偉.非傳統安全論[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5]蘇暢.中亞宗教極端勢力研究[M].北京: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