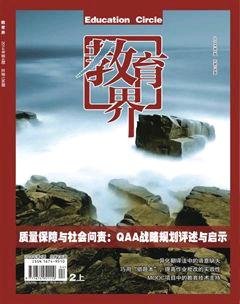都是病,不是風景
張小莉
【摘 要】本文從文章的題目開始,指出《風景》用反諷的手法、舒緩的語氣來釋放內心的苦悶和對前途的擔憂,文章主要是按照原文本身的行文順序進行解讀,從文本每句的含義到整篇的架構、從詩歌單行的寓意到全文的思想、由具象的描寫到抽象的思維。
【關鍵詞】憂患 忠于現實 反諷手法 色彩搭配
40年代的九葉派詩人所處的時代充滿了變數和動蕩,抗日烽火燒遍了神州大地、國共內戰又使受傷的國家雪上加霜,有良知的詩人面對如此景象,或者扼腕嘆息,或者潑墨書憤。九葉派詩人繼承一貫關注現實的優良傳統,且用冷峻的筆法、玄妙的構思、真誠的思想表達著他們自己的憂患和憤懣。辛笛更是一個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人,祖國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積淀著他深厚的感情。列車行駛之處,滿目瘡痍的祖國母親令他痛心疾首,于是,在他眼中,一切東西“都是病,不是風景”。
刻意為詩者,使有些詩太像詩,讀起來很不自然。如同裝出的處女,即不溫柔 也不高雅,只是有一種騷動的喧嘩;有些似乎是漫不經心的作品,即不想有驚人的創造,也不做刻意的雕飾,只是平靜的敘述著一種遭遇或偶遇的一件惆悵或遺憾。但這卻著實地能反映出詩人真實的心境和美好的創造,讀了讓你沉思或讓人深刻或讓人心痛。這樣的創造,即收獲了詩,也收獲了讀者。辛笛的短詩《風景》就是這樣一首詩。
20世紀西方現代派有一個重要寫作手法是“反諷”,如艾略特、卡夫卡等人就慣用此法,他們以客觀冷靜的態度,揭露虛偽丑惡的社會現實,讓事實本身在矛盾中打圈,有時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中國詩人和作家也借鑒這種手法。《風景》就用的是這種反諷的手法。
文章的題目是《風景》,給人一種奢想和熱望,急于想知道詩中“風景”的醉人和美麗。但事實是我們在詩中找不到通常意義上的風光綺麗、陶醉誘人的“風景”,既沒有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恬然,也沒有林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悠閑。我們在詩中找到的“風景”卻是“一節接著一節的社會問題”,“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風景”。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如同拋在空中的鐵彈,瞬忽又墜落在地,摔得很痛很痛。這正是詩歌的精妙所在,在一種預設的想望中,用冷峻的筆法心平氣和地點出了矛盾所在、問題所在,雖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令人掩卷后還咂摸數日,深刻的啟迪在平靜中滲入得很透很透。這正是道家的深刻義旨:即“無為”更“有為”,同時又符合西方現代派手法的“反諷”,二者在這里得到了完美的對接和整合。
在一般的現代詩歌中,都有具象的描寫和抽象的思維、簡單的意象和深刻的意念的結合。這首詩也是這樣許多種思維和形象的結合。當1948年夏,詩人乘車在滬杭道中,看到即將解放又還沒有定型的中國大地,滿眼是戰爭的創傷,民生的凋敝;詩人百感交集,遠處的田野不再是美麗的風景,而是密集的彈坑;近處的耕牛和行人不再是健康的生靈,而是病態的動物。于是他用沉重的心情寫下:“列車軋在中國的肋骨上/一節接著一節的社會問題”。詩人用擬人手法,形象的寫出一節節的鐵軌如同窮人的肋骨一節節。這里借中國腹地上行駛的列車,表達了對祖國的熱愛和對國運的關切。“鐵軌”和“社會問題”本來是兩個不相干的東西,但詩人卻用“一節接著一節”的具體量詞將二者銜接起來,二者的共性于是便很明朗,“社會問題”如同“一節一節”的“鐵軌”那樣復雜和繁多。這可想而知人民的基本生活狀況。有人說:詩人是國家和社會的晴雨表。這話一點不假,惠特曼是美國自由與民主的呼吁者,屈原是中國開民封建制度的捍衛者。很明顯,作為有良知的詩人,辛笛也為當下的社會問題而心痛。這開頭兩句既是對全詩的概括,也為全詩定下了感情基調。
下面兩句,通過強烈的對比,從視覺上給人一種啟示。一個技巧圓熟的詩人和作家往往在作品中充分搭配色彩,達到新奇和深化主題的目的,如同中國大餐,講究色、香、味俱全。“夏天的土地綠得豐饒自然/兵士的新裝黃得舊褪凄慘”,“綠得豐饒自然的大地”和“黃得舊褪凄慘的新裝”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既寫出戰事的頻繁,又寫出士兵生活的艱苦和中國現實的殘酷和腐敗。這種顏色的強烈對比更突出“反諷”的效果。很顯然,作者在這里用了很高超的寫作技巧。這也體現了形式為內容服務的詩歌宗旨。
詩歌的最后四句,如同乍破的銀漿、散落的玉珠,收來得婉轉而有力。全詩前面部分主要是具象的描寫,而到這里主要是抽象的議論。或者說,由前面的寫“外”轉到寫“內”。“慣愛想一路來行過的地方/說不出生疏卻是一般的暗淡”,正是因為作者懷著沉重的心情,觀察到一路的荒蕪和頹廢,這些都情不自禁勾起他種種的思考和憂慮。這種陌生,究竟說不出“生疏”在什么地方,但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暗淡”,這份“暗淡”就是黑暗的社會現實,腐敗的社會現狀,冷漠的社會世情。無論在什么地方,處處都令作者那樣心痛和失望。最后,他一反冷靜的慣態,一發不可收拾,好像仰天大喊一聲“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風景”。這聲大喊是對現實的詛咒,也是作者痛苦心情的宣泄。
“都是病,不是風景”,——雖然控訴和宣泄完了。但詩人痛苦的心情還遠遠沒有結束。聽,那“一節接著一節社會問題”的火車聲又仿佛由遠而近,喀嚓、喀嚓、喀嚓……
這首詩可以說是辛笛40年代詩風轉變的一個成功典例。40年代的詩人大多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融合,辛笛在這方面的嘗試是較成功的,《風景》既有對現實的關注,同時藝術手法較可熟練運用西方現代派技巧,卻融合中國傳統的詩歌技巧和古典詩的意蘊,所以他的詩顯得厚重、蘊藉、新奇。
【參考文獻】
[1]程光煒.中國當代詩歌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張新.20世紀中國新詩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3]陸耀東.中國新詩史(1916—1949)·第一卷[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
[4]吳曉東.20世紀的詩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