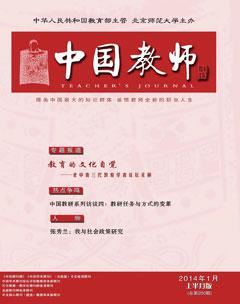李曉輝:校本教研應提升學校教育教學的品質
林靜
李曉輝,北京市特級教師,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副校長,北京師范大學“新世紀”版《生物學》實驗工作指導委員會專家組成員,《生物學通報》常務編委,北京市中學生生物學競賽培訓教練,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兼職教研員。
《中國教師》:李校長,您好!能否先請您談談對校本教研的看法?
李曉輝:我們學校在校本教研方面抓的工作還是挺多的。在我的頭腦中,校本教研的熱點已經過去,現在我的熱點沒在這個地方,但是,通過今天的談話,我覺得還可以給校本教研以新的內涵。
我第一次是在北京教育學院聽說校本教研的。當時,教育部出臺了一個“以校為本”教研制度的推進文件。我們在北京教育學院開座談會,北京教育學院的一位教授認為,校本教研由學校來完成是不現實的,應該由教育學院、教科所、大學來完成。當時,他發言之后,我就表明了一個非常鮮明的觀點:校本教研一定是以學校為基礎的。
我們撇開它的定義,先從教師發展的角度來看校本教研的作用。要成為一名好教師,需要三方面的知識:本體性知識、條件性知識、實踐性知識。本體性知識指的是本學科的知識,條件性知識指的是教育學、心理學等怎么教課的知識,本體性知識和條件性知識都可以向別人學,而實踐性知識最大的特點是,一定是自己在實踐中得來的。所以,若脫離了實踐,教師專業發展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比如說,我們學校有位老先生呂老師,他上課的話非常少,但他的每句話非常到位,別的教師可能講三、四遍學生還是不明白,而他一句話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點。這種本領你怎么學?即使你最終學得像,但是絕對達不到人家的程度。可見,實踐性知識一定是在教學實踐過程當中生成的,這是教育學院、研究所、大學都做不到的。因此,從教師專業成長的角度來講,校本教研一定是以校為主發展教師的實踐性知識。
校本教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作用。各個學校都各有特色,那么學校的特點怎樣得以體現?這也不是一個教育學院或者大學能完成的,是需要依靠學校的校本教研。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以下簡稱實驗中學)為例,不提它所有的歷史因素,它的特點,咱們就說一個最現實的,就是學生的整體程度比較好,這個體現在哪里呢?知識,學生知識基礎比較扎實;興趣,學生對什么東西都感興趣;活躍,學生善于表達。其實,并不一定說善于表達的學生就一定比不善于表達的學生優秀,這只是一個學校的特點。那學校就要針對學生的程度研究學校教學等一系列的工作。早在1992年我剛到實驗中學的時候,我們學校就有一種說法:教學要源于大綱,高于大綱;源于教材,高于教材。這種提法現在已經不稀奇了,但在當時,可以說實驗學校是很有氣魄的。這就是一個學校的特色。
所以,校本教研最起碼有兩點可說明它的價值。第一,針對教師個體的專業成長,校本教研的價值是非常大的。第二,從學校的發展與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來講,它本身的價值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個人覺得校本教研概念的提出是有價值的。雖然,在提出校本教研之前,學校的教師也做教研,但是校本教研的提出確實能促使學校對教研的含義與任務價值的理解有所不同。原來,學校對教研的理解可能更多的是新教師去參加區里的教研活動,現在,學校是在考慮如何做校本教研這件事情。所以,校本教研的價值,從實踐的角度來看是無可爭議的。
《中國教師》:您對校本教研進行了很好的概念與價值闡述。那么校本教研該怎么做?可否請您為大家介紹一下貴校校本教研的經驗與做法?
李曉輝:校本教研到底應該怎么做,我們也嘗試了很多的途徑。我們在最開始做校本教研的時候,先是對原來的教研方案做了整合。比如,有幾種基本的方式,最簡單的一種方式是學科備課組的集體備課制度,這種備課制度直接指向教學工作,這是最基本的組織形式。學校每周為學科備課組安排出一節課的時間,給予集體備課時間上的保障。其次,我們一直在堅持學科教研組的辦公機制。不僅如此,這幾年,我們也在做一個叫“4+1”的組級教研活動。所謂“4+1”組級教研活動是什么概念呢?比如,一個學期20周,大概有效時間5個月,這5個月中,我們每個月會拿出一個周二給學科教研組自主設計教研活動,一個月共4次。而“+1”,就是每個學科教研組每個學期可以有一次外出集體學習、集體研討的活動。另外,我們會在學校層面召開各種形式的研討會,這為校本教研提供了形式上的保證。比如,我們每學年在年級大考之后,會有一個年級分析會,該年級所有學科的教師坐在一起研究學生的特點,一學期有兩次。再比如,每年有畢業年級的工作研討會、起始年級的工作研討會,以及教育教學年會等,這都要求全校教師參加。我們從學科備課組、學科教研組、年級組和學校的層面,將所有教研整合到一塊兒,從形式上來講,這就是在為校本教研搭建平臺。
當然,除此之外,我們在校本教研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方面,還專門有一項計劃:教師成長促進計劃,意思是教師是主體,成長是教師的事情,學校起促進作用。我們采用的是項目式、主題式的工作方式。例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四科的教師組成一個組,專門研究數學、科學的教學,指向數學、科學的本質。這幾個學科的教師形成一個項目組,這個項目可能會維持一個學期,或者兩個學期,大家針對問題,一起來研討、解決。這項工作,我們也堅持了幾年。教師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我們完全用的是業余時間。剛開始時,我們利用周五下午4—6點的時間,當時大家研討的內容涉及面非常廣,只要有想法,幾個志同道合的教師就可以組成小組進一步討論。后來,研討的主題慢慢走向實用、現實,這也是在搭建校本教研的平臺。
所以,校本教研從形式上來講,應該有一些組織形式,如果沒有組織形式,校本教研是沒有辦法實施的。在這個基礎上,校本教研單有組織形式是不夠的,還要搭建另外一個平臺,即主題的平臺。
那么,主題的平臺怎樣來搭建?比如說,搭建備課組的內容很簡單,因為有備課的任務,教師只要備課就行了。學科教研組也是如此。但搭建主題的平臺怎么做呢?
第一,課堂教學。因為在學校里,我們一直說“兩課兩教”,“兩課”指課程、課堂,“兩教”指教師、教研。我剛才已經談到,我們抓課堂的時候,校本教研的形式已經有了,而主題就是課堂教學。在課堂教學方面,我們先是提出了做“有效課堂”的探索。把這個話題拋出去之后,我們會給予教師專業引領,引導教師認識和理解“有效課堂”的內涵。這個引領基本上是基于別人的研究而進行的資料整理與摘編,然后我們會把材料發給各位教師。同時,為了配合有效課堂研究,所有的學科組都要圍繞這個話題進行研究并做研究課。從形式講,研究課是要錄像的,這是我們基本的教學要求,叫“一人一課”,即一人做一節課,內容可以自己隨意選擇。在那段時間里,大家談論的都是有效課堂的內容,到一定階段后,我們召開一次教育教學年會,各個學科組進行交流。
有效課堂的探索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我們又提出了一個主題——高效課堂。我們在引導教師認識和理解高效課堂時,首先明確地提出“高效課堂”的探索旨在砍掉課堂中無效的部分;其次是請北京師范大學的劉儒德教授來講有效負荷的理論,分析課堂上的認知負荷哪些是內在的,哪些是外在的,哪些是關聯的,怎樣進行整合;最后是要求教師做課,將探索落實在課堂中。
到了2010年,我又回歸到葉瀾教授提出的課堂的生命活力,提出了“活力課堂”。之前我們做了很多關于提高學業質量的探索,現在我們提出了生命活力,目標的指向不僅僅是學業成績,而是人的全面成長。只有指向人的全面成長,才能把人內在的東西全面挖掘出來。所以,我們提出了三個活力:學生的生命活力,教師要關注學生學業成績之外的全面發展,關注三維目標特別是第三維目標的落實情況;教師的活力,課堂不僅是學生的生命體驗過程,也是教師的生命體驗過程;知識活力,它其實是最低級的,但大家平時容易忽略。什么是知識活力?或者說什么樣的知識是活的?簡而言之,抽象的東西就是死的,與現實聯系的東西就是活的。然后,我們用這個主題作為一個平臺,開展“學科月”活動,由準備成熟的學科教研組申報活力課堂的展示,研究對活力課堂的理解,做活力課堂的研究課。最關鍵的是一個月之后,教研組要在全校教師面前匯報自身對活力課堂的理解與實踐。這項工作目前持續了一年半,現在除了音樂、體育、美術之外,其他所有學科的課全部都展示了一遍。我覺得這次展示有效地解決了下列問題:第一,最有效地解決了教師的活力,因為教師在匯報的時候,我們會給他提一個最核心的問題,要求教師匯報的內容,反映出如何用自身學科的獨特性,讓聽課的其他學科的教師了解自己對學生成長的貢獻。比如說語文,我們要解決聽說讀寫的問題,但目前考試只考讀與寫,怎樣把聽與說相結合來解決讀與寫的問題。再如,英語,在選擇話題的時候,會選擇與學生生活比較密切的內容。初一的一個單元講如何為別人準備生日禮物,一般的教學流程會有一個對話,學生進行模仿。但我們的一位教師一開始就讓學生來回憶自己過生日的情景,都做了些什么,完全與學生的實際生活相聯系,然后,這位教師繼續問學生有沒有經常收到禮物,收到的禮物是什么,最后講如何給別人準備禮物。原來的課堂設計是學生看別人怎么做,然后把相關的詞語學會,但現在不是,學生自己有話說。這樣,教學就與實際生活相聯系。作為一所學校,校本教研最終要解決的問題還是要把學校教育教學的品質提上去。既然要把教育教學的品質提上去,這里一定會有主題詞與方向的引導,不然可能會流于形式,或者沒有深度,沒有生命力。
這里,我們還有一條線索,就是從課程的角度來抓校本教研。高中實施新課程之后,與原有課程有比較大的變化。我個人理解,第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就是教材的權威性被打破,因為現在教材的種類比較多,教師們也發現各種教材之間居然有這么大的差異。我們就從課程實施的角度提出要做國家課程的校本化實施,這是有學校特色的。
那么,怎樣實施校本化?我們做了兩件比較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學科教學知識體系的構建,將學科知識體系與學生認知體系結合到一塊兒。學科知識體系是專家的認識,教師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專家的認識、學科專業知識體系調整順序,以符合學生認知的方式傳授給學生,然后學生結合自己的認識整合到自己的學科知識體系中。
為了落實這項工作,我們讓大家做兩件事:一是有實力的學科教學組編寫校本教材,我們稱之為讀本,實力相對弱的可以編學案。這里的學案與一般意義上的學案不同,我們暫且用這個名稱。比如說,我們編校本教材的時候,必須明確要遵循課程標準。我們要以現有教材作為參考,特別是北京地區同時使用兩套不同版本的教材,東片使用一套教材,西片使用另一套教材,所以校本教材最起碼要包含東、西片兩套教材的共性內容,不是共性的但又有價值的內容也可以放進去。目前,校本教材比較成熟的是三個學科:生物、化學、歷史。在校本教材編寫過程中,我們較好地解決了學校發展與教師個人發展這兩個問題。1999年,我在《學科教育》發表過一篇關于用教材教的文章,那時候還是停留在用教材教還是教教材這個層面,但是現在已經發展到學校教師可以編教材的水平。我們現在就是要引導大家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目前不是所有的學科都具備這個條件。二是所有學科都必須編學案。這個學案的概念是與教案相對應的學生課堂學案。因為教案解決的是學科教學知識體系構建的問題,教師要把教學知識體系轉化為學生可見的東西。我們最早提出這個學案的時候,是由于新課程課時不夠,但當時的概念是模糊的,后來就慢慢變得清晰,就是與教案相匹配的學生課堂學案。學案里首先應有課堂目標,然后引入話題,甚至一些案例。教材是完整的,但是在學案中呈現的順序,就是教學內容的順序與組織形式已經變得不一樣了。學生可以通過學案在課堂上生成學習。
第二件事是學科訓練體系的構建。所謂的基礎知識與技能,到底什么是技能?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就是技能。比如說,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人家考你的時候,會給你一個代數式,而不會問你定義是什么。而技能的習得又有自己的規律,它與一般知識的獲取不同。技能性知識可以通過模仿、訓練而熟練化。因此,我們首先要確定訓練的價值,訓練一定是有價值的。其次,我們要研究如何讓訓練變得有效。比如說,我給學生出六道題,兩道題一個層次,共三個層次,到最難的第三個層次,基本做對,就意味著學生理解了概念。對于學科訓練問題,既要有質,又要有量。我們要避免出現什么情況?就是教師是給了六道題,但六道題全部是第一層次的,或者都是第三層次的,那么學生就會不知所措。可見,這個量不在于多與少,也許就留兩道作業題,學生一晚上也做不完,也許留了20道作業題,學生5分鐘就完成了。我們最后的指向就是最基本的想法:必須把時間高效化。所以,我們開始編學科訓練體系。到今年本學年結束,學科訓練體系應該能全部完成。這樣一來,所謂校本教研,就是教師們有非常實的事情在做。為了保證這項工作的完成,我們還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從可操作角度來講,只能是備課組編,第一年編完后,第二年有非常明確的要求,只能修訂,不能重編,修訂范圍在30%,不能大量地修訂,也不能不修,這樣,三年一輪,基本就將其變成學校的成果。當然,做這件事,還有經費的保障,我們是給教師付稿費的,而學生是免費使用的。
《中國教師》:您能就校本教研促教師個體專業成長方面談談貴校的舉措與寶貴經驗嗎?
李曉輝:我剛剛談得比較多的是學校層面,教師發揮的作用,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談。
我們首先還是從平臺組織形式來談。我經常講,教師一定是在戰斗中成長的。在課堂教學過程中,不管是有效課堂、高效課堂,還是活力課堂,我們都提出了“一人一課”。而這“一人一課”的活動過程都是以備課組的形式將課進行打磨后往外推的。而在課堂教學方面,年輕教師的課是我們整個學科備課組重點打磨的一類課,那要打磨到什么程度?舉個例子,我們有一位年級教師,準備一節課最后形成了三個教案,第一個教案在一般人看來已經是很好的一個教案了,在這個基礎之上,又繼續打磨修改到第三個教案。在做活力課堂的過程中,受益最大的是年輕教師,而比較成熟的教師也會受益,會有思想上的碰撞,會產生新的想法。在全校教師面前展示成果的時候,教研組長一般都是推舉年輕教師的課例,重點打磨年輕教師的課,這樣年輕教師課程環節的精細程度與語言的準確程度會高,這對年輕教師的成長是很有利的。再比如,我們校本教材的編寫與學案的編寫模式,是“總分總”的模式。大家集體討論綱要,集體討論章節內容,定稿之后,個人獨立完成,完成之后,大家又聚在一起共同討論。所以,大家的起點也許不同,但是寫成內容的水平是對等的,這樣老教師自然就把年輕教師拽上來了。在這個過程中,第一次討論的時候,大家可能基本在聽老教師在那討論,討論幾次之后,大家就都可以發表觀點了。所以,校本教研一定是解決學校的事,但在這一過程中,對青年教師的成長促進作用是最大的。
《中國教師》:您在前面提到,校本教研要提升學校教育教學的品質。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提法。請您再談談校本教研如何提升教育教學品質?
李曉輝:我建議還是要做好這兩個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有組織形式。一定要有精心設計的組織形式,這個組織形式一定要給予落實。第二,一定要有主題。這個主題要從教師教學實踐中產生。目前,我們還在做北京市的一個重點課題“持續改進課程教學”。什么是持續改進?它就是發現問題,分析、思考問題解決方案,進行實踐,然后再發現新的問題。所以,我們是不斷地在往前走的。這是學校自我挑戰、實現自我超越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如果沒有這個條件,我覺得還有兩件事是可做的,一是加入某一項研究的共同體。現在的研究共同體非常多,如民間的、官方的、半官方的。有的人說這些共同體不好,我覺得不在于好不好,而在于我們的教師是否動起來。加入一個共同體。它有現成的東西,教師加入之后,就可以進行模仿。我覺得,做教師,模仿一點都不丟人。
如果沒有這種共同體,則可以做一些課題、項目的引進。比如,有段時間,我們就在瘋狂地學習馮忠良教授的“結構定向化教學”。我們學校有個小型的讀書會,大家都讀馮忠良教授的書,讀完之后交流,交流之后開始嘗試做課。作為學校的引領者,我一定要把這項工作推下去,得讓教師們有那種想去做事、想去嘗試的沖動。我們覺得這是每所學校都應該做的。
另外,作為學校的領導,要做好這件工作,應該有兩方面能力,一是他的頭腦中應該時時刻刻有本學校的情況,這是往里看;二是往外看,看到外面的世界。比如,上星期我們學校做了期中分析,重點談了兩個變化給教師們帶來的影響。北京市中高考改革方案已經發布,2016年高考英語100分,分值減少。相對應的,學生對英語的學習有了變化,其他學科教師也提出了各種問題,家長對英語學科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我們就對教師們講,首先,課程計劃沒變,課標沒變,教材沒變,課時也就不能變。其次,如果2016年英語真的提前考試,我們的對策是高一高二趕緊先把外語抓出來,而不是不管。第二個變化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明確寫了要取消重點校、重點班。管、辦、評分離,這要怎樣應對?我們要提前思考,而不是等到事情發生了再去應對。我們一直在想,什么時候是機遇?有變化的時候會存在機遇。所以,這對所有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對教師講,原來大家都承認實驗中學的教師能力很強,能把學生的好成績教出來。那么現在北京的高考,2013年之前,理科狀元是710分左右,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錄取分數線是650分到660分,中間相差50~60分的范圍。但2013年就開始發生變化,理科高考狀元726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錄取分為691分。這種情況下,分數的差距并不明顯,別的學校的教師也能教出那么高的分數,這時教師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我們就明確地給教師講,下一個教育教研的重心就是所有學科都要搭建除了必修課之外的讓學生個性化發展的學術平臺。
那么,做學術平臺是什么概念?比如說,前不久,地理教師談學生參加地理競賽,成績很好。上午的競賽形式是讓每個學生看電腦中的景觀圖,然后給學生材料,用這些材料來解決一些問題,下午的競賽形式是四人一組外出,進行考察,搜集植被、地質等資料,回來后每個人獨立完成相關的問題。我們覺得這個競賽方式不錯,建議把這項活動做成一個平臺,而不僅僅是臨賽之前簡單地組個隊參賽。這個活動平臺有考察,有研究,能把學生持續性地吸引過來。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所有學科都要搭建學術平臺。這樣一來,即使整體的高考變得比較簡單,即使重點大學的錄取不再只看高考成績,我們仍然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我們要以不變應萬變,按照教育規律做事。所以,在校本教研上,學校既要明白自己學校的實際情況,還得有向外看的視野。
(責任編輯:馬贊 孫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