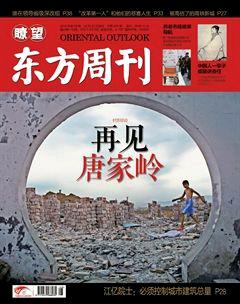家庭醫生的一天
呂爽+楊卓琦

上海正在全面推廣家庭醫生制度,力爭到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每個家庭與一名家庭醫生簽約。按照上海醫改方案的規劃,每2000~3000人將配備1名家庭醫生。
邱宏亮是一名在上海200多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的家庭醫生之一。他已經在社區做了8年的全科醫生。
上午門診,下午上門。這兩個角色貫穿邱宏亮一天的工作中。“這就是家庭醫生的節奏。”
誰來看病
邱宏亮所在的社區衛生服務站點并不好找,在長興坊一條小巷盡頭的右手邊,而小巷的左手邊是一個菜市場。
全科門診從早晨八點開始,而邱宏亮一般在七點半就已經穿好白大褂坐在診室里了。在這里,經常見到住長興坊的居民們穿著睡衣、趿著拖鞋提著菜就過來了,掛個號看好病,買好菜再回來配藥。
2014年的1月中旬,邱宏亮的門診格外忙碌。他從一早坐進診室直到11點才抽空去了趟洗手間。“去年的醫保額度提前用完了,以至于最后兩個月很多藥只能限量供應,所以今年剛開始就出現居民們蜂擁而至來配藥的情況。”邱宏亮介紹。
在康健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服務的片區,原來只有5萬~6萬人,現在有9萬人了,“但是醫保卻在近十年沒有什么增長,每年只有四千萬到五千多萬元,這就很矛盾了。”
“我們這個服務中心,藥品很齊全,很多大醫院能配的中外合資的基本藥物我們幾乎都有,但是醫保額度不夠用,很多別的社區的人也過來配藥。”據邱宏亮說,甚至有人從寶山坐公交車來這里的社區醫院配藥。
在他的掛號病人中,80%是來配藥的,只有20%的患者是來看病的,“也只是些傷風感冒什么的。”
這個社區衛生服務站點一共有四個全科醫生,其中有一個特色中醫門診。“現在天冷看不出來,天熱的時候這個門診每天人很多的,都是來做針灸推拿的。”邱宏亮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本刊記者觀察到,來社區醫院看全科門診的,幾乎都是50歲以上的上海人。“大家一般都說上海話,有些年紀大的病人也不會說普通話。”邱宏亮是上海人,語言關沒有成為他工作上的問題。
“這個也好理解,上海居民持社保卡在社區醫院看病能報銷的比例最大,配藥也便宜。上年紀的人多是慢性病,只需要長期配藥而不是診斷,所以幾乎都是他們過來看病。”邱宏亮說。
2014年開始,上海市居民醫保參保人員住院發生的醫療費用,超過起付標準以上部分,基金支付比例作相應調整:60周歲及以上人員、城鎮重殘人員,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者一級醫療機構)住院的,基金支付比例從85%調整為90%;60周歲以下人員,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者一級醫療機構)住院的,基金支付比例從75%調整為80%,均高于二級、三級醫療機構。
而上海醫保報銷比例的政策傾斜并非從近幾年才開始。早在2007年,上海市政府常務會議就審議通過了《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意見》,明確提出將適當拉開醫保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大中型醫院支付比例檔次,引導參保市民到社區醫院就醫。
除了醫保報銷的優惠政策以外,基層衛生機構藥品配備范圍采取“307(國家基本藥物目錄)+X(本市社區衛生機構補充基本藥物目錄)+Y(目前醫保藥品目錄)”的方案。對納入307+X范圍內的藥品,將實行全市統一招標、集中采購、統一價格、統一配送,并在基層衛生機構實行零差率銷售。
換句話講,找社區醫生看病,報銷多,藥便宜。
這里沒有醫患矛盾
在這個社區家庭醫生團隊中,邱宏亮是團隊里的首席醫生,也是深受居民歡迎的家庭醫生。在毗鄰的三間全科診室中,數他最忙碌,社區醫院也專門為他掛牌:小邱工作室。
“我在社區衛生中心工作八年,幾乎沒跟患者有過紅臉的情況。”邱宏亮說。在社區衛生中心,患者經常不掛號就進來做些咨詢、問問情況的也有。“他們都說,在大醫院不掛號就看不見醫生面,掛了號就見5分鐘面。”
在全科醫生門診的門外,有一排等候座椅,但是一上午過去,都沒有患者坐著等待。因為服務的小區居民幾乎都是熟人,最多的時候門診里涌進六七名患者,圍著邱宏亮看病、開藥,居民患者之間還能聊上幾句,問問病情。
當居民得知記者來采訪邱宏亮的時候,一位患者對本刊記者說:“他可是十佳家庭醫生,劉延東副總理接見過的哦!”
邱宏亮特別不好意思地笑笑,“當初投票都是居民們幫的忙。”
201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調研考察上海醫改工作推進情況。在徐匯區康健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劉延東與家庭醫生和簽約居民交流,勉勵家庭醫生更好地與自己的簽約居民聯系,讓居民對自己的健康情況更有底。
2011年4月起,作為上海醫改五大基礎性工程之一,上海在長寧、閔行等10個區率先啟動了家庭醫生制度試點,共有136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展了家庭醫生制度構建,覆蓋2277名家庭醫生,簽約居民達374萬。
在邱宏亮不到8平方米的診室里,常年放著徐匯區衛計委每月刊發的健康快報,居民患者可以瀏覽閱讀,也可以拿一份回家慢慢學習。
轉診難
上午門診結束后,邱宏亮下午的家庭訪視工作更隨意些,背著黃挎包,帶上聽診器、血壓計等簡易的醫療設備,騎著一輛電動自行車在幾個小區之間來回跑。
在這個片區,有兩個養老院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共建,需要每周抽半天去查房看病。除此以外,百歲老人、離休老干部、傷殘軍人以及烈屬需要定時上門,再加上簽約家庭,邱宏亮每天下午大約要跑10到15個家庭。
本刊記者隨邱宏亮上門訪視的都是空巢老人。每到一家,測血壓是一定要做的。“老年人都是慢性病,其實我們上門也很難發現什么隱疾,主要是慢性病監測,也讓老人放心。”
在上門的幾家里,除了測血壓以外,居民也會詢問下什么東西能不能吃,什么藥該怎么吃。家住某棟1307的老人拿著一包旺旺仙貝問:“這個能吃一點嗎?”她的愛人患有膽囊炎,很多食物都是經過詢問才能吃。endprint
“有家庭醫生是好事情,但是要我說,最多能給我們的就是關心。比如我要是生病了要住院怎么辦,邱醫生能幫我住進醫院嗎?好多問題還都不能解決。”家住某棟5樓的老先生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居民健康管理,說到底是要和二三級醫院對接的,但眼下轉診通道阻塞,我們有些底氣不足。”康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易春濤曾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說。目前,康健社區與市八醫院建立了“預約轉診”平臺。但在社區醫院的負責人看來,這還是憑借“私交”,或者由三甲醫院做社區課題的需求促成,況且“一對一”總會對不攏:各家醫院及其科室各有特色,而老百姓的健康問題多種多樣。
邱宏亮在2012年曾經去臺灣學習了兩個星期。“臺灣都是綜合性醫院牽頭在做全科診室,轉診很方便,我們這里轉診還真是不方便。”
2013年3月,原上海衛生局(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的《關于本市全面推廣家庭醫生制度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家庭醫生的服務內容,包括對簽約家庭提供健康管理服務、建立家庭醫生首診機制和建立暢通的轉診渠道。但這三點在推進上都步履維艱。
每月的稅后收入只有4500元左右
家庭醫生人手不夠的常態也并沒改變。以家庭醫生承諾的健康咨詢為例,邱宏亮說,有時候每天都要接到好幾十個咨詢電話,不分白天黑夜。有的家庭醫生實在撐不住,只好每天晚上一過十點就關機。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那個周末,邱宏亮依然接到了幾個患者的咨詢電話。“他們打電話,希望我上門看一下,其實如果情況不好的話,應該直接送醫院,我去了基本不管用。”老百姓把現在實行的家庭醫生責任制和國外的私人醫生有點混為一談了。
現在,邱宏亮有950戶簽約居民,但這并沒有給他帶來更多的收入。“簽約的家庭多并沒有額外的獎金拿,就像我們多看幾百個病人,體現在工資上也就是100多塊錢。” 在臺灣,家庭醫生很少上門服務,“因為他們的人力成本太高了。我們雖然家庭醫生缺乏,但出診一次的費用只有十幾塊錢。”
在邱宏亮看來,家庭醫生的工作中,有太多細節需要在政策和規定中明確下來。“比如上門插尿管、插胃管、傷口換藥,這些都是有風險的(損傷、出血、感染等),家庭醫生到底做不做,每個醫生選擇是不一樣的。我是想難道讓患者來回叫救護車跑去醫院排隊只為了換個尿管或者胃管?所以我做。”
邱宏亮今年36歲,級別是主治醫生,每月的稅后收入只有4500元左右,“我們跟大醫院醫生的收入比不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