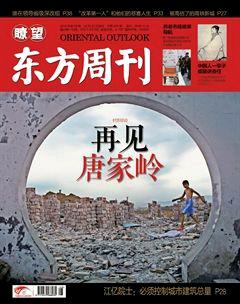宋襄公的“戰爭禮”
張宏杰:
清華大學博士后,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
宋襄公的泓水之戰,《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的。說是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隊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
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爭規則。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須發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于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
等到楚軍全部渡過河后,雙方才開戰。結果宋軍因寡不敵眾,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確實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詮釋。
中國貴族文化的首要標志是“禮”。 春秋時代的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錢”的無所不在一樣。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爭禮”。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春秋時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致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后,鳴起戰鼓,驅車沖向對方。這就是所謂的“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在今人看來,這些老祖宗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太迂闊了,其實不然。因為春秋以前的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與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時期的軍隊都是以貴族為主體,戰士人數不多,幾百輛戰車而已,每次戰爭一般不超過一天。因此那個時候的戰爭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斗。貴族們在戰爭中比的是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說:“春秋戰爭禮最大的特點,在于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
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范。
即便是血腥的戰爭中,優雅仍然是春秋時期貴族的基本追求。雖然彼此的目的都是擊敗對方,但他們言辭卻仍然處處得體。如錢穆先生所說:“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作為殷朝貴族后代、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宋襄公,講究貴族風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觀念。在戰爭中,他既要取勝,也要贏得“漂亮”、贏得“合理”、贏得“高貴”。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風度大于勝敗。那些今天看起來迂腐的禮儀,更是一個階級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
宋襄公的“愚蠢”,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光彩流露。后代中國人對宋襄公的唐突,證明了貴族傳統在中國大地的斷裂。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