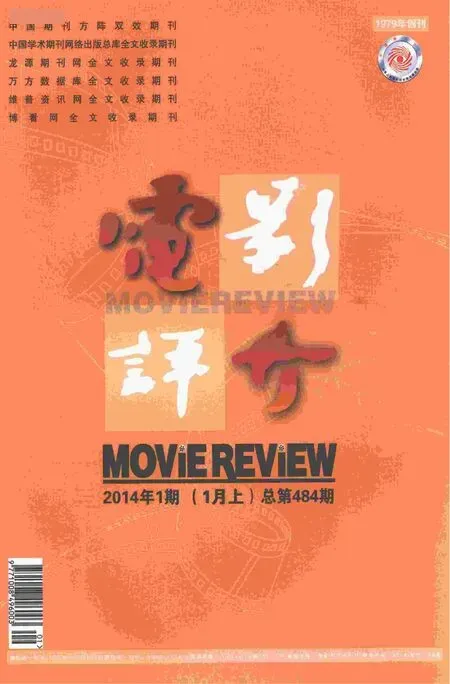中國80后電影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
吳 堅

電影《香魂女》海報
“80 后”,在我國眾所周知特指1980 年至1989 年出生的年輕一代。在這里借用指同時期及稍后創作的中國電影。電影在中國已有百年的歷史,女性一直是電影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但在中國或由于女性的社會地位所致,或因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女性在電影中經常是以比較單調的形象面貌出現,比如20 世紀20 年代被侮辱被損害的女性、30 -40 年代找不到出路的女性以及建國之后新時期之前作為時代政治傳聲筒的“鐵娘子”式的女性等等。女性形象的塑造真正有改觀是80 后的事情,“1979 年對電影界來說,是轉折之年,思想解放之年,大膽探索之年,多方面有所突破之年。”[1]中國80 后的電影出現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
如果按類型來分,中國80 后電影中的女性主要有:賢妻良母型、女強人型、“邪惡”型、邊緣人型等等。
一、沿襲傳統的賢妻良母型女性形象
建國之后盡管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主流意識形態對文藝的影響,所以在電影里幾乎很難找到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有的只是一些概念化的所謂“女性”。當封閉壓抑的時間長了,一旦迎來解禁、撥亂反正,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尋根”,文學有尋根文學,電影也有尋根電影;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電影最先尋到的“根”就是傳統的賢妻良母。相夫教子是傳統對女性的規范,幾千年來忍辱負重、任勞任怨、默默奉獻一直是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盡管在建國17 年和文革10 年中,女性的性別差異被人為地抹殺了,女性“因獲得解放而隱沒于文化的視域之外”[2],但由于傳統的觀念、思想在人們頭腦中已根深蒂固,所以一旦尋根,這一對女性的規范與要求馬上就被凸現。于是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就成了80 年代電影中可觀的人物畫廊,也得到了那一時期觀眾的熱烈追捧和充分的肯定。最典型的是謝晉導演的一系列電影中的女性,如《天云山傳奇》(1979 年)中的馮晴嵐、《牧馬人》(1981 年)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環》(1984 年)中的梁大娘和玉秀等等,謝晉的電影把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塑造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在王啟民、孫羽導演的《人到中年》(1982 年)中,作為當代知識分子典型的陸文婷,還常常為自己在賢妻良母方面做得不夠好而內疚呢;甚至到90 年代末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中,盡管不是主角,盡管父親也有愧疚的心理,但影片里的母親仍然還是一位典型的只會默默等待、無怨無悔的賢妻良母型形象;還有馮小剛《一聲嘆息》(2000 年)中的能讓曾一度離去的丈夫回歸的妻子宋曉英,也是一位典型的丈夫根本不可能真正舍得離開的賢妻良母;胡玫《芬妮的微笑》(2002 年)里還給我們塑造了一位黃頭發藍眼睛的賢妻良母呢;這說明在往后的時間內賢妻良母式的女性還是相當部分人們心中的天使,在觀眾中也還會很有市場,因此在將來的影片中還會源源不斷地出現。
當然這一類形象,在經歷了長期的女性缺失時期,確實能極大地滿足觀眾的審美和心理需求,尤其在80 年代,這一類人物形象的出現使得當時的許多觀眾心里都認為:女性本來就應該如此,賢妻良母型的女性成了人們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可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社會的發展、觀念的更新,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賢妻良母式的天使畢竟是過于傳統的女性,在新的時代里,女性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有這單一的面孔。其實,早在80 年代塑造的陶春(《鄉音》)和劉巧珍(《人生》)身上,我們已看到編導和觀眾的猶豫、矛盾與困惑;走出社會的女性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新面貌出現,才能符合社會、時代的要求,也才符合觀眾日益增長的審美以及生活現實的需要呢?在這樣的背景下女強人形象應運而生。
二、改革開放中的女強人形象
隨著我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推進,女性在社會中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社會和家庭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關鍵是女性自身也逐步意識到自我價值實現的重要性。1981 年女導演張暖忻的《沙鷗》就給觀眾塑造了一個愛榮譽甚于愛生命的女強人形象。縱觀80 后電影女強人形象主要可概括為兩類:一類是真正具有開拓精神與時俱進的女強人;另一類是既自強自立又受傳統羈絆的女性。
由張弦、秦志鈺夫婦打造的《獨身女人》(1992年)歐陽若云就是一位在改革的浪潮中,充溢著現代都市職業女性自強、自立、自信又勇于開拓的女強人形象。在農村題材的影片中,同樣也不乏此類女強人,《喜蓮》(1996 年)中的喜蓮,盡管對影片的結尾所留下皆大歡喜的光明尾巴,不同的觀眾有不同的看法,但總的來說,喜蓮確是一位在農村改革大潮中成長起來的敢想敢干、個性鮮明的女強人。《女帥男兵》(1999 年)是一部體育題材的電影,是一部關于一個女人孤單單地闖進“男人世界”干一番事業的電影,盡管觀眾對女教練聞捷在期間所遇到的困難過于簡單有質疑,盡管觀眾對影片最后落入大團圓結局的俗套有些遺憾,但不可否認聞捷是一位敢于面對復雜的社會現實,有魄力而且充滿性格魅力的女強人。這些是在時代感召下涌現出來的新型的有血有肉有個性的女性形象,她們有別于不食人間煙火的“鐵娘子”,因此影片在塑造這類形象時當然不回避她們在工作、生活、家庭、情感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難與困惑,她們也有性格缺陷也有脆弱的時候,所以這些呈現在觀眾面前的形象都是些活生生的感人的形象。應該指出此類女強人不僅包括事業上的女強人,還包括意識上的女強人。胡玫的《女兒樓》(1985 年)中的喬小雨通過痛苦的掙扎,最后毅然去追求一份女性的獨立意識;黃蜀芹的《人鬼情》(1987 年)被認為是“在當代中國影壇,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女性電影’的唯一作品。”[3],影片中秋蕓的“強”不僅僅簡單地體現在事業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盡管艱難但卻能呈現出來的女性的意識,發出了女性的聲音。喬小雨和秋蕓們是經過痛苦和艱難的“化繭”才能涌現出來的美麗的蝴蝶——新時代真正的女性,盡管數量不多,但作為先驅,相信往后電影中她們的聲音會越來越大、越來越有力度。
時代在進步,人們在不斷地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觀念,但由于舊的思想、舊的觀念有著沉重的積淀,對人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在這一時期電影中所塑造的女強人也不是單一的,許多形象身上都表現了性格的復雜性甚至是矛盾性。張藝謀憑著他的《紅高粱》(1988 年)一炮打響,給觀眾塑造了一個全新的女性——“我奶奶”的形象,“我奶奶”從表面看來確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強人:“野合”、“祭酒”、“犧牲”,每一場戲都以“我奶奶”為主角,張揚了強勁的生命激情,但另一面我們也很清晰地看到,“我奶奶”仍沒脫離傳統女性的窠臼;謝飛的《香魂女》(1992 年),是一部很具悲劇感染力的影片,影片中的香二嫂就是一位典型的既是一位農村中的女強人但又身受傳統羈絆的形象:在改革的大潮中,她不失時機、精明能干,很有魄力,把自己的香油坊經營得有聲有色,絕對稱得上女強人,而且在情感的追求上也很有勇氣,她敢于與自己心愛的人保持二十多年的情感來往,這在偏遠的農村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可同時在她身上又存有矛盾的一面,她不僅忍受了自己包辦婚姻的極度痛苦,而且還親手制造了另一樁悲劇婚姻。思想意識的復雜直接造成了性格的復雜,這一類型的女性正是由于她們身上的復雜性、矛盾性而使得她們的個性更加鮮明、獨特、可信,也更充滿魅力。

電影《天下無賊》劇照
三、具有傳統文化根源的“邪惡”型女性
孔子有道: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俗話也有:最毒不過婦人心。當然我們說這是“男尊女卑”時代的思想,是對女性的偏見,但這些思想、這些偏見直到現在還余威猶存,殘留在不少人的骨子里。魯迅就曾在《阿Q 正傳》里調侃地說:“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都可以做圣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4]“女人禍水”歷來是中國文學藝術作品中的一大主題原型,因此在電影中出現邪惡型的女性形象也就不足為怪了。謝晉的《芙蓉鎮》(1986 年)中的李國香就是一個為人所不齒的邪惡女性;李少紅《紅粉》(1995 年)中的小萼完全是一個好逸惡勞,致使丈夫墮落、被槍斃的“禍水”;作為主旋律電影《生死抉擇》(2000 年)為了突出嚴陣反腐倡廉的高尚品質,嚴妻就成了反襯的角色;《手機》(2004 年)中的武月,被塑造成一位既是欲望的化身又是不擇手段的“狐貍精”般的“壞女人”,令人望而生畏;《天下無賊》(2005 年)中的小葉,盡管由漂亮的李冰冰扮演,但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被看”,另一方面是更加地使人物邪惡化,小葉本來就是“賊隊伍”中的一員,在影片中導演把她塑造得比賊還“賊”,最后賊王黎叔也栽倒在她手里。
關于這一類型的女性形象,我們不可否認在她們身上也有著某些時代社會某些女性的影子,但應該說也有著如女性主義批評家所說的在男權社會中對女性的恐懼以及歪曲的成分,猶如美國女權主義者吉爾伯特和古芭所稱的“閣樓上的瘋女人”,這是一類值得人們關注和深究的女性形象。
四、多元化社會中的邊緣人女性形象
所謂邊緣人女性主要指的是處于社會或家庭的非中心地位的女性。
建國之后,在政治上婦女曾有過“頂半邊天”的火紅年代,女性確實也取得了一定的家庭和社會地位,但男女平等的政治口號畢竟不能徹底替代男權中心的社會歷史觀念;另一個突出的原因就是改革開放的雙刃劍作用——既更新觀念,推動時代社會發展,同時許多社會問題也接踵而來,比如貧富差異問題、待業下崗問題、婚姻家庭問題、道德滑坡問題等等……因此作為生活真實反映的電影,在這一時期:“過去多少有所顧忌的東西都堂皇登場,中國電影真正是復雜多樣了。”[5]電影邊緣人女性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出現的。其實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經有電影把鏡頭對準社會的弱勢群體,出現了邊緣人的形象,比如《大橋下面》(1983年)中插隊回城的裁縫個體戶秦楠,因在路邊擺攤妨礙交通,差點被吊銷營業執照,而且身邊還帶著個私生子,秦楠就是一位既處于社會邊緣又處于生活邊緣的女性;邊緣人女性是我國80 后尤其是90后電影女性人物畫廊中涌現的又一引人注目的新型形象。邊緣人女性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家庭邊緣人;另一類是社會邊緣人。
張元的《媽媽》(1990 年)敘述了一位被丈夫拋棄、獨自撫養殘疾兒子的母親歷盡艱辛的故事;孫沙《九香》(1995 年)中的九香,是一位飽經風霜無私地奉獻母愛卻又是失去自我生命價值的母親形象,當九香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長大之后,她自己也就完全徹底地淪為家庭的邊緣人了,影片中展示九香與老關的戀情時受到已成為一家之長的大兒子的阻撓,就足以呈現九香作為家庭邊緣人的悲劇性人生,影片對九香寄予了深切同情;王小帥的《青紅》(2005 年),描寫了60 年代從上海到貴州的三線工人家庭到了80 年代處于遷回上海還是留在貴州的兩難境地,青紅就是一位處于兩難境地家庭的邊緣人物,在整部影片里青紅基本是處在“失語”的狀態,影片作為王小帥殘酷青春系列之一,當然可說是父母一輩人的殘酷青春,但更是青紅作為邊緣人的具有悲劇色彩的殘酷青春。這是家的邊緣人,而作為社會的邊緣人更是導演所關注的對象(當然家和社會經常是不可截然分開的)。孫周《漂亮媽媽》(1999 年)中的孫麗英不只是一位單身的、失聰孩子的媽媽,也是一位下崗女工,生活社會的雙重邊緣,使得她為了生活、為了兒子,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包括事業、尊嚴等,影片展示了邊緣人女性生活的艱辛。彭小蓮《美麗上海》(2003年)中的靜雯是一個守寡的與老母親和女兒一起生活的下崗女工,但她不卑不亢,有著獨立自主的現代價值觀,有著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第六代導演的一大貢獻就是用“不撒謊”的攝像機對準這些弱勢人群,而且不再把邊緣人物簡單化處理。《扁擔姑娘》(1996 年)中黑幫老大的情婦、《安陽嬰兒》(2001 年)中的妓女……給觀眾呈現了一個個處于邊緣的女性、一幅幅無奈的復雜人生。
任何時代有主流人物就必然有邊緣人物,主流與邊緣是相對存在的,當然過去的影片也有邊緣人女性的塑造,但由于導演極力彰顯的是主流人物,因此難于關注到處于家庭和社會最底層的邊緣人物的豐富性、復雜性,過去的影片往往把邊緣人女性簡單化、臉譜化,而現在在電影中觀眾不僅能看到邊緣人生活的不易、人性的復雜與豐富,而且還能感受到影片中所隱含的人們對邊緣人的理解、同情以及人文關懷,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電影的進步。
把這一時期電影所塑造的女性按類型來分也許并不科學,因為這些類型不可能完全囊括所有的女性形象,況且任何的分類都是相對的,標準不同就有不同的分類,不能一概而論,這樣的分類充其量也只能說是給我國80 后電影精彩紛呈的女性形象畫一個大致的輪廓。
女性形象的多姿多彩首先是因為生活的豐富多彩,同時是由于人們思想意識包括女性自身思想意識的豐富復雜所致;縱觀80 后中國電影的女性形象,我們看到了社會發展的投影,看到了時代精神的體現,看到了男權思想的積淀,也看到了女性意識的滲透。電影就猶如社會的一面鏡子,女性是這面鏡子里不可或缺的鏡像,電影女性形象畫廊的多姿多彩,讓這門藝術更加異彩紛呈。
[1]封敏.中國電影藝術史綱[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407.
[2][3]戴錦華.不可見的女性: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與女性的電影[J].當代電影,1994(6):44.
[4]魯迅.魯迅經典作品選[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474.
[5]周星.中國電影藝術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