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
◎馬旭琴
古城
◎馬旭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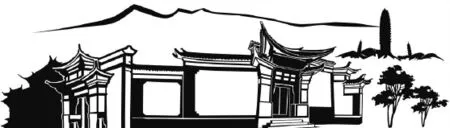
我早就知道,C城的西長街下有條古城墻,那時候我太小,別人微弱的目光傳遞的都是天真與各種不信任。沒有人相信,所以我選擇獨自走過那片河灘,看地上有沒有鬼子留下來的子彈。
每個年幼孤獨的小孩對一切事物都好奇。我也不例外。我喜歡在奶奶家的門口端把小凳子坐著,窺視著路過的每一個人。奶奶家門口坐著一個修高壓鍋的中年男人,他是這條路上修高壓鍋技術最好的人。他很奇怪,因為他有張支離破碎模糊的臉,我一直懼怕這張難看的臉,可他是個好人。據說這張臉是在一次高壓鍋事故中被炸的,從那之后他便開始研究高壓鍋。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里為什么會車水馬龍,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路過。不過很快我知道了答案——這里是城市。
因為這里是城市,也就必須要面對人來人往,和所有必要的變遷。
買菜回家的女人在夏天穿著寬松的衣服,我跟猥瑣的小販一起看著俯下身挑選小菜的中年婦女疲軟的胸部,我沒有獲得一絲快感,但卻因為觀測到了某種隱秘并且故作神秘的事物而暗自歡喜,足夠讓我在小學三年級的課堂里幻想一下午。我也喜歡看中年婦女與小販因為一兩毛錢爭個焦頭爛額,那會兒我并不曉得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時間在旁白里殘酷地告訴我這才是生活。
我奶奶家住在吉祥巷。吉祥巷33號,這政府給的新門牌號,聽我爸爸說民國的老門牌很吉利,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吉祥巷東面還有條巷子,叫如意街,南面有條小巷子,叫一路吉祥,西邊有條街,叫接貴街。都是非常好聽同時也非常俗氣的名字,想必取這些名字的人都是別有用心的。確實,西邊一點叫鹽道坪,我曾想是不是那里有許多賣油鹽醬醋的,所以才叫這名字。然而,即便是城市里所有的人證都離開了,老墻上黑色的,被文夕大火燒過的痕跡總能在緊要關頭跳出來告訴新來的人。原來,清末這里是鹽道衙門的地方,管鹽的部門自然有錢。
從鹽道坪往西走百把米,就到了西長街了。那里是賣牲畜水產的地方,因此惡臭無比。而且,西長街小學也在那塊,里面上學的大多是附近販子的兒女。西長街做水產生意的,大多跟其他地區的碼頭幫派沒什么區別,為了搶生意不惜以刀相向,一旁又忙著給“上面”各種好處。我懂事早,知道西長街有些人跟那牲口沒什么區別,都是任人宰割的貨。所以這幫人的子女也好不到哪去,經常在街上拉幫結派,敲詐我們吉祥巷的好學生(當然后來我也因為認識了一個西長街小學的朋友而沾沾自喜)。有次,西長街打架打死人,跟著第二天,一幫不務正業的學生為了搶錢,好學生不從,也把人給捅死了。我還記得,在我上四年級那一年,街上有個跟我一般大小的小孩去湘江游泳溺死了,名字也叫小熊。我很后悔我沒有認識他。如果認識的話我可以教他游泳。
所以西長街總是黑血橫流,從布滿毛屑發著青霉的鐵籠子一直流到黑乎乎的下水道。趁機逃走的小龍蝦不會有什么好下場,無助的土狗白長了一副鋒利的獠牙。放學回家的時候我會根據心情看是否路過西長街,年幼的男孩身上會帶有更多的動物兇猛。有一次我在一幢屋頂有個十字架的房子面前停下,十字也被大火燒得漆黑,里面掛著一排排狗頭,表情猙獰,我知道那是它們死去的那一瞬間的模樣。這里的小販大多身強體壯,天熱的時候都是光著膀子,露出一身橫肉以及漸漸模糊的紋身。我記得有個賣小龍蝦的小哥,在長達三年的時間里我一直認為他的左臂上紋了一只小龍蝦,因此每次路過的時候都會略帶嘲笑地看著他,后來我認識了一個新品種叫蝎子。嘲雜的小巷子里,雞鴨羊狗的鳴叫聲不絕于耳,不時還會傳來狗與羊失去生命時凄慘的叫聲,而我毫不畏懼。
仁慈在這里是不管用的,這點我從城管身上學到許多。白天,年輕的城管不定時地來檢查,沒有按時交錢的賣小菜的商販會棄菜而逃,不過也有舍不得那幾斤紅薯的老人婦女,她們鎮守在菜攤前,像童話里的公主等待惡龍的到來。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城管隊長那張猙獰的面孔,在踩斷秤桿,踢翻婦女搶走一把把從遙遠的農村,應該是三輪車,運來的蔬菜之后,轉而一種興奮的幸福的面容。他們滿載而歸,剩下地上的一片狼藉。
可是混亂的地面總是過一會就好了,我并不知道是誰在打掃。
繼續說我在放學時路過的西長街,一日我的心情極糟,我想在這里游蕩,以獲取某種快感。闖進陌生巷子深處對于一個三年級的小學生來說是件神圣的事,因為里面總會有不可預見的事物。小巷子里的天空窄窄的,上面有無數天線交織把天空分割成各種圖形。電線上總有曬不完的衣服,多數還滴著水,滴到身上還有淡淡的肥皂味。麻石路也變得滑溜起來,有個大胖子商人大搖大擺地從巷子深處走出來,身上的金鏈子碰撞時發出細細的呻吟聲。旁邊的窗戶里透過厚厚的窗簾,陣陣麻將洗牌的聲響,常常被我忽略掉。這都是稀疏平常聲響。我想我已經找不到出來的路了,此時天空變成了玫瑰色,一個骯臟的夜晚即將開始。
再往里走走吧。
我第一次迷路的經歷就在這里開始。當天完全黑下來之后,空著肚子的我還沒有找到從巷子深處走出來的路。我聞到每家每戶做飯的香味,本地辣椒炒肉的味道非常嗆鼻,可能是因為辣椒我有點想哭。巷子太深了,這里連狗都不敢出沒。
后來我總算知道那個帶十字架的大房子曾經是座教堂。教堂教人仁慈從善,以積累足夠的人品通向天堂。晚些年我在離西長街較遠的朝宗街也發現一座教堂,那天正是周日,我路過的時候聽到一陣唱詩班的歌聲,那種天堂的誘惑跟美艷的女人招呼你進去一樣。因此我扭頭走了,身后還跟著遠離塵囂的歌聲。我是否早已習慣于慘淡的人間而不再向往天國?
巷子里有許多弄堂,里面大多住著七老八十的人。年輕人大多不愛住木頭房子,因為晚上會經不起折騰。而我在小學的時期便開始偏愛這種老古董,因為他們本來是屬于豪華大氣的。因為一個弄堂大多住了許多戶人家,所以基本上是出入自如的。這便助長了我一個與眾不同的愛好。
吉祥巷同仁里有處弄堂,大門特別氣派,圓形實木拱門,門拉環跟我小時候的頭差不多大。門常常是半掩著,里面采光不好,因為東邊建了座十幾層的高樓。大廳里沒人,我就溜了進去。然后踩在木頭樓梯上樓。我喜歡那種咯吱咯吱的木頭聲,不僅僅是我的,還有別人的。后來我還能從能上下樓的木樓梯的聲響中分析出這個人。這是生命的重量,是存在的證明。在二樓的公共陽臺上,種著各式各樣的花花草草。我會趁機掰幾片葉子玩,有次正準備掰的時候,一個老大爺從我身后走來,看也沒看我一眼就開始澆花。我愣住了,不知道是跑著離開還是走著離開。卻又看見老大爺指著一盆花,慢吞吞地說:“這是我最喜歡的海棠花。”我沒有回應,只是看了看。“鴛鴦被里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哈,哈,哈。”老大爺不知道是什么緣故笑了。我對這些花花草草頓時沒了興趣,轉身輕聲走掉,下樓的時候都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有些弄堂裝飾得很漂亮,且大門總是鎖著的。大概是某家的產業保留了下來。“不要小看這些房子啦,毛澤東逃難的時候還住過這里。那邊街上的幾號幾號房子是當年革命的議事廳。什么什么公館還印過革命報紙……”街上老頭說起這些故事時總是手舞足蹈,手揮得能夠打下幾只蒼蠅。還有老人喜歡跟我講長毛的故事,講長沙會戰的故事。為什么跟我講呢,因為我在聽。后來等這些老爺老太死去,那些曾經輝煌的房子便轟然倒下。城市總是這樣,戰火無情燒了又重新建起,看著以驚人速度拔起的高樓,我不得不佩服我國人民之勤勞,同時也佩服他們的無情。
某年,我的奶奶跟著老爺老太的部隊死了。我似乎能看到她一路上對城市發展的稱贊,因為她已經近二十年沒有出過這條巷子了。追悼會的時候,隔壁患老年癡呆的王奶奶沖過來認真地磕了三個響頭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曾屢次向紅衛兵告密而悔恨,還是街上只剩下她這一個老人了。然而,王奶奶繼續癡呆著,幾年后便也跟著走了。
我渴望做一個向巷子深處跑去的夢。那里留著我從未發現的寶藏,留著永恒的單純和真實。那時的古城,也在做夢。
(作者單位:解放軍藝術學院)
(責任編輯 劉月嬌)
馬旭琴,解放軍藝術學院2012級文藝學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