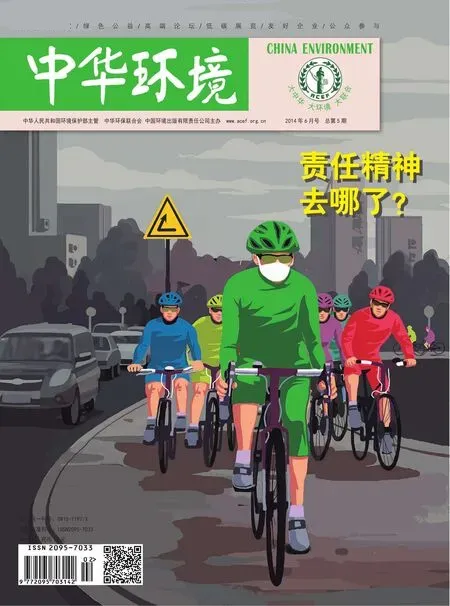打通環境NGO盡責的“任督二脈”
劉洋 中國文化產業研究會秘書長,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研究員、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楊美瓊、李沖、李明明 中國文化產業研究會研究人員
打通環境NGO盡責的“任督二脈”
劉洋 中國文化產業研究會秘書長,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研究員、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楊美瓊、李沖、李明明 中國文化產業研究會研究人員
歷經30年傳統城市化、工業化歷程,我國正面臨著空前巨大的環境挑戰和資源壓力,并在公眾環境意識不斷覺醒的雙重擠壓下,造成大范圍社會恐慌、焦慮、悲觀、激憤甚至沖突。2014年5月10日,杭州市余杭區中泰鄉及附近地區人員因反對九峰垃圾焚燒廠項目選址,發生規模性聚集,少數人蠱惑群眾堵截高速焚燒車輛,圍攻警察和過往無辜路人,這是最新一起以環保為名的群體性事件。而四川“什邡事件”、江蘇“啟東事件”、浙江“PX事件”等早已多次刺激考驗各方神經。自2005年以來,環保部直接處置的事件達1000多起,重特大事件72起,且呈現年年增長態勢。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政府、企業、公眾三者之間重要的環境監督協調力量——環境NGO幾乎集體“隱形”與“失聲”。

5月11日,杭州市政府召開余杭區“九峰”環境能源項目新聞發布會。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邊衛躍稱,余杭在少數不法分子的煽動下確有規模性聚集,事件處置中未現人員死亡。杭州副市長徐立毅還表示,未經過法定程序和取得群眾支持,九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絕不會開工。中新社/供圖 攝影/李晨韻
環境對抗——政府與公眾解不開的結?
誠然,推動地方經濟發展,離不開引進項目、吸引投資,甚至對于中西部落后地區來說,還應該搶抓產業轉移的戰略機遇期。但是,任何發展都不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公眾不需要“帶血的GDP”。在對政府習慣性信任缺失、環境決策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公眾更容易產生不安全感與不公平感,引發過激自我保護行為。根源何在?
一是公眾環境覺醒、覺悟日益提高。隨著生活水平由溫飽型向舒適型過渡,公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而在粗放式發展帶來巨大環境代價的現實下,全國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僅46%, 1/3城市空氣質量不達標,廢水、廢氣、固體廢物排放量持續增加,“砷毒”、“血鉛”、“鉻水”、“鎘米”等致畸、致癌、致突變現象頻現,加劇了公眾的“環境恐慌”。
二是受“狹隘的GDP優先,余可不問”的發展觀綁架,地方官員拼的是經濟數據,為的是政績,而環境代價具有滯后性,滋生了他們“敢上、快上”大項目的“邪念”,不顧及環境保護,對外又缺乏透明度,使公眾在事實上和心態上都感覺在“為官員的烏紗帽買單”,無形中自毀公眾信任。
三是社會轉型期帶來一系列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占比最大的底層社會公眾怨言很多、矛盾很大,加之微博、微信等草根媒介帶來未經確認信息的快速傳播,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質疑,公眾將“環境標準”聚焦到顯微鏡,“環境問題”置于放大鏡下,任何一個“引進項目”都可能演變成官民對抗。
環境NGO去哪了?——數量不等于質量
我國環境NGO分官辦和民間兩個梯隊。1978年第一家由政府部門發起的環境組織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成立,1991年第一家由民間自發組成的環保組織遼寧省盤錦市黑嘴鷗保護協會成立。至2009年全國正式注冊的環境NGO激增至3539家,環境NGO已成為數量龐大的環保力量,在拯救藏羚羊、披露淮河污染、金光集團APP事件、圓明園防滲工程環境影響聽證會等環境事件中發揮了作用。但日趨嚴峻的環境形勢一次次面臨“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時,環境NGO在環境治理盡責上顯然存在嚴重缺陷。
傳統體制約束
由于“大政府”傳統體制及思維根深蒂固,環境治理習慣性成為政府特別是環保主管部門的“獨角戲”,忽視了環境NGO、公眾參與的正能量。有的政府部門還為環境NGO參與設置和提高門檻,例如:環境NGO設立需要同時接受民政部門和主管單位的雙重管理、同一個城市難以注冊多個名稱類似的環境NGO、經營范圍有明確的限制等。
公眾代言人和利益集團代言人間搖擺
環境NGO本質上是給政府上“緊箍咒”,讓經濟發展受到環保約束,消解無節制的發展沖動,自然難以成為地方政府的優選項。官辦NGO人事上多由在任或者離退休官員主持,資金主要依靠政府撥款,發出獨立聲音掣肘重重。民辦NGO資金幾乎全靠自籌,且多為企業捐贈為主,組織建設、日常活動往往捉襟見肘。因此,在與地方政府、污染企業的博弈中,環境NGO很難充當公眾代言人為弱勢群體爭取長遠利益,甚至淪為利益集團掩飾環境代價的“幫兇”。
民意基礎不足
受傳統思想影響,公眾對公共事務普遍持冷漠態度,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不高。隨著人們環保意識逐漸增強,公眾在環保參與方面呈現出“關注度高,但參與性不強;要求度高,但主動性較差;權益增加,但責任心淡薄”的特點,更不用說積極參與環境NGO了。只有切身遭受環境污染或者發泄社會不公時,才能更多見到公眾的身影。
自身能力較弱
發達國家環境NGO能夠廣泛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影響、參與政府決策。而我國環境NGO發展還比較初級,業務主要集中在諸如植樹護林、環保宣傳教育等淺層次,專業化程度不高,資金不足,組織動員能力較低,缺乏與政府、企業的有效溝通,難以產生重大的社會和政策影響力。
治理突圍——讓環境NGO盡起責來
環境NGO無法有效盡責,必然會失去公信力,面臨生存空間邊緣化、自身價值日益縮小的窘境。《憲法》、《環境保護法》、《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1996)等法律法規都明確鼓勵環境NGO參與環境保護工作,這是環境NGO發展與盡責的堅實法律基礎。
治理卓越的環境NGO終極目標在于:一是獨立,由組織自主設立和管理,不依附和聽命于利益集團;二是公益,自覺主動保護環境,維護公眾的環境權益;三是自愿,內部不設藩籬,組織成員可以自愿加入和退出;四是專業,擁有針對性的知識、社會資源和解決方案;五是非營利性,不以營利為動機,收益主要用于環境事業。
賦權環境NGO
環境公共利益具有廣域性與擴散性,決定了環境不能明確由誰擁有。當環境受到侵害時,并非所有被害者都能及時挺身而出,尤其是環境遭受侵害的風險時,很難找到直接的環境破壞者去維權,前文所述政府和公眾都存在維權的天然缺陷。《環保法》修改讓環境NGO有了站出來維權的可能。修改后的《環保法》將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確定為:在設區的市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的,有五年以上公益經驗并信譽良好的環保組織。這將為環境NGO常態化地維護公眾環境利益,預防環境侵權、犯罪,在環境事件中及時、充分行權提供法律保障,真正推動責任倒逼,使得環境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能夠有效整合實施。
如果環境NGO通過內外治理體系建設優化,加強盡責能力,更容易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支持,也能有效約束更多“經濟利益綁架環境利益”的行為和事件,成為環境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優化環境NGO的制度環境
結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應在環境NGO制度環境層面加快深化改革。
一是增加獨立性。改革《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等政策法規關于“雙重分層管理”等約束條件,避免業務主管單位基于自身利益過多限制干涉環境NGO。尊重環境NGO的法人主體地位,保障其合法權利,促進其依法自治并獨立承擔法律責任。
二是創新培育扶持機制。政府可以向環境NGO移交一些監督、審核、評估、認證等職能,購買宣傳、培訓、咨詢、研究、法律等環境公共服務,給予獎勵、補貼、貼息、稅收等優惠扶持,鼓勵其更好地參與環境公共事務管理。
三是嚴格依法監督管理。政府要引導建立機構評估定級、從業人員職稱評定、社會榮譽授予等環境NGO聲譽激勵機制,逐漸替代過去的直接監督管理機制。完善環境NGO的申辦注冊、撤銷登記、注銷登記等制度,建立無法盡責的環境NGO退出機制。
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強化自身獨立性
鼓勵環境NGO引入和建立競爭機制,通過更好地在政府、企業、公眾之間溝通、協作、說服、互惠、合作,以優質服務獲取資金等資源。擺脫過去由于資金來源單一導致的受利益集團左右的狀況,建立多渠道籌資機制,包括地方、國家、國外政府和組織資助,企業和社會捐贈,會員費,申請承接國內外項目,開展與自身業務相關的有償服務等,確保環境NGO保持自己的公益價值取向,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
完善法人治理體系
環境NGO要高效有效開展工作,終極目標依然是在法律框架下,建立健全以章程為核心的法人治理結構,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發展、分權制衡。
一是做實環境NGO章程,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社會組織申請的文件材料,要以章程為核心明確法人治理結構的構成和權責關系,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秘書處的權利和責任。
二是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制度,包括重大事項報告制度、會員登記管理辦法、財務管理制度、秘書處工作制度、會員意愿反映制度、民主集中制度、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等,強化內部管控。
三是加快環境NGO監事會建設,強化內部剛性監督。監事會應代表多方利益,監事一般由不同利益方選派,具備相應專業水準,對環境NGO開展的重大活動及財務收支等事務進行指導與監督。
四是建立第三方評估機制。可以引進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財務審計,引入咨詢機構或者評估機構進行業務評估,建立信息披露機制,自覺接受公眾和媒體等社會監督,倒逼環境NGO提升自身能力。
政府、企業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環境問題上往往難以避免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分散的個人無論數量多大,其專業性無法保證,矛盾沖突多發生在環境侵權的事后,做不到事前“未雨綢繆”和“扼殺在搖籃中”,并且在面臨政府公權和企業財力時顯得軟弱渺小、力有不逮。而環境NGO的潛力、能力無可比擬,能夠廣泛聚集基于共同環境信仰的專業人士、群體,用組織化、社會化的力量來捍衛環境尊嚴和權益。